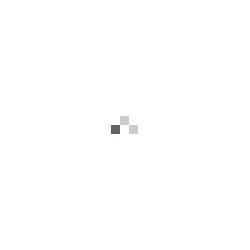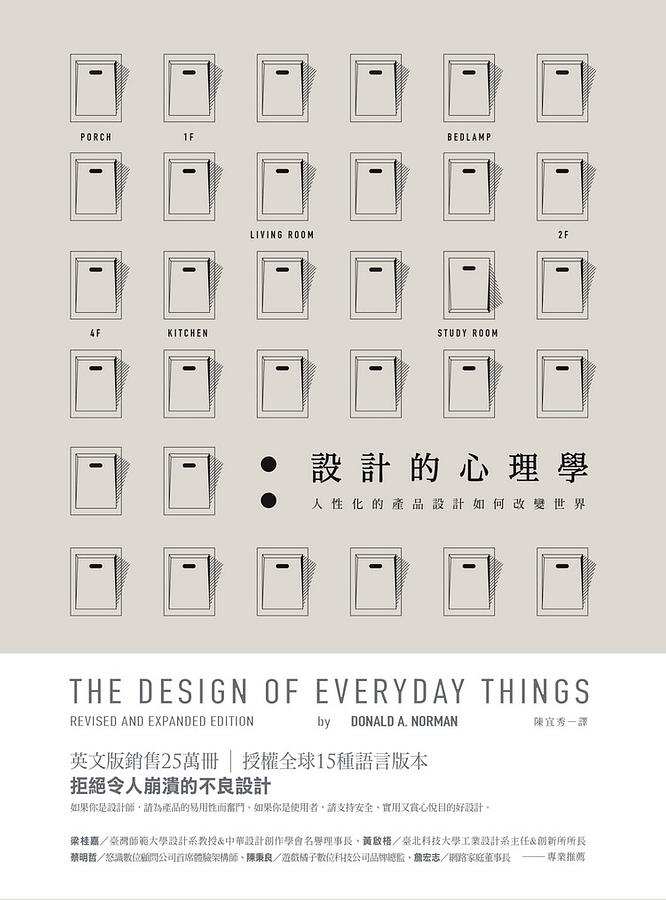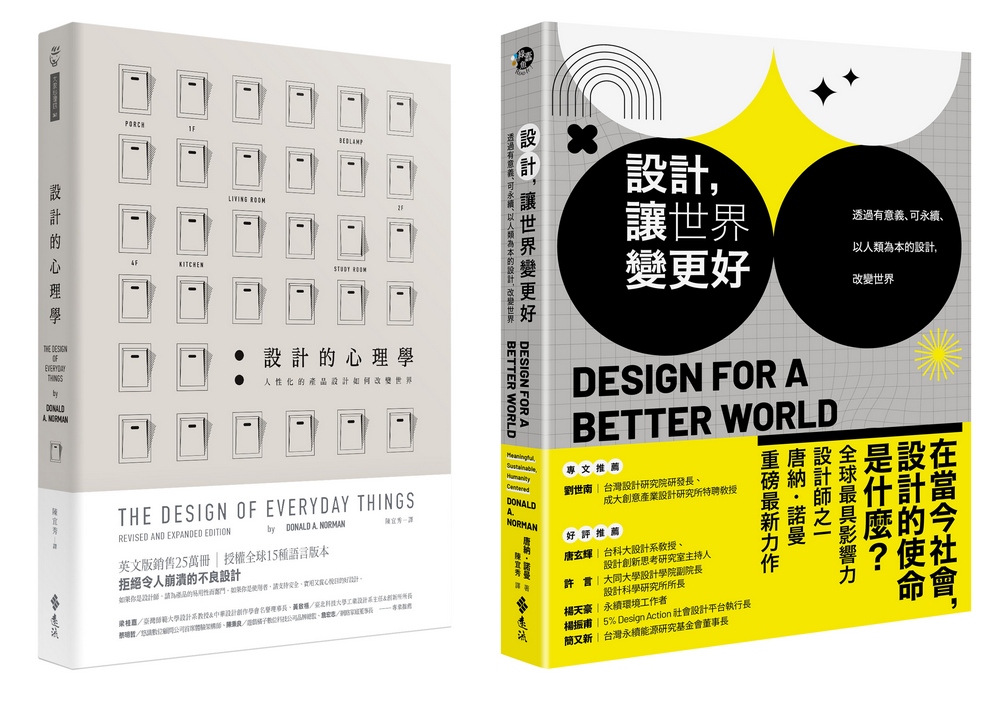設計, 讓世界變更好: 透過有意義、可永續、以人類為本的設計, 改變世界
Design for a Better World: Meaningful, Sustainable, Humanity Centered
全球最具影響力設計師之一唐納.諾曼,重磅最新力作
內容簡介
在當今社會,設計的使命是什麼?
全球最具影響力設計師之一唐納.諾曼,重磅最新力作
如果設計是讓我們陷入今日困境的罪魁禍首,
或許設計也可以拯救我們脫離這種困境
幾乎所有我們看到的事物,都是人工化的,而這些人造物都是被設計出來的。我們設計了世界,但也反過來被世界所影響。
世界已出現許多問題,諸如氣候變遷、充滿廢棄物、貧富差距擴大,現在是改變世界運作方式的時候了,我們可以重新思考設計在生活、治理和產業中的角色。我們應該要設計能夠永續的系統、考慮設計對人類的影響、確保每個人都被考慮在內,並以永續和公平為目標。
設計必須從無意的破壞性,轉變為有意的建設性,這正是當今世界所缺乏的。此書以三大層面探討設計的使命:
1.有意義:注重生活品質,而不是經濟收益。
2.可永續:調整我們的生活方式,以保護環境。
3.以人類為本:關注全人類,讓人們參與設計。
此書提供了發人深省的診斷,告訴我們哪裡出了問題,並為改善現狀開出明確的處方。就讓改變從現在開始,在為時已晚之前。 / 幾乎所有人造的東西都是設計過的
我剛坐下來,開始寫作。從左邊的窗子,可以往南眺望窗外的風景。我住在加州聖地牙哥,當地稱為索利達山的一座陡峭山丘上。從我的窗子可以俯瞰數英里的風景,包括樹木和植被,裡頭住著蜜蜂、蜥蜴、蜂鳥、燈草鵐、烏鴉、紅色胸脯的老鷹以及我說不出名字的許多生物,偶爾還會出現兔子。遠處,我可以看到教會灣(Mission Bay)有許多小船在遊弋。右邊是太平洋,時有大船或貨輪經過;在晴朗的日子裡,甚至能看到科羅納多群島以及鄰國墨西哥的山巒。
我所能看見的東西,幾乎都是人造的,是設計過的。這棟房子由人所設計而建造,院子則是配合山丘和溝壑的地形,進行了挖掘整理,才能如此平整光滑。有些地方挖土填平,而一部分的土來自於建造教會灣時所開挖的土方。那裡曾經是一片濕地和沼澤,後來被改造成美國最大的水上娛樂設施;通常在這種開發建案中,休閒娛樂的要求常常會凌駕於生態的考量之上。
這裡的植物和動物都是自然的,但是都受到人類的精心栽培與管理,不符合我們喜好的會被移除。房屋及道路都有明確的設計:從草地到高達三十米的棕櫚樹,每一棵植物都經過慎重的種植和維護。雜草不在人類的計畫之中;即使雜草總是在意料之中,它們只是一種計畫外的副作用。
野生動物又如何呢?這裡的動物仍然存在,但是牠們的棲息地和生存環境全然依賴於這個社區的植物和建築,為動物提供了庇護所、巢穴以及食物。有些鳥類食用葉子和花朵,有些食用種子、昆蟲和蠕蟲;而像老鷹這樣的猛禽,則需要捕食一些小型動物和鳥類。因此,你可以說這些生物的存在是另一種副作用。我猜一些動物是被預期和受歡迎的,但是其他生物就像雜草一樣,鼴鼠和響尾蛇這樣的生物就被視為人類的麻煩。
請注意,「雜草」或「害蟲」這些名詞也是人為的概念,而非自然界本身的描述。雜草也是種天經地義的植物,而被稱為害蟲的動物只是遵循其進化的軌跡生存而已。是人們基於對植物、動物的偏好,對這些自然生命加上了標籤。人們愛好整齊修剪、保養得宜的草坪,而雜草並不雅觀。人們喜歡不會干擾周圍環境的動物(或者至少不會在人類視線之內產生干擾),而地鼠在草坪上挖洞,破壞了人工栽種、修剪、維護的「自然」風貌。這種偏好代表了世界上的許多問題:我們喜歡多樣化和自然之美,只要它們不干擾我們的生活。
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人所設計的世界中,人造物比比皆是,從我們的家和衣服,到我們使用的工具、我們的書。國家的觀念和政府的形式是人為的,是人所設計的。即使是我們認為的「自然」──例如地球、環境、動物和植物──也已經被人們的創造和活動所塑造和影響。設計並不僅僅影響物件;我們發明(也就是設計)組織結構與各種管理人的方式。舉凡狩獵和耕種、處理和烹飪食物的方法。還有哪些呢?一旦說出來,你就會意識到它是人造的、設計好的。金錢、法律和律師、服裝、國家的概念、人們的名字。正如這些設計塑造、成型並限制了這些事物,他們反過來也塑造了我們,因此,我們也不再是純粹自然的。
我們所設計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人造物」,改變了我們的行為和作為。我們藉著設計改變了事物,同時,這些事物也在改變我們,影響我們的行為和生活:我們設計了世界,而我們又反過來被世界所影響。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複雜、交織、動態系統中的一部分,而這個系統涵蓋了人類、整個地球,甚至是整個太陽系。我們的生命(甚至是我們的遺傳因子)和周圍事物的存在,都依著天氣、潮汐、日照和氣候等週期而發展──這些都受到地球在太陽系中位置的影響。我們既不能獨立生存也不能獨自行動,我們只能存在於我們所屬的群星之中。
為什麼我們的人造世界看起來如此自然?
當英國統治印度時,他們對印度人實施嚴格的限制和行為規範,將他們視為二等公民。1947年,當印度人逼迫英國人離開之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成為印度的第一任總理。然而,即使印度上層階級的孩子能進入英國的頂尖學校(伊頓公學、哈羅公學、溫徹斯特學院、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受教育,「他們仍然被認為是二等公民。」在此之後,尼赫魯寫道,「讓人驚訝的是,我們大多數人仍然將這種階級制度視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及宿命。」這點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我們存在的方式和出生以來的生活經驗,給我們帶來視野上的限制,我們難以想像還有什麼其他選擇,也很難意識到事情不一定必須如此。也因為這樣,在我們遇到使用科技的困難時,我們時常會責怪自己。我經常說:「不,這不是你的錯,是因為設計得不好。」現今的世界是一團亂麻,當人們抱怨世界的雜亂時,我的回答也是一樣的:「這是個糟糕的設計。」我所指的「設計」並不是今天專業設計師所做的設計工作,而是所有在人類歷史上用來發明、建造、發展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個世界,所實踐的設計。
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假設地球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以為它的資源是無限的。另一方面,有些統治階級簡單地假設人人並非生而平等,有些人被定義成上等階層,而有些人因為他們的膚色、宗教、出生地或信仰,而被認為是低等人民。人類似乎具有形成小型合作團體的能力,同時也讓自己的群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與其他團體區隔開來。這種過程引起了20世紀30年代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注意,並稱這種趨勢為「分裂創始」(schismogenesis)。人們會強調自身與其他人之間的差異,而非借鑑或複製鄰近的族群。這樣的結果可能導致極端的扭曲,並將實際上非常相似的社會變得非常不同。這種差異可能是極端的、人為的,並且在此之前不曾存在。
人們能夠透過「分裂創始」現象或任何相似的機制,將原本不明顯的分歧轉化為之前完全不存在的分裂和偏見。這種傾向是造成膚色、性別、宗教、國籍、語言或口音歧視的原因。同樣的,它也是一種人為的現象,將任何區別群體的表面特徵,定義為一種兩個群體之間的本質差異。將這些不重要的差別加以放大之後,能夠導致群體之間的重大歧視。
我們必須從根本開始改變我們的生活和存在的模式。我們必須改變我們存在於地球上的方式,同時認識到我們都在這個系統之中:人類本身、自然、生態環境構成一個複雜的系統,改變任何部分都可能影響整體。要理解這個系統,我們必須考量它的歷史,因為我們現在的狀態是由歷史的走向所決定的。然後,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的方式。
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意味著改變所有事情:我們如何生活、我們製作什麼、我們相信什麼、我們如何行事。我們必須質疑和重新檢視所有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不論它們看起來多麼正常、合理、具有邏輯。許多我們過去以為天經地義的事情,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框架;只有當我們認識到它們只是前人構築出來的框架,我們才能踏出新的開始。
如果設計讓我們陷入今天的困境,設計是否也能帶領我們走出困境?
今天的世界亂成一團。氣候變遷固然是所有人關注的明顯問題,但是它只是整個困境的症狀,而非根本原因。氣候變遷是許多其他根本性疾病的結果。是的,我們還是必須處理症狀,但是除非我們也處理潛在的根本病因,否則困境將繼續存在。主要的困難在於我們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以為人類可以對地球資源隨意支配,隨意用來增進我們的舒適和生活水平。更複雜的是,這個「我們」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統治階層,那些擁有權力和財富的人,可以支配其他人來增進自身的享受,可以征服和統治領土。強國支配弱國,首先是殖民,然後在經濟上對資源進行剝奪。
我們生活在一個包含許多面向的複雜社會技術系統中:社會、經濟、信仰和行為、商業、教育、健康、疾病傳染和生態災害。有些面向是直接而明顯的,但是大多數是間接、緩慢而且不容易看見的;後者可能是最危險的,因為它們悄無聲息地向我們接近,等我們意識過來並且試圖挽救時,可能已經太晚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儘管我們早就預測到傳染病的大流行,但是當COVID-19在2019年末爆發時,我們的反應遲緩而混亂。疫情後的復甦也是同樣手足無措,不同的政治團體(甚至於同一個政治團體)不斷提出矛盾的建議,讓社會在樂觀和失望之間反反覆覆。與此同時,COVID-19不斷突變,越來越多變異株能突破防疫或治療,讓科學家必須不斷改變方向和防疫建議。當病毒發生變化時,防疫的對策當然也需要改變,但是由此產生的反覆更改卻被怪罪在科學家的身上,這也導致我們對醫學建議的信任下降。
偏見、極端民族主義和社會不公平的惡化,也是這個複雜系統的間接結果。少數生活舒適的富人與多數民眾之間的收入及生活水準落差巨大,使得某些政治領袖利用大多數人的不滿來推翻政府,承諾改進,但是結果只增加了他們自己的權力和收益。
現代資本主義是其中的罪魁禍首之一。資本主義的概念本身並不是件壞事;然而,由許多大型企業所進行的變形資本主義,藉著全球大型金融市場和跨國銀行體系,讓少數企業累積的財富超過許多國家。對利潤的渴求主宰著這些金融行為,忽略了對人類或環境造成的代價。利潤不一定是實質性的東西;利潤是一種隨時出現、分秒必爭的價值變化。經濟學家創造出經濟模型來支配這種活動,僅僅以金錢價值的增加作為成功標準,而忽視了對人類生命、環境、社會價值的影響。更何況,即使這些模型對人類行為所做的假設並不正確,經濟模型還是會對人類的行為產生影響。
一個新的開始,不是由個人或單一群體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動員更多人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改變整個世界的觀念。這種改變的成功,不能用金錢或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這種指標來衡量,而是以全人類的健康和幸福為依歸。
對於種種複雜的問題,設計如何能成為解決方法?對於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這似乎說不通。然而,為了撰寫這本書而進行研究,與世界各地的眾多學者討論這些問題,重新思考自己的基本假設時,我認識到設計是眼前問題的核心,因此認為重新定義設計工作,可以幫助我們擺脫這些問題。我們今天的生活、信仰和行為的結構,是早期的政府和宗教團體所發展的一種設計,因此所產生的社會階級和偏見也都是人為的結果。設計作為一門專業領域,同樣被過去的歷史所定義,變成一種資本主義用來銷售工業革命產品的工具。因此,現今的設計工作和設計教育,都致力於滿足僱主和客戶的獲利需求。
現代產品的設計在不知不覺中加劇了問題。為了獲取產品原料所進行的採礦作業對生態是有害的;在使用產品期間造成的能源消耗,以及人們受到引誘而購買產品,使得整個產品製造的過程對生態是有害的;產品刻意被設計得難以維護或更新,只能拋棄,對生態是有害的;最後,在產品最後被丟棄時對環境的破壞—這些全部都將會在本書的第三部分「永續性」進行討論。這些傷害並非故意為之,而是由於人們缺乏系統性思維、無法了解產品設計對現有社會態度、行為的影響,尤其是缺乏對於西方世界以外文化的理解。
這些行為全部都是人為的,這意味著它們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因此同樣可以透過重新思考和重新定義設計專業來改變。我們可以重新定義設計在教育和活動方面的意義,重新思考設計在生活、治理和產業中的角色,這些題目是本書探討的主題。隨著許多設計師看到設計領域重新框架的重要性,這項任務也會變得更加容易。對於這些問題的早期警訊,在19世紀末期以及20世紀前期就已經響起。如今,越來越多設計師加入了這個行列,我也希望為此發聲。也許與眾不同的是,我的觀點聚焦於人類的行為。許多設計師和非設計師都已開始表達關切並採取行動,我們可以樂觀地相信,我們能夠改變現狀。
產品目錄
推薦序
台灣版序
譯者序
PART 1 人造物
幾乎所有我們看到的事物,都是人工化的
1 幾乎所有人造的東西都是設計過的
2 人工化的生活方式無法永續
3 為什麼歷史很重要?
4 精確卻人工化的測量
5 如果科技把我們帶入了今天的困境,或許科技也能幫我們脫離困境
6 關於此書:有意義、永續性、以人類為本
PART 2 具有意義
以容易了解的方式進行溝通
7 意義的必要性
8 自然科學中的測量技術
9 測量對人們重要的事物
10 國內生產毛額
11 什麼才是對人真正重要的測量?
12 人類行為與經濟學
PART 3 永續
扭轉並且修補世界生態系所遭受的損害
13 我們生活在一個廢棄物的時代
14 世界如何陷入今天的困境?
15 永續性的多重元素及影響
16 設計、產品、永續性和循環經濟
17 落實循環設計所面臨的實際困難
18 永續、強固和有韌性的系統
19 人們對於系統的理解
20 複雜的社會技術系統
21 為時未晚
PART 4 以人類為本
世界上與生活相關的方方面面
22 從個人轉向整體人類
23 設計和開發的民主化
24 為自己設計的人們
25 設計X:大型複雜系統的設計方法
26 漸進主義(摸索前進)的挑戰
27 漸進式模組化設計
28 必須進行大型、跨領域專案的時候
29 面對「規模」這件事
30 設計是必要的,但是並不夠
PART 5 人類行為
重大的挑戰
31 為什麼改變這麼困難?
32 人們會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動員
33 什麼必須改變?
34 科技的主導地位
35 科技的未來
PART 6 行動
學習、反思、決定、行動
36 可以怎麼做?
37 我們能做些什麼?
38 總結:這本書的要點
附註
參考文獻
各界推薦
劉世南|台灣設計研究院研發長、成大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特聘教授
◎好評推薦
唐玄輝|台科大設計系教授、設計創新思考研究室主持人
許 言|大同大學設計學院副院長、設計科學研究所所長
楊天豪|永續環境工作者
楊振甫|5% Design Action 社會設計平台執行長
簡又新|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本書反思人造物世界所面臨的困境,及設計所造成的影響,強調價值測量與意義溝通的重要性,提出以人類為本的思考框架,挑戰人類永續與科技主導的系統問題。值得關注人本設計思考實踐者詳細閱讀與反覆思考。──唐玄輝,台科大設計系教授、設計創新思考研究室主持人
這本書不僅揭示了設計的力量,更提供了實用的方法和策略,讓我們可以將設計思維應用於創造一個更美好永續的世界。──許言,大同大學設計學院副院長、設計科學研究所所長
For a better world,不能只有感性善心,更要有實踐善法。本書就像是將人類環境待解議題的浩空繁星,透過設計思考連結成有意義且具想像的星座,為永續之路指引出多種可能的參考座標。──楊天豪,永續環境工作者
本書深入探討「設計」對人類和地球的影響,從設計思考到永續行動的最佳串接,鼓勵大家藉由此書共創未來地球解方!──楊振甫,5% Design Action社會設計平台執行長
◎國外好評
此書是一個勇敢的嘗試,擴大了人們對優秀設計的可能性和責任的認識。──Worth
諾曼的書雄心勃勃,令人欽佩。──快公司Co.Design
唐納.諾曼曾在學術界和工業界從事電子工程、認知心理學、電腦科學和設計工作。現在八十多歲的他利用這些經驗,解釋了設計師、政府和工業界為何必須將設計的概念從「以人為本」擴大到「以人類為本」。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強調生活品質,而不是金錢回報,並摒棄有害的經濟指標。他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當前的環境和經濟危機中生存下來。──《自然》(Nature)
諾曼描繪了一個飽受氣候變遷、不平等和不合理浪費困擾的世界。儘管如此,他還是很樂觀。他相信人類可以改變自己所創造的一切。設計是關鍵,因為它可以調動各種系統來解決技術、政策和人之間的複雜問題。──《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這本書向讀者提出了挑戰,要求他們批判性地審視指導和建構我們日常生活的現有規範系統。透過務實的探索,本書揭示了日曆系統、科學測量和其他結構中的偏見,這些偏見限制了我們的生活,進而難以帶來有意義的改變。對以人為本的設計、設計正義、系統設計,以及設計的永續角色感興趣的人來說,這是一本極好的入門讀物。唐納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且樂觀正向,敦促每個人思考拆除現有的權力系統,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平面設計師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Registered Graphic Designers)
唐納.諾曼提倡負責任和可永續的設計,對設計從以使用者為中心,轉變為服務社會和整個地球的需求,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力。──Leyla Acaroglu,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地球衛士」獎得主
透過科學、技術、設計、哲學和人類行為的實例,諾曼敘述了當前的全球挑戰,並展示設計如何在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又是一部經典之作!──Srini Srinivasan,參議員、世界設計組織(World Design Organization)前主席
諾曼又寫了一本必讀的書!他深刻的智慧為每個人提供了一種動員意識。在這個浪費、不注重永續和完全不負責任的時代,這本書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Anne Asensio,世界設計組織董事會成員、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循環設計領袖圈成員
作者介紹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認知科學與心理學榮譽教授及設計實驗室榮譽創始主任。美國《商業周刊》將其評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設計師之一。曾擔任蘋果公司副總裁、多家公司的顧問和董事會成員,並擁有三個榮譽學位。多部著作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包括《設計的心理學》和《情感@設計》等書。 / 陳宜秀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畢業,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畢業後任職於美國與台灣的科技業逾二十年,從事互動設計和通訊產品的研發工作,累積三十餘項專利,所設計的產品於2006年得到德國iF設計獎,以及2016年ISDA設計研究獎。2017年起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數位內容與科技學程。
規格
退貨說明
退貨須知:
- 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您享有商品貨到次日起七天猶豫期(含例假日)的權益(請注意!猶豫期非試用期),辦理退貨之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不得有刮傷、破損、受潮)且需完整(包含全部商品、配件、原廠內外包裝、贈品及所有附隨文件或資料的完整性等)。
- 請您以送貨廠商使用之包裝紙箱將退貨商品包裝妥當,若原紙箱已遺失,請另使用其他紙箱包覆於商品原廠包裝之外,切勿直接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若原廠包裝損毀將可能被認定為已逾越檢查商品之必要程度,本公司得依毀損程度扣除回復原狀必要費用(整新費)後退費;請您先確認商品正確、外觀可接受,再行拆封,以免影響您的權利;若為產品瑕疵,本公司接受退貨。
依「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下列商品不適用七日猶豫期,除產品本身有瑕疵外,不接受退貨: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蔬果、乳製品、冷凍冷藏食材、蛋糕)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如:客製印章、鋼筆刻字)
- 報紙、期刊或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襪類、褲襪、刮鬍刀、除毛刀等貼身用品)
- 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若您退貨時有下列情形,可能被認定已逾越檢查商品之必要程度而須負擔為回復原狀必要費用(整新費),或影響您的退貨權利,請您在拆封前決定是否要退貨:
- 以數位或電磁紀錄形式儲存或著作權相關之商品(包含但不限於CD、VCD、DVD、電腦軟體等) 包裝已拆封者(除運送用之包裝以外)。
- 耗材(包含但不限於墨水匣、碳粉匣、紙張、筆類墨水、清潔劑補充包等)之商品包裝已拆封者(除運送用之包裝以外)。
- 衣飾鞋類/寢具/織品(包含但不限於衣褲、鞋子、襪子、泳裝、床單、被套、填充玩具)或之商品缺件(含購買商品、附件、內外包裝、贈品等)或經剪標或下水或商品有不可回復之髒污或磨損痕跡。
- 食品、美容/保養用品、內衣褲等消耗性或個人衛生用品、商品銷售頁面上特別載明之商品已拆封者(除運送用之包裝外一切包裝、包括但不限於瓶蓋、封口、封膜等接觸商品內容之包裝部分)或已非全新狀態(外觀有刮傷、破損、受潮等)與包裝不完整(缺少商品、附件、原廠外盒、保護袋、配件紙箱、保麗龍、隨貨文件、贈品等)。
- 家電、3C、畫作、電子閱讀器等商品,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退回之商品已拆封(除運送用之包裝外一切包裝、包括但不限於封膜等接觸商品內容之包裝部分、移除封條、拆除吊牌、拆除貼膠或標籤等情形)或已非全新狀態(外觀有刮傷、破損、受潮等)與包裝不完整(缺少商品、附件、原廠外盒、保護袋、配件紙箱、保麗龍、隨貨文件、贈品等)。
- 退貨程序請參閱【客服專區→常見問題→誠品線上退貨退款】之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