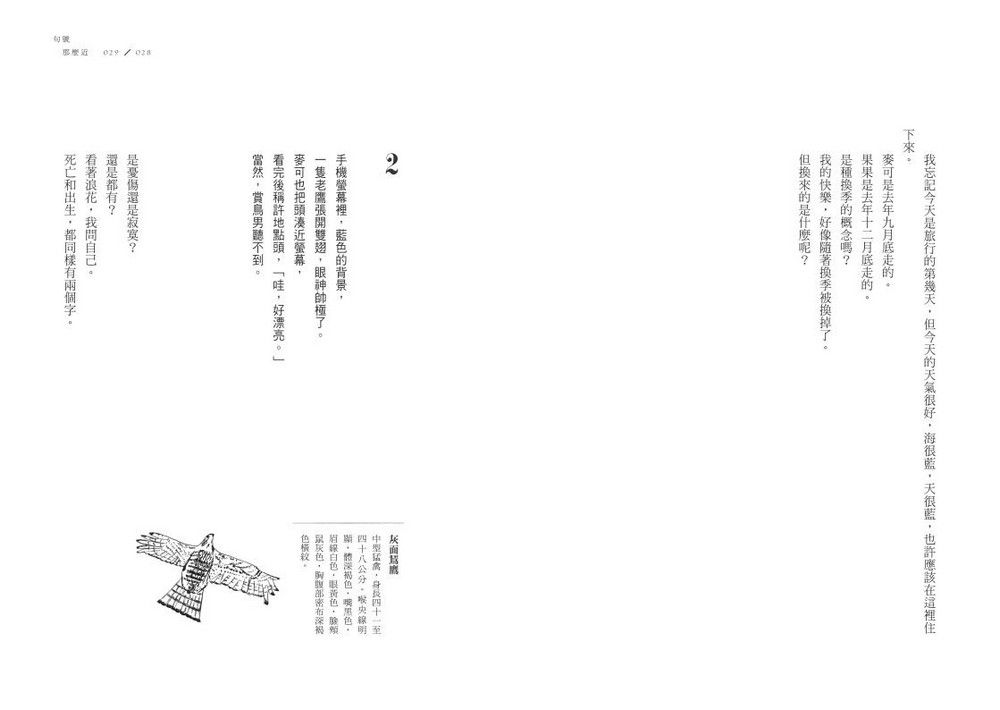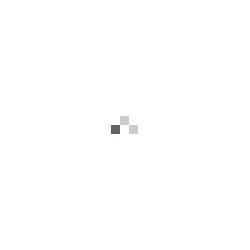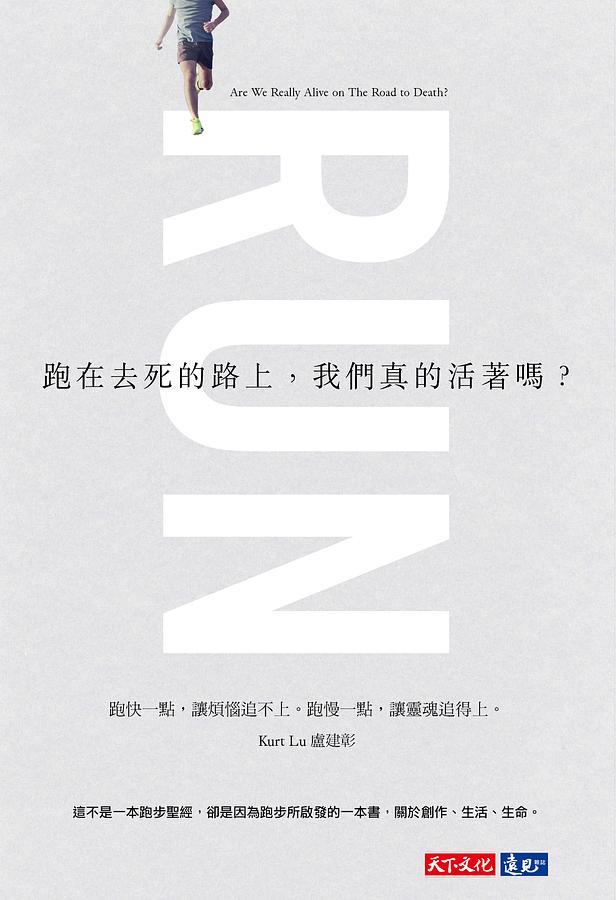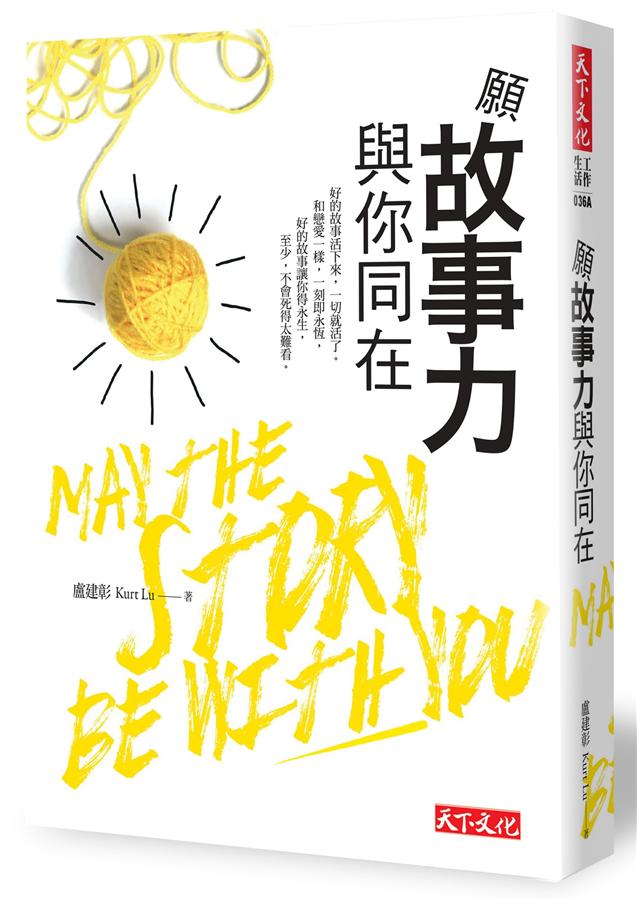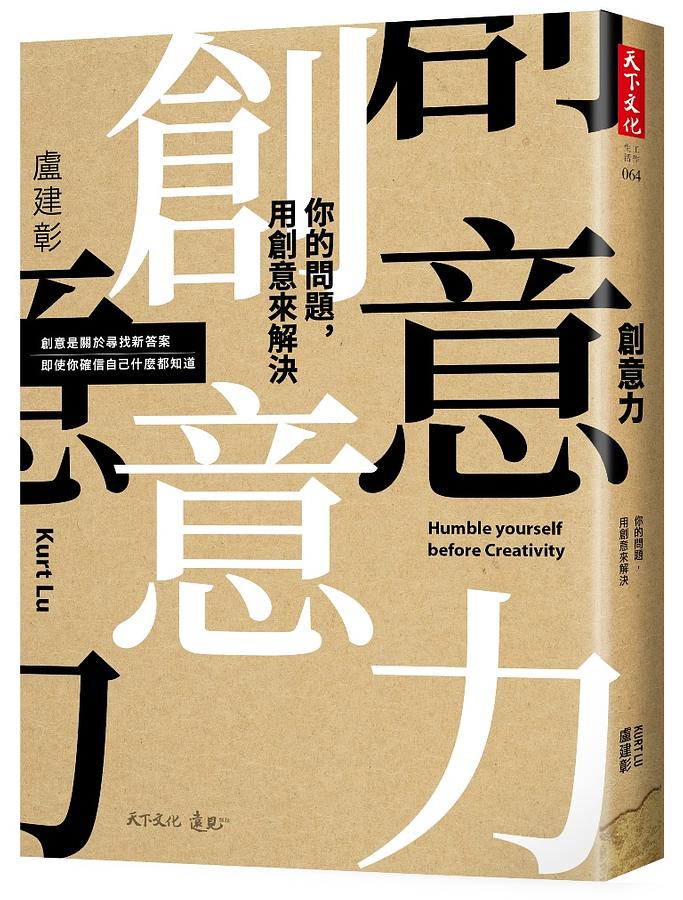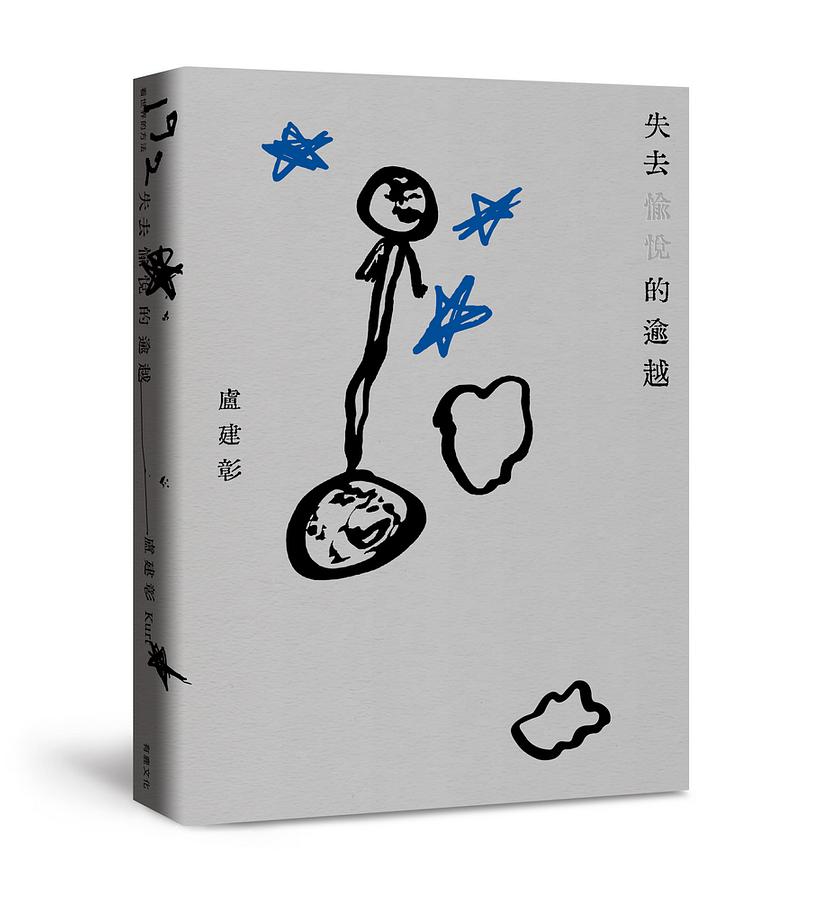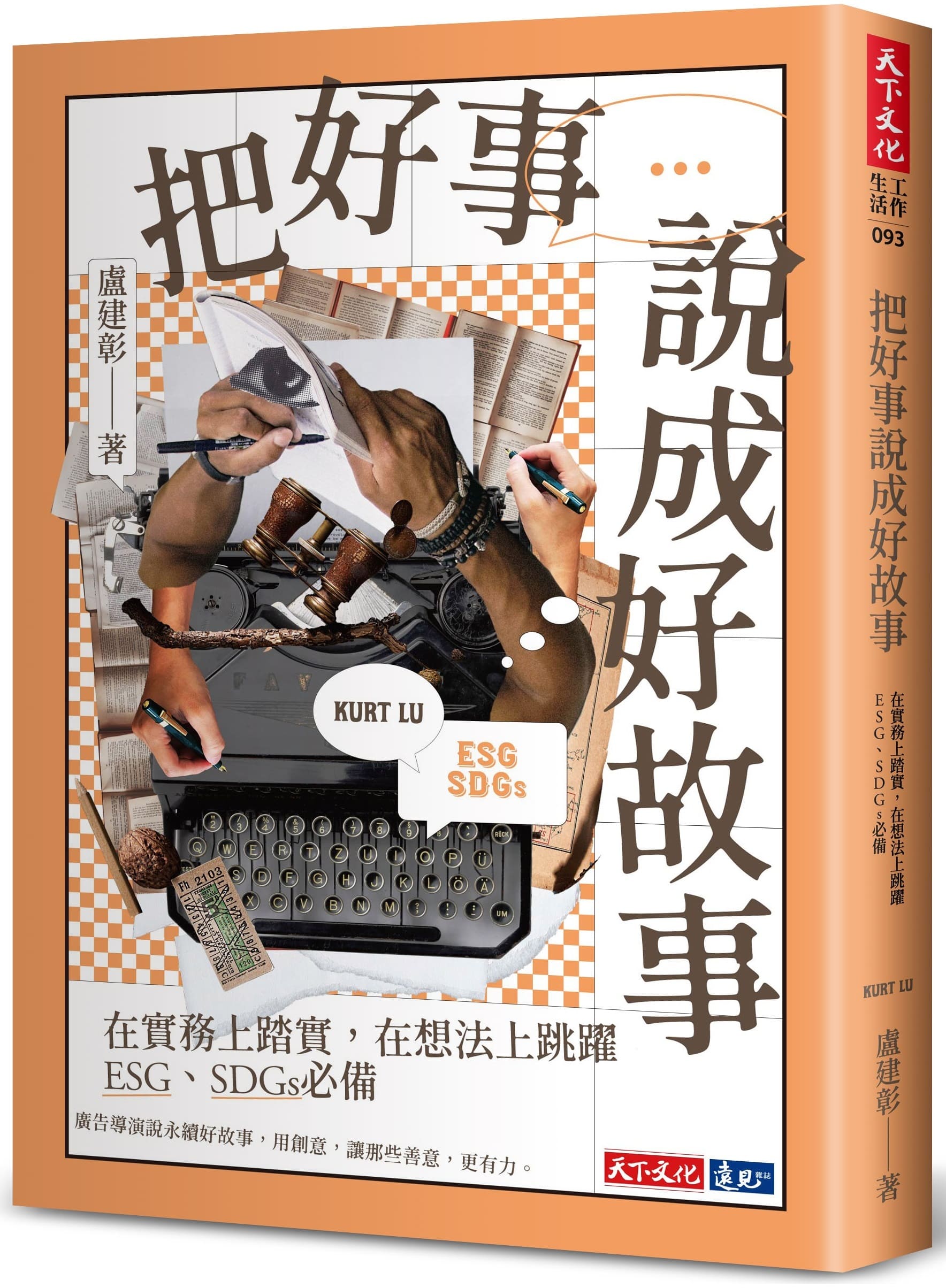沒有誰能說,路上的指標,是不是都真的正確。
但願你能說:「我還滿享受這一趟路的旅程。」
人人都有捨不得放開手的時刻,是不是?--平路
旅程未完,作者猶在途中奔赴。--廖玉蕙
內容簡介
當生命的波瀾不斷襲來,你是否也……很想死?
上路吧!
詩人導演盧建彰直衝內心的島嶼旅行小說,邀你一起──
去沒去過的地方,做沒做過的事,
更不遺餘力的,認識這塊土地
一場公路旅行,一路劃開,一路結痂。
沒有誰能說,路上的指標,是不是都真的正確。
但願你能說:「我還滿享受這一趟路的旅程。」
人人都有捨不得放開手的時刻,是不是?--平路
旅程未完,作者猶在途中奔赴。--廖玉蕙
●埋在心底的兩場告別式,交織出一部關於想念的小說──
詩人導演盧建彰的第十九號作品,寫的是埋在心底的兩場告別式。2022年9月,台灣民主運動前輩林世煜「麥可」於他深愛的台灣百岳過世;同年12月,送走了陪伴16年的狗兒「果果」。他們總是對台灣充滿好奇,更喜愛深度旅行。如果,讓他們在小說裡展開旅途呢?他們會看見什麼?為了什麼而停?而書中的「我」,又會隨著他們的腳步去哪裡?
●從天而降突然的暴力 VS. 土裡長出的文化記憶──
隨著書中主角行經遺址,瞻仰神木,在旅社撫觸已少見的「棉被花」技藝,並且在大水中救人,走上災後重建的蹊徑,看似悠悠的公路之旅,其實路過的都是往昔記憶。全書奠基於真實事件與台灣地景,但添以途中聽聞的聲色光影。是歷史?或是奇談?讓人不禁恍惚:此刻看不見的,是否曾經存在?更深深思考:我們能以何種方式,將自然與文化保留下來?
●旅程中最讓人驚懼的,不是意外,而是牽掛──
書中除了奇想的公路之旅,更有一道隱形的線,牽起主角與失智三十餘年的母親。母親沒走,卻不可能與「我」分享旅行的種種。如果承認人生的終點是死亡,我們想繞路而行,或選擇最短的路徑?面對唯一一次、直通內心的冒險旅途,我們真的做好畫下句號的準備了嗎?
。.。
故事的開始,麥可與果果,已經在車上。麥可微微笑,果果搖尾巴。他們一個在2022年9月底遠行,一個則在12月離開。我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因為太想念他們而出發,但只要展開旅程,他們就會出現在我的身旁。
一趟有想像朋友與寵物相伴的島嶼旅行,會看見什麼?詩人導演盧建彰以小說包藏大議題,搖下車窗迎來蔓延整座山的相思樹。走進國小校舍,這裡有八十歲耆老唱著他們小學時的歌;二樓教室的白牆上,泥漿的痕跡是否代表底下已經滅頂?通往人生盡頭的路還能怎麼走,他不敢去想,只能睜大眼直視。伸手又放手,我們或許會更想好好把握此刻,與這裡。
從天而降突然的暴力,是天災,是意外;土裡長出的故事種子,要傳唱,要記憶。劃開可見與不可見的傷,這本看似奇想的公路小說,實是直通心底的悲傷冒險。循著書中的標誌,彷彿能夠指認出台灣先賢、在地生態、獨立書店、瀕危動物等曾經存在/發生的印記。而路途上的奇人異事,既是作者面對個人傷逝的癒合,也是對於台灣諸多遺憾事件的結痂書寫。 / 3 相思樹
昨晚兩點醒來,迷糊間想著耳朵裡的到底是什麼聲音,是時間的聲音嗎?那彷彿沙漏裡的沙子流瀉,再透過擴大機來到我耳邊的。究竟是什麼?好想把它轉小聲,但沒辦法,我找不到按鈕。
那是海浪聲呀。
當更深沉的黑降臨時,浪會變大聲,愈深愈大聲。
此刻,迥異於深夜,海浪聲不再是主旋律,退回為背景聲,輕輕柔柔。我從包包裡拿出跑步短褲,彎腰穿上襪子,果果早就興奮地在房間裡來回奔跑,她意識到我要出去跑步了。
小庭院裡,有股清晨特有的氣味,你一定知道,有點清涼,有點乾淨,簡直像是為早起的人準備的美好,總之,就是晚一些就會消失的氣味。
我低下身子,仔細拉了左腳的後側大腿肌肉,接著換邊。果果已經等不及了,在小小的庭院裡,不斷繞圈。我總覺得,她好像有回春的感覺,彷彿回到兩歲的時候,那麼興奮開心,身體強健。
「果果,等一下啦。」我請她退後,才把小庭院的小鐵門打開,走出去。海浪聲大了一點,頭上的棕櫚樹,腳下平整的草地,讓人感到清新。
我轉轉脖子,點開手機裡的跑步App,「三二一,開始!」有點太興奮的女聲傳出。我對腿邊的果果說:「開始囉!」
昨天翻的書叫《我在跑步》,是說一個人到處亂跑的心情。我覺得不賴,可以試試。
但該怎麼跑呢?我其實沒有想法,先順著海灘邊的水泥小徑跑,來回一段差不多一百公尺,實在不過癮。跳下水泥堤防,跑在鵝卵石堆上,腳掌不斷翻來轉去,很不習慣,但有種奇妙的新鮮感。而海浪聲很貼心的,打開更大的音量了,好舒服。
海平面上,風把海浪帶成一道道白線。遠處的沙灘上方,輕輕淡淡的,好像有人提著一片巨大的布幕,正要罩上灘頭。我想去看看,愈跑愈近,發現那是另一個海灣,一道用鉛筆隨手畫出的柔和曲線,也像是大波浪捲髮,躺在海與陸的交會。
若要過去,大概得先跑上外面的柏油路。
我左右張望,看到一條貌似廢棄的小徑。沿著小徑跑,經過無人使用的一排小屋,殘破的招牌,似乎以前是餐廳。透過骯髒的玻璃,可以看到裡面寫著美味的廣告字眼仍舊留著,在垃圾雜物之間,簡直就是我殘敗的人生翻版,一點也不美味。
出了小徑,迎面就是大馬路。早上的貨車奔馳著,可能因為車少,車速就快了。這樣跑步有點危險。
我看馬路的對面是座山,太陽正從山頂照下,光如同一塊黃色的布,掛在山坡上。
還是去跑對面呢?至少可以看到來車,雖然離藍色的海就遠了,但至少還有綠色的山和自己的命。
我跑向最近的紅綠燈,呆立著,等那燈號變換。雖然一台車也沒有,但你就該等,與多數時候一樣,等候,常常是人做最多的事,但不等,什麼事都不能做。
總算到了馬路的另一邊,我開心地跑,對著腿邊的果果說:「真的開始了喔!」
結果跑了兩步,看到左邊草叢間,隱隱約約透出一些水泥色,是墳墓,愈來愈多,可能是當地人的墓地吧。
我心裡覺得怪怪的嗎?還好,我比較擔心果果會害怕,但一邊喘著一邊想,果果已經過世了啊,應該不會怕吧,更何況,我們只要尊重對方,不會打擾的,沒問題的。
果果在我腿邊,很開心的樣子。我拜託她靠路邊,避免被車碰到。雖然我也不知道她被車碰到會是如何,但我不想冒險,我太喜歡她了。
過了那片墓地,我繼續沿著省道旁跑,兩旁的山坡上有許多樹,是相思樹。有種說法,相思樹是恆春半島原產,在日本時代大量造林,現在台灣海拔一千公尺以下都見得到,變成低海拔的主要景觀植物,以前作為家庭用的木炭,有重要的經濟價值。所以,眼前的相思樹,是台灣其他相思樹的發源嗎?各位阿公阿媽好,我在心裡向它們問好。
相思樹的名字好美,可是為什麼,我覺得曾經在美術館裡看過相思樹呢?那到底是怎樣的情境?我的記憶力模糊,不是一、兩天的事,最近變得更嚴重,可能太多想忘掉的事了。
突然,麥可跑在我前面。本來沒有的啊,是我伸手擦臉上的汗,略微閉上眼睛的時候嗎?睜開眼時,汗水讓視線有點模糊,加上慷慨的陽光,麥可就出現在十公尺前。黃色的運動上衣,藍色的運動短褲,白色的頭髮,渾圓有智慧的頭。
我用力跑向前去,喘了一點,但可以接受。我從他身後喊,「麥可。」
他往左後方回頭看我,緊閉著嘴唇,但弧度朝上,嘴上修剪整齊的白色鬍子也跟著改變弧度。無框眼鏡下的眼睛充滿笑意,是我喜愛的麥可。
再往前兩步,就與麥可肩並肩地跑起來了,兩個人的步伐一致,連呼吸也調整到一樣的頻率,呼呼吸,呼呼吸,是種奇妙的和諧。
果果在我的左腳旁,矯健的姿態,張大嘴,伸長舌頭,快速地用她的短腿交換著前進。實在太愉快了,左邊是綠色的山,右邊是藍色的海和天,金色的陽光從中間抹上一大片。
看著麥可,我突然想起來了,相思樹是在北美館看到的。
白色的空間裡,擺放在地上,一落相思樹幹。
那是一個以礦工為主題的畫展,我和麥可去看過。
那位前輩畫家,一輩子都在礦坑工作,於是他的畫多以身旁的礦工們為素材,裸露的上身,強健的肌肉線條,頭上戴著頭燈,全身只穿內褲,正舉著十字鎬,或使勁地把煤炭堆入台車裡,也有礦工群聚在洗澡的畫作。
據說,礦坑裡非常熱,也缺少水,所以這位畫家有時便用汗水來調墨,每幅畫作裡可能都有他的汗水。真正字面上的意思,揮灑汗水完成的鉅作。
那位畫家算是陳澄波的後輩,一樣到日本習畫,但家境不佳,是由地方上的仕紳支持贊助。學成回國後,畫畫無法立刻成為謀生工具,因家境需要,就也進到這仕紳的礦坑工作。雖然做的是文書相關,但身旁全是以勞力拚搏的礦工們,他也愛上了這股生命力,以肉體和大自然對抗的生命之美。
相思樹的材質較堅硬耐磨,當時大量地用在礦坑中,作為支撐坑道的主要用料。我們看礦坑裡頭一根根木頭架起,用的就是相思木。
記得那畫展的說明文字還提到,當時的礦坑簡陋無比,沒有安全保障,災難頻傳,往往一次坑道崩塌,就死上幾十人,許多家庭瞬間家破人亡。
我想像,在幾十公尺下的漆黑礦坑,充滿了危險,唯一擋在死亡和人之間的,就是相思樹。倘若相思樹擋不住的話,便是天人永隔,只能相思。
想到這,我看向麥可,他似乎也意識到我的目光,對我微微笑。
畫展現場擺放了好幾截相思樹幹,其中一支特別粗大,面向一道巨大的白牆。牆上黑色如煤炭的墨字,是一首由畫家寫的詩。
記得還有一件事,非常奇妙,當下覺得荒謬,但此刻我怎麼想不起來了。怎麼會這樣?
我看向麥可,汗水浸溼了他白色的頭髮。白色的相反是黑色,黑色是煤炭,是畫作。
我想起來了,對了,怎麼會忘記呢?那和麥可也有點遙遠的關係呀。
我向麥可開口:「麥可,你記得我們去北美館嗎?」
「記得啊,你想起來了?」他似乎也知道我心裡想的,臉上的微笑,慈祥裡有深意。
「你記得那個畫家,有畫我們老家安平的漁港?」
「有啊,是你先看到,叫我過去看。我後來站在那邊看很久。」
麥可和我都是安平出身,安平的漁港是畫家某次旅行時的繪畫素材。那幅畫,其實就是把我小時候慣常看到的景象給描繪出來。我看到的時候很興奮,好像自己的家鄉名字被超級搖滾樂團提到一樣,一種奇怪的與有榮焉。
「那你記得他上民生報頭版?」我問。
「當然,看,那真的是超級荒謬!」
「對啊,我每次想到上面的報導,我就想笑。」
「嘿啊,畫家當初看到自己的前輩陳澄波死得那麼慘,才終身躲在礦坑創作,卻因為美展得首獎,蔣經國來看展,還當面嘉勉,看,我不知道這些獨裁者在想什麼。」
麥可繼續說。
「看,那些獨裁者一定知道,知道畫家的背景,知道他去日本學畫,知道他的賢拜是陳澄波,知道他害怕威權,可是,硬要,硬上,要這個害羞古意的台灣人來面聖,只差沒叫他在畫展現場磕頭,看!」
麥可說得激動,最後一個「看」字,和著一個圓形的小白點飛出。是唾沫吧,是不小心的。麥可是個紳士,從不隨地吐痰。
「仔細想想,滿變態的。」
「看,你看,搞得畫家後來還要寫一封信,謝謝皇上,誠惶誠恐的,看。」以「看」開始,以「看」結尾,表示這事對麥可而言,真的很巨大。
「其實我不太懂,都已經政權無虞了,到底這樣欺壓一個藝術家有什麼意思?」
「那種心態很變態,權力者不時會有這種顯明的時刻,除了政治上的宣告,凸顯自己附庸風雅外,最要緊的是背後那種『因為我可以,所以我就要』的權力展現,那是人類最卑劣的惡行之一。」
「那你當時被起訴上法庭,面對這種威權體制,你不會怕嗎?」我好奇地問。
「會怕的,一定會怕的。我們是小個體,對方是大機器,你會被輾碎,你當然會恐懼。我站在那個法庭被告席,都覺得身體自己抖起來,無法控制。」
「那怎麼辦?」
「我跟你說,不怎麼辦,就站著,等它過去,等害怕過去。」
儘管談論著恐懼的經驗,麥可臉上卻是一種堅毅。
「害怕會過去,歷史會留下來。我真的很佩服你們那時候,那麼害怕卻還是去做。」我勉強說出。
「那也沒什麼,你遇到,你也會。」
麥可臉上一片平靜,海在他身後,白色浪花朵朵揚起。
一樣的話,我之前聽過,所以,我不知道這是來自我的記憶,還是麥可真的在這個奇幻的時間點說了,但那一點也不重要,不是嗎?如果我只是想要有他作陪,而他也真的陪伴著我在路上前行了,那不就好了?我到底還奢求什麼?
畫展牆上的文字寫著,那位畫家在被當權者眷顧後,可能深感不安,沒幾年便想方設法移民出國,去到太平洋的彼岸,住在洛杉磯。
但他太想念他成長的台灣了,於是每日傍晚都走到海邊,往西邊凝望,凝視著夕陽,凝視著大海,凝視著他回不去的故鄉。
當時有媒體到他的居所做採訪,為他拍了張照片。我記得,在畫展最後的角落,白色的牆上擺著那幅照片,美麗的夕陽正要落入海中。畫家背對鏡頭,碧藍的海,鮮橘太陽,透著巨大落寞的背影。
黃昏的故鄉。
完完全全就是那首歌。
眼前,相思樹蔓了整座山,綠意如此確實。我拚命喘著,海浪聲間只有我粗濁的呼吸聲,彷彿我的世界,除了呼吸,一點問題也沒有。
我只是相思。
各界推薦
平路|作家
宋怡慧|作家、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張嘉祥|作家、裝咖人樂團團長
曾文誠|棒球評論人
黃崇凱|小說家
楊斯棓|《要有一個人》作者、醫師
葉丙成|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廖玉蕙|作家、語文教育學者
鄧惠文|作家、精神科醫師
羅文嘉|水牛出版社社長
作者文字生動,輪轉著畫面,彷彿在流利地運鏡。這本書是療癒系……或許讀者跟作者一樣,漸漸會走出傷逝的週期。面對最無能為力的那件事,終於有力氣說一聲再見,來生再見。──平路/作家
閱讀盧導的文字,像是瀏覽人生或快或慢的交疊畫面,關於陰暗幽微的,關於幸福有光的……是不是慢慢地接近句點,你亦接近如光的所在?──宋怡慧/作家、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我也在《句號那麼近》中,窺見建彰和世煜前輩所處的星光時空片段,儘管那有可能是在虛構的時間線中延伸出來的平行時空……我是這麼理解的。──張嘉祥/作家、裝咖人樂團團長
死亡就是一切的終結嗎?Kurt也許想藉由他的書寫來跟我們說:未必。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本生命重啟的書。我真的這樣看……因為,我也愛麥可!──曾文誠/棒球評論人
在一場極哀傷的不捨告別,互聞其聲。友誼於是蔓生。這是真實,還是小說呢?……《句號那麼近》儼然是一場療傷之旅。──楊斯棓/《要有一個人》作者、醫師
一場Kurt自導自演的公路電影,與他一起跑遍台灣……雖然很異想天開,卻又如此扣人心弦。──葉丙成/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盧建彰以近乎人子的虔敬,學習麥可的君子模樣……他用生活態度的臨摹,訴盡對那人、那狗和那山的相思,還有,對母親的牽腸掛肚。──廖玉蕙/作家、語文教育學者
作者介紹
全家和鄭成功上岸後賜住安平古堡王城西,流放到台北做廣告24年,幸運到曾是The Gunn Report廣告創意積分台灣第一名。寫了19本書,寫過3首歌,和鋼筆是舞伴,每天游自由式1公里或跑5公里。相信創意就是生活的各種面向,覺得故事比權勢強悍,認為如果抓到一個信念就要有抓到一個信念的樣子,不然就別怕北七過日子。
FB粉絲專頁|盧建彰Kurt
導演作品連結|http://www.youtube.com/user/kurtjjlu
規格
退貨說明
退貨須知:
- 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您享有商品貨到次日起七天猶豫期(含例假日)的權益(請注意!猶豫期非試用期),辦理退貨之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不得有刮傷、破損、受潮)且需完整(包含全部商品、配件、原廠內外包裝、贈品及所有附隨文件或資料的完整性等)。
- 請您以送貨廠商使用之包裝紙箱將退貨商品包裝妥當,若原紙箱已遺失,請另使用其他紙箱包覆於商品原廠包裝之外,切勿直接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若原廠包裝損毀將可能被認定為已逾越檢查商品之必要程度,本公司得依毀損程度扣除回復原狀必要費用(整新費)後退費;請您先確認商品正確、外觀可接受,再行拆封,以免影響您的權利;若為產品瑕疵,本公司接受退貨。
依「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下列商品不適用七日猶豫期,除產品本身有瑕疵外,不接受退貨: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蔬果、乳製品、冷凍冷藏食材、蛋糕)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如:客製印章、鋼筆刻字)
- 報紙、期刊或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襪類、褲襪、刮鬍刀、除毛刀等貼身用品)
- 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若您退貨時有下列情形,可能被認定已逾越檢查商品之必要程度而須負擔為回復原狀必要費用(整新費),或影響您的退貨權利,請您在拆封前決定是否要退貨:
- 以數位或電磁紀錄形式儲存或著作權相關之商品(包含但不限於CD、VCD、DVD、電腦軟體等) 包裝已拆封者(除運送用之包裝以外)。
- 耗材(包含但不限於墨水匣、碳粉匣、紙張、筆類墨水、清潔劑補充包等)之商品包裝已拆封者(除運送用之包裝以外)。
- 衣飾鞋類/寢具/織品(包含但不限於衣褲、鞋子、襪子、泳裝、床單、被套、填充玩具)或之商品缺件(含購買商品、附件、內外包裝、贈品等)或經剪標或下水或商品有不可回復之髒污或磨損痕跡。
- 食品、美容/保養用品、內衣褲等消耗性或個人衛生用品、商品銷售頁面上特別載明之商品已拆封者(除運送用之包裝外一切包裝、包括但不限於瓶蓋、封口、封膜等接觸商品內容之包裝部分)或已非全新狀態(外觀有刮傷、破損、受潮等)與包裝不完整(缺少商品、附件、原廠外盒、保護袋、配件紙箱、保麗龍、隨貨文件、贈品等)。
- 家電、3C、畫作、電子閱讀器等商品,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退回之商品已拆封(除運送用之包裝外一切包裝、包括但不限於封膜等接觸商品內容之包裝部分、移除封條、拆除吊牌、拆除貼膠或標籤等情形)或已非全新狀態(外觀有刮傷、破損、受潮等)與包裝不完整(缺少商品、附件、原廠外盒、保護袋、配件紙箱、保麗龍、隨貨文件、贈品等)。
- 退貨程序請參閱【客服專區→常見問題→誠品線上退貨退款】之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