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雜燴 (新版)
| 作者 | 唐魯孫 |
|---|---|
| 出版社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大雜燴 (新版):【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內容簡介】作者出身清皇族,是珍妃的姪孫,是旗人中的奇人,自小遊遍天下,看得多吃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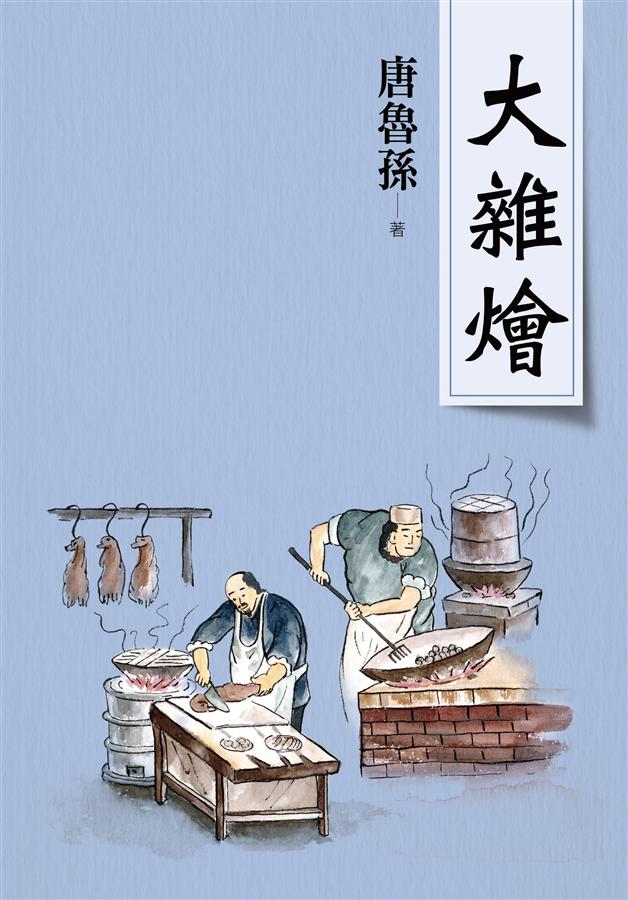
| 作者 | 唐魯孫 |
|---|---|
| 出版社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大雜燴 (新版):【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內容簡介】作者出身清皇族,是珍妃的姪孫,是旗人中的奇人,自小遊遍天下,看得多吃得 |
內容簡介 【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 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 【內容簡介】 作者出身清皇族,是珍妃的姪孫,是旗人中的奇人,自小遊遍天下,看得多吃得多,所寫有關掌故、飲饌都是親身經歷,「景」「味」逼真,《大雜燴》集掌故、飲饌於一書。
作者介紹 唐魯孫唐魯孫,本名葆森,魯孫是他的字。民國前三年九月十日生於北平。滿族鑲紅旗後裔,是清朝珍妃的姪孫。畢業於北平崇德中學、財政商業學校。擅長財稅行政及公司理財,曾任職於財稅機關,對於菸酒稅務稽徵管理有深刻認識。民國三十五年臺灣光復,隨岳父張柳丞先生來臺,任菸酒公賣局秘書。後歷任松山、嘉義、屏東等菸葉廠廠長。當年名噪一時的﹁雙喜﹂牌香煙,就是松山菸廠任內推出的。民國六十二年退休,計任公職四十餘年。先生年輕時就隻身離家外出工作,遊遍全國各地,見多識廣,對民俗掌故知之甚詳,對北平傳統鄉土文化、風俗習慣及宮廷秘聞尤其瞭若指掌,被譽為民俗學家。再加上他出生貴冑之家,有機會出入宮廷,親歷皇家生活,習於品味家廚奇珍,又見多識廣,遍嘗各省獨特美味,對飲食有獨到的品味與見解。閒暇時往往對各家美食揣摩鑽研,改良創新,而有美食家之名。先生公職退休之後,以其所見所聞進行雜文創作,六十五年起發表文章,民俗、美食成為其創作基調,內容豐富,引人入勝,斐然成章,自成一格。著作有《老古董》、《酸甜苦辣鹹》、《天下味》等十二部(皆為大地版)量多質精,允為一代雜文大家,而文中所傳達的精緻生活美學,更足以為後人典範。民國七十二年,先生罹患尿毒症,晚年皆為此症所苦。民國七十四年,先生因病過世,享年七十七歲。
產品目錄 饞人說饞 逯耀東 007 唐魯孫先生小傳 014 海天萬里為盧太夫人壽 016 蹻乘 021 扇話 034 鐵臂大元「蟀」 053 談失傳的「子弟書」 075 我所見到的梁鼎芬 079 故都茶樓清音桌兒的滄桑史 084 從綜藝節目「三百六十行」 097 蠍子螫了別叫媽 100 搖煤球燒熱炕 105 近代曹子建—袁寒雲 115 閒話故都年景 123 猜燈謎、拜三公 136 民初黑龍潭求雨憶往 147 張辮帥與褚三雙 152 談談清裝服飾與稱謂 161 再談清裝服飾 166 中國菜的分布 169 說煙、話茶、談酒 176 爐肉和乳豬 186 白湯麵和野鴨飯 191 北平的餑餑鋪 197 金雞一唱萬家春 208 老湯驢肉開鍋香 217 楊花滾滾吃新蚶 221 從梁壽談到北平的盒子菜 225 漫談紹興老酒 230 讀《烹調原理》後拾零 233 過橋米線的故事 239 談談《竇娥冤》 241 成吉思汗大祭跟那達穆競技大會 243 唐魯孫先生作品介紹 249
| 書名 / | 大雜燴 (新版) |
|---|---|
| 作者 / | 唐魯孫 |
| 簡介 / | 大雜燴 (新版):【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內容簡介】作者出身清皇族,是珍妃的姪孫,是旗人中的奇人,自小遊遍天下,看得多吃得 |
| 出版社 /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4023288 |
| ISBN10 / | 9864023284 |
| EAN / | 9789864023288 |
| 誠品26碼 / | 2681845065003 |
| 頁數 / | 256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唐魯孫先生小傳
唐魯孫,本名葆森,魯孫是他的字。民國前三年九月十日生於北平。滿族鑲紅旗後裔,是清朝珍妃的姪孫。畢業於北平崇德中學、財政商業學校。擅長財稅行政及公司理財,曾任職於財稅機關,對於菸酒稅務稽徵管理有深刻認識。民國三十五年臺灣光復,隨岳父張柳丞先生來臺,任菸酒公賣局秘書。後歷任松山、嘉義、屏東等菸葉廠廠長。當年名噪一時的「雙喜」牌香煙,就是松山菸廠任內推出的。民國六十二年退休,計任公職四十餘年。
先生年輕時就隻身離家外出工作,遊遍全國各地,見多識廣,對民俗掌故知之甚詳,對北平傳統鄉土文化、風俗習慣及宮廷秘聞尤其瞭若指掌,被譽為民俗學家。再加上他出生貴冑之家,有機會出入宮廷,親歷皇家生活,習於品味家廚奇珍,又見多識廣,遍嘗各省獨特美味,對飲食有獨到的品味與見解。閒暇時往往對各家美食揣摩鑽研,改良創新,而有美食家之名。
先生公職退休之後,以其所見所聞進行雜文創作,六十五年起發表文章,民俗、美食成為其創作基調,內容豐富,引人入勝,斐然成章,自成一格。著作有《老古董》、《酸甜苦辣鹹》、《天下味》等十二部(皆為大地版)量多質精,允為一代雜文大家,而文中所傳達的精緻生活美學,更足以為後人典範。
民國七十二年,先生罹患尿毒症,晚年皆為此症所苦。民國七十四年,先生因病過世,享年七十七歲。
海天萬里為盧太夫人壽
今夏是盧母李太夫人八旬榮慶,旅美知好提到,在臺七十五以上年紀,當年在大陸聽過盧母元音雅奏的朋友,寫點文字,以申祝頌。前年盧燕女士應中華電視台之約,在國語電視劇裡爨演《觀世音菩薩》,在下在《華視週刊》上寫了一篇︿盧燕盧母﹀,被盧燕看見,堅欲一晤。當時我住屏東,經《民族晚報》王逸芬兄電約北來,在王府跟盧燕賢伉儷敘晤一番,欣悉盧母在美精神健朗,遇有可造之材,靡不悉心教誨,循循善誘。平劇能在美國生根發芽,盧母實種其田。記得當年我也少年好弄,在北方與軒蓀兄共讌樂,今荷其敦囑,為文以壽盧太夫人,不能不勉力以應了。
我從小就是標準戲迷,從民國初年聽小馬五《紡棉花》起,一直到抗戰初期為止,日常生活大概總離不開戲園子。早年男女分班,除非祝壽彩觴公府酬賓堂會,很難得聽到男女合演好戲。肉市廣和樓的富連成早年不賣女座,四大名旦各班雖然賣女座,大多是樓上賣堂客,樓下賣官客,聽戲也得男女分座呢!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家裡人聽戲以坤班為主,小孩也就隨同成了坤班小客人啦。先是鮮靈芝、張筱仙的奎德社在文明茶園唱白天,可以說風雨無阻,天天光顧煤市街的文明茶園,後來鮮靈芝、張筱仙隱息,又改為城南遊藝園聽京戲。那個時候由琴雪芳挑大樑,唱了不久,琴雪芳就自行組班,在開明戲院唱白天了。琴雪芳的戲班除了琴雪芳、秋芳姐妹外(秋芳原名秋選浮),老生就是盧母李桂芬。還有青衣李慧琴,武生梁月樓,後換蓋榮萱,花旦金少仙、于紫仙,小生胡振聲,小丑宋鳳雲,後換一斗丑。這個戲班樑柱齊全,在坤班來說夠得上硬整二字。
我從小最愛聽冷門戲,因為若干幾近失傳的老戲,偶或在開鑼戲裡能夠發現。例如《神州擂》、《瘋僧掃秦》、《五雷陣》等等一類老腔老調的戲,全部淪為開鑼戲,所以我幾乎每場戲都可以聽到拔旗吹喇叭。琴雪芳所組的戲班在華樂園改建後又加上唱夜戲,樓上包廂是四個座位一間,琴秋芳有時沒有戲,見我在樓上入座就拉了胡振聲到包廂裡來聊天。有一天盧母貼的是《斬黃袍》,雖然劉鴻升的「三斬一碰」走紅一時,人人都喜歡唱上一兩段,可是坤班敢動這齣戲的還不多見。記得那一天盧母勾一字眉,龍衣華袞,唱起來滿工滿調,當時坤角有「三芬」,是張喜芬、金桂芬、李桂芬,稱一時瑜亮。可是「孤王酒醉桃花宮」,張、金二人都沒動過,只能讓盧母一人專美了。
有一天琴雪芳貼演新排本戲《描金鳳》,前場盧母跟李慧琴唱《黑水國》。名票陶畏初、何友三、管紹華三位聯袂而來,全神貫注,一言不發的聽戲,聽完了整齣《桑園寄子》,我問他們何以如此入神,陶畏初比較爽朗,他說這是奉命聽戲。他們三位正跟老伶人孟小茹(工鬚生,為早年梅蘭芳搭檔)學這齣《寄子》。據小茹告訴他們說,李老闆這齣《桑園》的身段非常細膩,特地前來「摟葉子」的(「摟葉子」係梨園行行話。意指偷學名角的特長。余叔岩曾於臺下偷學譚鑫培之技藝,如《問樵鬧府》出箱身段,《定軍山》下場耍大刀花等等,即從「摟葉子」而得),焉能不聚精會神的琢磨?我想這件事,直到現在盧母自己還不知道呢!
當年琴雪芳在華樂園的夜戲趙次老(即曾任東三省總督之趙爾巽,張作霖乃經其收編)跟貢王爺都是池子裡常客,奭良、瑞洵、樊樊山、羅癭公、王鐵珊(王瑚之號,北洋時代北平市市長︹舊稱「京兆尹」︺)也是每演必到,其中貢王、瑞洵兩位對盧母的唱做最為讚賞。當時盧母的琴師,也是經常給貢、瑞二老說腔調嗓的。他經常稱讚盧母氣口尺寸拿得準,噴口輕重急徐勁頭巧而寸,所以盧母一登場,池座有兩位戴帽頭的老者,每人用包茶葉的黃色茶葉紙,摺好壓在小帽邊上,遮擋煤氣燈的強光,就是貢、瑞二老了。盧母有兩次經紳商特煩唱《逍遙津》,就是此二老的傑作呢。當年趙次老在世,對於世交子弟之文采俊邁、蘊藉儼雅的青年,獎掖提攜,無所不至。春秋佳日時常邀集大家為文酒之會來衡文論字,記得王懋軒、薛子良先生的令公郎都是當年與會的文友,其中有一位年方弱冠汪君,能寫五六尺的大字,次老教他行筆運腕,並且拿出盧母寫的大字給他借鑑,從此才知道怪不得盧母對於大字筆周意內,敢情平日是真下過一番臨摹工夫的。有一年,冬令救濟義務戲,盧母貼的是《戲迷傳》,當場揮毫,寫了「痌瘝在抱」四個大字,現場義賣,被藍十字會會長王鐵珊將軍,以五百元高價買去,救濟了不少貧困。在北平專給人寫牌匾的書法名家馮公度,後來知道《戲迷傳》現場賣字的消息,深悔未能躬逢其盛,跟王鐵老一較短長呢。
趙次老對於度曲編劇興致甚高,琴雪芳所演《桃谿血》,即係次老手編,由羅癭公出名。劇中漁父一角,初排原請盧母飾演以壯聲勢,以盧母與趙府的交誼,似乎未便推卻,可是她格於搭琴雪芳班不接本戲原則,也加以婉拒。後來趙次老以「旡補老人」名,給琴雪芳編了一齣《風流天子》,是爨演唐明皇楊玉環故事。唐明皇一角應當是老生應工,可是幾位老人家斟酌至再,始終都沒開口,最後由琴秋芳以小生姿態串演。盧母的風骨高峻、硜硜自守的精神,在當時梨園行可算是操履貞懿,令人欽敬。
自政府播遷來臺,海外歸人每每談到平劇在美國已經播種生根,近幾年更是日趨茁旺,盧母在美凡事虛心求教,真想學點玩藝的男女,無不掰開啦、揉碎了傾囊以教。今當盧母八旬設帨吉辰,敢弁數言,都是五六十年前往事,以介眉壽。
推薦序 : 饞人說饞—閱讀唐魯孫 逯耀東
前些時,去了一趟北京。在那裡住了十天。像過去在大陸行走一樣,既不探幽攬勝,也不學術掛鉤,兩肩擔一口,純粹探訪些真正人民的吃食。所以,在北京穿大街過胡同,確實吃了不少。但我非燕人,過去也沒在北京待過,不知這些吃食的舊時味,而且經過一次天翻地覆以後,又改變了多少,不由想起唐魯孫來。
七○年代初,臺北文壇突然出了一位新進的老作家。所謂新進,過去從沒聽過他的名號。至於老,他操筆為文時,已經花甲開外了,他就是唐魯孫。民國六十一年《聯副》發表了一篇充滿「京味兒」的〈吃在北京〉,不僅引起老北京的蓴鱸之思,海內外一時傳誦。自此,唐魯孫不僅是位新進的老作家,又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從那時開始到他謝世的十餘年間,前後出版了十二冊談故鄉歲時風物,市廛風俗,飲食風尚,並兼談其他軼聞掌故的集子。
這些集子的內容雖然很駁雜,卻以飲食為主,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談飲食的,唐魯孫對吃有這麼濃厚的興趣,而且又那麼執著,歸根結柢只有一個字,就是饞。他在〈烙盒子〉寫到:「前些時候,讀逯耀東先生談過天興居,於是把我饞人的饞蟲,勾了上來。﹂梁實秋先生讀了唐魯孫最初結集的《中國吃》,寫文章說:「中國人饞,也許北京人比較起來更饞。」唐魯孫的回應是:「在下忝為中國人,又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可以夠得上饞中之饞了。」而且唐魯孫的親友原本就稱他為饞人。他說:「我的親友是饞人卓相的,後來朋友讀者覺得叫我饞人,有點難以啟齒,於是賜以佳名叫我美食家,其實說白了還是饞人。」其實,美食家和饞人還是有區別的。所謂的美食家自標身價,專挑貴的珍饈美味吃,饞人卻不忌嘴,什麼都吃,而且樣樣都吃得津津有味。唐魯孫是個饞人,饞是他寫作的動力。他寫的一系列談吃的文章,可謂之饞人說饞。
不過,唐魯孫的饞,不是普通的饞,其來有自;唐魯孫是旗人,原姓他他那氏,隸屬鑲紅旗的八旗子弟。曾祖長善,字樂初,官至廣東將軍。長善風雅好文,在廣東任上,曾招文廷式、梁鼎芬伴其二子共讀,後來四人都入翰林。長子志銳,字伯愚,次子志鈞,字仲魯,曾任兵部侍郎,同情康梁變法,戊戌六君常集會其家,慈禧聞之不悅,調派志鈞為伊犁將軍,遠赴新疆,後敕回,辛亥時遇刺。仲魯是唐魯孫的祖父,其名魯孫即緣於此。唐魯孫的曾叔祖父長敘,官至刑部次郎,其二女並選入宮侍光緒,為珍妃、瑾妃。珍、瑾二妃是唐魯孫的族姑祖母。民初,唐魯孫時七八歲,進宮向瑾太妃叩春節,被封為一品官職。唐魯孫的母親是李鶴年之女。李鶴年奉天義州人,道光二十年翰林,官至河南巡撫、河道總督、閩浙總督。
唐魯孫是世澤名門之後,世宦家族飲食服制皆有定規,隨便不得。唐魯孫說他家以蛋炒飯與青椒炒牛肉絲試家廚,合則錄用,且各有所司。小至家常吃的打滷麵也不能馬虎,要滷不瀉湯才算及格,吃麵必須麵一挑起就往嘴裡送,筷子一翻動,滷就瀉了。這是唐魯孫自小培植出的饞嘴的環境。不過,唐魯孫雖家住北京,可是他先世遊宦江浙、兩廣,遠及雲貴、川黔,成了東西南北的人。就飲食方面,嘗遍南甜北鹹,東辣西酸,口味不東不西,不南不北變成雜合菜了。這對唐魯孫這個饞人有個好處,以後吃遍天下都不挑嘴。
唐魯孫的父親過世得早,他十六七歲就要頂門立戶,跟外面交際應酬周旋,觥籌交錯,展開了他走出家門的個人的飲食經驗。唐魯孫二十出頭就出外工作,先武漢後上海,遊宦遍全國。他終於跨出北京城,東西看南北吃了,然其饞更甚於往日。他說他吃過江蘇里下河的鮰魚,松花江的白魚,就是沒有吃過青海的鰉魚。後來終於有一個機會一履斯土。他說:「時屆隆冬數九,地凍天寒,誰都願意在家過個閤家團圓的舒服年,有了這個人棄我取,可遇不可求的機會,自然欣然就道,冒寒西行。」唐魯孫這次「冒寒西行」,不僅吃到青海的鰉魚、烤犛牛肉,還在甘肅蘭州吃了全羊宴,唐魯孫真是為饞走天涯了。
民國三十五年,唐魯孫渡海來臺,初任臺北松山菸廠的廠長,後來又調任屏東菸廠,六十二年退休。退休後覺得無所事事,可以遣有生之涯。終於提筆為文,至於文章寫作的範圍,他說:「寡人有疾,自命好啖。別人也稱我饞人。所以,把以往吃過的旨酒名饌,寫點出來,就足夠自娛娛人的了。」於是饞人說饞就這樣問世了。唐魯孫說饞的文章,他最初的文友後來成為至交的夏元瑜說,唐魯孫以文字形容烹調的味道,「好像老殘遊記山水風光,形容黑妞的大鼓一般。」這是說唐魯孫的饞人談饞,不僅寫出吃的味道,並且以吃的場景,襯托出吃的情趣,這是很難有人能比較的。所以如此,唐魯孫說:「任何事物都講究個純真,自己的舌頭品出來的滋味,再用自己的手寫出來,似乎比捕風捉影寫出來的東西來得真實扼要些。」因此,唐魯孫將自己的飲食經驗真實扼要寫出來,正好填補他所經歷的那個時代,某些飲食資料的真空,成為研究這個時期飲食流變的第一手資料。
尤其臺灣過去半個世紀的飲食資料是一片空白,唐魯孫民國三十五年春天就來到臺灣,他的所見、所聞與所吃,經過饞人說饞的真實扼要的記錄,也可以看出其間飲食的流變。他說他初到臺灣,除了太平町延平北路,幾家穿廊圓拱,瓊室丹房的蓬來閣、新中華、小春園幾家大酒家外,想找個像樣的地方,又沒有酒女侑酒的飯館,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幾乎沒有。三十八年後,各地人士紛紛來臺,首先是廣東菜大行其道,四川菜隨後跟進,陝西泡饃居然也插上一腳,湘南菜鬧騰一陣後,雲南大薄片、湖北珍珠丸子、福建的紅糟海鮮,也都曾熱鬧一時。後來,又想吃膏腴肥濃的檔口菜,於是江浙菜又乘時而起,然後更將目標轉向淮揚菜。於是,金霽玉膾登場獻食,村童山老愛吃的山蔬野味,也紛紛雜陳。可以說集各地飲食之大成、彙南北口味為一爐,這是中國飲食在臺灣的一次混合。
不過,這些外地來的美饌,唐魯孫說吃起來總有似是而非的感覺,經遷徙的影響與材料的取得不同,已非舊時味了。於是饞人隨遇而安,就地取材解饞。唐魯孫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多年,經常南來北往,橫走東西,發現不少臺灣在地的美味與小吃。他非常欣賞臺灣的海鮮,認為臺灣的海鮮集蘇浙閩粵海鮮的大成,而且尤有過之,他就以這些海鮮解饞了。除了海鮮,唐魯孫又尋覓各地的小吃。如四臣湯、碰舍龜、吉仔肉粽、米糕、虱目魚粥、美濃豬腳、臺東旭蝦等等,這些都是臺灣古早小吃,有些現在已經失傳。唐魯孫吃來津津有味,說來頭頭是道。他特別喜愛嘉義的魚翅肉羹與東港的蜂巢蝦仁。對於吃,唐魯孫兼容並蓄,而不獨沽一味。其實要吃,不僅要有好肚量,更要有遼闊的胸襟,不應有本土外來之殊,一視同仁。
唐魯孫寫中國飲食,雖然是饞人說饞,但饞人說饞有時也說出道理來。他說中國幅員廣寬,山川險阻,風土、人物、口味、氣候,有極大的不同,因各地供應飲膳材料不同,也有很大差異,形成不同區域都有自己獨特的口味,所謂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雖不盡然,但大致不離譜。他說中國菜的分類約可分為三大派系,就是山東、江蘇、廣東。按河流來說則是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的菜系,這種中國菜的分類方法,基本上和我相似。我講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流變,即一城、一河、兩江。一城是長城,一河是黃河,兩江是長江與珠江。中國的歷史自上古與中古,近世與近代,漸漸由北向南過渡,中國飲食的發展與流變也寓其中。
唐魯孫寫饞人說饞,但最初其中還有載不動的鄉愁,但這種鄉愁經時間的沖刷,漸漸淡去。已把他鄉當故鄉,再沒有南北之分,本土與外來之別了。不過,他下筆卻非常謹慎。他說:「自重操筆墨生涯,自己規定一個原則,就是只談飲食遊樂,不及其他。以宦海浮沉了半個世紀,如果臧否時事人物惹些不必要的嚕囌,豈不自找麻煩。」常言道:大隱隱於朝,小隱隱於市。唐魯孫卻隱於飲食之中,隨世間屈伸,雖然他自比饞人,卻是個樂天知命而又自足的人。
一九九九歲末寫於臺北糊塗齋
最佳賣點 : 【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
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