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幾顆洋蔥? 精神分析想說
| 作者 | 蔡榮裕 |
|---|---|
| 出版社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憂鬱幾顆洋蔥? 精神分析想說:日常生活的普遍用語:憂鬱,十幾年前被叫做「懶惰病」,也曾被形容是,有顆石頭壓在心上,無法說出口......為什麼出了事就說是有「憂鬱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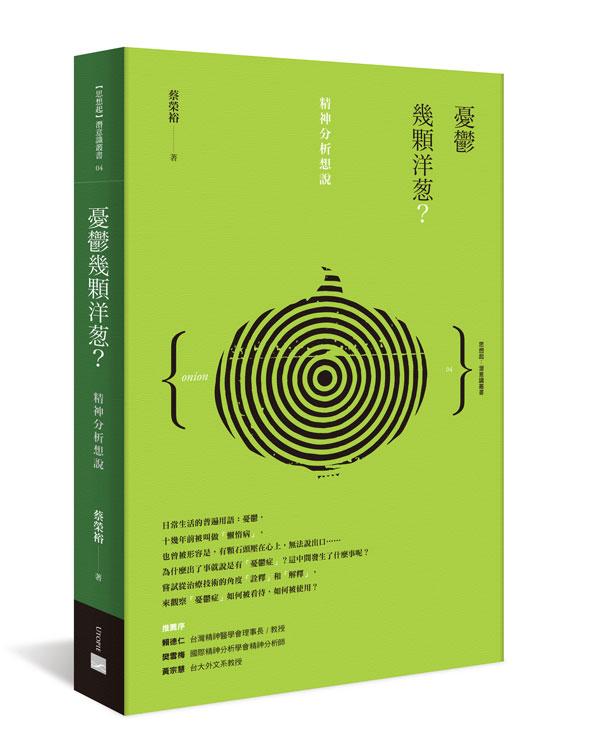
| 作者 | 蔡榮裕 |
|---|---|
| 出版社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憂鬱幾顆洋蔥? 精神分析想說:日常生活的普遍用語:憂鬱,十幾年前被叫做「懶惰病」,也曾被形容是,有顆石頭壓在心上,無法說出口......為什麼出了事就說是有「憂鬱症」? |
內容簡介 日常生活的普遍用語:憂鬱,十幾年前被叫做「懶惰病」,也曾被形容是,有顆石頭壓在心上,無法說出口......為什麼出了事就說是有「憂鬱症」?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嘗試從治療技術的角度「詮釋」和「解釋 」,來觀察「憂鬱症」如何被看待,如何被使用?就是不信邪吧?困惑著一個真實無比的現象。 何以複雜人性經驗的多元描述憂鬱,被窄化成只來自於負向想法?然後,順勢變成只要正向想法,就可以取代人性的複雜? 我需要說說不一樣的想法,不是為了不一樣而不一樣,而是臨床現實上就是如此多元性,實在無法硬擠進正向想法裡,否則,反而變成無法多加思索的限制。 是誰決定什麼是正向想法呢?重點在於,人性裡有光,也有暗處,是千百年來文學、藝術、哲學的經驗描述,怎麼會被現代版的普通心理學,簡化弄成只是一道光線呢?精神分析有些話想說,也有短詩、隨筆和劇本嘗試發聲。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蔡榮裕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心理治療資深督導高雄醫學大學《阿米巴詩社》成員《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員《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運用和推廣委員會主委
產品目錄 推薦序 /賴德仁/樊雪梅/黃宗慧小小說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經驗談第一章 噁心,是愚蠢或聰明絕頂呢?第二章 人的欲望是光明或是黑暗的事?第三章 你不是愛情的結晶,只有噁心?第四章 你說,你只希望父母的性有愛情?第五章 深奧吧!你說你有伊底帕斯情結?第六章 什麼!你說要和父親再重新生下自己?第七章 你說父母之間根本沒有愛情?第八章 多少黑的黑暗才是勇敢?第九章 道德的尿撒在父親的褲管上?第十章 父母的性遊戲要替小孩負責愛情?第十一章 沒有愛情的精卵竟然可以長出小孩?第十二章 孤單需要幾把刷子?第十三章 沒有愛情的精子和卵子如何打招呼?第十四章 噁心的方程式裡有愛情嗎?第十五章 我為什麼無法幫你判斷他有多邪惡?第十六章 什麼是美化自己的經驗呢?第十七章 如同飢餓的嬰孩先咬痛提供奶水的乳房短詩 漏網的魚隨筆 夢幻倫敦巫婆的奶水,以及足球和吊車都沒有說話異議份子在倫敦的咖啡屋觀光客的多重主義和枝節聖詹姆士公園下凡之後博物館的幽靈都已經忘記回家的路了貝爾賽斯公園路在寒冷的時候至於,那把孤獨的低音大提琴聲蝴蝶結和宗教畫掛在午夜的車廂華格納《帕西法爾》在迷宮裡相遇了困惑來倫敦要找尋什麼呢?卻有不知名小花誤闖雜文 三篇徘徊在憂鬱裡的風雨聲創傷經驗裡抑鬱「做自己」的困境心理治療技術「詮釋」或「解釋」的差異 兼探索憂鬱症如何被談論的多樣性憂鬱和悲傷的淚水各有幾行?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交纏劇本 另一種劇本:叫做內心戲的憂鬱的空洞裡,誰在沈睡?跋作者謝辭
| 書名 / | 憂鬱幾顆洋蔥? 精神分析想說 |
|---|---|
| 作者 / | 蔡榮裕 |
| 簡介 / | 憂鬱幾顆洋蔥? 精神分析想說:日常生活的普遍用語:憂鬱,十幾年前被叫做「懶惰病」,也曾被形容是,有顆石頭壓在心上,無法說出口......為什麼出了事就說是有「憂鬱症」? |
| 出版社 /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9297288 |
| ISBN10 / | 9869297285 |
| EAN / | 9789869297288 |
| 誠品26碼 / | 2681496781000 |
| 頁數 / | 316 |
| 開數 / | 30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3.7X21CM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序/導讀
摘自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黃宗慧教授之推薦序
繞道文學的精神分析?
蔡榮裕醫師的新書《憂鬱幾顆洋葱?精神分析想說》所集結的作品文類有小說、散文、評論、劇本,除了被作者自己歸類為「雜文」的「三篇徘徊在憂鬱裡的風雨聲」屬於理論評述性質,直接探討了憂鬱問題的不同面向,其他幾類作品都有著高度的文學性,一如洋蔥般有待讀者層層瓣瓣地剝開。莫非,要進入精神分析的世界一窺其堂奧,最好的方式是繞道文學?然而,這真的是一種繞道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也容我也先「繞道」文學,談一下美國導演伍迪艾倫創作的一則短篇故事〈庫格馬斯插曲〉(“The Kugelmass Episode”)。
故事的主角庫格馬斯,是一名離婚又再婚的大學教授,但和第二任妻子的關係依然陷入瓶頸,他嫌棄妻子不復過去的苗條,腫成一顆海灘球,又指責妻子如同他的枷鎖,於是,他求助於精神分析師。故事的開場就在治療的診間,庫格馬斯一面抱怨生活,一面斷定外遇可以改善自己的狀況,這時分析師對他說:「外遇解決不了問題。你太不實際了。你的問題深層得多。」然而儘管分析師數度打斷他關於外遇的幻想,庫格馬斯還是不予理會,逕自說起他的焦慮之夢,夢中的他手裡提著野餐籃,籃子上寫著「各式選擇」,但這時他卻發現提籃有個破洞!夢的訊息很明顯:步入中年危機但又還想不斷戀愛的男主角,擔心自己已經沒有多少選擇的機會了。分析師聽完這夢境,只是告誡他,他最不該做的事情就是「行動化」(act out)(簡化地說,就是因壓抑的回返造成個案突然出現衝動行為)。分析師說,「你必須就在這裡把你的感覺表達出來,然後我們一起來分析。你接受治療也已經很久了,應該知道沒有一夜之間就治癒的療法。我是分析師,不是魔術師。」但也就是這樣的回答,讓庫格馬斯毅然決定終止治療,悻悻然地說 ,「那也許我需要的就是魔術師」。對於一篇精彩還在後頭的短篇故事來說 畢竟之後男主角可是要穿越時空遇見包法利夫人啊 這段與分析師之間的對話當然不會是伍迪艾倫的重點所在,分析師只是伍迪艾倫要嘲弄的角色之一,無能的分析師和稍後要登場的,貪財但戲法卻又不靈光的魔術師一樣,說明了這世界上充滿贗品與郎中:分析師只會要求個案盡量述說,卻拿不出一點「成果」,還好意思叫治療很久都無效的個案要體認分析並非一蹴可幾的道理!
既然如此,為何非要繞道這個短篇故事,才能談《憂鬱幾顆洋葱?精神分析想說》?因為單從引述的故事段落我們就已不難看出,〈庫格馬斯插曲〉裡的分析師形象,正符合一般人對於精神分析治療的刻板印象與粗淺理解:要個案「自由聯想」,卻又不輕易提供詮釋。不論是對於不相信精神分析的人而言,或指望分析師「對症下藥」、「藥到病除」但期待落空的個案而言,庫格馬斯決定終止分析都看似是明智的選擇,畢竟精神分析的開山始祖佛洛伊德就直接表示過:「治療的成功不是我們首要的目標。我們所致力達到的是讓病人意識到他的潛意識願望」(SE 10, 120),而自認其理論乃回歸佛洛伊德的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也認為,「被假定知道的主體」(subject supposed to know; sujet supposé savoir)並不是分析師,而是個案本人;那麼,我們還能對分析師抱有甚麼期待?
事實上,分析師也並不希望個案對他有太多期待,因為精神分析的特殊性與重要意義,就在於它不認為人類複雜的心靈活動可以被任何科學充分解釋。換句話說,看似不知道、不能確定任何事的分析師,可能正是稱職的分析師,也更有機會讓個案完成「意識到自己的潛意識」這個艱鉅的工作。比起一昧鼓勵個案正向思考、追求自我的完整,精神分析更想說的,是那些關於人類慾望將如何無止盡地流動的故事,這些流動,或許會構成生活的擾動,卻也是人活著的證明。從這個角度來看,精神分析想說的,和文學想說的,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更接近。
也因此,蔡醫師的新書並不是一本繞道文學的精神分析之書,因為繞道一詞本身可能就是需要商榷的,畢竟精神分析和文學的軌道,經常是重合的,而這點也早已為佛洛伊德所指出,他在小說家詹森的《格蒂沃娃》(Gradiva)中驚喜地發現了許多可以用來印證《夢的解析》的線索,發現了從詮釋這部小說所能歸納出的原則,竟然和觀察分析疾病的所得致的看法一模一樣,於是他說:「看來唯一的結論就是,要不是我們兩者,作家和醫生,都以同樣方式誤解了潛意識,要不就是我們都正確地理解了它」(SE 9, 92),而佛洛伊德的答案,當然是後者。
至於蔡醫師的這本書,特別是將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場景小說化的做法,更是「一人分飾兩角」地以作家和醫師的身分為佛洛伊德的說法做了絕佳的註解,同時,也實踐了拉岡所謂的「分析師論述」。我們看到,小小說中的個案不斷訴說與父母的關係如何造成她的陰影、影響了她現在的行為與選擇,但聆聽的分析師卻不願扮演那個套用理論去解釋創傷來源的大他者,聆聽越多,理解越多之後,他形容自己如同在狹窄的細縫裡看見了光明和黑暗,但「又不再只是條條分明,而是交叉地存在著」。換句話說,在細縫裡看見更多的可能性,弔詭地也意味著單一明確答案的可能性越來越少。............................................
內文摘錄 憂鬱的空洞裡,誰在沈睡?
她:約二十出頭的女性
她的媽媽:喜歡突然失蹤離家幾天或幾個星期
她的爸爸:喜歡無厘頭責打家人
我:一個喜歡聽人說話的女人
故事:
她的爸爸在很小的時候逃離家。她的媽媽在很小的時候逃離家。她的爸爸和她的媽媽後來在一起,為了有一個家。這個家是個防空洞,也是空洞。防空洞堅持古典不願長大,空洞卻會自己長大,直到擁擠得待不住......故事很簡單,只是人性太複雜。
佛洛伊德路過台灣,要尋找一個家,和川端康成擦身而過,佛洛伊德能嚴肅認真想些什麼嗎?
地點:
每個人都在現場,摸索佛洛伊德說的自我的空洞,各種白色構成的牆壁,阻隔著每個人之間的流動,可以在森林裡,在海灘上,在房間裡,在劇場後台......
第一幕第一景:她想說的話
很久很久以前,佛洛伊德這麼說過,在重要的照顧者過世後,一般是很傷感難過,但是一陣子後,就會覺得那個人離開了,自己會再度走下去。但是有些人卻變得自己被帶走了,不只是那個人離開人世,他們覺得自己也跟著走了。佛洛伊德說,那是因為自我裡留下一個空洞化般的陰影,自己也跟著不見了。
不過,她的故事卻顯示了,那個空洞不是一般的空洞陰影,也不是一般的陰影。那是什麼呢?難題就從這個地方開始,這是佛洛伊德說話的現實所呈現的侷限,他的侷限卻是她的開始。我只是事後聽到這些故事後,深怕有什麼重要的經驗會流失掉,因此就一直緊盯著這個現象。
她說:
我想,她一定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才會在上次碰面時,跟我說她了解我。
這怎麼可能啊,我不過說了一點點,連皮毛都還沒有說出口呢。除非她真的這麼厲害,我在前一陣談自己心情不好,好像頭腦裡有個空洞時,說到川端康成是個老色迷,才會寫出《睡美人》這種故事。
她一定搞得懂,我偏偏就是被這個故事激活起來,不然,我早就真的不在人世了。她一定以為我是厭世的人,其實,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樣子。從其它角度來說,我一點也不厭世,只是對於活著要幹嘛,唉,如果硬要說,活著要幹嘛,我後來找到的出路是,要填滿佛洛伊德所談失落的陰影。
嗯,要填滿那個陰影。
我這麼說,她一定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因為她就是搞這行,說的是這些行話,只是當我在場的時候,她卻根本不談這些。我只好從書裡努力地找出來,到底我在說什麼,或者她沒有說的是什麼?我說的佛洛伊德的陰影或空洞,是我自己看書看來的,但是當我知道,她會把我塞進那個空洞裡的說法後,我就極力的抵抗。
我就極力的抵抗。
每當她要說的話可能跟這有關,我就閉著耳朵,或者只是一直點頭,點得她知道我根本就是毫不同意,多麼神奇的同意,竟然可以因為點頭的速度和長度,而變成完全相反的意思。
我發現只要我說得很空洞時,她就會被我激惹得想要說些話,好像怕我被自己說話所形成的空洞所淹沒了。我真的很難形容,要說些什麼會形成這種空洞感?仔細想想,應該不是我說了什麼,而是當我在說些事情時,會留下更多沒有說出來的事情。這樣子,空洞就成形了,真的很巧妙,這些技能是我跟她開始說話後,我才發現自己有這種特殊技能。並不是和她說話時,我才有這種技能,而是我早就會了,只是以前不知道。和她說話後,我才發現自己有這種能耐,我說是能耐,但對她來說,應該是一個大問題吧。
因此她一直很想要我,把事情說得飽滿些,不然,我的說話方式是愈說就愈把我的人生過得愈來愈空空洞洞。我不是那麼在意有這種空洞啊,只是每次看她出力要說些話填滿那種空洞,我就覺得好笑。尤其是當我開始說《睡美人》的故事後,她變得更不安了,我可以輕易看出她的不安。但是,但是啊,她大概不會承認自己的不安。不過,我也沒興趣要跟她正面對抗,指出她的不安,如果我有嘗試這麼做,一定不是我刻意要那麼做的。
我就來談談《睡美人》吧。我的朋友都覺得這個故事好噁心,怎麼會有這麼噁心的故事啦。但是看見朋友的表情,反而讓我有了興奮的感覺,連腳趾頭都想要跳起來的感覺。我看了《睡美人》後,我覺得自己就是那些睡美人。唉,唉,竟有人興奮地說,扮演睡美人可以等待王子,這種等待是值得的。後來我告訴這位朋友說,我看的這個《睡美人》的故事,是吃安眠藥後睡著的少女,讓老人來陪著她們睡。川端康成的說法是,老人才是重點,是那些老人陪著她們睡。我覺得是先被餵藥睡著後的少女,陪著那些老人過夜。
我有個讓她很驚悚的想法。
我就是那些睡美人。我一直就是那些睡美人。如果跟她說這個想法,一定會嚇壞她。因此我就一直沒有這麼說,但是我覺得自己的人生,真的就是那些陪老人睡覺的睡美人。其實,是不是美人,對我來說並不是很重要,硬說她們是美人,是有些造作了。她們是少女,這是重點,我要自己是少女,永遠的少女。不論是醒著或是睡著了,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都是睡著的,我是指佛洛伊德談憂鬱時的那個空洞,或者陰影。反正不論是空洞或陰影,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啦,因為我都是那個睡著的少女,睡在那個空洞裡。
我這樣說,她是不會懂的,真的,我絕不相信她會懂得,那個空洞裡睡著的少女是什麼意思?如果我說那個失去後留下來的空洞,其實一點也不空洞,而是睡了不少像我這樣的睡美人,只是一直睡。睡著前,我知道等一下會有老男人來睡在我旁邊,老人覺得我在陪他們睡覺,度過漫長的夜晚,但是我知道是老人在陪我睡。這樣子說會不會太奇怪?算了,算了,我一直要自己不要管別人怎麼想。是不是太奇怪,是別人的事,我的人生只有自己能過啊。我何必管佛洛伊德在百年前,描寫和猜測憂鬱者的那個空洞,是怎麼樣的洞,或怎麼樣的陰影?反正,我覺得是有那個洞,也有那個陰影,但是我卻覺得自己就在裡頭,我是專指那個想要當睡美人的我在那裡頭。不過這麼形容好像怪怪的,我要再想一下,是這樣嗎?是我想要當睡美人嗎?是這樣子嗎?嗯,這麼說怪怪的,是那個睡美人,就是我。不是我想要當睡美人,沒有我要不要當的問題。
這麼說是很嚴重的說法,如果說是我想要當睡美人,那麼就還有改變的餘地。如果說那些睡美人就是我,這是一切都無法改變了,只要改變了,就不再是我了。我深刻記得,是這樣開始的。是這樣,旅館的女人囑咐一位叫做江口的老人,要他不要對少女惡作劇,而且不要把手指伸進睡著的少女嘴巴裡。好美的開場白,讓我在《睡美人》裡能夠安心的睡著,不會有人在我睡著時,將手指伸進我的嘴巴,是憂鬱令人難解的空洞。我不喜歡有人將手指伸進我的嘴巴裡,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高度象徵的說法,手指不再只是手指,嘴巴不再只是嘴巴。直接的說法就是,性啊。
算了,算了,我要節制一點,說我憂鬱心裡的那個空洞,是性,這鐵定被批評是亂說。雖然我年紀這麼大了,大概不會有人對我說,小孩子不要亂說話。因為我是大人了,但是我的心停在少女階段,旅館裡每晚昏睡的少女。那是一種高度的孤獨,不過算了,算了,我先不要使用孤獨這兩個字了。
孤獨是相當困難理解的字眼。
我甚至覺得,自己根本就毫無資格,說出孤獨這個兩字。沒有人會了解,我說出這兩個字,因為我只是含在嘴巴裡,從來沒有出口過。因此老人在我昏睡時,手指伸進我的嘴巴時,孤獨這兩個字,如果突然從我的嘴巴說出聲音,搞不好會嚇著老人心臟麻痺。
也可以說,我根本就沒有孤獨的權利。
有人知道嗎?當一個人不被允許有孤獨的權利,那是什麼樣的人生?我早就放棄問這個問題,那是對人生還有期待的人,才會問的問題,包括,關於是不是孤獨?我曾想過,在我睡著後,不再醒來,除非隔天的太陽曬進來,驚醒我,不然我是在昏睡的晚上,陪伴老人度過他們的孤獨。因此孤獨是他們的,不是我這個少女的。絕不是我刻意要推開孤獨這個字眼,真的,我毫無必要推開它。因為我是明明白白,知道我是讓孤獨在我身邊安睡的人,他們都是老人的模樣,或者,至少走著如老人的步伐,那是他們的孤獨,我一點也不孤獨。或者說,我並沒有沾染到孤獨的氣味,但是我相信睡在我旁邊的是,無邊的孤獨。因此陪伴孤獨的人,會是孤獨嗎?不過,我實在沒有必要替自己辯解,是不是孤獨的問題?可能我一直想要跟她解釋吧。
嗯,是這樣子。我是在跟她解釋,我不要她誤解我,因為她喜歡說,我是孤獨的。但我偏偏不這麼覺得,她對於我說自己的空洞裡,是自己的睡美人,其實她很難了解,甚至她覺得不可思議。我為什麼硬要把那個早就失去的時間空洞,說成是睡美人?不過,這只是一兩次吧。後來我覺得她根本不可能了解和體會,睡美人是什麼意思?甚至她覺得我太墮落了,怎麼會去做這種工作呢?唉,這不是工作,這是小說,日本小說家的小說,不是我的工作。
那是我內心空洞裡的人,不是工作,是我自己的空洞,就是睡美人。她說,我是失去了什麼,才會有空洞。這點,她是說對了,我是失去了媽媽,也失去了爸爸。但是心中空洞,是跟佛洛伊德有關的內心空洞,不過,我對是不是佛洛伊德的空洞,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後來,當我無意間讀到了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後,我終於了解,原來,我是什麼?早就有人說過了。就是這個故事,才讓我看見自己,是為了明天早上可以活著醒過來,才會在前一天傍晚閉上眼睛。這是永遠無法被別人了解的,自己不是快樂,也不是悲傷,只是一種活著。我是睡美人,是少女的美夢,我是自己的乳頭周圍會滲出血的情人,雖然我一點也不喜歡有夢出現,那讓我的人生變得多餘。
第一幕第二景:失去前的媽媽在說話
佛洛伊德有些話沒說完,由別人來說就會更到位。這個時候,佛洛伊德只有仔細聆聽的份,不論,他是不是還活著。
她媽媽說:
我不了解她。
她只會說我恨她。這是她執意堅持的,好像沒有恨我,她就無法活下去。但是因為她這樣,我就不能有我的恨意嗎?難道,只因為她說,我恨她,因此她所有問題都來自於我恨她?這樣子,我就不能對人有恨意嗎?真的是這樣子嗎,何況,就算是我真的曾經恨過她,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也認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能夠怎麼辦?我現在再千百次的道歉,會有用嗎?她就不再認為我曾經恨過她了嗎?何況,我都不是很確定,我真的有如她所說的那麼恨她嗎?我不確定,雖然自從有一天,她回家後就對我說,我是恨她的。她還說,以前都不敢對我說,直到她開始找人談後,她才敢對我開口。後來幾乎只要我們碰面,她就這麼說,好像我一定要吞下她的說詞,要承認我是恨她的,而且恨得很深很深。她舉了很多例子,起初,從我故意不讓她吃飽,到後來連我是否跟她揮手招呼,都是恨意了。反正說到最後,所有我所做的,和我沒有做的,都是我恨她。
我需要那麼恨她嗎?就算我曾經說過,她是出生來找我麻煩的人。如果她不出生,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但是,這些話有那麼嚴重嗎?我並沒有常常跟她這麼說啊。不過說個一兩句,她就把我說成,我是恨她的,而且我的恨是她現在所有問題的原因。她現在會出現的所有問題,都是我曾經恨她。如果真有那種恨,能夠收回來嗎?就算能夠回收當年的恨意,去哪裡回收呢?回到從前嗎?不,不要,我絕對不想再回到從前,那是痛苦的日子。我絕對不想再回去,現在,連回頭想到往事,心頭都是蒙上一層酸澀。我最好不要真的問這個問題,如果讓她知道,有這種可能,到從前回收恨意,她一定要求我這麼做。如果我拒絕,她又加了一條證據來怪罪我,是真的恨她,才會不想回頭,向過去收回恨意。
我還記得,那一天,她回到家,一臉的臭氣沖天模樣,好像我欠了她一輩子。她大聲罵我,說她跟人深談後,才發現自己會落得沒有任何朋友,都是我害的,都是我曾經恨過她。我還以為她是開玩笑,我就回應,最好啦,我的恨意有那麼厲害,能夠影響你那麼多,連你的朋友都會受到那恨意的威力。她生氣地回我說,都是你害的啦,然後又說了一些奇怪的話。例如,她是睡美人。我還以為她是想男人想瘋了,自以為是睡美人,在等待男人來吻她。真是奇怪的女孩,只沈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那有什麼睡美人?不過是童話,她真的那麼相信,這才是她交不到朋友的原因,怎麼可以怪我曾經恨她呢?
如果一個人一直是這樣找麻煩,能夠讓人不恨她嗎?
她一直在激我,讓我說出我恨她。然後要藉著我現在說出,我恨她,來證明我曾經恨過她。我真的沒有那麼恨她,真的沒有那麼恨她啊。但是她後來每天這麼說,以各種方式來激怒我,我怎麼會知道,她到底為什麼這麼恨我呢?就算我曾經一度離開她。那也不是恨她,是她爸爸太過份了,我只好短暫離開這個家。我可是飽受煎熬,才會這麼做的啊。
那不過半年多,她也還那麼小,怎麼會記得這些事呢?我也是不得已啊。如果不離開,我根本就活不下去啊。我就要死掉了,我不知道幹嘛活在這個世界上,這是多麼奇怪的世界啊,整個世界空空洞洞,都不是我容身的地方。我容身的地方,要有花花綠綠的野草,野花,還有一條小河。不必是很大的地方,這麼期待難道有錯嗎?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期待,但是我卻活在很廣闊的空洞裡,什麼都沒有的空洞,只有我的心跳聲,不是鳥叫的聲音。
我不需要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我不需要在大白天還要被提醒,我還活著。
心跳聲,卻要跟我作對。這是什麼世界啊,連我摸自己的乳房入睡,都會變成空洞裡的回聲。她能想像,那是什麼樣的日子嗎?只能摸著自己腫脹的乳房,入睡,然後就發現,世界變成一個大空洞,卻不斷地迴響著,我撫摸自己的聲音。那不是愉悅的事情,我不是為了愉快啊。只是為了確定,這個空洞的世界裡,還有一些感覺存在。
我只要一點點存在的感覺。這樣子算過份嗎?誰說這過份,就請他們自己來過過看。唉,算了,我不想再怪任何人了。這是沒有人可以了解的事,有誰能了解?周遭有人走來走去,卻覺得每個人都很遙遠。我,如果大叫,也不會有人聽得見,不會有人回應我的呼叫。我只不過是希望,有人可以回應一下,甚至是罵我的聲音也沒關係。回應的聲音卻只有自己的呼吸聲,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想要摸自己的乳房,配上呻吟聲?我想要聽聽,有什麼聲音會傳回來,從空洞的廣闊迴音裡,回來,卻只是無力下墜的,模糊聲音。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發現,回聲裡,夾雜著嬰兒哭聲。我摸乳房的聲音,怎麼會有嬰兒哭聲的迴響呢?我大叫,要蓋過嬰兒哭聲。從空洞裡回來的聲音,只是嬰兒更大的哭聲。我再大叫三聲,回音仍是嬰兒哭聲。直到我再大力地喊叫,我恨你,然後聲音突然不見了。空洞裡來來回回的是,安安靜靜。過了一會兒吧,才突然傳來回聲,我恨你。
不是我的聲音,是嬰兒的聲音,太奇怪了,真不可思議,怎麼會有嬰兒說得出,我恨你,這三個字呢?後來,我就不曾再說出口了,我恨你,這三個字變成了火把,不再是聲音。連我也不想再聽見這三個字的聲音了,我不能這麼說,甚至連想也不要想了,但是這把火卻一度讓我要一直摸著自己的乳房,才能好好睡覺,睡在一個空曠無邊的大空洞裡,睡著的人一度是美麗的女人。
後來,都走樣了
一切都走樣了,我幾乎不再叫自己的名字了,我的名字不再是名字,更不是屬於我的名字。有沒有名字,有沒有自己,已經不重要了。甚至可以說,重不重要,也不再是需要判斷了。我只是過著日子,愛和恨都不見了,就只是睡著了的一個人。我現在強調一個人,是現在這麼想,在當時是什麼都沒有的那種一個人。就像吃東西會進到胃裡,那時候連胃的感覺都沒有了。
外頭的世界很多人,很擁擠,我就是不見了。既然我不見了,也就不需要再多說話了,失去名字的人,說話,都是多餘的聲音。甚至連呻吟聲,也是多餘的。這是沒有恨,但是愛也不見了,只覺得外頭很擁擠。我如果想要跟他們擠,至少也要有自己存在,但是這種是連自己都不見了,而外頭是吵雜的,可以擠碎所有東西。有時候我突然有感覺時,是覺得自己很空曠,每個人都可以走進我的空曠。但是他們很快就消失了,消失在我的空曠,那種空曠竟然可以吞沒所有走進來的人影。甚至自己也會被吞噬掉,就是不知道後來他們都還去了什麼地方?不可能憑空消失。就是這樣子憑空消失了,消失在我的空曠裡,唯有那種空曠感,才是我僅有的。我後來才知道,自己僅有的,就是那種空曠,大到可以吞噬所有事物,連自己,也被這種空曠吞下去了。
我很難相信有人會了解。
我在說什麼?我只是無病呻吟?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病,但是連呻吟都會被那種空曠吞掉,偏偏有時候知道那種空曠是自己,如果完全都不知道就算了,卻留下這種感覺,是知道的,是屬於自己的。每個人都可以踩扁我,都可以罵我的不是,雖然他們可能不知道,我不會因為他們的責罵或踩踏,我就會覺得傷心。我根本就不會覺得傷心,那些踩踏和責罵聲,有些時候,進來我的空曠後就突然消失了。這才是最大的寂寞,最大的驚恐。
我不知道空曠的場地,曾如何表現它的驚恐?我只記得,再度從這種寂寞裡醒過來時,我是手摸著自己的乳房。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自己?那是我刺激自己,讓自己沒有完全被自己的空曠吞沒的原因嗎?有誰會相信這種說法?我最後是以摸索自己的乳房,讓自己沒有被淹沒在,比死掉還要寂寞的空曠裡,走出來。我不能說這是一種方式,因為我不是刻意那麼做。
甚至是不是這樣子,我也無法確定。我只是發現自己醒過來時,自己的姿勢,雖然只是一瞬間,其他人可能看不出來,我的手突然快速地移動,從乳房的位置移開。人們可能只看見了我的手的移動,就說我已經回來了,是我回來了。但是那種比死還要空曠的寂寞,不曾再消失過。每當我要想像那是什麼時,腦海裡卻只是一片空白。
這種空白,被一層紗遮住了,它想要遮住自己,不想讓我再看見時間。............
——摘自 劇本(另一種劇本:叫做內心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