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經的真面目, 你讀對版本了嗎? 八種譯本的比較 以派系思想為主
| 作者 | 釋定泉 |
|---|---|
| 出版社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金剛經的真面目, 你讀對版本了嗎? 八種譯本的比較 以派系思想為主:古來皆知金剛經各譯本有所不同,其差異有哪些?內容是什麼?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是翻譯者?還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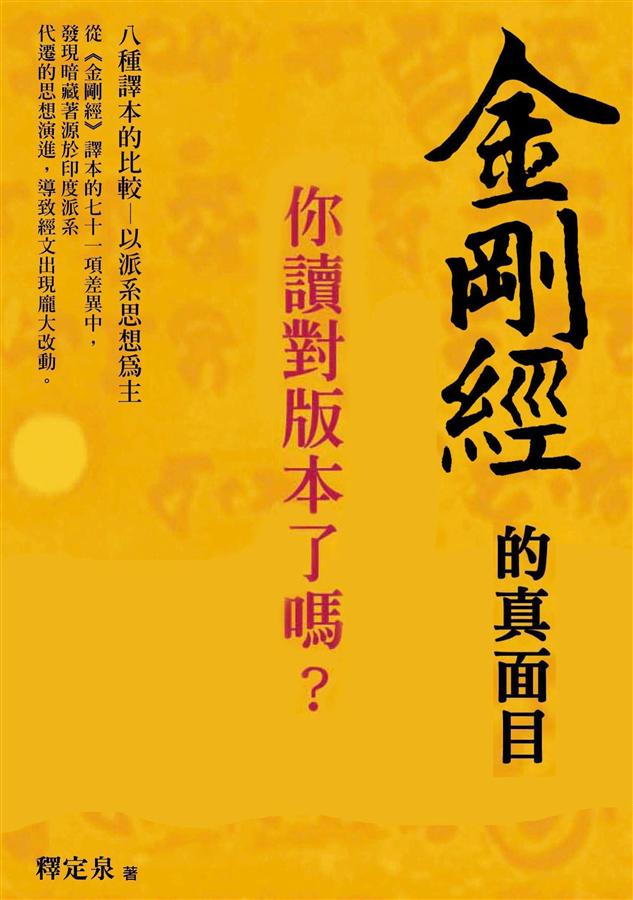
| 作者 | 釋定泉 |
|---|---|
| 出版社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金剛經的真面目, 你讀對版本了嗎? 八種譯本的比較 以派系思想為主:古來皆知金剛經各譯本有所不同,其差異有哪些?內容是什麼?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是翻譯者?還是 |
內容簡介 古來皆知金剛經各譯本有所不同,其差異有哪些?內容是什麼? 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是翻譯者?還是源於底本? 若源於底本,所牽涉的內容是什麼?是否與印度的派系代遷有關? 若與印度的派系代遷有關,是否表示各譯都有各自所要發揚的義理?當中用詞可否互相取代? 若義理不同,用詞又不可互相取代,那麼,純粹文本對比的研究方法,便可能對問題提供不正確的結論了。如此,我們應該如何改進? 在《金剛經》的近代二英譯本和古代六漢譯本中,差異較大的鳩摩羅什大師譯本廣受質疑與批判。本書採現代文本對比的佛學研究方法,對八譯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義理對比,從71項差異中,發現《金剛經》不同的譯本,暗藏著源於印度派系代遷的思想演進,導致經文出現龐大改動。現代學者作為對比之用的梵本,極可能是古代已被改動過的《金剛經》新型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釋定泉俗姓吳,1968年出生於中國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商業管理系學士、台灣淨覺僧伽大學大乘佛教研究所碩士。 1996年開始學佛,2012年於上暢下懷長老座下剃度出家。2014年受具足戒,泰國華宗大尊長上仁下得長老為授戒和尚。 曾在香港《雷音》、《香港佛教》和台灣《淨覺》等月刊撰文。又獲 上暢下懷長老選用其偈語作為香港圓明寺山門對聯和五觀堂對聯。2016年以《金剛經八譯的文本比較》一文通過碩士論文答辯,並獲A等成績。後得 上淨下心長老推薦繼續往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進修博士課程。 法師早期以般若、空宗理論作為禪修的操作方便;後以禪宗無心和不動心作為看心要領;出家後有因緣修學天台止觀,同時又修學帕奧系統的禪法,後於泰國修讀博士課程時學習馬哈希系統的禪法。 法師以「度眾而無相,無相而度眾」作為自修與推廣佛法的大綱,並認為種種佛法皆有其用途,究極與否取決於眾生的根器。而佛教的發展,法師認為是一種「流行論」,而非「進化論」,故一切佛法皆根源於2500多年前的釋迦牟尼佛世尊,只不過流行的程度有所參差而已。
產品目錄 第壹章 緖論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一、研究動機二、研究目的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一、研究範圍二、研究方法第三節 文獻回顧第四節 論文架構第貳章 七十一項文本差異(前)第参章 七十一項文本差異(後)小結第肆章 重要思想的演進第一節 大乘正宗的開教一、須菩提前後二問二、發菩提心與行菩薩乘三、住、修行、降心四、世尊的回答五、無四相第二節 前半菩薩應無「所」住的開示一、無住布施二、無為法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四、是名般若波羅蜜的存廢第三節 後半菩提心無「我」相的悟入一、諸法如與真如二、心與心流注三、善法與無上菩提四、三十二具足相五、四句與八句偈第四節 度眾而無相的證入境界一、不生、不取與不住二、一切有為法第五節 能斷與瑜伽行派第伍章 義理以外的翻譯對比問題第一節 羅什與流支的翻譯風格第二節 直譯與意譯第三節 經本序幕與大乘初興第四節 印度本土的派系代遷第五節 時空與底本第六節 底本的時空位置第七節 現存梵本的對比局限第陸章 結論第一節 研究的總結與功用第二節 研究的限制與展望參考書目
| 書名 / | 金剛經的真面目, 你讀對版本了嗎? 八種譯本的比較 以派系思想為主 |
|---|---|
| 作者 / | 釋定泉 |
| 簡介 / | 金剛經的真面目, 你讀對版本了嗎? 八種譯本的比較 以派系思想為主:古來皆知金剛經各譯本有所不同,其差異有哪些?內容是什麼?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是翻譯者?還是 |
| 出版社 /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9541602 |
| ISBN10 / | 9869541607 |
| EAN / | 9789869541602 |
| 誠品26碼 / | 2681720604006 |
| 頁數 / | 288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1X14.8X1.5CM |
| 級別 / | N:無 |
| 重量(g) / | 259.8 |
推薦序 : 自序
本作《金剛經八譯的文本比較──以派系思想為主》,是2016年筆者就讀碩士班時的畢業論文,並經過若干修訂後進行出版的。
撰寫本文的近緣是筆者決定剃度前,為免貽害眾生,便曾以另一本至今仍未出版的《金剛經八家譯注》,交給家師 上暢下懷長老鑑定內容是否吻合佛法,方敢出家。那算是我十多年來研究《金剛經》的一個總歸納吧!老師父認可了,結果便使我加入了僧人的行列。
首先必須向廣大的讀者說明,這是一本非常學術性的書刊。若然讀者是以純粹修行佛法的立場閱讀它的話,甚有可能會令閣下感到沉悶無趣。但還是請各位按捺一下心情繼續閱讀,因為您在其他佛典上遇到的問題,也許在本書多元的討論中會找到一點點線索,助您破除障礙。
研究《金剛經》,一是因為我初信佛時,它給與了我新的生命,因此我對它感情深厚,珍之重之;二是因為在研習的過程中,曾面對過無數各式各樣的問題,在一一解決的同時,往它更深處發掘便成為了我的樂趣!尤其是研究《金剛經》的現代學者們,都會拿久遠遺留的梵文斷片作為準則,來裁決漢傳譯本的不正確。對於既是學者又是修行者的我而言,這是件值得追查探討並研究清楚的事,是絕不能敷衍了事的。因此,把過去搜羅的資料和一直研究所得的見解加以整理,便是這篇論文,更希望能藉此提升我國古代譯典的學術價值和地位。
本書之能夠出版,首先必須多謝恩師 上暢下懷長老,他的多次認同,每令我信心培增,知道所說離佛不遠。其次是淨覺僧伽大學校長 上淨下心長老,感謝他提供了優良的環境和師資,讓我安然地在幾個月內整理文章,更要感恩他為本書撰序,並在我往泰國進修給與莫大幫助。還有感謝五位當日論文答辯的主考老師,分別是 上從下慈法師、鄭振煌教授、楊永慶教授、黃運喜教授和陳劍鍠教授(排名不分先後),幾位教授的評價與支持,都是本書出版的最大力量。特別是 陳劍鍠教授,他極力提議本書出版,乃至百忙中為此撰序,內容既專業,又充滿著對佛學研究的熱情,實在令我深深感動!本書的刊印工作是由 鄭振煌教授領導的中華維鬘學會所襄助的,故此必需向學會的各位成員,特別是 鄭教授與 李倫慧居士表示至高的謝意。另外, 曾泓議先生不但在資源與聯繫上出力,更為此書擔當義務校對,實在感恩非常。
最後,筆者願以此書,奉獻給我那已過世的父親 吳水桃居士,以紀念他常懷護念眾生的情操,以及一直以來對我的幫助;也要獻給所有古代的翻譯家,他們的忘我法施,實應獲得我們的肯定與尊重!
筆者自知才疏學淺,故文中若有所不善處,還望各方大德及善知識勿吝指正為盼。
釋定泉
序於泰國曼谷
導讀 : 第壹章 緖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若論古往今來中國佛教中註疏義解最多的經論,當首推《金剛經》。從首位翻譯者的弟子僧肇大師起一直到現代,就有上百家書刋問世,可見它確是學者們一直熱衷的研究對象。想來在佛教家庭長大的筆者,也是約廿年前開始,才因某種因緣通過《金剛經》正式學佛的。因此,我對此經感情深厚,能夠細緻地探索它,可說已成生平的願望。
《金剛經》的漢譯版本不少,合共六譯。一般談及《金剛經》,大概都是指流通最廣,鳩摩羅什大師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而六部漢譯文字有相當出入,是古來已公認的。若翻查釋論註疏,古德已有整理列出種種差別。而且,建基於中國佛教獨特的圓融思想,古德多會站在會通的立場,給與各譯平等的評價。但在慧能大師於《金剛經》開悟、禪宗自唐代興起以後,什譯便因禪宗鍾情,而有凌駕他譯的趨勢,並為釋經者所偏寵。
然而,時至今日,情況逆轉。現代的佛學研究,流行以現存梵本及不同譯本互相對比,然後作出此對彼錯的批判。對於《金剛經》,因為漢譯便有六個不同版本,材料充足,更是學者們熱愛研究比較的對象。這類研究,甚至有時會獲得如近人張宏實所說的結論:「幾乎可以確認鳩摩羅什版要作適當的更正。」然而,筆者對這種見解不敢苟同。
就以什譯來說,首先,從現實上看,我們如何能確定,什師所用的底本,相同於其他譯本採用的底本,乃至現存梵本?二,從實踐上看,什譯是否與法義相違,並且無法對治眾生的煩惱,而必須作出詞彙上的更改?三,亦是最重要的,若然真的將什師譯本中的文字,改寫成學者們的建議,結果是否會違反其所述佛法義理的一貫性?就以經題是否應該加入「能斷」二字為例;若是,為什麽什譯沒有加入?若否,為什麽某些版本卻有?在對比時,學者是否也應考察譯本各自的義理立場?
二、研究目的
為了對這類疑問作出正確的了解,筆者利用六個漢譯本及兩個英譯本,進行全面性的研究,希望能為當中的疑問,提供合理的答案。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說明:
1.古來皆知各譯本有所不同,其差異有哪些?內容是什麼?
2.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是翻譯者?還是源於底本?
3.若源於底本,所牽涉的內容是什麼?是否與印度的派系代遷有關?
4.若與印度的派系代遷有關,是否表示各譯都有各自所要發揚的義理?當中用詞可否互相取代?
5.若義理不同,用詞又不可互相取代,那麼,純粹文本對比的研究方法,便可能對問題提供不正確的結論了。如此,我們應該如何改進?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為回答以上疑問,本文主要依據鳩摩羅什大師的漢文譯本,附以菩提流支、真諦、笈多、玄奘、義淨等大師的譯本,和Friedrich Max Müller與Edward Conze的英文譯本,作為研究對象。現簡介如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處使用的是《大正藏》0235版本,文長5143字,是後秦時,由龜兹國般若空觀巨匠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約公元403年(後秦弘始年間)譯出。普通稱為《金剛般若經》或《舍衛國本》,本文稱作「什譯」。這是流行最廣的、註疏最多的版本,也是現存漢文譯本中,年代最古舊的一本。通常所說的《金剛般若經》或《金剛經》,便是指此版本而言。禪宗更以此本為日常的誦本。據《六祖壇經》所傳,五祖弘忍大師的時代,便已勸導人持誦本經。而惠能大師就是兩次得聞此經的經文而開悟見性的。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0236版本,文長6138字,是元魏時,由印度唯識思想家菩提流支(亦作留支)大師翻譯,約公元509年(後魏永平二年)譯出。普通稱為《婆伽婆本》,本文稱作「支譯」。內容與什譯差異不大,故經常被學者認為是受到什譯的影響。因流支翻譯世親菩薩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下文簡稱「世親《論》」)時,是應用支譯本身的經句的,故唐代學者,尤其是唯識學者,甚多使用此經作研究。《大正藏》中所收錄的,亦載於《麗本》、《元本》、《明本》的支譯,與載於宋本的,二者之間,字句頗不相同。《大正藏》中另有0236b的版本,是因「思溪(即宋湖州版思溪資福藏)經本竟失其傳,誤將陳朝真諦三藏者重出,標作魏朝留支所譯」的重覆本。其內容與下面諦譯完全一致,故本文只會使用0236的版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0237版本,文長6461字,是陳朝時,由印度唯識學者真諦大師翻譯,約公元559年(陳永定年間)譯出。又名《衹樹林本》,本文稱作「諦譯」。據傳真諦是依世親的《金剛經論》內的引文,而非直接以梵經原文,譯出此經的。這便馬上讓入聯想到唯識家對經文的影響有多少了。另外,什、支、諦三譯的經題,均未涉及「斷割」或「能斷」的用詞和意思。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0238版本,文長7110字,是隋朝時,由印度唯識思想家達磨笈多大師翻譯,約公元590年(無考)譯出。本來經題為《金剛斷割般若波羅蜜經》,後人改為「能斷」,是第一本涉及「能斷」這意思的經題。此經為逐字翻譯,故又名《直本》,即依照梵文文字之順序,一句一句譯成相當的漢字,故僅看譯文則較難讀通。本文則稱作「笈譯」。據朱慶之的研究,笈譯「這個本子並不是獨立存在、供中國信眾閱讀學習的,而應當是與梵文配合使用的,作用是幫助漢地信眾學習佛教原典和原典語言。當然,它也可以幫助那些精通梵語的西域僧人學習漢語」。因此,憑文法排序與字詞的重組,笈譯在某程度而言當可給予我們某些特别的啟示。笈多於後翻譯無著大師所造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下文簡稱「無著《論》」)時,引用的經文卻是支譯的版本。楊白衣認為那是笈多重新以漢文翻譯,那是錯誤的。或許楊氏是想說另一同是冠名無著造、笈多譯的《金剛般若論》吧!此論內有散見經文,然而仍與笈譯內的用詞不盡相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能斷金剛分》:《大正藏》0220h版本,文長8221字,由我國唐代法相唯識巨匠玄奘大師譯,約公元648年(貞觀二十二年)譯出,本文稱作「奘譯」。原本玄奘曾先譯一卷,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又名《室羅筏城本》,但未收入《大正藏》中,而是收錄於《頻伽藏》第四十冊中。《大正藏》和本文使用的版本為《頻伽藏》的後代版(相信是已被修改過),重複《頻伽藏》內譯文很多。據傳,現在的為初譯,後曾譯出第二次,但已逸失。
《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0239版本,文長6102字,是唐朝由我國留學印度歸來的義淨大師翻譯,約公元703年(武周長安年間)譯出。又名《名稱城本》,本文稱作「淨譯」。是已知的古代漢文譯本中最後的一個譯本。義淨大師是稍遲於玄奘大師五十年左右,到印度那爛陀寺學法的華籍高僧。這兩位的譯本所表現的分別,甚可成為有趣的焦點作比較。
The Diamond Cutter: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的版本,Friedrich Max Müller約於公元1894年前後譯出,本文稱作「M譯」。本版本是根據北京本(在北京印刷的赤字版)、西藏本 (梵文、西藏字音譯、西藏譯)、日本傳寫本(收於慈雲尊者之《梵學津梁》第320卷,與高貴寺伎人戒心師抄寫之寫本) ,並參照其他諸本,而由Max Müller出版。坊間有認為,若以今日觀點來看,本譯有種種不正確之處。
The Diamond Sutra: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Heart Sutra的版本,Edward Conze約於公元1960年前後譯出,本文稱作「C譯」。Conze氏可算是英文佛典的大譯經家,尤其是般若系的佛典,自1951年後的二十年間,Conze氏翻譯過超過三十部般若系的佛典,當中便包括了《金剛經》及《心經》。本譯是根據Conze氏找到的梵文版本,而非漢藏文本,意譯為英文版的。
本文的研究範圍主要圍繞以上八譯中的差異點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事實上,英譯本除Müller氏及Conze氏外,還有數家如Josh Pritikin氏、Charles Patton氏、F.A. Price氏等等版本。不過筆者認為Müller氏及Conze氏二者,已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皆因Müller氏本身是東方思想的權威研究者,在西方有崇高聲望;下面文獻回顧裏所提及的蕭玫的論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從梵文原義到禪學新詮〉,便是引用了Müller氏所整理的梵文本來做對比研究的。而且M譯是前世紀的,屬西方世界較早期的譯本,從中可讓我們了解到當時西方對佛教思想的看法。而Conze氏是近年西方翻譯佛典的主要學者。他的譯文常被其他學者所引用,如下面文獻回顧裏所提及張宏實的《圖解金剛經》一書,便大量應用了C譯來進行對比;而且C譯是近代之作,當可讓我們看到它與一世紀前M譯的差別,使我們從其變化,明白到西方人如何理解佛法及其進展。本文應用了八譯,作用亦是為了研究其中的流變,看是否與派系代遷有關。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以文本對比法,將八譯的每項差異點抽出,並以列表顯示及加上編號,方便討論;
2.以法義的邏輯合理性,分析各項差異點的差異內涵、性質與原因。當中會參考各宗派古師的見解,作為佐證;
3.對重要的差異點展開詳細的研究,內容主要圍繞派系義理對該項的影響;
4.綜合以上,最後對問題作出整體回應,並提出筆者的結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從來對《金剛經》各譯進行全面並深入對比研究的,無論中外,實在不多。現就比較相關的幾則,概述如下:
一、高永霄,〈金剛經六譯本的研究〉:
高氏從漢傳的六譯中,挑選了幾個部份來作出對比與論究,誠屬相關研究的第一人。高氏的觀點,從他文章中當可見端倪;譬如說:「金剛經六譯本差異的地方,與所用的梵本原文不同,是有莫大的關係。」又如他對「相」、「想」、「想轉」的見解是:「什本……指整體……(但)後來之譯本……獨標其中之主要因素。這便是空有兩宗差別的所在了。」而在最後的結論中,他說:「前者(指羅什)乃依經中的性空義,後者(指玄奘)乃據典中的妙有理而譯成是經。」這種訴諸於思想乃至派系代遷,導致譯文差異的主張,實在是相當有意思。只可惜高氏文章的內容未能全面深入,尤其舉證時只有原文的列舉,卻欠缺審細的說明,至使每項的結論,總留有耐人尋味的感覺。或許就正如高氏自己所說的:「碍於篇幅關係,衹好從畧,待讀者自己去研究吧!」但不論如何,高氏的主張相當有價值,與筆者的見解亦多有類同的地方。相信其中的缺點,本文將會為他作出相當的補充與論證。
二、楊白衣,〈金剛經之研究〉:
楊氏的論文,原本是為說明大乘佛教初期居士佔主導地位而研究的。不過,楊氏卻用了一些篇幅,列舉了各譯之間的主要不同點出來,並加上淺析。譬如在「若以色見我」偈的四句與八句的疑問上,楊氏便說:「羅什認為以前四句反顯後四句即可,因此省略後四句。」不過楊氏並未說明此是引述自清代沙門通理法師的見解而已,未必就是羅什的本意!又例如在諦譯的起問部份,出現了有別於他本的「云何發起菩薩心?」楊氏只解釋了一句:「這可能是真諦將降心誤譯為發心而來。」這只能說是一種粗糙的猜測吧!發菩提心的梵語可以是bodhicitta-samutpāda;降伏心的梵語卻可以是citta-pragrahītavya。作為西印度人的真諦大師,真的會出現誤譯嗎?筆者對此很有保留!不過,楊氏對古今中外一切有關《金剛經》的梵文古本、譯本、論註等等,皆做過一翻詳細的了解,並在論文中羅列了出來,實為後人省卻了不少整理功夫,理應嘉許。
三、張宏實,《圖解金剛經》:
這是一本解釋《金剛經》內名相與經文的專書,資訊性豐富。當中經常引用奘譯與C譯的見解,並對比張氏手上的梵本。其普遍的結論是:奘、C二譯精準;什譯錯譯、欠譯之類。例如在「發菩提心」的起問上,張氏認為「還可以找到更理想的譯法……(因為)梵本……是bodhisattva-yana-samprasthiyena......即為『發心追求菩薩乘的人』。」張氏更說:「鳩摩羅什都統一譯成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讓讀者產生很大困擾。」因此,「幾乎可以確認鳩摩羅什版要作適當的更正。」又例如「實相」與「實想」的差異,張氏依手上的梵本中的bhuta- samjñā,便判定C譯的 'true perception' 與奘譯的「真實想」「講得很清楚了」。但這樣的結論,顯然是忽略了:1、唯識法相學中的「相」與「想」是要分別界定的。「想」作為「唯識百法」中「心所法」的一支,才是唯識家主要要處理的東西;所以經文有機會因此改成「想」;2、「實相」可以有多種梵文詞彙去表達,卻並非bhuta-samjñā。如Lamotte在翻譯《智論》時,便用了多個不同的梵文詞彙去翻譯「實相」;所以,誰可保證什譯所用的底本,就是用上唯識家的用詞samjñā?3、如依上面楊白衣的考證,《金剛經》的梵本便有多種,甚至有些是比較接近什譯的,如在「東土耳其的Dandan Uiliq發見,而由赫恩烈認定的梵文斷片,由F. E. Pargiter刊行,有若干缺漏。較現存之梵本簡潔,接近羅什羅本。」因此又如何可以肯定張氏手上的梵本,就是最原始的版本了?張氏的這些問題,明顯都是因為過份信賴手上的梵本所致。
四、蕭玫,〈「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從梵文原義到禪學新詮〉:
蕭氏主要是利用Max Müller所編的梵本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中,羅什譯為「應如是生清淨心」的梵文,與漢傳的六譯作出比對。蕭氏立論於Max Müller所編梵本的可靠性,以及認為什譯是「自由剪裁的意譯風格,使這……名句,最後竟異於原義……從而……演繹出『自性清淨』的如來藏義」的前提假設,判定什譯不忠於梵文原典,近乎翻譯失真。但正如筆者一直追問的,我們如何確定什譯所用的底本,與Max Müller所編梵本一致?再說,什譯的剪裁準則,只是因為如《智論》序中所說的「梵文委曲……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但絕無理據證明羅什是會在決定翻譯一句時,連關鍵詞都删減或改動的。而且,「生清淨心」中的「生」字,已清晰界定「清淨心」是「生滅」法。這又如何會是蕭氏所想的「如來藏義」?《智論》中就出現過26次「清淨心」這詞彙,難道《智論》亦是弘揚「如來藏義」?「清淨心」的梵文是viśuddha-citta,在西晉的譯典中便已出現過這個詞彙!可見類似的以梵本直接對比的研究,在其前提處便有很多疑點,實是我們所必須知道的。
綜合而言,學術界以純粹文本對比的方法,評定各譯的優劣,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同時也是對譯者與譯本不公的。既對佛教存在傷害,更令信眾與發心修行的佛子產生猶豫。因此,全面而深入的譯本對比,實刻不容緩。
第四節 論文架構
筆者的論證架構如下:
在第壹章,即本章「緖論」,先行概述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然後再回顧有關文獻,檢視前人的研究成果與見解。
第貳及叁章「七十一項文本差異(前)與(後)」,我們會以學術界的一般作法,以文本對比,將八譯的各項差異,用列表的方式呈現,並加上簡短的淺析。此將有助於俯瞰全部的差異點,並輕易掌握當中的來龍去脈,同時亦為往下的深論部份鋪路。
繼之,在第肆章「重要思想的演進」,我們會對重要的差異,如發菩提心與行菩薩乘、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有為法」偈等等的八譯重要差別作出深論,藉此詳細窺探各譯重要的思想變動,明其背後推動力究屬為何。
在第伍章「義理以外的翻譯對比問題」,將會從其他角度,討論與八譯有關的翻譯對比問題。這將詳述純粹文本對比的研究局限,以及派系代遷如何影響古代的譯本。推而廣之,或可為其他經典的研究,注入新的考量因素。
最後第陸章「結論」,我們將會為本文的問題,作一總結,並會為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提出展望。
最佳賣點 : 從《金剛經》譯本的71項差異中,
發現印度派系代遷的思想演進時,
讓經文有龐大的改動!
這將令古譯的研究價值再次受到關注,
更可能令現代佛學文本對比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受到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