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 作者 | David W. Anthony |
|---|---|
| 出版社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馬、車輪和語言: 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六千年前的歐亞大草原並非蠻荒之地,而是印歐文明的起源地!草原居民駕著猶如現代跑車的四輪車、馬戰車,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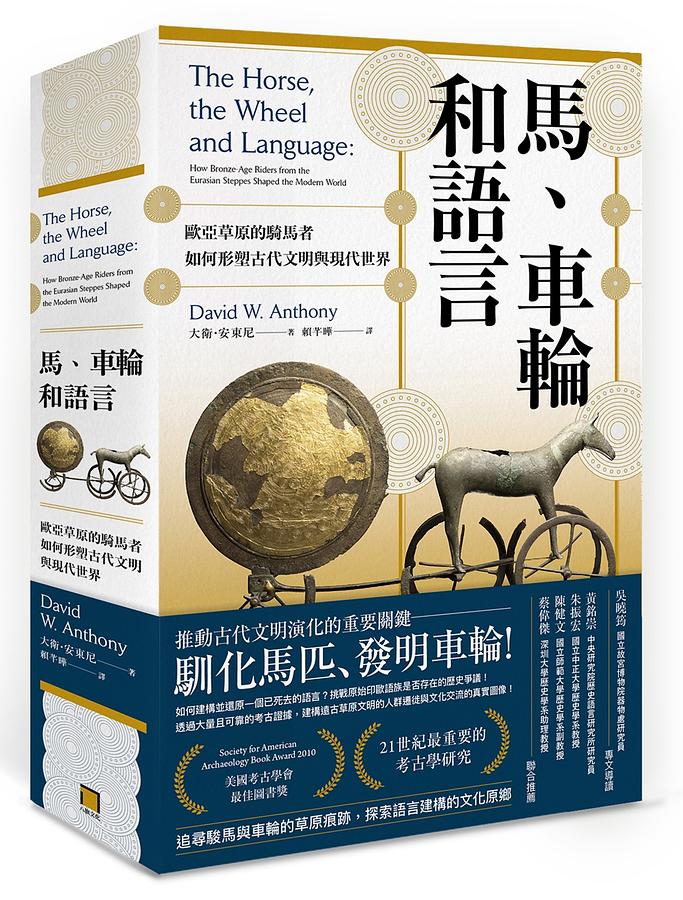
| 作者 | David W. Anthony |
|---|---|
| 出版社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馬、車輪和語言: 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六千年前的歐亞大草原並非蠻荒之地,而是印歐文明的起源地!草原居民駕著猶如現代跑車的四輪車、馬戰車,循 |
內容簡介 六千年前的歐亞大草原並非蠻荒之地,而是印歐文明的起源地! 草原居民駕著猶如現代跑車的四輪車、馬戰車,循著大草原四處移居, 無形中推動了歐亞大陸的文明演化,開創最早的「全球化」時代! 馴化馬匹+發明車輪=推動文明演化最重要的關鍵! 本書榮獲美國考古學會最佳圖書獎,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考古學研究 ★★挑戰二百年來「原始印歐語」是否存在的重大爭議★★ ★★透過考古學證據,證明印歐語起源於中央歐亞草原★★ ***** ◎原始印歐語是否存在?如何建構並還原一個已死去的語言? ◎人類最早馴化馬匹約在何時?馬匹最早的功用又是什麼? ◎車輪是什麼時候被發明的?其重要性又是什麼? ◎原始印歐語居民如何透過大草原移居各地?他們的移動路線為何? ◎草原文明的傳播如何推動及影響希臘、埃及、印度等古代文明的發展? ■歐亞文明的起源,要從馬匹的馴化開始說起 從世界史來看,人類文明的黎明期往往都是從四大文明古國開始說起。但是,在古埃及、古美索不達米亞等西亞文明之外,其實還存在著同樣古老的文明體系,那便是發源於歐亞大草原的「草原騎馬者文明」。 「草原騎馬者文明」所處的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是一片從黑海連綿至蒙古高原、遼闊無際的大草原。草原居民從西元前四千多年開始馴化各種野生動物,包括牛、羊、馬。馬匹最早被當成食用的家畜,直到西元前三千年左右,才開始被當成交通工具,最後成為大草原的社會權力象徵。 草原騎馬者將馴化的馬匹結合車輪等機械技術,發明了由馬匹拉動的有輪車與馬戰車;他們透過創新的技術,將「草原海洋」從原先的無人地帶轉變為四通八達的交通要道,其功能有如今日的「高速公路」。因此,草原騎馬者得以透過「馬與車輪」,四處移居、建立聚落,最終在歐亞大陸形成繁榮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網絡,從而開創充滿活力的變革時代。 ■騎馬者使用的原始印歐語,是現代世界的文化之根 在希臘、北歐、西亞、印度等地的古代神話中,都有著駕馭戰車或馬車的神祇形象,比如希臘神話中著名的太陽神。而這些地區所使用的語言,如古希臘語、日耳曼語與印度的梵語,也有著驚人的高度相似性以及文化共通性。 「草原騎馬者」所使用的語言,在今日被稱為「原始印歐語」,其中就有大量關於「馬」、「車輪」的相關詞彙;透過「原始印歐語」所建構的宗教習俗與社會組織,隨著草原騎馬者的開枝散葉而在歐亞大陸廣為傳播,成為許多古文明的文化基礎。 遊牧民族的騎馬者所建立的社會,並非農業文明的邊陲或邊疆,而是與之對等的文明體系;他們所使用的語言,透過騎馬者的移動擴散,最終傳播到歐亞大陸各地,成為今日多數民族在文化上的的「共同先祖」。因此,探索古代草原騎馬者文明的生活痕跡,不只是單純的考古學意義,更具有追尋歐亞大陸歷史起源的文化意義。 ■深入古老騎馬文明的生活,重新理解世界史的開端 馬匹馴化、馬車使用的史前時代考古史,不只反映了草原居民的社會生活,更是理解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全球化」時代的關鍵。本書作者認為,受益於交通革新的草原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的交流,基本上是和平與互助的,而與傳統印象中的「軍事侵略」大不相同。 本書所關懷的不只是考古學及語言學,更有著深刻的現實意識。作者將歐亞草原視為一種「文化橋樑」,而草原文明就肩負著重要的文化傳播功能。作者透過大量可靠的考古證據,建構出遠古草原文明的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的真實圖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西元前兩千年左右、晚期草原文明的「斯魯布納亞文化」及「安德羅諾沃文化」,它們統合了整個歐亞草原,並且連結東西兩端的文明區塊,推動歐亞大陸形成一個整體,堪稱是最早的「全球化時代」;正如作者在書中所指出的:「中國的商王朝和希臘的邁錫尼諸王分處古代世界的兩端,他們同時駕馭著馬戰車,並擁有與歐亞大草原青銅時代晚期牧民相同的技術。」 草原文明的影響──不論是技術上或語言上的,儘管歷經數千年地變化,至今依然在今天的生活中留下許多痕跡。且讓我們追尋駿馬與車輪的草原足跡,探索遠古語言建構的文化原鄉,重新理解現代世界的歷史開端。"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朱振宏∣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健文∣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蔡偉傑∣深圳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作者介紹 大衛.安東尼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美國人類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博士,紐約哈特威克學院人類學榮譽教授,創建「古代馬研究所」(Institute for Equestrian Studies),曾在烏克蘭、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從事過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二○○七年發表《馬、車輪和語言》(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一書,勾勒了古代印歐語族的遷徙線索,並在馬的馴化、有輪車的發明,以及歐亞大陸的古代人群遷徙等問題上提出重要觀點;另有合著作品:《舊歐洲的失落世界》(The lost world of old Europe: the Danube valley, 5000-3500 BC, 2009)、《俄羅斯大草原上的青銅時代景觀》(A Bronze Age landscape in the Russian steppes: the Samara valley project, 2016)等,並發表有數十篇研究論文。二○一○年以《馬、車輪和語言》獲得美國考古學會的最佳圖書獎。賴芊曄賴芊曄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譯作有《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先知之後: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共譯有《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
產品目錄 【第一部 語言與考古學】 第一章 母語的承諾與政治 .語言學家與沙文主義者 .母語的誘惑 .舊題新解 .語言滅絕與思想 第二章 如何重建死去的語言 .語言變化與時間 .語音學:如何重建死去的語音 .語彙:如何重建死去的涵義 .句法與構詞:死去語言的形狀 .結論:從死亡的語言中復活 第三章 語言與時間(一):原始印歐語的最後使用者 .編年窗口的大小:語言能活多久? .原始印歐語的終點:母親成為她的女兒 .年紀最大、最奇怪的女兒(或表親?):安納托利亞語族 .下一個最古老的銘文:希臘語和古印度語 .估算親戚數量:在西元前一五○○年有多少個? 第四章 語言與時間(二):羊毛、車輪與原始印歐語 .羊毛相關詞彙/車輪相關詞彙 .車輪是何時發明的? .車輪的重要性 .四輪車與安納托利亞語族原鄉的假說 .原始印歐語的出生與死亡 第五章 語言與地點:原始印歐語原鄉的位置 .「原鄉」概念的問題 .尋找原鄉:生態與環境 .尋找原鄉:經濟與社會環境 .尋找原鄉:烏拉爾語系與高加索語的聯繫 .原始印歐語原鄉的位置 第六章 語言的考古學 .持久的前線 .遷徙是持久物質文化前線的成因 .生態前線:不同的謀生方式 .小規模遷徙、菁英拉力與語言轉移 【第二部 歐亞大草原的序幕】 第七章 如何重建死去的文化 .東歐大草原的三個時代 .定年和碳定年法革命 .他們吃什麼? .考古文化與生活文化 .未來的大哉問 第八章 首批農民和牧民:東歐大草原上的新石器時代 .馴化的動物與東歐大草原的生態 .東歐大草原地區的首批農民─採集者前線 .農民與採集者的相遇:布格河─聶斯特河文化 .超越前線:牛到來之前的東歐大草原採集者 .眾神賜予牛 第九章 母牛、銅器和酋長 .古歐洲的紅銅時代早期 .庫庫特尼─特里波里文化 .聶伯河─頓涅茨河II期文化 .窩瓦河畔的赫瓦倫斯克文化 .納契克與北高加索文化 .頓河下游與北裏海大草原 .森林前線:薩馬拉文化 .母牛、社會權力與部落的出現 第十章 馬的馴化與騎馬的源頭:馬齒傳說 .馬最早在何處被馴化? .馬為什麼被馴化? .何謂家馬? .馬銜造成的磨損與騎馬 .印毆人的遷徙與德雷耶夫卡的馬銜磨損痕 .波泰和銅石並用時代的騎馬 .騎馬的起源 第十一章 古歐洲的終結與大草原的崛起 .戰爭與結盟:庫庫特尼─特里波里文化與大草原 .瑟斯基島文化:來自東方的馬匹和儀式 .遷往多瑙河流域:蘇沃羅沃—諾沃丹尼洛沃卡集團 .多瑙河流域下游的征戰、氣候變遷與語言轉移 .衰落之後 第十二章 改變草原邊界的種子:邁科普酋長與特里波里鄉鎮 .大草原上五個銅石並用時代末期的文化 .特里波里前線的危機與變革:村鎮大於城市 .第一批城市及其與大草原的接觸 .高加索北麓:邁科普文化之前的銅石並用時代農民 .邁科普文化 .大草原上的邁科普─新斯沃博德納亞文化:與北方的接觸 .原始印歐語:變遷世界中的區域性語言 第十三章 大草原上的拖車住民:原始印歐語的使用者 .為何不算墳塚文化? .跨越東方的前線:從阿凡納羨沃到阿爾泰 .大草原上的四輪車墓/顏那亞層位文化始於何處? .顏那亞層位文化始於何時? .顏那亞人遊牧民? .東歐大草原北方的石碑 第十四章 西方的印歐語系 .庫庫特尼─特里波里文化的終結與西方語族的根源 .草原領主與特里波里附庸:烏薩托韋文化 .顏那亞移民遷徙至多瑙河谷 .顏那亞與繩紋陶層位文化的聯繫 .希臘語的起源 .結論:西方早期印歐語系的傳播 第十五章 北方大草原的馬戰車戰士 .森林前線的盡頭:森林中繩紋陶的牧民 .東方草原上的前辛塔什塔文化 .辛塔什塔文化的起源 .辛塔什塔文化中的征戰:防禦工事及武器 .價值競賽 .辛塔什塔及雅利安人的起源 第十六章 歐亞大草原的序幕 .青銅時代的帝國及馬匹貿易 .巴克特里亞─馬爾吉阿納文明體 .歐亞大草原的序幕 .斯魯布納亞文化:西方大草原的放牧及採集 .烏拉爾山以東、第一階段:彼得羅夫卡文化 .森林─草原帶的塞伊瑪—圖爾賓諾層位文化 .烏拉爾山以東、第二階段:安德羅諾沃層位文化 .中亞接觸帶的原始吠陀文化 .大草原躍升為橫跨歐亞的橋梁 第十七章 言與行 .馬與輪 .考古與語言 .附錄:作者對碳定年的說明 .謝辭 .中英字彙對照表 .注釋 .參考書目
| 書名 / | 馬、車輪和語言: 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 |
|---|---|
| 作者 / | David W. Anthony |
| 簡介 / | 馬、車輪和語言: 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六千年前的歐亞大草原並非蠻荒之地,而是印歐文明的起源地!草原居民駕著猶如現代跑車的四輪車、馬戰車,循 |
| 出版社 /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0763140 |
| ISBN10 / | 9860763143 |
| EAN / | 9789860763140 |
| 誠品26碼 / | 2682038982008 |
| 頁數 / | 672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3X15X4CM |
| 級別 / | N:無 |
推薦序 : ★榮獲美國考古學會最佳圖書獎(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Book Award 2010)
★《紐約時報》及各界媒體、學術期刊一致好評
★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研究成果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吳曉筠專文導讀
★結合語言學與考古學等跨領域方法,探索歐亞大陸文明演化的經典
★透過百張珍貴文物圖片、地圖,重現遠古草原社群生活史
---國際書評---
本書通過檢驗最相關的語言學議題及綜觀性的考古學材料,試圖解決關於印歐語系起源上長久存在的問題。就我所知,沒有哪一本書在探索印歐語系原鄉的問題上能與之相比。
——詹姆斯.帕特里克.馬洛利(James P. Mallory),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史前考古學教授
大衛.安東尼他不是第一個試圖證明原始印歐語族人來自烏克蘭及俄羅斯草原的學者,但是鑑於他提供的大量證據,他可能是最成功的人……《馬、車輪和語言》詳細地闡述了歷史上影響最巨大之語言的複雜系譜,並匯集了歷史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儘管這些研究者歷來對彼此的方法持懷疑態度。
——克莉絲汀.肯尼利(Christine Kenneally),《紐約時報書評》
大衛.安東尼的書毫無疑問的是傑作。安東尼是人類學教授,他匯集了考古學,語言學以及對俄羅斯學術研究和氣候變化歷史的罕見了解,從而重塑了我們對早期人類社會形成的理解。
——馬丁.沃克(Martin Walker),《威爾遜季刊》
《馬、車輪和語言》繪製了俄羅斯大草原的早期地理圖景,並重建了失落的印歐文化世界。這個古老的世界就像任何一部神秘小說一樣令人深深著迷。
——亞瑟.克里姆(Arthur Krim),《地理評論》
在語言和考古學的融合中,《馬、車輪和語言》總結了解印歐語系語言的起源和早期歷史的內容。我認為,本書取代了以前有關該主題的所有研究。
——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古物》
如果您想了解英語和相關語言的早期起源,以及我們熟悉的許多習俗,例如節日和交換禮物,那麼本書將為您提供生動活潑,內容豐富的介紹。在此過程中,您將學習到人類何時、以及為什麼要馴養馬匹?何時第一次騎馬?以及為什麼雙輪馬戰車的發明徹底改變了戰爭的性質?
——彼得.威爾斯(Peter S. Wells),《阻止羅馬之戰》作者
導讀 : 〈導讀:當世界史由車輪轉動〉
——吳曉筠(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
我初次接觸並開始追蹤美國哈特威克學院(Hartwick College)人類學教授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是讀到他在一九九一年發表於《古物》(Antiquity)上,分析烏克蘭德雷耶夫卡遺址(西元前四二○○至三七○○年)馬齒磨損痕的文章。他提出這些磨損痕很可能是馬銜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這便可以說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馴化馬匹。套上馬銜的馬在此後數千年伴著人類奔馳、征戰、炫耀的歷史就此展開。但這一研究引起學術界對馬匹馴化年代的激烈討論,正反觀點蜂擁而起。二○○九年,哈薩克北部銅石並用時代波泰遺址(西元前三七○○至三○○○年)出土的馬齒被確認為最早的馴馬遺存,這一爭論似乎平靜了一陣子。最近幾年,科學家以波泰馬出發,通過基因組的對比分析,提出了現在生活於俄羅斯、蒙古及新疆準噶爾一帶的普氏野馬不是野馬,而是五五○○年前波泰馴化馬的後裔。並且,通過數量不少的古代、現代馬的基因組對比,呈現馬在馴化後,作為最強而有效的交通及戰爭工具,隨著歐亞間的大規模交流,經歷了複雜的轉變分化,成就了今日馬匹多元的生理及地域特徵。但這一研究結果又衍伸出一列的問題。若是一直被視為原生野馬的普氏野馬是波泰馴馬的後裔,那麼遍布在世界各地馬場、馬廄裡的馬,難道與截然不同的普氏野馬同源?因此,就在幾個月前,又有學者試著推翻波泰馬齒上的磨損痕與馬銜有關,而其與現代普氏野馬的關係,更表示現在以及歷史上的馴馬來自他處。顯然,馬匹馴化的故事又在重新撰寫中。
安東尼教授追索馬匹馴化問題,連動的是探索另一個富有悠久歷史、牽涉面更廣的學術爭辯,即印歐語系是怎麼出現的?這一問題約在一七八○年代由在印度生活的英國語言學及東方學學者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提出。他發現在廣大的歐亞大陸,印度梵文與英文、希臘文等等歐洲語言在某些詞彙(例如Mother)的發音上有極高的共性,應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有同一個源頭。自此,探索印歐語系的結構、發展,甚至是探源,便成為歐洲語言學及東方學研究中的悠久議題,至今已將近兩百五十年。
這些饒富興味、吸引無數學者投入的問題,並不專屬於晦澀的學術領域。當我們輕鬆搭乘飛機、火車在歐洲愉快旅行時,我們聽到的英語、德語、波蘭語、俄語,甚至是隔壁乘客聊天使用的印度語,都帶著印歐語系的前身—原始印歐語的DNA。今天,以印歐語系語言為母語的人口占了歐亞大陸的一半以上,若再加上自小學習英文或是學習其他印歐語系語言的人數,其影響範圍更是廣大。今日的飛機、高鐵雖不再依靠車輪,但這些都是人類數千年來對高速交通工具渴求下促成的結果;另一方面,不論技術如何進步,馴養的馬匹血統及擁有的汽車廠牌、性能(例如馬力),甚至是輪框樣式的選擇,仍是社會身分、財富、高貴與品味的指標。這些攸關交通方式、語言訴說,甚至社會結構的發展,如何經由數千年人群流動、學習模仿,在廣闊的歐亞大陸開枝散葉,進而塑造出今日世界的樣貌,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二十世紀,考古學成為探討原始印歐語起源的利器。但一開始,主要的考古資料不是沒有公布,就是以英語以外的語言撰寫,再加上政治因素,使得研究推進困難。幸運的是,隨著近年來歐亞草原考古發現的陸續刊布與譯介,國際合作發掘盛行,更全面、細緻的通過考古學研究探索原始印歐語的發展似乎成為可能。安東尼教授二○○七年以英文出版《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即是他廣泛整合考古資料及二十餘年來研究成果的一部集成之作。
如果說,語言學者可以通過詞彙比較分析,建構出印歐語系發展的架構,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親戚關係,那麼,這些語言最初的使用者是誰?是使用這種語言的一群人隨著移民將之傳播出去?還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經過外來者學習到這種語言,進而成為這一語系的一分子?安東尼教授的解決途徑是通過歐亞大陸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通過語言及物質文化前線(frontiers)的概念,挑戰現在以劍橋大學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為主的原始印歐語原鄉在安那托利亞高原的說法,將原始印歐語追溯至歐亞草原西部黑海與裏海北邊的東歐大草原一帶的銅石並用時代及青銅時代。
此書結構分為兩大部分、十七章:〈第一部:語言與考古學〉(第一至六章)及〈第二部:歐亞大草原的序幕〉(第七至十七章)。前半部著重於語言學,後半部則以考古學為中心,提供了東歐大草原從新石器時代、銅石並用時代至青銅時代文化發展及後續擴張至阿爾泰、天山山脈的一個綜述性的框架,挖掘語言學與考古學的可能交集,開闊的展現作者個人的研究觀點。將語言學與考古學巧妙結合,動態追索原始印歐語的發源地及散播模式,並論證他所服膺的墳塚理論(Kurgan theory),即原始印歐語的擴張與考古所見東歐大草原青銅時代的墳塚文化(Kurgan Culture)具有對應關係。此書甫出版即獲得廣大迴響,並於二○一○年榮獲美國考古學會頒發年度最佳著作的獎項。雖然學術上的老問題仍存在許多爭議,但如著名印歐語學者詹姆斯.帕特里克.馬洛利(James P. Mallory)教授對此書的評價:「本書通過檢驗最相關的語言學議題及綜觀性的考古學材料,試圖解決關於印歐語系起源上長久存在的問題。就我所知,沒有哪一本書在探索印歐語系原鄉的問題上能與之相比。」其重要性及代表性可見一斑。
◎神話訴說的身世:如何以有形的考古印證無形的語言?
在文字出現之前,印歐語系經歷了很長的口傳過程。因此,傳承自遠古的詩歌傳說便成為重要的依據。兩百多年來語言學者沉浸於兩部由口傳神話轉化而來的宗教文本:印度梵語《梨俱吠陀》(ṛgveda)和波斯經典《阿維斯陀》(Avesta),試圖藉之探索原始印歐語的樣貌。
本書採用神話傳說對應考古發現的作法是危險又迷人的部分。〈第一部:語言與考古學〉,描述了印歐語創世神話的一些主要構成要素:天神、雙子與牛,以及隨之而來生生不息的祭祀。迷人的神話語言朦朧記錄著牛隻引進大草原時,對狩獵採集的生活及經濟型態帶來的巨大影響。畜養牛隻可提供更穩定的肉食、骨髓及乳源等營養來源,也提供了更強健的畜力。為保護如此重要的資產,加強了社會分化,推進了宗教祭祀。牛成為了神,權力的擁有者成為了祭司。對表現權力的裝飾品、財富、精緻的武器、可視的儀式及墓葬的需求越來越強,刺激著對外來物品及原物料的渴望,區域分化以及以誓詞加強人與神及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逐漸形成。如作者引述《梨俱吠陀》中人向神獻祭馬匹時的誓言,「讓這匹賽馬為我們帶來好牛好馬、男孩和所有的豐富財富。」兩者間存在著忠誠和庇護的契約關係。另一個迷人的例子來自第十六章。《梨俱吠陀》中印度教的中心神祇因陀羅,在之後的《阿維斯陀》中被視為次等的惡魔。作者解釋這種反差可能反映了當時北方草原人群對南方文明的態度。
安東尼教授更進一步試圖將《梨俱吠陀》所描寫的祭牲儀式與烏拉爾山的考古發現對應。這種明確的對應關係或許還有待商榷,但這是作者在本書所致力證明的論點之一。在以有形的考古印證無形的語言上,作者在第四章以相當篇幅討論西元前四○○○至三五○○年原始印歐語車輪及四輪車詞彙,以及時代更晚的梵文及波斯神話中提及的馬及戰車,應是更確實的交集點。
◎馬戰車的發明是由文明到野蠻,抑或相反?
使用原始印歐語的人群是如何因為開發了馬的性能及改良了輪子,將自身的語言、鑄造技術、陶器製作及審美,逐步推向居住在廣闊地域的人群,最後將不同地區的人群由個別的點,連結成一個互動網?本書〈第二部:歐亞大草原的序幕〉即由考古發現給出了清楚的發展脈絡。
最初作為肉品、奶源的馬,在青銅時代東歐大草原人群的潛能開發下,翻轉成尊貴動物的契機,很可能是從人們騎上馬背開始。由馬來控管牛羊牧群的效率遠高於人力,馬的耐力及速度均遠高於牛或其他的牲畜,騎馬改變了人類每日可移動的空間範圍。對馬的性能開發、利用,極大的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這也是為什麼考古學家們執著於尋找馬匹馴化及馬銜證據的原因。
西元前四千紀前段,從近東城市的學來的一種車子,改變了東歐大草原上的生活景觀。帶有板狀輪子的四輪車模型開始出現在高加索山脈北部的邁科普文化中。隨之發展而來的顏那亞文化運用這種四輪車,並將之直接隨葬於墳塚中。西元前三三○○至三一○○年間的草原景觀可能是,牧民愜意地騎在馬背上驅趕著牲畜,不遠處是牛拉著帶有結實木板大車輪的四輪車,像是帳棚車一樣沉重卻安穩,載著全部的家當,隨著季節展開移居生活。人員、牲畜及財產機動性的提升,使牧民得以利用更多的土地,也促進社會發展出人群間互利共生的賓主關係(guest-host relationship)。這些人群死後被埋葬在一座座墳丘中,形成了草原上的獨特景觀。而隨著不同地域人群的結盟與分化,作者提出原始印歐語也隨之擴張,不斷分裂、衍生出多樣的方言。
這樣的遊牧、結盟、擴散特徵非常符合一般認知的草原牧民形象。由高等文明區輸入技術及財富觀念,更是天經地義。因此,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甚至到了今日,仍有許多人認為是近東城市文明發明了馬拉輕型戰車,或是認為草原馬具是模仿自邁錫尼希臘文化。不過,由考古發現看來,這一技術革新發生在約西元前兩千年的烏拉爾山一帶。大約三十年前,俄國考古學者以出版形式公布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馬戰車,翻轉了傳統的觀點。在辛塔什塔遺址的一座墓葬中,明確發現了兩個以輻條及輪框構成的輻輪印痕。與之前使用的實心木板車輪相比,輻輪輕巧許多,製作方式也更為精細。與之搭配的是窄小、僅供一至二人站立空間的車廂,而車的動力是兩匹馬。馬的嘴角處發現了內側帶有釘齒的馬鑣。這種馬具的功能是將馬銜固定在馬轡頭上。馬鑣的出現一方面暗示了馬銜的存在,另一方面則表示一種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系駕法。與這種輕型車同時發現的物品有長矛及箭頭,說明這種馬車是用於作戰。將馬的速度與耐力與輕量雙輻輪車完美結合,絕對是草原帶給世界的重要貢獻。隨著馬戰車的出現,戰爭的型態改變,草原上築有高牆、壕溝的內向式防禦堡壘一座座建立了起來。為了競爭鑄造兵器所需的金屬礦藏,激起了嚴峻的保衛戰。另一方面,金屬礦等原物料的流通,也加速了區域貿易網絡的密度。在敵對狀態的戰爭及突襲掠奪之外,更多是以和平交流、貿易的方式與中亞、近東及其他地區的商人、村鎮及城市密切接觸。馬匹以及之後到來的輕型雙輪馬戰車以新奇事物之姿,進入了近東、西亞、中亞、南亞,成為當地的戰爭利器以及身分象徵。
安東尼教授提出的歐亞語系擴張模式,是由裏海、黑海北側的東歐大草原,向東到烏拉爾山,深入中亞,並進入南亞。這一地理空間與人群飛速串連的物質表現,是西元前兩千紀青銅時代晚期橫向分布於歐亞草原的斯魯布納亞文化及安德羅諾沃文化。以最初出現雙輪馬戰車的烏拉爾山為界,斯魯布納亞文化向西延伸到黑海北邊的聶伯河;安德羅諾沃文化則向東延伸,順著阿爾泰山,一路到天山山脈一帶。大量的考古遺址都發現了相近的兵器及工具類型。這兩個由辛塔什塔文化發展而來的文化,將整個歐亞草原統合起來,把東西兩端的強大文明區塊連結在一起,使整個歐亞大陸成為空前的交流網絡。作者將歐亞草原視為橋樑,正如他在書中所指出的,「中國的商王和希臘的邁錫尼諸王分處古代世界的兩端,同時駕馭著馬戰車,並擁有與歐亞大草原青銅時代晚期牧民相同的技術。」
這些互不相識的文明主體共同使用著源自歐亞草原的創造發明,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時候的歐亞草原世界沒有文字,這些交流史都掩蓋在東西方有文字的文明主體的論述中。在東方,車子的發明者被認為是夏王朝來自東夷的奚仲。對於古典文明影響甚鉅的冶金術,在文獻中並未被視為重要發明,其最初的狀態似乎僅是以禹鑄九鼎的傳說帶過。而歐亞草原東部的人群又是如何看待、接受這些居住在黃河流域的人群,並從與他們的交流中獲取養分?都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並非置身事外的漢語
閱讀這部著作,讓人想起詹姆斯.帕特里克.馬洛利教授及漢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於二○○○年出版、同樣具有爭議性的名著《塔里木的木乃伊:古代中國與來自西方的人群之謎》(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塔里木的木乃伊》從歐亞草原東端的新疆木乃伊以及已消亡的吐火羅語,試圖探討印歐語系在東方的發展與流向,可以為本書故事的終結——安德羅諾沃文化擴及新疆,提供一個後續發展的銜接。《塔里木的木乃伊》的作者提出,商王朝接受了草原的作戰工具及模式的同時,也借用了原始印歐語輪子的發音,將之用於漢字的「車」上。在字形上,商代甲骨文對「車」字的象形表現也如著名漢學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所指出的,與歐亞草原東端南西伯利亞地區的古代岩畫馬車幾近一致。這些,以及早已引進的草原合範鑄銅技術,都說明著使用原始印歐語的人群在語言及文化上對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
張騫通西域打開的絲綢之路豈是「鑿空」?考古發現已表明,舶來品或具有草原風格的物品在漢代以前已十分常見,反之亦然。如本書所呈現的,歐亞大交流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便以超乎想像的方式漸次展開。雖然原始印歐語起源、傳布及變異的研究仍觀點紛呈,本書將原始印歐語如何影響世界的討論,直接上推至西元前五千年,從東歐大草原上的人們開始養牛牧馬、鑄造銅器,談論他們的羊毛、車子,從一開始緩步成長,到西元前兩千紀的猛爆式貿易交流網絡。作者抽絲剝繭,以語言學及考古學證據溯源,從根本改變文明與野蠻的優劣觀、畜牧與農業的分隔線、遊牧與定居的二分法等等充滿成見的認知方式。由此展開的壯闊歷史圖景,令人讀來大呼過癮!
在我們熱衷於全球化議題的同時,不妨藉由本書將時間段直接拉到最遠,檢視語言、馬及車輪如何成為有效的推進力,將世界串聯在一起,應會對我們再次檢視世界史上人類的區域連動關係,不論是流行的古今絲綢之路或海洋絲綢之路,全球化乃至去全球化,都能有所回應,帶來深刻的價值。
(摘自:導讀 當世界史由車輪轉動)
內文 : 〈母語的承諾與政治〉
◎祖先
當你攬鏡自照時,印入眼簾的不僅僅是自我的臉龐,而是一整座博物館。就某種意義來說,我們的臉是自己的,但也可以說這張臉是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曾曾祖父母……繼承而來的種種特徵所湊成的一張拼貼畫。不管是否喜愛自己的嘴唇和眼眉,這些都不僅僅是自身的、也都是祖先的特徵;就算他們已經作古了千年,其碎片仍然在我們的身體裡鼓動著。即使是像平衡感、音樂能力、在人群中的羞怯感,或者是疾病易感性這類複雜的特質,都曾經存在過。我們無時無刻不承載著過去,而且不僅僅是在自己體內。過去也存活於我們的習俗中,包括我們說話的方式。過去是我們一直戴著的無形鏡片,我們透過這副鏡片感知世界,世界也透過這副鏡片感知我們。我們永遠是站在祖先的肩膀上,不管我們是否願意垂眼承認他們曾經存在。
大多數人通常對祖先知之甚少,往往連名字都不知道,這實在令人困窘。每個人都有四位曾祖母,這些女性和我們在基因上十分接近,每當注視自己的倒影,都能看到她們臉龐、皮膚、頭髮當中的元素。這些曾祖母們在結婚前都有著各自的本姓,但我們也許連一個都想不起來。夠幸運的話,我們可能會在族譜或文獻中發現她們的名字,可惜戰禍、遷徙、紀錄受損等因素,都讓這對多數美國人來說不過是奢望。我們的四位曾祖母皆有過完整的人生和家庭,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格特質都是由她們傳下來的,但我們卻徹底丟失了這些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先祖。又有多少人能料想得到,接下來區區不過三代,自己的後代就會將我們忘得一乾二淨,連名字都記不住?
生活在仍然由家庭、擴散式親族與村落組成的傳統社會中,人們往往更能意識到自己與祖先的深厚淵源,甚至還能感受到祖先靈魂和精神的力量。馬達加斯加農村的薩菲馬尼立族(Zafimaniry)婦女,從她們的母親與阿姨那兒學到如何在帽子上編織複雜的圖案。這些圖案在不同村莊之間有著明顯區別。某個村莊中的婦女向人類學家牟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說,這些設計是「祖先傳下來的珍珠」。就算是再普通不過的薩菲馬尼立族房屋,都被視為其建造者的靈魂所宿之處。在現代消費文化的思維當中,多半已找不到這種對先人力量的虔信。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依賴消費經濟,需要不斷接納新事物。然而,透過考古學、歷史、族譜和祈禱儀式所累積的豐富資料,讓我們能夠更加貼近對先人的認識。
考古學是認識前人的人性和重要性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理解我們自身的人性。這是唯一一門探究往昔日常生活紋理的學科──雖然未曾有人書寫過這些紋理,但這才是絕大多數生命所過的生活。縱然考古學家已經從那些無聲的史前遺骨中得到了許多驚人的細節,但是對於這種沒有留下想法、話語或姓名等文字紀錄的人群,我們的所知十分有限。
有沒有辦法能克服這些限制,復原史前人類究竟如何生活,以及至關重要的價值觀和信仰?他們是否在其他媒介中留下過任何蛛絲馬跡?許多語言學家都確信,這個媒介就是我們每天使用的語言。我們的語言當中包含大量的「語言化石」,來自於古代語言使用者所遺留的痕跡。教師說這些「化石」充滿著各種「不規則」的語言形式,而我們往往是不加思索地就這麼學會了。我們都知道,英語的過去式通常是在動詞字尾加上t或ed(例:kick-kicked, miss-missed),或者改變某些動詞的詞幹中間的母音(例:run-ran, sing-sang)。然而,通常沒有人會跟我們說,這種母音變化,其實是古老、原始的語言形式。事實上,藉由改變動詞詞幹中的母音來形成過去式,在大約五千年前是很常見的。儘管如此,知道這些仍無法讓我們知道當時人們的想法。
我們今時今日所用的字彙,真的是五千年前人類語言的化石嗎?一部字彙表將能夠闡釋過去歷史中許多晦澀難懂的部分。正如語言學家愛德華.沙皮爾(Edward Sapir)所言,「一種語言的完整字彙表,確實可被視為一個社會所關注的所有思想、興趣和日常事務的商品清單」實際上,目前已經重建出一個完整的字彙表,屬於五千年前人們所使用的一種語言。這個語言便是現代英語的祖先,也是許多現代和古代語言的祖先。所有源自這個母語的語言都屬於一個語系,即「印歐語系」。今天印歐語系的使用者約有三十億人,遠遠多於其他任何語系的使用者。而印歐語系的母語,也就是「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的研究至今已有大約兩百年的歷史。然而在這兩個世紀中,印歐語的各個研究面向幾乎都存在著分歧與爭論。
不過,熱烈的爭論總是帶來解決問題的希望。本書或許有機會解答「原始印歐語」的核心課題,即「原鄉」(homeland)的問題──是誰使用、在哪使用,以及何時使用原始印歐語。這個問題讓幾個世代的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爭論不休,許多人懷疑尋找「原鄉」是否有其必要性。過往的國族主義者和獨裁者堅持「原鄉」起源於他們的國家,並且屬於他們自身的優越「種族」。但是,今時今日的印歐語言學家正試圖改進研究方法,並且有了新的發現。他們重建原始印歐語字彙中成千上萬個語詞的基本結構和涵義──這樣的研究本身就是驚人的壯舉。分析這些語詞有助於描繪出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群的思想、價值觀、在乎的事物、家庭關係和宗教信仰。但我們得先確定他們生活的地點和時間。如果我們能將原始印歐語的字彙與特定的考古遺跡相結合,便有機會掙脫考古知識的一般性限制,並且更加豐富我們對這些特定祖先的認識。
我與許多學者的觀點相同,都認為原始印歐語的「原鄉」位於黑海和裏海以北的大草原,也就是在今天的烏克蘭、俄羅斯的南方地區。草原上新的考古發現極為豐富,讓「原鄉」起源於大草原的說法比過去更有說服力。
印歐語言的「原鄉」位於大草原上,這點為什麼如此重要?要想明白,就需要一腳踏入既複雜又迷人的草原考古世界。「草原」在俄羅斯農業國家的語言中,意指「荒地」(wasteland)。類似北美中西部的大草原──被遼闊天空所壟罩的一大片單調草原海洋。連綿不絕的草原地帶,從西方的東歐(草原帶結束於烏克蘭的敖德薩〔Odessa〕和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之間)一直延伸到中國北方的萬里長城,亦可說是一條橫跨歐亞大陸中心七千公里不斷的乾旱走廊。數千年來,這片巨大的草原強而有力地阻隔了思想和技術的傳播。如同北美的大草原,這樣的環境十分不利於徒步旅行的人群。而且,就像在北美一樣,打通草原通道的關鍵是馬,再配合歐亞草原上普遍馴養的綿羊、牛等放牧牲口,讓草原上的「草」可以加工、轉變成對人類有用的產品。最後,騎馬和放牧牛羊的人群獲得了車輪,接下來不管在哪裡,都能跟著自己的牲口走,並能使用沉重的馬車來運送他們的帳篷和物資。只有在馬被馴化、且發明了有蓋四輪馬車之後,中國和歐洲的史前社會才有可能模糊地意識到彼此的存在,並且結束彼此的隔絕狀態。同時,這兩種運輸革新也使得歐亞大草原人群的生活變得可預測且富有生產力。歐亞大草原的打通──從一道對人類極不友善的生態屏障轉型成跨大陸交流的走廊──永遠改變了歐亞大陸的歷史發展方向,並且,本書主張,這更深深影響了印歐語系的第一次擴張過程。
◎舊題新解
近兩百年來,語言學家不斷努力重建原始印歐語的文化─語彙。而距今不到一個世紀,考古學家才開始爭論原始印歐語社群的考古特徵,似乎比語言學家慢了一步。這一個多世紀以來,印歐語系源頭的問題始終與歐洲智識史和政治史交纏在一起。為什麼在考古學和語言學證據之間,未能產生被廣泛認可的一致性?
因為有六大問題擋路。一是西方學術界最近的智識風氣使許多嚴肅的人開始質疑整個原始語言的概念。現代世界見證了日漸增加的文化融合:音樂領域(雷村黑斧合唱團〔Black Ladysmith Mombasa〕和保羅.賽門〔Paul Simon〕、帕華洛帝〔Pavarotti〕和史汀〔Sting〕)、藝術領域(後現代折衷主義〔Post-Modern eclecticism〕)、資訊服務領域(八卦新聞〔News-Gossip〕)、人口混合層面(國際移民達到最高水準),以及語言領域(多數人身處雙語或三語世界)。隨著一八八○年代對文化融合現象的興趣日增,深思熟慮的學者開始重新思考那些曾被詮釋為個別、獨特的實體語言和文化。就連「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也開始被當作「克里奧語」(creole)看待,即來源多樣的混合語。在印歐語研究中,此運動顯示出學者開始質疑語系和語族樹狀模型的概念是否牢不可破,有些人宣稱尋找任何原始語言都不過是妄想。許多人將印歐語系間的相似性歸因於相異歷史源流的鄰近語言間的融合,這意味了單純的原始語言從不存在。
其中大多都很有創意,但不脫模糊的臆測。語言學家如今已經確立,印歐語系間的相似性不能歸因於克里奧化和融合。根本沒有哪個印歐語系的語言類似克里奧語。印歐語系必定取代了非印歐語系的語言,不僅僅是改造它們。當然,有跨語言的挪用,但其並沒有達到所有在克里奧語中所見到的混合和結構簡化的極端程度。「唯有」從一個共同的原始語言出發,才能產生威廉.瓊斯爵士在印歐語系中發現的相似之處。多數語言學家都同意這一點。
因此,我們應該要能將重建後的原始印歐語字彙當作史料,推測出它被使用的地點和時間。但這衍生出第二個問題:多數考古學家顯然不認為有可能如實重建「原始印歐語」語彙的任何部分。他們不承認重建字彙的真實性。這抹煞了追尋印歐語系源頭的首要原因,以及搜尋中最具價值的工具之一。在下一章中,我將為比較語言學辯護,簡單說明其運作方式,並解釋重建字彙的方針。
第三個問題是原始印歐語有多古老?考古學家尚無法取得共識。有人說它的使用年代在西元前八千年,另一批人則說應該遲至西元前兩千年,還有一些人認為「原始印歐語」只是抽象概念,僅僅存在於語言學家的腦袋中,因此無法定於任何一個年代。當然,這使得它無法專指特定時代。但造成此長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多數考古學家並不關注語言學。有些學者提出的解釋與眾多語言證據相悖。藉著解釋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可信度和真實性的問題,我們將能大幅解決第三個問題(原始印歐語在何時被使用),此問題縈繞整個第三章和第四章。
第四個問題是考古方法在那些對印歐語系源頭研究最為關鍵的領域中,恰巧並不發達。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史前語言群體與考古文物無法等同,因為語言在物質文化中不會以任何一致的方式反映出來。說不同語言的人群可能會使用類似的房舍或陶罐,但說同一種語言的人群也可能用不同的方式來打造陶罐或房舍。但在我看來,語言和文化在某些情況下「具備」可預見的相關性。在這些情況中,我們看到一道「非常明確」的物質文化邊界──不僅止於不同的陶罐,還包括不同的房舍、墓葬、城鎮格局、塑像、飲食和服飾──「延續」了幾世紀或幾千年,這往往也是一道語言界線。不管在哪裡,這都不會發生。事實上,這種「民族語言」(ethno-linguistic)的界線似乎很少出現。但是,如果一道強大的物質文化邊界確實延續了數百、甚至數千年,語言往往牽涉其中。這種觀點使我們能在純粹考古文化的地圖上指認出至少「些許」語言界線,此為追尋原始印歐語原鄉的關鍵一步。
當代考古學理論的另一弱點是考古學家通常不太了解遷徙,而遷徙是語言變異的重要載體──當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也彌足重大。二戰之前,考古學家單純用遷徙來解釋史前文化中所觀察到的任何變化:在考古遺址中,如果第一層中的陶罐A型被第二層中的陶罐B型取代,那便是B人群的遷徙導致了此種變化。此一簡單的假設被後來的考古學家證明非常不充分,他們意識到「內部」變異,其實源於各式各樣的催化劑。工藝品型態的移轉顯示出受到社會聚集的規模和複雜程度所影響,其移轉包括經濟變遷、工藝品管理方式的重組、工藝品社會功能的變異、技術革新、新貿易的引介和交換商品等等。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每個西方考古系學生都學過「陶罐不是人」(pots are not people)這條金科玉律。遷徙從一九七○和八○年代西方考古學家的解釋工具箱中徹底消失。但遷移是至關重要的人類行為,若忽視遷徙或假裝它在過去歷史中無關緊要,就無法理解印歐語系的種種問題。我試圖從現代的遷徙理論來理解史前遷徙及其在語言變異中的可能角色,這些問題將在第六章中討論。
問題五關乎我在本書中所擁護的特定原鄉,其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綠茵草原上。近來的草原史前考古資料,以一些只有少數西方考古學者可以閱讀的語言,發表在一些冷僻期刊中。其所採的論述方式,讓人憶起五十年前那種「陶罐是人」(pots are people)的陳舊考古學詮釋。在這二十五年的時間裡,我嘗試理解這些文獻的成果十分有限,但我可以說,蘇聯和後蘇聯時期的考古學自有一段獨特的歷史和理論基礎,而不單單是在重現西方考古學的哪一個階段。在本書的後半部,我綜合呈現了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草原地帶新石器、銅器和青銅時代的考古發現。雖然帶有選擇性且無可避免的不完美,但其直接承載了早期印歐語系人群的本質及身份。
馬躍上歷史舞台,這引發了最後的第六個問題。百餘年前,學者發現最早被好好紀錄的印歐語系語言──西臺帝國語、邁錫尼文化的希臘語和最古老的梵語形式(或稱古印度語),是軍事社會在使用的,似乎是隨著由快馬拉著的馬戰車(chariot)爆發式的進入古代世界。也許正是這些說印歐語系的人群發明了馬戰車。也許他們是第一個馴化馬的人。這能否解釋印歐語系最初的傳播?距今大約一千年前,西元一千七百年至七百年間的古代世界,從希臘到中國、從法老到國王,無不對馬戰車這項武器青睞有加。在宮廷的軍備清冊所描繪的戰役中,炫耀性的記錄了數以百計的戰利品,包括多不勝數的戰車。在西元前八○○年之後,最早一批訓練有素的騎射部隊出現,也就是最早的騎兵,革新了戰爭的型態,馬戰車便逐漸遭到棄用。如果說印歐語系的人群是最早使用戰車的人,便能解釋他們早期的擴張;而若他們是最早馴化馬匹的人,便能解釋在古印度雅利安人、希臘人、西臺人和其他印歐語系使用者的儀式中,馬為何會成為兵力和權力的核心象徵。
但直到最近,人們仍然很難或根本無法確定馬是在何時何地受到馴化。早期受到馴化的馬在骨骼上留下的痕跡少之又少,所有我們能找到的古代馬都是牠們的骨頭。十幾年來,我和研究伙伴及妻子朵卡絲.布朗(Dorcas Brown)持續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相信自己如今已經知道人類是在何時何地開始馴養馬。我們也認為,儘管在古代世界中,馬戰車比騎兵還早出現於有組織的國家與王國的征戰;但早在馬戰車發明的很久之前,人們就已經開始在草原上策馬奔騰了。
(摘自:第一章 母語的承諾與政治)
最佳賣點 : 六千年前的歐亞大草原並非蠻荒之地,而是印歐文明的起源地!
草原居民駕著猶如現代跑車的四輪車、馬戰車,循著大草原四處移居,
無形中推動了歐亞大陸的文明演化,開創最早的「全球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