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雨水
| 作者 | 王定國 |
|---|---|
| 出版社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昨日雨水:王定國2013年重返文壇第六本書長期追逐王定國的讀者,將可發現他以文學作為人性救贖的意志,在這本書中全新鍛鑄了最黑暗卻也最溫暖的一瞬之光所有的悲傷耗盡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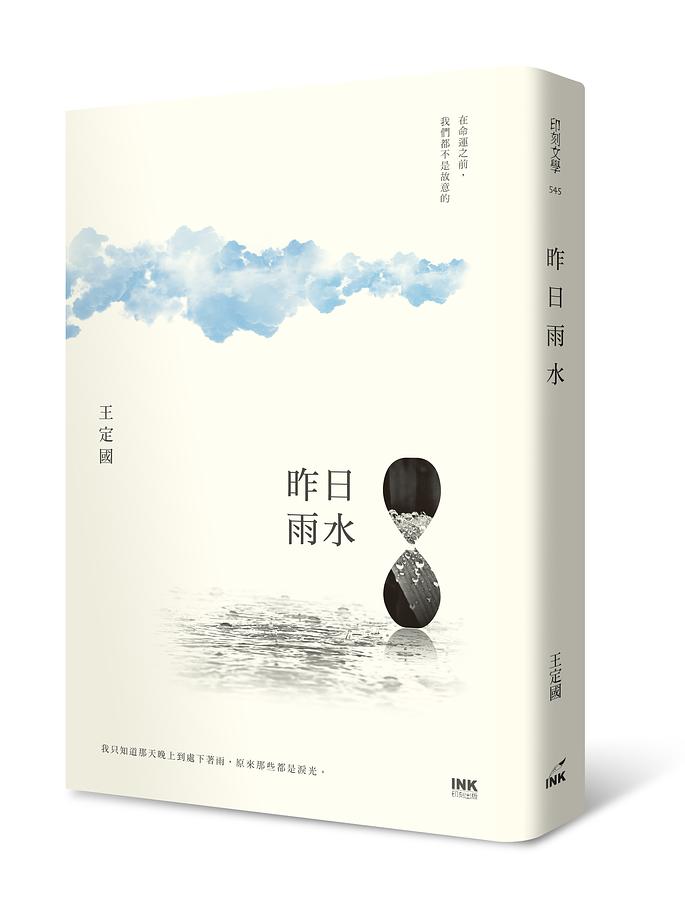
| 作者 | 王定國 |
|---|---|
| 出版社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昨日雨水:王定國2013年重返文壇第六本書長期追逐王定國的讀者,將可發現他以文學作為人性救贖的意志,在這本書中全新鍛鑄了最黑暗卻也最溫暖的一瞬之光所有的悲傷耗盡後, |
內容簡介 在命運之前,我們都不是故意的王定國絕境之愛,最新長篇王定國2013年重返文壇第六本書長期追逐王定國的讀者,將可發現他以文學作為人性救贖的意志,在這本書中全新鍛鑄了最黑暗卻也最溫暖的一瞬之光所有的悲傷耗盡後,我冷靜下來,決心開始找她。主角是個法務人員,一路懷著無故被拋棄的悲傷潛入掠奪者的世界,原本只想找出失愛的真相後遠走他鄉,卻從此墜落在黑暗的深淵中難以自拔。為了見那女孩一面,他淪為掠奪者的犬馬,送錢行賄,代行不法,所有的忍耐與等待皆來自當初相愛的女孩毫無預警就離開他。你不是他的孩子,但我覺得他在扮演被你懷恨的父親。故事裡的掠奪者,正是法界惡名昭彰的梟雄律師,卻默默背負著一個死囚的糾纏,蟄伏多年後突然化身為魔鬼與天使,一面巧取豪奪為著那些有錢有勢者脫罪,另一面則以他不為人知的良善投照在這對傷心戀人身上。小說刻意採以第一人稱的「我」,對自己的失落痛心難受,卻對他人的悲劇一無所悉,直到一個個令他心碎的故事撲面而來,他才發覺包含自己在內的幾條飄蕩的靈魂,已經交纏成為彷彿同屬一人的命運。人性中最卑微也最高貴的就在這裡了。在命運之前,沒有人是故意的,一切只因為那個逃家女孩,十年前冒著大雨所帶來的悲劇…。為了等待,他走上歧途:「如果司法是公正的,我想我會被原諒。然而司法的深度還不到這裡,它不會原諒我……。若要衡量我的處境再來懲罰,則我不應該受到懲罰,因為愛本身無罪,愛的質地清晰透明,無法隱藏快樂或悲哀或任何傷痕。」為了找她回來,他翻山越嶺:「人的困境中如果真有所謂的峰迴路轉,我想就是這個時刻,唯有這個時刻出現的奇蹟降臨在我身上,我所有的愚蠢才會被愛原諒。何況我所愛的已不純粹是愛,是包含著一個人的品格、信仰以及從我生命中自然萌發出來的使命感。」愛與罪與人世的蒼涼,以及雨水灑淨後的彩虹的天空……
各界推薦 「在台灣小說史裡,大概很少有作家的作品包含著那麼多悖反對立的元素,卻又能調配得如此妥貼和諧的。」--政大台文所特聘教授兼所長/范銘如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王定國一九五五年生,彰化鹿港人,定居台中。十七歲開始寫作,曾獲全國大專小說創作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早期著有小說、散文十餘部,轉戰商場後封筆多年,短期任職法院書記官,長期投身建築,二○一三年重返文壇。二○一三年 小說集《那麼熱,那麼冷》,獲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 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好書、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二○一四年 小說集《誰在暗中眨眼睛》,獲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 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好書、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二○一五年 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獲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 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好書、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博客來 年度之書、誠品閱讀職人「最想賣的一本書」。已售出 英國、荷蘭、德國、義大利、韓國和簡體中文等海外版 權。二○一五年 獲頒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二○一六年 小說集《戴美樂小姐的婚禮》,獲博客來2016年度選書。二○一七年 出版散文集《探路》。
產品目錄 推薦序第一章通常每個男人都會認為只要說出愛,對方就會記住一輩子,不像說早安那樣每到天亮後就得重來。男人怎能理解愛這個字對女人而言只是氣體,是說了之後很快就會飛走的聲音……第二章 妳知道神來居嗎?啊,妳當然不知道。那是愛與勇氣,柳太太。我和他們簽約時,外面的風好大,而我的手一直在發抖,我害怕的竟然不是錢夠不夠,而是當我在買方那一欄寫下妳的名字,那種突然豪邁起來的天真使我感到非常害羞和光榮。第三章 我看過死者的檔案照片,包括完整的和破碎的。完整的是她生前的美貌和微笑,留著一頭長髮,酒渦在她臉上盪漾著,命案發生前她把長髮攏在右肩,死後當然都不見了。至於那些破碎的……第四章我去那裡超過五次,同時也在精神科拿藥,每晚服藥時順便把他的安慰一起吞下,結果還是撐不到兩小時就醒來,醒來後的世界一樣黑,只好繼續裹在棉被裡暗暗地傾聽,不敢錯過萬分之一的文琦的動靜。第五章她突然大笑,誇張得有點狂浪,整個上身莫名地往後躺,沙發背雖然把她咯咯笑的脖子暫且撐住,那最危險的開襟處卻還是鬆脫了,細細的腰帶像蛇一樣滑溜到地毯上,胸前那兩袋垂奶突然非常惶恐地對著我。「你醉了喔,要不要進去躺一下?」她說。第六章文琦並沒有哭。啊,我不確定她有沒有哭。她被女記者羞辱一番後,一轉身戴上了口罩,臉上那唯一剩下的眼睛只有濛濛的雨水,我不確定一個口罩能掩飾多少淚水……第七章 我相信任何男人都會去尋找一個無傷的懷抱,因為那時還沒有深愛,還來得及脫逃,就像剛跳車的囚犯偷偷沿著鐵軌摸黑回家。那時也不會有任何痛苦,身上頂多只有輕微的傷,沒有人會特別在意那種傷,何況這世上還有愛,沒有任何一種愛如此傷人。後記
| 書名 / | 昨日雨水 |
|---|---|
| 作者 / | 王定國 |
| 簡介 / | 昨日雨水:王定國2013年重返文壇第六本書長期追逐王定國的讀者,將可發現他以文學作為人性救贖的意志,在這本書中全新鍛鑄了最黑暗卻也最溫暖的一瞬之光所有的悲傷耗盡後, |
| 出版社 /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3871880 |
| ISBN10 / | 9863871885 |
| EAN / | 9789863871880 |
| 誠品26碼 / | 2681505392005 |
| 頁數 / | 248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H:精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4.8X21CM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第一章
我本來計畫兩年後的秋天,帶著文琦搬進那棟神來居。
那是我瞞著她悄悄預購的一個未來夢,兩房之外有個開放式的書齋,木地板延伸到臥房,每個隔間角落擁有臨街的窗光。洗衣間旁邊還有個兩坪寬的小露台,建設公司答應圍起斜切面的鐵隔柵,文琦最喜歡的草本植物每天都會在那裡開花,旁邊還能擺放兩張小椅子,我們喝茶的時候看得到轉角的夕陽。
文琦離開我的時候,地下室的土方才正在進行開挖。
外面的世界並無改變,人間事物依照著原來的狀態進行。
唯一的改變大概就是連續收到的催款通知,賣方的語氣從客套到翻臉,最後甚至充滿憎恨,僅以一封存證信函就把那間房子沒收了。失去愛還不夠,連我唯一的夢也被剝奪,強悍的白紙黑字,在那無情的瞬間彷彿把我的人生化為烏有。
因此,接到沒收通知時,我除了強烈感到被羞辱,怎麼辦,只好開始打電話,電話由相關人員輪流接聽,最後轉到一個女性主管手上。我問她有沒有存過錢,有沒有覺得每個月存個一兩萬塊要很卑微,而且要非常艱辛扮演著令人討厭的角色,例如任何同事間的聚會都不能參加,甚至用盡各種理由來疏離別人的世界。
我告訴她,我已連續多少年過著這樣的人生,直到去年突然強烈湧起想要有個家的渴望,才會不知天高地厚把那間房子訂下來。小姐妳有自己的家嗎?妳能體會我說的家是什麼嗎?我盡我所能傾出所有的積蓄,結果竟然付不起你們的地下室那堆土方……。
「妳能原諒我嗎?我竟然不知道自己這麼渺小。」
「先生,你別這麼說,我幫你打報告上去爭取看看。」
「那就把報告寫清楚,契約上的名字是文琦小姐,再怎麼說,權益還在她身上,你們至少要給我一點時間,讓我把這件事轉告她。」
「啊,難道她還不知道你買了這間房子……」
「這沒什麼,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要離開?」
「怎麼會這樣?」
「我們現在談的是房子。」
「那……如果你繼續繳款,我替你想辦法把她的名字換過來。」
「千萬不要,」我鄭重地說:「我只剩下這個理由可以找她。」
.
文琦去過我們鄉下,當然也見過了我的母親。
初見面時母親有些驚慌,那時她正在曬棉被,乾淨的兩隻手猛搓在身上,想要上前迎接卻又狐疑地看著我,好像很怕認錯人又空歡喜一場。
母親喜歡文琦那暱著人的笑容,嘴巴甜,舉手投足一副城市女孩的伶快。她一來,家裡真的熱鬧許多,鈴子般清脆的嗓音不斷輕盪在瓦簷下,埕上雞啼狗躍,連睡午覺的鄰人都紛紛開門探出頭來。母親那天還特別留她住宿一晚,清晨又帶她去逛早市,回來時滿手的蔬果魚蝦,而且悄悄地炫耀於我,說今天的菜市裡她最風光,一直被人誇讚這未來媳婦生得好,漂亮又貼心,女兒再好也不見得這麼乖巧。
文琦離開我的時候,身上那些被人稱許的特質已不復見。
這麼說並非意味著她有所改變,其實那少女般的樣貌依然都在,只可惜緊繃在現實中的線條好像把她綑綁了。不然她還有個很可愛的習慣,在我鬱悶的時候,或我們同時感到無助的時候,她會在某幾個低迷的瞬間突然轉念,悠悠哼唱著清亮的曲音,然後跑進浴室裡沖臉,像在自己的臉上澆花,那迷人的笑靨這時就會稍稍漾開,而且捨不得全瓣打開,像一朵花分兩次綻放,好像很怕開完就什麼都沒有了。
有她那麼貼心的陪伴,照理說我們不可能分開。
只有一種例外,兩個相愛的人突然不知所措的時候。
這麼說是有點虛幻了。
若把時間倒返回去看,我們是在那最後的四天內分手的。
那四天剛好也是她出國旅行的時間,出發時臉上充滿著喜悅,輕巧的衣箱也都打理妥當放在門口,門外她朋友的漂亮跑車等著載她去機場,有生以來她第一次搭飛機。
沒有任何跡象,不像一般情侶還要經過爭執或累積多少背叛。
「好可怕,咻一聲就到香港了嗎?」她說。
「嗯,很快就到了,飛機上有輕食,妳就想像和朋友吃著下午茶。」
去香港的機票是免費的,那位做直銷的朋友由於業績達陣,特別邀她一起分享。她搭車出門後,那顆心還黏在我身上,「你自己要記得吃飯,這幾天就讓你耳根清淨囉。」手機一路暢通,震耳的搖滾樂從跑車中頻頻傳來,半小時後大概是忽然減速了,音樂轉小,傳來的是她小鳥般的驚叫聲,「怎麼辦,起霧了,看不見了,這裡是哪裡啊?」
「妳們大概正在爬坡,轉彎的地方霧特別濃。」
她的朋友準確地按響了一聲喇叭。
「哇,好厲害,你好像就在我們車子裡。」手機裡她附和著說。
她穿著那件花裙子出門,顯然這時的裙子有些慌張了,忙著把她縮回來的膝蓋罩下來,然後她傾身看著擋風玻璃,外面已是漫天濃霧,那台跑車就像螢火蟲飛了進去,很快消失了蹤影。
即便是那短短幾分鐘的慢速摸索,車子雖然逐漸離我更遠,我的心卻還是與她同行,沒有任何異樣顯示出我們兩人正在分離。
而且那時的我甚至是有些慶幸的。難得她有機會出門,我們暫且都能鬆弛一下神經,不用再顧慮著彼此顛倒的作息。何況她是經過猶豫才決定了這趟遠行,冰箱裡有她為我準備的菜蔬,也替我把飲水機補滿了水,還把一支竹掃帚藏到屋後的倉櫃裡,當我掀開櫃子想要拿它來掃掃落葉時,才發現她貼上了字條,玩遊戲那樣,寫著「別掃啦,等我回來」的字樣。
她以這種離不開的方式離開我,任誰都不相信她真的會離開。
何況後來她也從香港回來了,就在這第四天的下午。
倘若命運操控著時間,那也快要捱過去了,只要再撐過幾個時辰。
.
我在一家企業集團的法務室任職。
只要稍懂一些法律知識,大概就能在法務室裡寫寫書狀兼跑腿。我的職務介於法務助理和律師頭銜之間。作為一個長期參加考試而又屢次落榜的法務課員,我參與審閱各家廠商送來的書面資料、草擬各項合作條文,以及為各階段的進出貨事項訂定買賣合約。當然,有些牽涉到訴訟的行政業務也是我該做的,那就是跑法院。
我在法警室後面的大庭園穿廊下認識了文琦。
一開始,她只是個戴著口罩的女人,捧著一堆卷宗從我後面穿越而過。那時黃昏的廊外正在下著雨,整條走道在灰暗的淅瀝聲中提早點了燈,我跟在她後面疾走,趕著要去聆聽最後一審的民事庭。而走在前面的這灰色口罩卻突然停下來,連續打了兩聲噴嚏,瞬時把她滿手的卷宗震落一地,有些甚至散開了頁面垂掉在水溝邊緣。
我並不能因為有人擋路就停下來,時間已經有點遲了,根本無暇理會她那一副散亂的狼狽,所以急著跨過那些卷宗也是難免的,不料被她叫住了。
「喂,見死不救喔?」
我回頭一看才知不妙,大半個鞋印已經落在那些卷宗封面上。
我趕緊掏出衛生紙,蹲在地上幫她擦拭,沒想到那鞋印拖曳過的字跡卻愈擦愈模糊。「我死囉。」她在口罩裡慘叫著,一邊胡亂收攏著散開的文件,一時卻又趕著時間,只好抽出其中一件匆匆起身,然後無助地看著我。
「我的律師老闆正在法庭等著這份案卷,你先幫我看管其他這些資料可以嗎?等我送去之後再回來拿。」
她透過口罩咕噥出來的鼻音,與其說是流感肆虐期普遍發作的生理症狀,在我看來應該只是內心的焦慮所引起,既然她已不那麼生氣,我暫時替她保管也是應該的,就算是對我自己的莽撞付出一點補償。
可是當我聽完民事庭出來時,手裡抱著一大疊卷宗,這個戴口罩的女人卻不見了。我跑到大門口附近張望了一陣,才發現原來戴口罩不只她一人。既然認不出誰是誰,我只好等著有誰主動來叫我,沒想到這一等竟然就是黃昏到夜晚,等到後來一個法警走過來關上了鐵門。
那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抱著她的那堆卷宗回家。
那些重要文件就這麼一整晚擱在我的書桌上,好比就是一個悲哀的暗示,預告著她將以如此荒謬的方式走進我的生命裡。
只是後來,當我以為我已經擁有她時,那份愛卻又被她拿回去了。
就像現在,此刻,房間裡只剩下梳子和幾個孤零零的髮夾留下來。
.
第二天我還不知道她叫文琦。我從卷宗裡循線去電詢問,那家律師事務所的總機告訴我,她們的小迷糊正在法院裡到處找卷宗。「你就是那個人嗎?那可不可以麻煩你現在就趕過去,或是請你留下電話……。」
她們口中的小迷糊,在我看來只是個還算豁達的歐巴桑,否則不會掉了東西還爆出那聲台語腔調的「我死囉」。聽起來像是怨怪著自己,且在那一瞬間似乎已經原諒了我。我騎著摩托車趕到法院時,本來心情還好,轉了幾圈後頻頻回望,卻就是看不到有人戴著口罩來。這時我已感到厭煩了,我既不能有事沒事出門太久,一直通不過律師考試的情緒本來就是十分沮喪的,沒想到無緣無故還惹來了這種麻煩……。
我打算趕回法務室上班時,一個穿白夾克的女孩從服務站跑了出來。
「是我啦。」笑盈盈地叫著。
不戴口罩的臉,反而使我認不出昨天的那雙眼睛。
這時她大概想要幫我喚醒記憶,竟然合起了雙手遮著臉,於是那雙眼睛便從指縫中滾亮著閃露出來了。玩著捉迷藏似地,還對著我的錯愕眨眨眼,像隔壁人家的女孩,好巧不巧來到法院遇到了童伴……。
我除了訝異還有些慌,尤其當她蒙著臉又拿開手掌的這一轉瞬間,猛然浮現出來的是一張姣好的臉,反倒讓我懷疑她是被人推派來捉弄我的吧?我雖然把卷宗交到她手上了,卻還不走開,反而問我是不是她的同業,說完卻又嘖聲否認著,「沒有啦,我也沒資格說是什麼同業,我在事務所裡就是個倒茶的,有時候兼收件,幫忙列印,當然也要拿東拿西跑來法院裡幫忙。」
她問我能不能給她一張名片,過幾天會找時間當面來謝我。
「今天沒帶在身上,而且我也很少用名片,只給一些當事人。」
「那我知道了,難道你是……,」眼裡溜著一股淘氣,連珠炮似地念著一堆名堂,「圍標的海蟑螂、司法黃牛、調解委員會代表、諮詢志工、替人搶標的仲介業,不然就是跑進來遛達的業務員……,哈,故意嚇你的啦,這些角色當然都不可能是你。」
我鬆了一口氣,她卻還沒說完,「我好像見過你好幾次,你是不是每次等開庭的時候都坐在樹下看書,對不對,一直都在準備考試喔?我們事務所的同事也都很會利用時間,可是身體都累壞了,其中一個去年還念到吐血。但我知道你絕對考得上啦,你看庭上那些人也不怎麼樣,還不是一個個很神氣的坐在台子上。」
我苦笑著告訴她,考試沒我的份,早就想要放棄了。
「那多可惜,喂,你不相信我料事如神嗎?」
「我已經考了很多次……」
「那又怎樣,不信的話,你考上那天我嫁給你。」
約莫是剛入社會的年紀,口氣火辣到令我傻眼。這是怎麼說的呢?
「開玩笑的嘛,還不是替你感到可惜,念都念了,笨蛋才放棄。」
「妳懂這麼多,說不定以後真的會嫁給律師。」
「嫁給法官也不錯呀,穿著法袍好有權威,我每次送完資料都捨不得走,有一些不相干的庭訊我都照聽不誤,只要多聽幾次大概就猜得出被告會判幾年,都很準的喲。怎麼樣,不信的話等你當上法官看我猜得準不準?說不定每個案子要判幾年都會問我呢,到時候你就娶我吧。我現在要趕快把這些卷宗拿回去交差了,本來今天早上已經寫好辭呈了說,幸好你把我救回來了。」
她一說完,隨著紅燈淹沒在人群裡,一溜煙在陰暗的騎樓下消失了。
人間事無奇不有,連我這麼平凡的人也碰上了。我看著她的背影離開後,才突然想到若有一天又在路上遇見她,說不定就認不出來了,因為那張臉不只好看,是一看就不便再看的那種美。我只記住了那雙長長的眼睛,還有就是那非常奇特的羞怯,當她說著那麼輕浮的語氣時,白皙的膚色竟然又一瞬間從額上紅到了臉頰,然後像是突然發覺說錯話,已來不及掩飾,只好抿起微翹的嘴唇低下頭來。
我雖不至於把她的挑逗當真,但畢竟她是那麼年輕,她若不是不懂事,那就是太懂事了,專挑我這種失意者尋開心。坦白說,我還因此忐忑好幾天,很想找她來問一問,妳是誰派來的,或者,妳說的……是真的嗎?
考律師,那多簡單,我每年都在考,每次放榜後都做著同一件事,懷著死心的恨意清空了混亂的書桌,所有的考試用書全都裝箱後疊高到天花板,然後趴在書桌上想著今後何去何從,有時還真希望那些紙箱突然塌下來把我壓死算了。
考上律師就嫁給我,那不是要等到下輩子嗎?
時間一過就是半年。
在這長達半年有點自慚形穢的落寞中,我卻養成一種習慣,只要騎著摩托車停在紅燈下的車陣裡,自然就會對著左邊右邊的口罩女郎多瞧幾眼。女人戴上口罩後唯一露出來的眼睛,其實最美。哪怕那是一張無望的臉,或她這時的情緒正在沮喪和感傷,或只是茫茫然等待著紅綠燈轉換,由於整個臉孔已被口罩覆蓋著,那雙眼睛便因為一直凝視著前方而顯得淒迷動人。
既然只記住了那雙眼睛,自然就在街頭一次次的凝視中逐漸淡忘了。
何況我已超過三十五歲,當初想要走入仕途的憧憬早已幻滅,苦讀的鬥志經過幾次挫敗還能剩下多少?而且我也被她嚇壞了,那種赤裸裸的用語使我懷疑她會不會是個很隨便的人,如果以後我注定要過著百無聊賴的人生,以她的年輕或那種美,對我來說無疑更是一種威脅。
然而第二年的三月,我卻又遇見她了。
那是某個律師團體每年春節過後固定舉辦的春酒會,我被公司主管指派去應景,本來打算簽到後就要提早開溜,這時會場角落卻突然傳來了一串輕伶的叫聲:小王子,小王子……。我一時聽不懂誰是小王子,然而那聲音卻是朝著我喚來的,聲音落定後那個身影才出現,白襯衫繫著蝴蝶結,捧著雞尾酒的小端盤,從那些寒暄的人縫中鑽出來,那喜孜孜的神態頗像法院那天的話題還沒說完,彷彿正在悄悄對我說著「娶我吧,娶我吧」那樣的嘴型……。
.
就是那一刻,她遞給我的那杯雞尾酒裡漂浮著一顆櫻桃。
她的嘴唇分明就是那櫻桃,甜甜地說著話,說她換了事務所,說她後來去過幾次法院都沒有遇到我,說完又鑽進賓客中分送著酒杯,回來時盤子裡多了一碟小點心,說要給我填肚子,轉眼又不見了。
一個星期過後。嗯,不會那麼久,應該沒有超過三天,一股喜悅撲著翅膀朝我飛來了,突然使我開始想念她。
我並不知道那是冒險,以為愛很簡單。
以我自身的處境,根本不允許自己像個混小子勾搭著一個豪放女。我的條件就只有家窮、平庸、老氣和沉默,有時還更要加上軟弱。我只能想像如果和她又見了面,那時我該怎麼和她說話?以她那樣爽朗甚且可說是有些……輕浮的性情,很有可能又對我說著那些突兀的字眼,譬如直接問我年紀、打算幾年內通過什麼考試,或者如果不參加考試還能做些什麼等等。
那麼,如何面對她的提問又不失趣味,這很重要。簡單說,我也很想趕快好好做個像樣的人,而不是永遠孤身一人,極不甘願地坐在別人的法務室裡浮浮沉沉。
我是認真的─這句話或許可以使她那雙眼睛專注起來。
-------------------------------------------------
後記
這本書雖然已來到了後記,故事裡隱密的部分其實沒有說完。
柳律師另外一面的內在,比如他真正的思維、情感以及情感世界裡的信仰與傷痛,我在寫作中並沒有刻意表達,除了以誇張又詼諧的言行來深藏他的憤怒,寫到終章時我還沒想好是否應該寬容,別讓他走入自己的牢房又關進了法律的監獄。
文琦自然也有她黑暗的內心,那種唯有女性才懂的巨大撕裂,除非不想活下去,否則她每天每夜受到的折磨幾乎比海深沉。寫作時原本應該另闢一個內心世界讓她自己說話,然而最後我還是把她可以對外傳遞的機會捨棄了。
讀者因此看到的幾乎就是人物表象的存在,他們原本可以袒露的聲音全都交由小說裡的「我」負責辨識和傾聽,藉由一路的摸索、看見、震驚和體會,把他們的苦難連結在自己身上而成為共同的命運。
小說裡的「我」雖不是我,但這幾年來我卻又經常扮演著「我」的化身,終歸就是一種極為單純的執念,想要藉由安靜的文字所能產生的療癒來探顧他人的生命,彷彿唯有這樣才能啟示我持續書寫的意義,其他任何飛簷走壁的文字技藝只不過是另一種說書人的本質,這在我的文學認知上一直是個難以靠近的距離。
我曾說過的一句話至今仍然是有效的:「我不是個喜歡說話的人,自然也不喜歡以說故事的形式來成為一個小說家。」證諸前面幾本書的實踐,我還發現自己的習慣現象已愈來愈明顯,有時僅僅為著一個忽然來到的懸念就能馬上動筆,這時往往還沒有一個明顯的故事架構等著我,直到寫作中途無以為繼時,我才自覺到這已不只是純粹的寫作,還隱含著一股想和自己說說話的動機,用獨自一人的腳印走進故事,然後在夜深人靜時傾聽著這些屬於自己的聲音。
只有我知道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在這麼黯淡的文學氛圍裡,我並不認為自己的寫作多麼虔誠,反而只是因為被一種莫名的純真所帶領,明知還不能寫出自己最想要的,卻還是會在落筆那一瞬間堅信著自己的美好,倘若文學這條路上沒有這樣的傻念,我不知道還有什麼難走的路可以如此激盪一個人的心靈。
寫作,這無用的寫作,幾年來就是這麼耐人尋味地折磨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