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遇胡適: 從文本縫隙中重構胡適的思想面貌
| 作者 | 高全之 |
|---|---|
| 出版社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
| 商品描述 | 巧遇胡適: 從文本縫隙中重構胡適的思想面貌:本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胡適研究,而是一次在閱讀與寫作中的「巧遇」。作者原無意專論胡適,卻在整理張愛玲文學、研讀《西遊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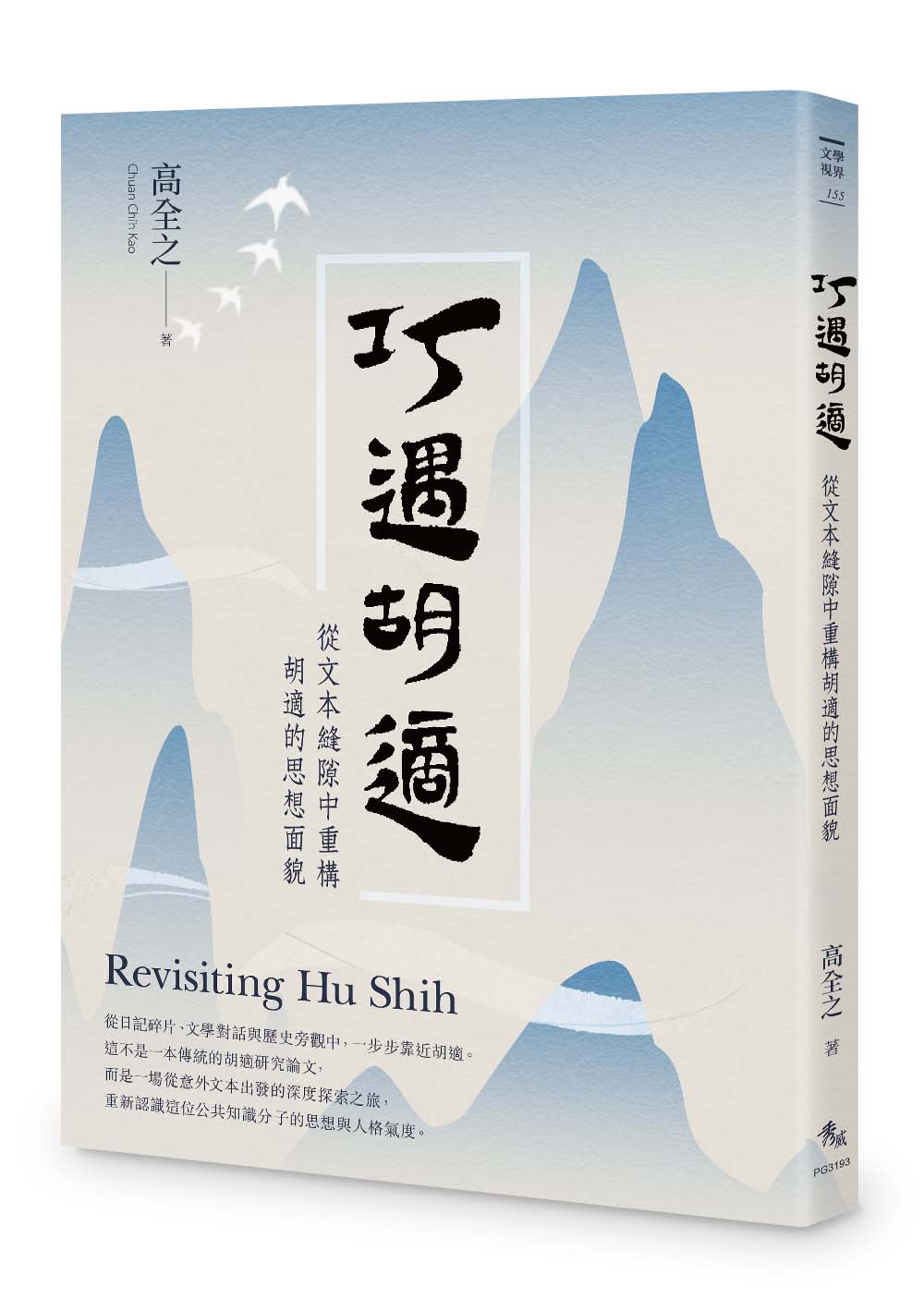
| 作者 | 高全之 |
|---|---|
| 出版社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
| 商品描述 | 巧遇胡適: 從文本縫隙中重構胡適的思想面貌:本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胡適研究,而是一次在閱讀與寫作中的「巧遇」。作者原無意專論胡適,卻在整理張愛玲文學、研讀《西遊記》 |
內容簡介 本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胡適研究,而是一次在閱讀與寫作中的「巧遇」。作者原無意專論胡適,卻在整理張愛玲文學、研讀《西遊記》過程中,反覆與胡適不期而遇,從而發展出對其思想與人格的細緻觀察。 不同於直接從胡適著作切入的研究方式,本書選擇從日記、書信、評論、他人筆記、歷史對話與邊緣文本出發,透過「微觀」的閱讀策略,拼湊胡適在思想、學術與時代現場中的樣貌。內容涵蓋胡適對《西遊記》的反覆著迷、與張愛玲的文學交集、對美國總統的理解,以及他在政論、宗教觀與文化態度上的多重轉折。 書中亦觸及胡適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自覺,如何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展現謙卑與包容。作者從文字縫隙與歷史細節中,慢慢勾勒出胡適的「中華民族觀」、思想包容性與人格深度,而非只停留在標籤化的評價或單一敘述。 《巧遇胡適》呈現的,是一種閱讀方法、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提醒:真正有價值的思想,常常隱藏在被忽略的文本角落。讀者將在這場文字與思想的探索旅程中,重新認識胡適,也重新思考我們理解歷史與人物的方式。
作者介紹 ▎高全之1949年生於香港,1953年移居台灣。1975年前往美國深造,於1977年取得電腦科學碩士學位,同年起擔任電腦工程師,並於2016年退休,現定居美國。自大學時期即以文學評論見長,曾多次入選台灣重要評論選集。著作:《當代中國小說論評》(幼獅,1976),改版為《從張愛玲到林懷民》(三民,1998);《王禎和的小說世界》(三民,1997);《張愛玲學》(一方,2003);《張愛玲學[增訂版]》(麥田,2008);《張愛玲學[增訂二版]》(麥田,2011);《張愛玲學續篇》(麥田,2014);《重探《西遊記》:神佛妖魔人間事,三藏師徒取經歷險的重新發現》(聯經,2018);《私札與私語──三顧張愛玲》(時報文化,2022);《西遊二論》(致出版,2023)。
產品目錄 自序 知其勢,察其心,處其地,籌其事寫作大字頭──胡適和虛銜胡適和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胡適和虛銜〉補記熱淚盈眶──胡適的三塊錢言教和身教──胡適談大專選系嫩葉和開花──胡適日記古典文學拾遺出乎常理──胡適談美國總統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型態一言而為天下法──〈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型態〉譯後記胡適‧白崇禧‧蔣介石──《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的一種讀法風尾巴還留在樹梢上──單德興《山東過台灣─流亡學生夫妻自傳合集》張愛玲的胡適粉絲情結──再談〈憶胡適之〉承先啟後──胡適和張愛玲鼓吹《海上花》齊邦媛的「黏土腳」──《巨流河》引起的問答聞歌起舞──張愛玲《秧歌》裡的歌舞偽書真情──胡適的「第八十一難」聆聽古音──「款款」和「聒噪」偉大與卑微──姚一葦《碾玉觀音》抬頭看星星──隱地自傳《雷聲近還遠》玩物尚志──張錯近年藝文著作輪廓
| 書名 / | 巧遇胡適: 從文本縫隙中重構胡適的思想面貌 |
|---|---|
| 作者 / | 高全之 |
| 簡介 / | 巧遇胡適: 從文本縫隙中重構胡適的思想面貌:本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胡適研究,而是一次在閱讀與寫作中的「巧遇」。作者原無意專論胡適,卻在整理張愛玲文學、研讀《西遊記》 |
| 出版社 /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
| ISBN13 / | 9786267511992 |
| ISBN10 / | |
| EAN / | 9786267511992 |
| 誠品26碼 / | 2682956605003 |
| 頁數 / | 304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4.8*21*1.56 |
| 級別 / | N:無 |
| 重量(g) / | 417 |
| 提供維修 / | 無 |
自序 : ▍自序 知其勢,察其心,處其地,籌其事
一
「巧遇」兩字表達本書的緣起、範圍和反省。
我原先沒有專文或專書研析胡適的計畫。前幾年整理張愛玲文學,探索胡張文學淵緣,順勢以胡適日記為主要依據,做了胡適宗教信仰的專題討論。稍後研讀《西遊記》,再次向胡適報到,追蹤他重複提及這部小說的記錄。那些「不期而遇」延伸至本書收錄的文章,仍然沒有全盤總結胡適的企圖和成果。
這種自我認知導致了極具意義的覺醒:我們讀寫白話文,都受惠於白話文學運動;即令白話文學普及可能是文化歷史上遲早會發生的事情,我們仍然可以同意胡適促進白話文學正統化以及深刻化的貢獻。所以「巧遇」意指淋浴在胡適影響裡駐足審思他的幾個現代意義。
二
這些反省並非微不足道。根據周質平,胡適的平反已經在中國大陸再現和傳播,但仍有其局限性:「胡適研究從五十年代的『喑啞』到如今的『吞聲』,表面上看來是從『無聲』到了『有聲』,但是離『放言』還有相當的距離。只要『網禁』不去,『吞聲的胡適研究』是不可能『還胡適本來面目』的。」其實在「放言」地區,仍時有貶斥胡適的噪音。
胡適曾感念台大校長傅斯年(孟真)經常挺身出來辯護說:「你們不配罵適之先生」。今日視之,傅斯年那種袒護所流露的交情和擔當,令人感佩,但無必要。在學術領域,胡適從善如流,三番兩次承認錯誤,公開感謝別人指正。在學術領域之外,胡適多次在公開辯論當中勇於納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學術界已經注意到的,胡適及時改「全盤西化」為「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之後,在國事評論,政治生涯等等方面,愈來愈不反駁外來抨擊。無論譴責如何嚴厲,胡適多半保持沉默。如〈偽書真情─胡適的第八十一難〉所示,胡適早早就決定以肚大能容的態度看待。他比那些一生只有學術界經歷或馴服於政治壓力的評論者更知道政治的複雜,更知道職場倫理的重要。
胡適曾多次引用明朝思想家呂坤。呂坤有句名言:「除了中字,再沒道理;除了敬字,再沒學問。」那個中字,是執兩用中的意思。呂坤另外一個精闢的原則是:「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以下他這幾句話進一步解釋那個概念: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秤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君子恥之。
如〈出乎常理─胡適談美國總統〉所示,胡適理解和欣賞美國總統,思維方法就是進入歷史情境去理解歷史人物。我們評估胡適的歷史地位,也應該採取同樣的歷史態度。不然的話,記住呂坤所說:君子恥之。
三
我嘗試補述前人未盡全功的論述,進一步瞭解胡適的志業和人格特質。全書主要由五個區塊組成:
‧注意具體而微的人格特質
‧揀拾宏觀視野的歷史話語
‧延續張愛玲和胡適交集研究
‧追蹤胡適的《西遊記》興趣
‧援引胡適論述的幾篇書評
本書所收下列文章的思辨範圍顯然具體而微:〈寫作大字頭─胡適和虛銜〉,〈胡適和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胡適和虛銜」補記〉,〈熱淚盈眶─胡適的三塊錢〉,〈言教和身教─胡適談大專選系〉,〈嫩葉和開花─胡適日記古典文學拾遺〉。話題雖小,仍然觸及尚未被任何學者充分探討的領域。如不深究,就無從全面瞭解胡適人格特質。
宏觀敘述包括以下五篇:〈出乎常理─胡適談美國總統〉、〈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型態〉、〈一言而為天下法─「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型態」譯後記〉、〈胡適‧白崇禧‧蔣介石─《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的一種讀法〉、〈風尾巴還留在樹梢上─單德興《山東過台灣─流亡學生夫妻自傳合集》〉。
〈出乎常理─胡適談美國總統〉探查胡適學習美國政治的歷程和他的美國總統評估。證據顯示胡適用心良苦,有時故意揚洋抑華,不迴避偏見(他稱為「出乎常理」),以便增強建言的聲量和力道,喚醒祖國讀者的某些愚昧或無知。這是閱讀胡適政論或時評,必須注意的一個切入點。同樣重要的發現是胡適假道美國總統的討論來反思現階段兩岸的統獨問題。這個研究令人再次認識:如果用最最簡短的語言來形容胡適一生行狀,「中華民族」較「中華文明」更為妥當。理由在於胡適積極參與學研之外的實務。中華文明研究可作遠近長短的範圍調整,中華民族生命延續卻是當務之急。學研是胡適的最愛,但他樂於充當國家實務的評論家,檢討中國人的價值體系、習俗、政治、以及未來的命運。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體會他許多作品,例如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國人之大恥〉,深切的關懷與灼燒的熱情。
「中華民族」的觀念常以「中國」兩字代之。舉個例子。周質平這段話裡的「國」,就是「民族」的意思:「在胡適的思想中,『黨』之上是有『國』的;『國』是『千秋』,而『黨』只是『朝夕』。」中華民族是胡適一生最大的關切。胡適的中華民族觀念悠久長遠。他說過:這個「國家」有「千萬年生命」。此項認知幫助我們體會胡適英文遺稿〈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型態〉的重要性,因為它預測中國未來命運。這篇遺稿收入周質平編《胡適未刊英文遺稿》。周質平為該書所收胡適英文遺稿做個別簡介,並中譯個別篇名。
本書所收〈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型態〉是我的中譯。〈一言而為天下法─「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型態」譯後記〉略作析論。這篇遺稿重申其他胡適文獻或曾揭露的理念:某些中國傳統思維和價值觀念不會被共產主義摧毀。然而這篇遺稿更進一步,預言共產主義華化之必然。沒有其他胡適文獻更清楚傳達這個訊息。胡適從思想史家的大歷史觀出發,接受共產主義在中國生根發展的現實,然後陳述共產主義被中華文化同化的歷史規律。那是發人深思的課題。
〈胡適‧白崇禧‧蔣介石─《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的一種讀法〉介紹白先勇和廖彥博合著的三冊本《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我用胡適日記來對照這套書裡的近代民國記事。胡適只比白崇禧大兩歲,屬於同一時代,一文一武,共事於蔣介石之下,謀求中華民族的福祉。他們與台灣有特殊淵源,在台灣天翻地覆的政治發展之中,一直受到朝野尊重。兩人彼此欣賞,最後終老於台灣。特別謝謝白先勇支援三張白崇禧和胡適的相片。非常珍貴。稍後我再提他們兩人另外一個共通性。
〈風尾巴還留在樹梢上─單德興《山東過台灣─流亡學生夫妻自傳合集》〉從大饑荒、殉節、以及土地改革三個角度來瞭解山東流亡學生單汶和孫萍夫妻自傳。這篇文章引用胡適日記關於土改政策溫和化的記錄,合併參考這本自傳合集的記憶,可知土地政策暴力實施確是歷史事實,非僅空洞的政策訴求而已,然而土地政策並非從頭到尾全面暴力。這恰是土改小說(如張愛玲《秧歌》、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姜貴《旋風》)珍貴的原因。抗議文學不必也無從等待灰飛煙滅之後的平靜。路見不平就得奮筆直書。
這篇文章引用了看來可靠、毛骨悚然的大飢荒死亡人數。大飢荒和土改暴力都得算在毛澤東的帳上。應該是豐功偉業裡的減分部份。這是胡適和白崇禧的另個共通性:不必因為參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反對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而向任何人道歉。最大的遺憾是戰敗。就政治選擇而言,他們俯仰無愧於天地。
四
在這本書之前,我的胡適討論都收在研究張愛玲或《西遊記》的專書裡。張愛玲或《西遊記》都是自身俱足的議題。
《私札與私語─三顧張愛玲》收入以下三篇:〈胡適和張愛玲的初晤─「憶胡適之」的一種讀法〉、〈胡適的宗教信仰─「胡適和張愛玲的初晤」補遺〉、〈赫貞江畔的胡適和張愛玲〉。胡適宗教信仰可以獨立於張愛玲研究範疇之外。當時納入張論之內,意在點明張愛玲曾經表露,但未能深入調查的人文關注。當然那不是負評,我們每個人都有知識涉獵的限制。
《西遊二論》收入以下兩篇:〈突破束縛─胡適和楊聯陞信扎裡的《西遊記》〉、〈時在念中─胡適的《西遊記》研究〉。由《西遊記》而想到胡適,其實相當自然。如本書所收新文所示,就世故人情的表述方式而言,《西遊記》比其他中國經典小說更為深刻影響胡適。
本書延續張愛玲和胡適的交集研究,並且爬梳胡適的《西遊記》牽掛。下列四篇文章屬於張愛玲和胡適交集研究範疇。
‧〈張愛玲的胡適粉絲情結─再談「憶胡適之」〉和〈承先啟後─胡適和張愛玲鼓吹《海上花》〉試答幾個有趣的問題。張愛玲崇拜胡適,但她的胡適粉絲情結為何曾經發生轉折,那個變化是否展示人生態度的成熟過程?張愛玲英譯或國譯《海上花》的啟因是什麼?為何張愛玲的努力,無論這部小說能否假道英譯或國譯而廣為流傳,仍然值得肯定?
‧〈齊邦媛的「黏土腳」─《巨流河》引起的問答〉解決《巨流河》拋出的文學公案:胡適曾經不欣賞的一部小說是否張愛玲的《秧歌》?齊老師告訴我,當年在武漢大學,她從來沒有上過大伯高翰教授的課。可是她和許多在台武大校友都非常尊重高翰老師。當年我是個理工學院的大學生,齊老師是外文系主任。我從來沒有上過齊老師的課,也把她當作自己老師那樣敬重。
‧我們不知道張愛玲是否親自跳過秧歌舞。但敦煌藝術學者常書鴻跳過。〈聞歌起舞─張愛玲《秧歌》裡的歌舞〉比較張愛玲和常書鴻的「秧歌」筆墨。這個嘗試足以印證胡適和張愛玲都同意的《秧歌》小說境界嗎?
下列兩篇文章和胡適的《西遊記》關切相關。
‧〈偽書真情─胡適的第八十一難〉追溯胡適「第八十一難」的表述歷史,比較胡適改寫故事的不同版本,並從夾詩的修訂來理解改寫的意義。胡適版本的第八十一難故事和《西遊記》原著的精神和諧一致還是相互抵觸?胡適改寫的目的僅只是,如他自己所說,要充分展現佛教理念?
‧〈聆聽古音─「款款」和「聒噪」〉報告兩個張愛玲和《西遊記》用詞的前人案例。它們仍在近代中國使用,但可以上溯八百多年。中國語文的強勁生命著實令人驚嘆。
趁便收入這本集子的幾篇引用胡適的書評如下:〈偉大與卑微─姚一葦《碾玉觀音》〉、〈抬頭看星星─隱地自傳《雷聲近還遠》〉、〈玩物尚志─張錯近年藝文著作輪廓〉。我們無需張愛玲那種「如對神明」的胡適敬畏。我們在多方各面的人文領域攻錯辯難,如有機會,大可放懷享受胡適的春風化雨。或許讀者會像我一樣,有興趣去讀姚一葦的劇作、隱地的自傳、張錯的文物記述。
五
非常感激《傳記文學》吳承翰主編和《文訊》封德屏總編輯大力支持,刊載本書所收的幾篇文章。特別要謝謝鄭樹森教授的指導。不會忘記單德興教授和廖彥博先生的個別指正。非常感激白先勇教授、董保中教授、張錯教授、陳器文教授、王德威教授,長期鼓勵我的文化和文學鑽研。如果讀者覺得書名附題─「從文本縫隙中重構胡適的思想面貌」─切合本書思辨方法,請歸功於細讀書稿、建議附題的責編洪聖翔先生。
本書最重要的成就是繼《西遊二論》之後,再度求得徐澄琪教授古樸灑脫的法書。「西遊二論」四字典雅大氣。「巧遇胡適」反映書法家的漢簡帛書研究,從容自若。這些墨寶讓人感受到中華文化薰陶的厚實和溫暖。
古隸書法歷久彌新。
胡適走入歷史,豐富了民族記憶。
內文 : ▍出乎常理──胡適談美國總統(節錄)
一
胡適的美國總統表述散佈以下胡適文獻:日記、致韋蓮司的信件、以及文章。本文引用的胡適致韋蓮司信文都出自周質平中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這個追蹤非僅體會胡適對美式民主政治的嚮往和學習而已。我們會發現胡適的美國總統評價,即使樣本數量很少,銳利並且謹慎。胡適注意到美式民主政治難逃事在人為的主觀因素。他明知美式民主政治問題重重,仍嘗試在其中尋找可借用於中國的東西。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九日致韋蓮司信有句:「也許美國選舉根本不干我的事。但是,我卻有點情不自禁!」這種努力一直持續到他的後半生。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胡適〈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藉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任期1953-1961)不懂實務的笑話來勸蔣介石放手讓下屬處理業務。別人嘴裡的艾森豪負評變成胡適筆下的讚美。胡適主張居高位者應該確認自己所知有限,充分授權部屬執行任務。當然,胡適的意見是否正確,在於那些高階幕僚的品質(幹練、公正、清廉等等)。很難一概而論。
胡適日記原意在於出版,供大眾閱讀。然而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計劃公開自己給韋蓮司的私信。他自己不留那些私信的副本。因此這些信件往往包含著他甚至在日記中都不會透露的訊息。本文將討論胡適對美國種族歧視的評論,以及美國總統排名順序,都再次證明這些私信的價值。
這個爬梳可以窺見胡適執著於中國人的立場去評估美國總統,然後回馬一槍,從美國統獨經驗反過來思考中國現況。所以這是個值得討論的議題。
二
一九一一年胡適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念書,美國總統是塔虎脫(William Taft, 1857-1930,任期1909-1913)。次年轉到文學院就讀。年底遇上總統大選,當選者是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任期1913-1921)。外國留學生首次見識美國民主政治運作,難免好奇。胡適尤其興致勃勃。日記一再記載關於總統選舉的見聞。
一九一二年十月九日日記,胡適親自去現場聽進步黨演講。這是目前所見文獻裡胡適首次觀摩美國選舉活動的記載。日記特別提到這是羅斯福的政黨。這位羅斯福指卸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在位期間1901-1909)。羅斯福因為結束日俄戰爭所做的貢獻而獲得一九○六年諾貝爾和平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一九一二年羅斯福失望於塔虎脫的保守主義風格,企圖捲土重來,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但未能成功。於是他創立了進步黨並於一九一二年參選總統。
十七日日記,胡適再去現場聽演講,並追記兩天前羅斯福演說遇刺未死的新聞,有句:「其鎮靜雄毅之態,真令人敬愛」。羅斯福遇刺發生於三天前(十四日)。羅斯福在登上講台之前遇刺。子彈貫穿鋼製眼鏡盒以及五十幾頁厚度的講稿,減慢速度,卡在胸部,沒有傷及重要器官。羅斯福不顧幕僚建議,發表演講,然後才離開現場。
日記列出三位美國總統遇刺身亡的姓名及其死亡年份。名列前茅的是林肯(Abraham Lincoln, 1865)。其他兩位是:加非爾(James A. Garfield, 1881),麥荊尼(William McKinley, 1901)。胡適很早就知道美式民主並非完美,政治人物可以成為暴力的犧牲品。
胡適的美國政治興趣牽動他的動員能力。一九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日記,胡適說自己在世界學生會餐堂發起「遊戲投票」,選舉美國總統。胡適列表記錄五十三個學生投票結果,並寫下五個值得留意的事項。第五項說中國學生拼錯候選人羅斯福的英文名字,「不可恕」,「真可恥」。
吾國人所寫票,有一人作Roosvelt,猶可原也;其一人作Roswell,則真不可恕矣。羅氏為世界一大怪傑,吾人留學是邦,乃不能舉其名,此又可見吾國人不留心覘國之事,真可恥也。
胡適日記盈篇累牘,激烈責備華人同胞的類似案例只有三十幾起,並不算多。胡適演講或行文都儘量避免人身攻擊,但常常抑制不住恨鐵不成鋼的焦慮。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致韋蓮司信說:
一個〔東方〕演說者面對美國聽眾時,〔聽眾〕所期望於他的,是泰戈爾似的信息,那就是批評譏諷物質的西方,而歌頌東方的精神文明。我可沒有這樣的信息。相反的,我寫了一篇文章(離開中國前剛發表),在這篇文章裡,我指責東方文明是完全唯物而又沒有價值的,我讚揚現代西方文明能充分滿足人類精神上的需要。誠然,我所給予東方文明的指責,比任何來自西方〔的指責〕更嚴苛,而我對西方現代文明的高度評價,也比西方人自己所說的更好。
這樣出乎常理的意見,一定會讓那些對泰戈爾這種人趨之若鶩,而又期望聽到所謂「東方」信息的人感到失望和震驚。
注意胡適政論或時評裡這個夫子自道的特徵:「出乎常理」。這種論述方式的核心哲學關乎中國思維的取恕之道:「取」作「學習」或「認可」解,「恕」作「原諒」或「忽略」解;承認對方並不完美;學習對方長處,不學對方短處。稍後我們將討論一個「出乎常理」的實例。
胡適沒有美國公民投票權,但可以參與學校的遊戲選舉。一九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日記說大學日報另有遊戲選舉,胡適投票給羅斯福。日記用琳瑯滿目的表格抄錄遊戲選舉結果。表格內容注意到粗糙但具體而微的選民區塊觀念,個別統計學生票、教員票、和女生票的各別趨勢。該則日記也兼顧紐約州長選舉。
十一月五日是美國大選日。當天日記記晚上胡適進城去觀察兩家報館即時報告各州選票結果。次日日記記下大選結果。威爾遜當選。此則日記刻意寫下美國總統雖然是全民投票,但計票時,僅以「選人票數」(現譯為「選舉人票數」)為準:「選人票數共得五百三十一,得二百六十六為過半,威氏得三百八十七,則其被選決矣。」那是沿用至今、具有爭議性的美國大選特色。全民得票總數和選舉人得票總數不一定一致。贏得全民選票半數以上的候選人未必羸得半數以上的選舉人選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幾次這種互不相容的選舉結果。胡適沒有深入分析這個奇怪制度的得失,但並未因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羅斯福)落選而表示不滿。當時胡適崇敬威爾遜。一九一六年威爾遜贏得連任。十一月九日致韋蓮司信:「選舉的結果讓我感到非常興奮」,「我希望威爾遜會當選」。稍後我將提為何後來胡適的威爾遜評價驟然下降。
胡適的動員能力促使他發起學習美國政治運作的活動。十一月七日日記,記錄自己動念成立「政治研究會」。十一月十六日日記,記在自己居室開第一次會:「會員凡十人」。除了決定研究會的運作方式之外,自己和另位同學充任第一次會議演講員,講題是:「美國議會」。可見胡適的好奇延伸至美國國會機制。接下來連續兩個星期六,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及十二月七日,日記都記錄在自己房間如期舉行會議,但無細節。
三
胡適的美國總統意見是他觀摩美國政治實際運作以及長期研習美國政治歷史的結果。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九日〈林肯序〉評論一部根據林肯生平故事改編的戲劇,公開表態敬佩林肯。然而根據最近的美國歷史研究,〈林肯序〉的事件總結有些過於簡化:
林肯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知道黑奴問題比統一問題輕得多,故他認定「維持統一」為戰爭的第一個目的。故他說:「如果不釋放奴隸,可以維持統一,我要做的;如果釋放全數的奴隸可以維持統一,我要做的;如果釋放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可以維持統一,我也要做的。我戰爭的第一個目的是要維持統一。」但他始終不曾忘記黑奴的問題。故國軍戰事順利之後,林肯知道南軍的敗挫已可決定了,他就不顧內閣的反對,毅然決然的宣布釋放黑奴的宣言。
胡適引用的「三個如果」出自林肯的一封公開信。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紐約論壇報編輯賀拉斯‧格里利發表致林肯總統的公開信,題為「兩千萬人的祈禱」,敦促林肯認識奴隸制度是戰爭根源,並且大膽解放奴隸。兩天後(二十二日)林肯回信給格里利,第三天(二十三日)發表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情資報》,明確表示當前政府的首要目標是統一全國。該信在胡適引用的「三個如果」之前有以下這句話:「我在這場鬥爭中的首要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毀奴隸制度。」林肯謹慎澄清官方立場,同時重申自己個人的願望:「無意改變我經常表達的個人願望,即讓天下所有人都能獲得自由。」
在撰寫公開回覆之前,林肯已經草擬「解放奴隸宣言」。為何林肯遲疑,沒有立即宣布「解放奴隸宣言」?可能原因是認為當時支持解放黑奴政策的民意仍不夠充分。
黑奴制度在美國行之有年。很多開國元勳包括國父華盛頓在內都是畜奴主。實施黑奴制度的名為「黑奴州」,禁止黑奴制度的叫做「自由州」。南北戰爭肇因與黑奴爭議相關:憲法是否明文禁止黑奴制度,黑奴制度是否可以施行於新近擴張的西部疆土之上,黑奴州的畜奴主是否可以進入自由州境內合法追捕逃跑的黑奴等等。南方十三個州叛變,自組新政府並發動戰爭。北方政府應戰,為了國家統一,允許隸屬北方政府、位處南北交界的四個邊境州續行黑奴制度。黑奴制度存在的主因是經濟:黑奴提供廉價的勞動服務,而且每個黑奴都是畜奴主可以自由買賣的財產。美國朝野沒有足夠的道德醒覺力量來主張:解放黑奴比國家統一更為重要。
一八六三年元旦北方政府實施「解放奴隸宣言」,最初只是戰爭手段:南方政府轄區內的黑奴被迫從事軍事後勤工作以及維持農業發展,實際在支撐南方軍力,所以解放南方黑奴乃順理成章的軍事策略。「宣言」沒有解放北方政府四個黑奴州內的黑奴。
林肯明言「宣言」是軍事策略,一方面安撫北方民心,一方面在統一全國之外,公佈了戰爭的第二個目的:解放南方政府轄區內的黑奴。一九六五年四月林肯被剌殺,五月南北戰爭結束,十二月修憲而全面解放黑奴。
胡適在中文或英文的公眾言論裡很少評擊美國內政。他的公眾言論往往雙標:要中國學習西方國家的優點,要爭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瞭解和支持。〈林肯序〉諱言林肯時代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原因誠如前引致韋蓮司私信所言:「出乎常理」,以便振聾發聵。
胡適絕非無知於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其中之一,是歧視黑人的問題。一九一五年一月十日致韋蓮司信,談美國參議院剛剛通過的移民法案對黑人(以及華人)不公:
人們一方面要公正,要「費爾波賴」(譯者按:fair play 即公平的對待),要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對他們認為的次等人,否認他們有享受這些「好事」權利的基本原則。他們要免除對比利時人的審查,而要把黑人排除在外!你看到了「有組織的洗衣同業公會」向中國洗衣工人所遞交的抗議書嗎?我真忍不住要發笑。
就個人來說,我可以原諒那些主張〔把黑人〕排除在外的人。他們並不知道在做什麼!但讓我感到痛苦的是那基本的原則。當然,我希望威爾遜總統會否決這個法案,就如塔虎脫總統(President Taft)在卸任前所做的一樣。我非常高興知道,你對這件事有興趣。
美國種種政治缺陷並沒有削弱胡適對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的熱情。同年二月五日致韋蓮司信,要韋蓮司「轉寄一份那則〈總統選舉章程〉新聞的複印件」給一位共同朋友,因為胡適要那位朋友看看這個「了不起的『選舉』制度」。胡適信文並無諷意,意在正面誇獎美國總統的選舉制度。
胡適始終未忘奴隸制度的罪行。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胡頌平記錄胡適言論如下:
我們唐宋時代的「崑崙奴」,就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黑人賣到中國作奴隸的。
歷史學家胡適認為奴隸制度不限於美國。唐宋社會也曾有與種族歧視相關的奴隸買賣活動。
(後略)
最佳賣點 : ★ 從微觀角度切入,揭示胡適其思想與人格氣度
★ 在胡適與白崇禧、蔣介石的微妙關係裡,核實他的真實想法
★ 追蹤張愛玲一生起起伏伏的胡適粉絲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