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鉛筆: 襲加詩集
| 作者 | 襲加 |
|---|---|
| 出版社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色鉛筆: 襲加詩集:下了火車故鄉和朋友便一一丟下了我而那銅的重鈴的索却依舊依依牽絆著流浪在外的我襲加為生於一九六○世代台灣中生代女詩人,曾參加「鳴蛹季刊」、「新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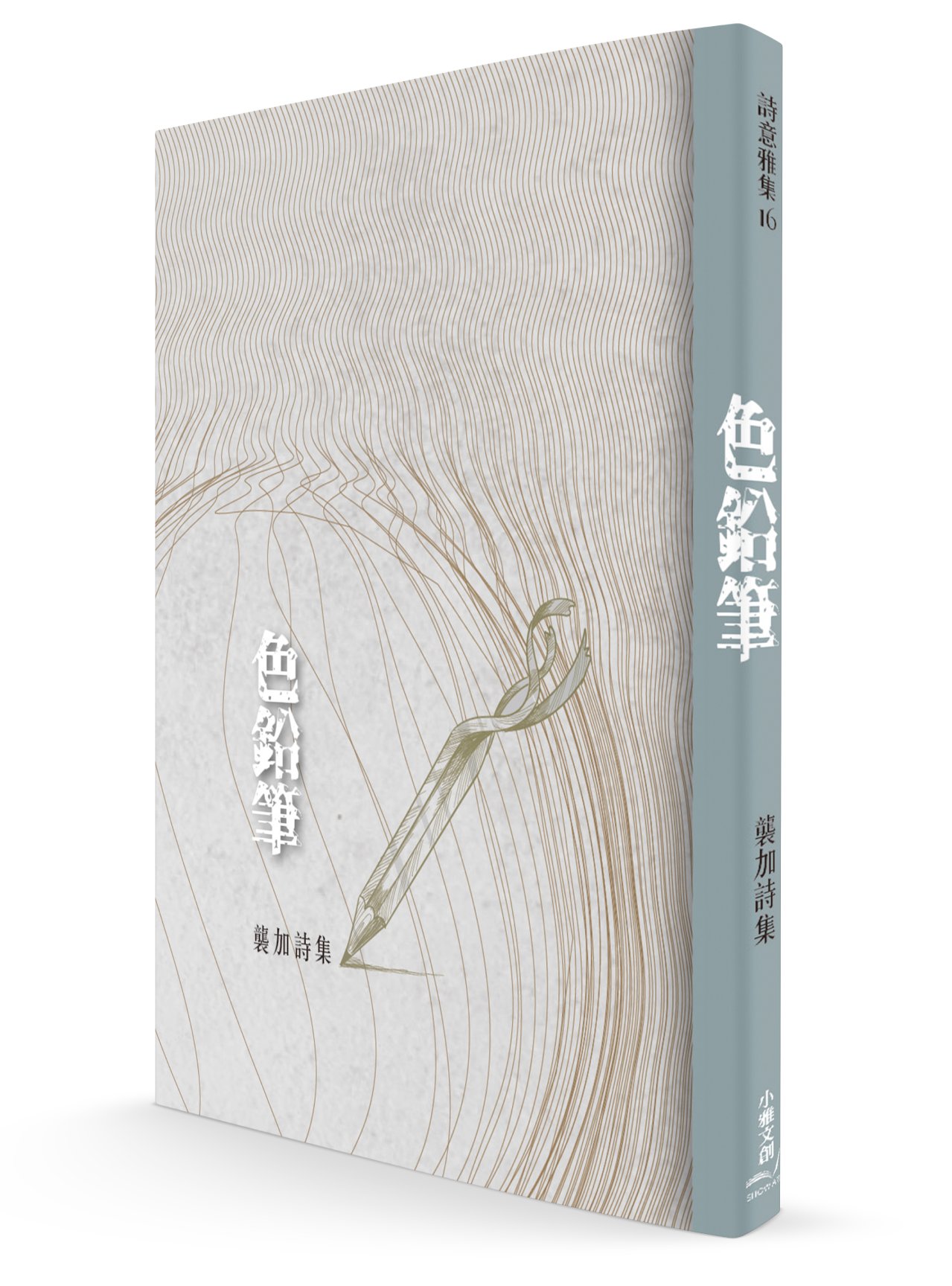
| 作者 | 襲加 |
|---|---|
| 出版社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色鉛筆: 襲加詩集:下了火車故鄉和朋友便一一丟下了我而那銅的重鈴的索却依舊依依牽絆著流浪在外的我襲加為生於一九六○世代台灣中生代女詩人,曾參加「鳴蛹季刊」、「新陸 |
內容簡介 下了火車故鄉和朋友便一一丟下了我而那銅的重鈴的索却依舊依依牽絆著流浪在外的我 襲加為生於一九六○世代台灣中生代女詩人,曾參加「鳴蛹季刊」、「新陸詩社」、「地平線詩社」、「台灣筆會」等,詩作入選《七十六年年度詩選》、《台灣1960世代詩人詩選集》。作品具有和風色彩,但又能靈巧融入台灣土地風物;除了現代詩創作,同時兼擅手繪插圖與劇場藝術。 《色鉛筆》收錄襲加1986-1996創作共57篇,其中包含5篇中日對譯及5篇日文詩作。全書計分為「隨想」、「詩想」、「青春」、「鳶飛」、「落著」等五部分。「隨想」為中日對譯作品,此外四輯為襲加青春歲月與台灣土地足跡之疊影。在台灣政治解嚴前後,青年詩人駐足於社會動盪氛圍的觀照,同時審視內心對於社會寫實的批判與藝術探索的極致視野,但也不忘從經典中取材,作為詩歌創作之養料。【本書特色】 書中部分日文詩作,為襲加首部詩集增添和風色彩。 她的詠物詩最能打動我,令我感覺真的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精準調配,且是未能從別處感受過的 ── 詩人 向明 這種詩意我稱之為生命孤獨的喜悅,是從生命靜觀與自得而來的 ── 詩人 張國治
作者介紹 毛襲加(蓮見)出生於台北。高校期間即展開文學創作、参加各詩社團體及編集活動。曾任《新陸詩刊》主編、「地平線詩社」成員。於八〇年代積極參與詩文創作及活動。曾入選《爾雅七十六年詩選》、《秋水詩選》《幼獅文藝四十年大系詩選》、《1960世代詩人詩選集》。旅日期間為演劇雜誌取材、三鷹市美術走廊作品參展、目前旅居日本。
產品目錄 毛襲加詩專輯「色鉛筆」讀後/向明想像是一張長長的椅——襲加詩集序/張國治自序:色鉛筆隨想想像以及…(中日)戲(中日)秋(中日)思念(中日)卡薩布蘭加(中日)誰が知っている(日)遠くないし近くもない(日)海の落書(日)カサブランカという名の花(日)寂しい花(日)詩想(青澀詩編‧1986~1987)訴蓮銅鈴念珠風的告白菇颱風雨泡沫在某個地方了解擱淺夜行清水寺日子思鄉戀的始末青春(1988~1990)踏青閑情走失的季節魚化石風化石影子春之雪路口川櫻秋書鳶飛(1990~1996)蚊祭之朝有霧的小路温度留言色鉛筆途中傳説去夏落著(1990~1996)潮濕的夜風春天的缺席戲劇性的憂鬱彼岸花墨鏡蓮的砂時計睡蓮花開的誘惑作家女子關於情緒芍藥的無奈游移浮遊在電車上的棉絮附錄午後輕輕響起的合聲再度溫習人生的袍子
| 書名 / | 色鉛筆: 襲加詩集 |
|---|---|
| 作者 / | 襲加 |
| 簡介 / | 色鉛筆: 襲加詩集:下了火車故鄉和朋友便一一丟下了我而那銅的重鈴的索却依舊依依牽絆著流浪在外的我襲加為生於一九六○世代台灣中生代女詩人,曾參加「鳴蛹季刊」、「新陸 |
| 出版社 /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6269780907 |
| ISBN10 / | |
| EAN / | 9786269780907 |
| 誠品26碼 / | 2682466751009 |
| 頁數 / | 136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4.8*19 |
| 級別 / | N:無 |
導讀 : 【序─向明】
毛襲加詩專輯「色鉛筆」讀後 /向明
近幾年來,由於年邁,作為一個老詩人,很多詩界酬酢的文章,總是應召去寫,推託不得,總是被問,「你不寫?誰人能寫?」於是我這詩壇剩不了幾人的孤哀子,便得承擔了下來。
自周公過世到去年的譯家宋穎豪歸天,我一路寫下來將近十人。而自去年開始,我又有一項新任務,即是為女性詩人的詩集寫序,到而今為這本毛襲加的詩集作序已是第六篇。家人說,你現在眼睛都快看不清字了,還接下那麼多幹什麼?我無言答對,只能說大家看得起我。
女詩人毛襲加屬於六○世代的女詩人,為六十年代主要出版詩集「新陸」的主要骨幹,曾任發起人和主編,也屬於「地平線詩社」的一員。祖父母輩為二戰時來台的日籍人士,她於1990年隨家人返回日本。早期作品除在台各大報刊詩刊發表外,曾入選《76年年度詩選》、《秋水詩選》及《幼獅文藝四十年文學大系》,且為日本西東京藝術家協會成員、演劇雜誌及劇場工作人員,目前虔心於佛道研究,為一虔誠的佛教徒。
六○年代詩人的出現,是繼五○年代詩人群作傳統與現代肉搏廝殺後的一群詩壇的新的生力軍。他們見證過那種互不相容的場面後,既不願作繼承的火山孝子,也不能作傳承的複製人,他們必須走出自己所尋覓的方向和具創意的目標,因之由於臭味相投或興趣相近的因緣而組織了好多不同的新興詩社,詩社同仁雖多,但也並不以同一詩風或同一定向作共同追求,而是以各別苗頭的方式作各自詩的表現。其中尤以女詩人毛襲加最勇於與傳統作切斷式的實驗,無論素材的選擇或語言的運作都勇於創新,她沒有依恃任何先聖先賢或主張派別,更不願作別人的應聲之蟲。
就以這本自1986─1996的十年間所寫的57首詩而言,十個春秋僅只有這麼多的詩,可說他對創作十分謹慎,絕不以量取勝,但如從這些詩的本質去估量,不得不令人驚嘆他作品的含金量,每首都足兩足重,不可輕視,更不可低估。她這57首全係短詩,但卻作了多種詩體的實驗,甚至還有台語歌曲或略像日語的歌謠。當然中文詩本係以抒情為主調,總離不開傷春悲秋,詠物述懷這些「思想起」的因子作反復推敲。在我的閱讀感覺中,我總覺得她的詠物詩最能打動我,令我感覺真的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精準調配,且是未能從別處感受過的精準,譬如〈銅鈴〉:
如老祖母古樸的聲音
將它放在手中
那銅的重
鈴的索
紅線結成的鈕扣
繞住了衣袖
下了火車
故鄉和朋友便一一丟下了我
而那銅的重
鈴的索
却依舊依依牽絆著
流浪在外的我
1986年.春
作者很細心也很專情,詠物述懷的詩很多,詩人都寫過,但少有人會想到童年衣服上的配飾銅鈴,那「銅的重、鈴的索」是她成長中永遠的牽掛。另一首只有七行的短詩〈菇〉,寫出野生菇類成長的艱辛,暗示任何生命的出世都賴以他者的相助:
它們僅僅擁有一朝的雲霧
它們睡在高高的山麓
千年的老樹 一株
鈎出胚芽無數
那賴以維生的泥土
竟也在它的傘下
沈思
也許曾被選入台灣《七十六年詩選》的這首〈在某個地方〉才是當年年輕的毛襲加對詩最勇敢且最大的挑戰。
我想你
在漫漫沙河裏
我就是那條黃魚
渴戀著下雨
在平原與臺地
獨自行了一個世紀
我已老了
想你
只剩那本陳舊的日記
落了漆
落了封底
落了流光與四季
輾轉難眠的琴音
我想你
就是落葉已盡
天下黃雨……
1987《葡萄園詩學季刊》九十七期
《七十六年度詩選》入選作品
這首詩被當年詩選最嚴苛的評委張漢良教授從一向主張詩要「健康明朗」的「葡萄園詩刊」中挑出來選入年度詩選本已是一個異數,他曾說他選詩「偏愛與傳統切斷的作品,無論素材的選擇或語言的運作皆然。」然而經他讀後,在「編者按語」中卻說:本詩最突出的意象為第二第三行,「在漫漫沙河裏」(的)「那條黃魚」。隨即引用古詩樂府中那首〈枯魚過河泣〉來與之比擬,並稱這首詩已成晦澀詩經典,並說清代詩人沈德潛不知其所云,註曰「漢人每有此種奇想」。乃說毛襲加的「沙河黃魚」,不教漢人專美於前。意即和樂府歌辭的〈枯魚過河泣〉同樣晦澀。按國風之詩原文為「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此詩不過是一首藉詠物來勸人不要消極頹廢的詩,意即一條枯乾的魚在看到河中流水的時候,後悔當時怎麼會離開,便寫信告訴它的同類魴魚與鰱魚,與人交往的時候應該謹慎。這種擬人化的口氣寫得古詩中已屢見不鮮,應不算晦澀難懂。毛襲加這首〈在某個地方〉中的那兩句「在漫漫沙河裏/我就是那條黃魚/渴戀著下雨」想必只是旅遊時在某個地方吃到該地的一道名菜而將之記入這首懷人詩中,因為「沙河黃魚」確實是一道在河北省太行山區沙河市的一道名菜。而這首詩的最後一句「天下黃雨」也是一個地方天候預警特色。香港天文台即有「Amber」風球的警告,告訴人即將下暴雨,Amber即黃色或琥珀色。我認為詩人在偶感時將俯拾即來的意象用在詩中,沒有這種經驗的人難免會感到不知所云,我想到現在後現代詩流行一種「陌生化」寫詩方法,可見毛襲加早就在嘗試這種新動作了。
最佳賣點 : 下了火車
故鄉和朋友便一一丟下了我
而那銅的重
鈴的索
却依舊依依牽絆著
流浪在外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