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第5版)
| 作者 | 聖嚴法師 |
|---|---|
| 出版社 |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
| 商品描述 |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第5版):「我把日記比喻作雪地的腳印,當我記錄的時候,非常地深刻而鮮明,那是我人生的經歷和生命的過程。過了之後,往往又覺得並不重要。就像人在雪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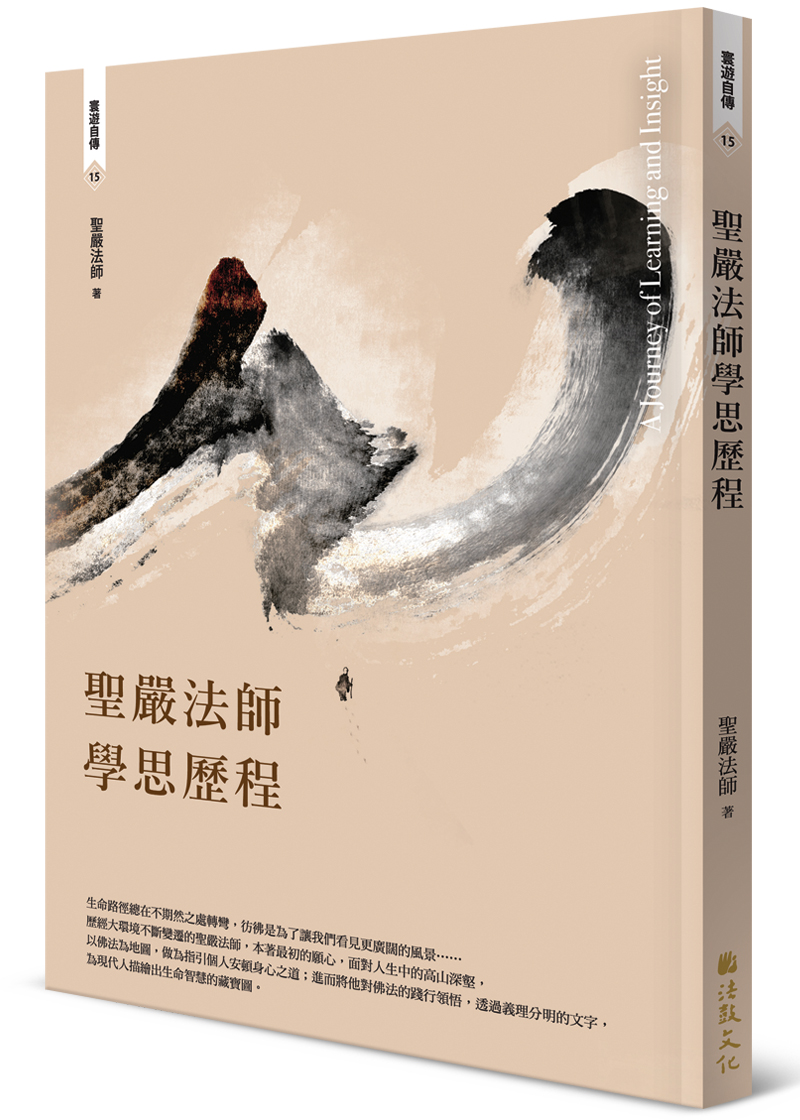
| 作者 | 聖嚴法師 |
|---|---|
| 出版社 |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
| 商品描述 |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第5版):「我把日記比喻作雪地的腳印,當我記錄的時候,非常地深刻而鮮明,那是我人生的經歷和生命的過程。過了之後,往往又覺得並不重要。就像人在雪地 |
內容簡介 「我發願,要用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介紹被大家遺忘了的佛教真義,讓我們重溫釋迦牟尼遊化人間時代的濟世本懷。就這樣,我便勤讀世間群書,尤其專攻佛典,不斷地讀書,也不斷地寫作。」 ——聖嚴法師
作者介紹 聖嚴法師(1930〜2009年)1930年生於江蘇南通,1943年於狼山出家,後因戰亂投身軍旅,十年後再次披剃出家。曾於高雄美濃閉關六年,隨後留學日本,獲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75年應邀赴美弘法。1989年創建法鼓山,並於2005年開創繼起漢傳禪佛教的「中華禪法鼓宗」。聖嚴法師是一位思想家、作家暨國際知名禪師,曾獲臺灣《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著作豐富,中、英、日文著作達百餘種,先後獲頒中山文藝獎、中山學術獎、總統文化獎及社會各界的諸多獎項。聖嚴法師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主張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推動全面教育,相繼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文理學院、僧伽大學等院校,也以豐富的禪修經驗、正信的佛法觀念和方法指導東、西方人士修行。法師著重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傳佛法,陸續提出「心靈環保」、「四種環保」、「心五四運動」、「心六倫」等社會運動,並積極推展國際弘化工作,參與國際性會談,促進宗教交流,提倡建立全球性倫理,致力世界和平。其寬闊胸襟與國際化視野,深獲海內外肯定。
產品目錄 自序童年和少年一、無憂的童年二、無憾的少年軍中的歲月一、我還是和尚二、從戎不投筆三、學佛與佛學出家與回家一、我真的出了家二、編輯和寫作三、求戒的紀錄戒律與阿含一、戒律學並不難二、適合時代的戒律三、《阿含經》是佛法的基礎宗教與歷史一、宗教戰爭二、我寫基督教三、宗教比較四、世界佛教通史留學生涯一、趕上了留學風潮二、初到東京三、碩士論文日本佛教的面面觀一、佛教的宗教活動二、不務正業的寫作目的三、日本佛教的學術會議我的博士論文一、學術與信仰二、資料蒐集的困難三、撰寫論文的發現東方和西方一、完成了博士論文二、我成了海外學人三、現實讓我改了行四、禪師.學者.教育家遊歷和寫作一、雪地留腳印二、闊別三十九年的故鄉三、我的西遊記四、我是開鑛工人站在路口看街景一、沒有目標的目標二、我的身分只有一個三、我的中心思想附錄 拿到博士的那一天
| 書名 / |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第5版) |
|---|---|
| 作者 / | 聖嚴法師 |
| 簡介 / |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第5版):「我把日記比喻作雪地的腳印,當我記錄的時候,非常地深刻而鮮明,那是我人生的經歷和生命的過程。過了之後,往往又覺得並不重要。就像人在雪地 |
| 出版社 / |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
| ISBN13 / | 9786267345412 |
| ISBN10 / | |
| EAN / | 9786267345412 |
| 誠品26碼 / | 2682855052007 |
| 頁數 / | 200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1x15x1cm |
| 級別 / | N:無 |
| 重量(g) / | 291 |
| 提供維修 / | 無 |
自序 : 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佛教僧侶,出生於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的冬天,那是江蘇省南通縣的農村,第二年的長江大水災,使我家被沖洗得一乾二淨,成為赤貧,隨著家族播遷到了長江的南岸。
我自幼瘦弱多病,九歲始入學,十三歲便失學,十四歲上山出家做和尚。我的基礎教育僅受完初小四年級,一般青少年的中學、大學時,我正在忙著做小沙彌,應赴經懺,從軍報國,但我從小便知道知識可貴,學問崇高,我會利用任何機會自修,讀到了許多書。並且以同等學歷及著作成果,考進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以六年時間,攻畢文學碩士和文學博士的學位。
從知道佛經本是用來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知識及方法開始,即慨嘆著說:「佛教的道理是那麼好,可惜知道的人是那麼少,誤解的人又那麼多。」一般人,不是把佛教世俗化,便是把佛教神鬼化,最好的,也僅把佛教學術化,其實,佛教是淨化人間的一種以智慧與慈悲為內容的宗教。
因此,我便發願,要用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介紹被大家遺忘了的佛教真義,讓我們重溫釋迦牟尼遊化人間時代的濟世本懷。就這樣,我便勤讀世間群書,尤其專攻佛典,不斷地讀書,也不斷地寫作。
我從少年時代開始作文投稿,從文藝性的到理論性的,從宗教的到神學的,從一般知識的通俗文章到專題研究的學術論文。寫了將近五十年,已出版的單行本包括中文、日文、英文的,達到四十種以上。分別在臺灣、東京、紐約、倫敦等地的書局發行,同時也有數種被譯成了義大利文、捷克文、越南文,分別在當地印行。
佛教是一種重視身體力行的宗教,由協助個人心志的堅定與安定,做到身心平衡,提昇自我,消融自我,以關懷他人,淨化社會。所以我個人讀書寫作的宗旨,是在理論觀念及實踐方法的疏通及指導。因此重視戒行的提倡、禪修的教學、知解的釐清,我的一般性的著作,大致都在這個原則下進行。我本人也被推著走向戒、定、慧三學並重的道路,故也不被局限於一般人所以為的「律師」、「禪師」、「法師」的範圍,而我自己,則恆以「法師」的身分自處,因為以佛法為師的意思最好。
由於佛教的內涵,既高明,又廣大,不論從任何一種學問的角度,來對佛教加以研究探討,都可發現佛教乃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寶藏。為了提高佛教徒的教育水準及學術地位,所以我自己必須從事佛教教育事業及佛教的學術研究。先後擔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的教授,並應邀為國立政治大學等博士班為論文指導。也創立了由教育部立案的「中華佛學研究所」,成就專門研究佛教的學術及教育人才。同時於一九九○年起,每隔二至三年主辦一次「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以「傳統佛教與現代社會」為永久主題,集合世界佛教學者之菁英,就各種專門領域的論文,探討問題,以期達成古為今用的目的。
也正因召開國際佛學會議的機緣,使我認識了執教於美國天普大學的名教授傅偉勳博士,他和他的美籍女友華珊嘉(Sandra Wawrytko)教授,不僅出席了我們的兩次國際會議,同時也給了我許多的建議,尤其兩次會議之後,均由他們兩位協助,分別將會中全部論稿,編輯成中、英兩種版本,向臺北的東大及紐約的綠林(Greenwood Press)兩大出版公司推薦出版,廣受世界學術界的重視。
如今,傅公偉勳博士,因受臺北正中書局主編鍾惠民女士之託,主持本叢書《當代學人學思歷程》的邀稿,我也何其有幸,被傅公選中,代表佛教界,也代表宗教界的學人身分,參與供稿,實在是我生平中的一項殊榮。由於工作繁忙,寄稿時未及寫序,今將清校出版,應編者之囑,故於訪問中國大陸之後,途經香港,轉往美國之際,謹補一序。
聖嚴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序於香港麗奧飯店
內文 : 二、編輯和寫作
我從軍中退伍,正式拿到的退役令,是從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而我再度出家披剃改裝的日期,則選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十二月初一日。因為我是因病而從軍中徵退,所以打算重回僧團之後,能好好休養身心。一方面藉以懺悔軍中十年來的恣意和放逸,同時抖落一身軍旅生涯的風塵,也希望鑽進東初老人所蒐集的佛教藏書堆中,飽餐一頓。
東初老人為了用文字達成宣揚佛法的目的,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鼓吹「人生佛教」的建立,所以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便集合了幾位志同道合的佛教青年,發行了一份月刊,就叫作《人生》,前後經過十多位主編的耕耘。當我投到東初老人座下之時,正好當時的《人生》主編提出了請辭的要求,我也就順理成章地,由該刊作者的身分,一變而成了它的主編。直到我往臺灣南部山中禁足為止,前後為它服務了兩年。
在這段時日之中,我的身體健康,始終沒有好過,經過氣虛無力、頭昏、氣悶、手軟、腳冷、食欲不振、腸胃失控。很多人說,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之前,就遇到種種的魔障,我這一點小毛小病算不了什麼!好在有一位前輩的長老,介紹了一位漢醫給我診斷之後,開了兩付藥膏,繼續服用了半年,身體才算從奄奄一息之中漸漸好轉過來。
但是,那一個階段,佛教界能夠為《人生》月刊提供稿件的不多,而且沒有稿酬,開發稿源相當困難,我真佩服前任的幾位主編,真是神通廣大,竟然能夠每月按期出版。因此我向東初老人請教箇中祕訣,他的回答是:「有什麼祕訣啊!沒有人寫自己動手。每天只要寫一篇,一個月就有三十篇了,然後,每篇都給它一個作者的筆名就成了。佛法那麼深廣,人間的問題是那麼地繁複,每天從所聽、所聞、所讀、所觸、所思之中,有寫不完的文章,大好的題材,俯拾即是!」
因此,我就向他請求供稿,他的回答更妙:「不會寫文章的人來編《人生》,我沒有辦法,只好寫嘍!如今你是很會寫作的人,而且我也老了,當然是你自己來寫。」
就這樣,從社論到編後記,我只好埋頭苦幹了。幸而,還有兩位長期供稿的居士,為我們的《人生》消化了若干的篇幅。他們的文章,雖然都是長篇大論,充滿了思想學問,也頗深入,但對於一般的讀者大概都略顯深澀。好在每期出版的數量不多,只有一千份上下,而且總有一、兩篇富有可讀性的文章。特別是偶爾由東初老人口述,而我筆錄成文的社論,經常是「擲地有聲」之作。
我為《人生》向各處邀稿、徵稿、求稿,佛教內外的幾家刊物也向我逼債,這使我除了為《人生》編校和撰稿,也得應酬外邊向我索稿的壓力,在健康狀況如此衰弱的情形下,實在感到寫文章是一樁大苦事。尤其,我編的這一份刊物,它的編輯部、發行部和財務部的辦公室,都在我的斗室裡。工作人員除了我還是我,常常為了版面的調整、新聞的穿插,乃至於一、兩個字的更正,必須親自從老北投火車站到萬華的一個矮小局促的印刷廠,跟排字工人打交道。雖然他們對我的態度都很好,可是每次出版,總要往印刷廠跑上五、六次,也就不是什麼好玩的事了。而據我所知,當時不管是佛教內或佛教外的文化界,大多數是在如此的情況下,把書刊一本本地出版了,送到讀者手上的。可見,文化工作的從業人員,應該具備如此的奉獻精神。
在那段時間裡,我也設法多讀一些大部頭的經論,利用編寫工作之餘,害病求醫之暇,讀完了一部八十卷的《華嚴經》、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經》,一百卷的《大智度論》則只看了二十多卷,同時除了早晚課誦及禪坐之外,我還每天禮拜一炷香的「大悲懺」。使得病弱的身心安住在信、解、行的三個原則之中。
三、求戒的紀錄
一九六一年農曆八月,我在基隆八堵的海會寺,依道源能信長老(西元一九○○─一九八八年)座下,求受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護國千佛大戒。佛教稱受戒的道場為「懺悔堂」,我本希望在戒場之中,除了努力學習戒律之外,好好懺悔,多拜些佛。可是,進入戒場第一天,就被選為沙彌首,等於現在一般學校訓練班集訓之時的學員長,要為全體的新戒學員服務。
接著戒場的書記真華法師為了提拔我,很慈悲地向道源長老推薦我擔任《戒壇日記》的執筆工作。他們的理由是:1.我從小出家,本來就是和尚,來為新戒大眾服務,一定能夠得心應手,如理如法。2.我已經是個著書立說、擔任編輯的佛教界作家,應該要為這一次的傳戒大會留下寫實的紀錄,由我執筆寫《戒壇日記》,是最適當的人選。
如此一來,我就被擺布得團團轉,凡是課堂以及各種的活動,我都必須參加,而且先到後退,照顧全場,留心全程。早上要起得早,晚上要睡得遲,白天沒得休息。凡是課堂,我還不能像某些戒兄那樣偷閒打盹,否則不僅要受戒師的罵,還要挨戒兄大眾的怨。真如俗話所說「出風頭的椽子先爛」,十手所指,十目所視,暴露在大眾的眼光下,無所遁形。
不過,這兩個身分與職務,鍛鍊了我的體魄、信心,以及待人、處事的能力,同時,也讓我提高學習的要求。到受完戒為止,經過四十天的訓練,在一百多位同戒之中,獲得心得最多的,可能也是我。我把戒場的各項規則、活動的次第,不但記在腦中,也寫進了日記。把每一位戒師的開示,以及他們對於戒律內容的解釋,例如《毘尼日用切要》、《四分律比丘戒本》、《梵網經菩薩戒本》的內容,我都把它們扼要地記錄下來。到最後就完成了一冊將近十三萬字的《戒壇日記》,交給戒場「海會寺」印行出版了,供給在那場戒期之中的相關人員,做為永久的紀念和參考。直到現在,當我翻閱那本日記之時,還有歷歷如新的感覺。
臨出堂下山之前,我們的教授和尚白聖長老,知道我在戒期之中,備極辛勞,同時也未必能夠面面俱到,偶爾會引來一些指責和怨言,所以向大眾給我慰勉,而說了四句話:「受戒切莫當班頭,生活行動不自由,戒師罵來戒兄恨,含著眼淚向內流。」
長老能夠對我這樣的慈悲與愛護,當然相當感激,可是我對於戒場所見所聞,並不感到滿意,因為戒師們多半只知道照本宣科,古人怎麼說,他們也怎麼說,過去人怎麼做,他們也照著做,戒子們聽不懂的,他們可能也不懂,特別是戒律學中的名詞,往往是用梵文的音譯,在漢地的中國文化中,沒有那些東西,沒有發生過的事,的確無法用相當的中文來表達,再加上中國的古人,解釋戒律學中的種種問題,都用極為間接的文字來說的。現代人,如果缺少古來學者們那樣的學識基礎和文化背景,看起來還是不知所云。
在受戒場中,新戒都不會發問,戒師說什麼就聽什麼,遇到許多不懂和不通處,他們還以為應該就是這樣子的罷!我每每不便在課堂發問,而在課後請教戒師。倒是道源長老,不只一次地對大眾說:「戒律深奧難懂,所以律宗弘揚不易,希望諸位新戒菩薩發大弘願,親自去看律藏,加以研究發揚。」我當時發現,佛教的戒律,不管是出家戒或在家戒、聲聞戒或菩薩戒,不僅僅是在義理方面需要下大工夫做一番釐清,就是在對今日世界、現實社會的因應而言,也需要做大幅度的審視。否則,等於執死方而應變病。徒見重視戒律之名,而缺少淨化人心、淨化社會之實。這也是使我在受完戒之後,便去全力地背誦《四分律比丘戒本》以及《梵網經菩薩戒本》的原因。這也成了我不久之後去專攻律藏的動機,希望自己先懂,再讓人家去懂,先自己去用,再讓人家來用。(摘錄)
最佳賣點 : 生命路徑總在不期然之處轉彎
彷彿為了讓我們看見更廣闊的風景
得獎紀錄
.中山文藝創作獎
.行政院圖書金鼎獎
面對人生中的高山深壑,法師以佛法為地圖來安頓身心,進而將對佛法的踐行領悟,透過義理分明的文字,為我們描繪出生命智慧的藏寶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