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戰爭史
| 作者 | 顧誠 |
|---|---|
| 出版社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明末農民戰爭史:【核心賣點】本書是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的標誌性著作,是《南明史》的“姊妹篇”,兩書並稱明末清初史學研究的“雙璧”。【一句話推介】本書重塑了明末農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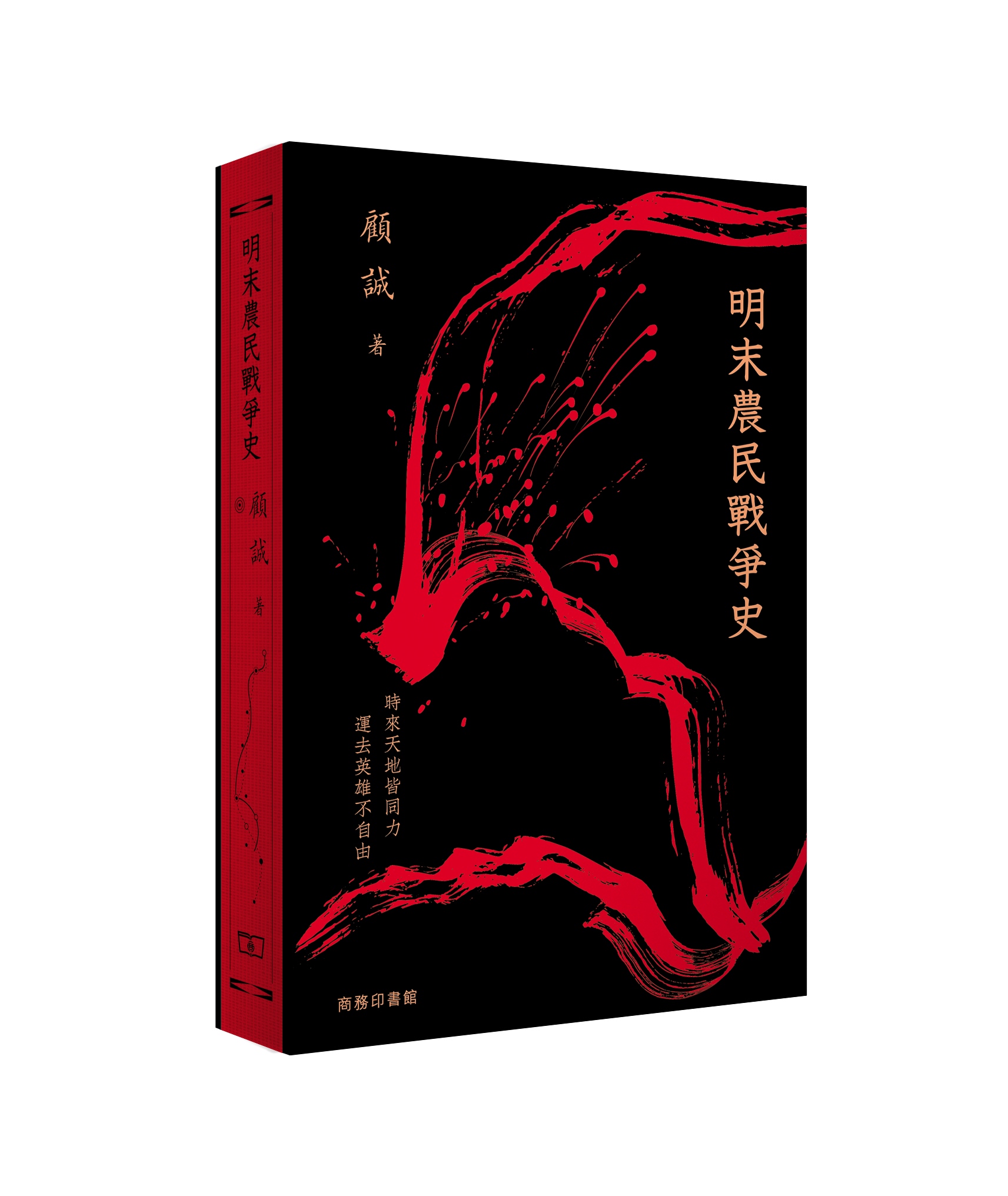
| 作者 | 顧誠 |
|---|---|
| 出版社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明末農民戰爭史:【核心賣點】本書是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的標誌性著作,是《南明史》的“姊妹篇”,兩書並稱明末清初史學研究的“雙璧”。【一句話推介】本書重塑了明末農民 |
內容簡介 【核心賣點】本書是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的標誌性著作,是《南明史》的“姊妹篇”,兩書並稱明末清初史學研究的“雙璧”。【一句話推介】本書重塑了明末農民戰爭的歷史敍事。【內容簡介】全書共15章,32萬字,從明末農民戰爭爆發,敍述至李自成大順政權和張獻忠大西政權失敗。作者在書中屢有不刊之論推出,尤其對幾成定論的所謂“流寇主義”、“起義軍封建化”,以及“李自成敗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歷史問題,均有精深獨到的見解。另對李岩其人的證偽,對“滎陽大會”的解構等,均不獨謹嚴,亦頗具趣味。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顧誠(1934—2003年),江西南昌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明清史專家。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顧問,中國明史學會常務理事。有《李岩質疑》等多篇學術論文,著有《明末農民戰爭史》《南明史》等專著,均為明清史研究領域最高學術水平的著作。
產品目錄 目錄第一章 明末農民戰爭的背景 第一節 明後期政治的腐敗第二節 土地高度集中第三節 國家財政破產和賦稅加派第四節 水利失修和災荒頻仍第五節 軍制的敗壞第六節 裁驛遞第七節 農民大起義的前奏第二章 明末農民戰爭的爆發 第一節 陝西農民首建義旗第二節 勤王兵的嘩變第三節 張獻忠、李自成參加起義第四節 起義早期的特點第三章 起義初期明政府的對策和義軍主力轉入山西 第一節 楊鶴主撫政策的失敗第二節 起義軍在山西的發展第三節 陝西起義軍的堅持鬥爭第四節 起義軍的詐降和突破黃河天險第四章 起義中期的千里轉戰第一節 向中原進軍第二節 起義軍的漢中突圍第三節 起義軍的大舉入豫和所謂“滎陽大會”第四節 起義軍攻克鳳陽第五節 崇禎八年起義軍在陝西的勝利第六節 明廷的剿撫並用和高迎祥的犧牲第七節 李自成等部進軍四川第五章 明末農民戰爭一度轉入低潮第一節 明廷十面張網和增兵增餉第二節 李自成等部連遭挫折第三節 張獻忠、羅汝才部的“受撫”第四節 穀城、房縣“受撫”的透視第六章 張獻忠、羅汝才重舉義旗和楊嗣昌督師的慘敗 第一節 剿餉延期和加派練餉第二節 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再次起義第三節 楊嗣昌奉命督師第四節 瑪瑙山之役第五節 張獻忠、羅汝才部轉戰四川第七章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大發展第一節 李自成起義軍挺進河南第二節 李自成起義軍攻克洛陽第三節 李自成起義軍首攻開封和項城戰役第四節 李自成、羅汝才聯軍二攻開封第五節 襄城之役和三攻開封第六節 侯恂督師和起義軍一敗孫傳庭第七節 革、左五營同李自成部義軍聯合作戰和攻克汝寧第八節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凱歌行進的原因第八章 李自成起義軍南下湖廣和襄陽政權的建立第一節 李自成等部南下湖廣第二節 起義軍走向統一和“羅、賀事件”第三節 襄陽政權的建立第九章 張獻忠起義軍進軍湖廣、江西第一節 張獻忠部轉戰豫皖第二節 張獻忠部佔領武昌第三節 張獻忠部南下湘贛第四節 大西政權在湘贛的設施第十章 孫傳庭部的覆滅和李自成西安建國 第一節 吳甡督師之議第二節 孫傳庭的出關和覆滅第三節 李自成起義軍佔領西安第四節 李自成起義軍收取三邊第五節 建國大順第六節 大順軍渡河東征和永昌元年詔書第七節 寧武之戰和勢如破竹的進軍第八節 大順軍的南線作戰第十一章 明廷在覆滅前的掙扎 第一節 李建泰奉命督師第二節 調吳三桂部進關之議第三節 南遷之議第四節 沒頂之際的幾根稻草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關之戰第一節 大順軍攻克北京第二節 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的措施第三節 山海關戰役第四節 大順軍放棄北京第十三章 大順政權的失敗 第一節 明朝官紳的叛亂第二節 李自成返回西安時的部署第三節 清軍佔領山西第四節 懷慶之役和清軍佔領西安第五節 西北地區明降官降將的叛亂和該地區大順政權的崩潰第六節 李自成的犧牲和大順政權的失敗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第一節 大西軍入川第二節 張獻忠在四川建國第三節 官紳地主的叛亂和大西政權的加緊鎮壓第四節 張獻忠犧牲及大西政權失敗的原因第十五章 弘光政權的覆亡和南方的階級鬥爭形勢 第一節 弘光朝廷“借虜平寇”政策的破產第二節 南方農民反對封建統治的鬥爭的特點第三節 南方的佃變第四節 南方的奴變附錄 說明 表一 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表表二 大西政權地方官員表 表三 山海關戰役後三個月內官紳叛亂情況表
| 書名 / | 明末農民戰爭史 |
|---|---|
| 作者 / | 顧誠 |
| 簡介 / | 明末農民戰爭史:【核心賣點】本書是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的標誌性著作,是《南明史》的“姊妹篇”,兩書並稱明末清初史學研究的“雙璧”。【一句話推介】本書重塑了明末農民 |
| 出版社 /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620706554 |
| ISBN10 / | |
| EAN / | 9789620706554 |
| 誠品26碼 / | 2683037610008 |
| 頁數 / | 512 |
| 裝訂 / | H:精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3.4x16 |
| 級別 / | N:無 |
自序 : 我的治學經歷 (代自序)
顧 誠
1957年9月,我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比較努力,從圖書館借閱的書籍既雜且多,就是不愛記筆記,考試時兩門主課往往得3分,還捱過批評。自己心裏不服,下個學期硬背一通,考了兩個5分。我並不覺得高興,只是證明要拿個5分不難,真正多讀點書才有點實際知識。1958年起掀起了“大躍進”運動,勞動多,政治活動多,上課徒具形式。1959年暑假,我們班為了勤工儉學,承擔了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現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清代乾隆朝一部分檔案的任務,地點就在我校工會俱樂部,檔案用汽車拉來,由檔案部的黃先生指導我們進行分類,然後按時間順序包裹。我們整理的是乾隆後期的檔案,其中有大量乾嘉白蓮教起義的材料和四川、貴州、湖南三省交界地區的苗民起義的材料。大約一個多月基本完成了這項工作,同學們又去“密雲鋼鐵公社”勞動,我剛到工地才住一天就接到通知讓我回校進行科研,在國慶以前完成,向黨獻禮。我趕回學校,心想要在一個月之內完成一個項目,比較可行的是向明清檔案部借閱全部苗民起義的檔案,再參考《苗防備覽》和相關的地方志,夜以繼日地全力以赴,力爭按期完成;當時還有患肺結核已愈正療養的兩位同學王君、張光華幫着謄清。那時年輕力壯,幹勁十足,腦筋也好使,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一本七萬字的《乾嘉年間苗民起義史稿》,如期在“十一”前夕把謄清稿交到系裏獻禮。國慶成果展覽之後,這部稿子就無影無蹤了。當時“政治覺悟”高,沒有甚麼“私心雜念”,連改寫得很亂的草稿在任務完成後也當成廢紙扔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著書立說”的經過。多年以後每想起來總覺得是件憾事,史稿內引用了大量當時無人閱過的第一手材料——原始檔案,參考的書雖然不多,畢竟經過自己的一番排比研究,文字表達也頗費功夫,即便不能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留着做個紀念和參考也是好的。
1960年,中央組織編寫全國高校統編教材,從各高等學校抽調教師和高年級學生參加編寫。世界現代史教材由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河北北京師範學院(現河北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人員組成。編寫組的大組長由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擔任,其他領導成員有人大的楊田、北京師大的王紹岳、北京師院的康泠等人。我當時還是三年級的學生,也被抽調到這個組參與編寫。說來可笑,世界現代史是四年級上的課,我還沒學過竟然來編寫全國高校的通用教材。這個編寫組在人大鐵獅子胡同的校舍待了一個多月,後來又搬到北京大學的十三公寓(那時剛建成)住了將近半年,北大校長陸平同志和哲學系主任馮定同志都給我們講過形式和編寫的指導性意見。剛過冬天,編寫組又遷到二里溝市委黨校的四號樓繼續工作,直到完稿結束工作,那時已經接近1961年暑假。參加世界現代史編寫工作對我後來大半生所走的道路可能起了關鍵性作用,前面講過,我在年級(三個班,同學有一百多人)裏並不是成績一貫名列前茅,在編寫組的後期,我的學識和寫作才能才表現出來。我成了一個小組的組長,組員四人差不多都是教研室主任,如北大王力等人,資歷比我這個學生要強得多,但他們推我當組長,寫的稿子交給我修改後再上交大組,有時改動得還相當大。我記得工作後期,編寫組從吉林師範大學借調了陳本善同志來,他是該校世界現代史教研室主任,看不起我這個學生組長,他把他寫的稿子交給我,直截了當地說:“我的稿子,你一個字也不能改!”讀過他的稿子,我覺得不能用,又不能違背這位老師的囑咐,只好自己動手另寫一章,連同他寫的那一章草稿上交大組審閱,結果大組決定採用我寫的稿子。由於在編寫組的表現,就有人認為我是個可培養的人才。人大的楊田同志私下找我談話,要我畢業後到人大歷史系去工作。週末回校就對總支書記馮效南同志談了,她立即告訴我系裏已經決定留我在系裏工作,叮囑我要嚴加保密,並且以服從組織分配為藉口婉言謝絕人大的好意。到畢業前夕我回到系裏,雖然還是掛着學生的白校徽,可是卻在總支辦公室參與同年級同學的畢業分配,這點是同學們都不知道的。
1961年開學後,我卻被系主任白壽彝先生要去,跟他搞中國史學史,那時我大約每個月到西單武功衛白先生家聽取他的指示並彙報治學情況。當時一起的有趙光賢、郭澎和另一位同事,他的姓名我現在已經記不得了。白先生讓我以明代史學史為重點。經過很短時間的摸索之後,確定第一個研究對象是明中後期著名的史學家王世貞,我大約用了三個月時間仔細閱讀了王世貞的史學著作,寫出了一篇題為《王世貞的史學》的文章,白先生看後似乎不太滿意,他寫了個批語:“王世貞先放下,繼續讀書。”這篇稿子直到二十年後才在《明史研究論叢》上發表出來,自然並不完全符合原貌。白先生分配給我的另一項任務是《明史》的編撰過程,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王鴻緒的《橫雲山人史稿》同欽定《明史》逐字逐句地對讀,凡遇不同的地方都抄出來,列成了對照表,有五十多張大紙;另外還寫出了一篇比較長的論文稿。我把文稿和作為根據的對照表一起交給白先生,白先生究竟仔細看了沒有,我不知道。過了不久,白先生宣佈史學史組改組,他同我們一起到北海公園(也可能是中山公園,記不清了)照了合影,原來的組就散了,郭澎回去教中國古代史,我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我們離開後,白先生要了楊燕起、李起民兩人去,工作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讓他們埋頭研讀《史記》,當時我們還有點羨慕呢!至於我寫的關於明史的稿子和對照表,問過白先生,他說全部交給趙貞信先生了。我和趙貞信先生很不熟悉,他又不住在校內,不便去問;“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更是不用提了。回想起來,花了半年時間(那時正是“三面紅旗”導致的生活極端困難時期,人人吃不飽,許多同學都浮腫。我們儘管飢腸轆轆,可是精神上沒有壓力,不搞政治運動,不用去幹重體力勞動,有時間專心讀書了)認真校讀兩部書的結果不能加工發表,成果付諸東流,實在是件可惜的事。但也不能說工夫白費,經過這次校讀,明代歷史的基本線索和重大事件多少留下個印象,為以後治明清史打下了基礎。
我離開史學史組以後,又回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其間兩度擔任班主任(59級、63級),那時當班主任(又稱輔導員)工作非常繁忙,和同學談話有時直到熄燈時分還安排不過來,至於下鄉勞動自然是和同學一道。比如1965年下學期到1966年6月,整整一年就是帶63級同學到山西長治參加“四清”,除搞運動外還要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等到回校時已經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北京各高校的時候了。這裏還有個插曲要講一下,1965年10月我還在長治鄉下時,接到系裏來信通知,我已同系裏另外三位同志調到學校新成立的外國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工作,編制上已不屬歷史系。1966年6月回到學校,“革命師生”正在造反,揪鬥校系領導人,五個年級的輔導員也多數被學生批鬥。我是同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一道下鄉“四清”的,回校後自己斟酌以到歷史系參加運動為好,如去外研所有躲避“史三”同學之嫌。所以約有半年時間工資在外研所領,卻在歷史系參加運動。幸好我和“史三”同學們關係不錯,除了一張督促我積極參加運動的大字報以外,沒有受到任何衝擊。我只是參加歷史系教師的運動,組織了一個保守的“戰鬥隊”,響噹噹的造反派“師大井岡山”紅衛兵得勢以後,我們的那個“老保”組織自動瓦解,我也就到外研所去了。由於自己是“老保”,只能跟着掌權的造反派抄寫大字報,跑跑腿,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隨波逐流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我心中暗想,連黨章規定的接班人林彪都成了叛徒,看來“文化大革命”不可信,不能再跟着跑了。從此對運動消極應付,私下裏重新閱讀明清史書籍。“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曾迫於壓力把抄錄的史料和一些史籍(那時藏書並不多)處理掉,且留了個心眼把農民起義的史料收藏起來,即便被人發覺也可以振振有詞地說這是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紅線,應當保存。當時圖書館和系資料室都不開放,我私下找到管資料室的馬國靖先生請她幫忙,她一口答應,要我在下午近六時利用人們去食堂吃飯的機會到資料室門前,她給我取出我要借的古籍,使我能在晚上和週末仔細閱讀。這在當時是要冒相當風險的,我至今還對這位善良的先生心懷感激之情。當然,歷史系資料室的藏書有限,遠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我就利用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到南京去看書。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在頤和路12號,離我五哥家極近,但當時也和其他圖書館一樣不開放。我請五哥幫忙,他找了當時任職於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一位老朋友寫了介紹信,說工作需要查閱古籍,我就冒名頂替地在南京圖書館讀了不少書,大約去過三次,每次近一個月,抄了許多較罕見的史籍和地方志中的史料;可能較晚一些時間,我還通過熟人在南京大學圖書館讀了一些書,其中就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編撰的河南《杞縣志》孤本,這部書裏的《李公子辨》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對於我後來研究李岩問題很有幫助。
總的來說,我從1971年冬天起開始偷偷摸摸地持續不斷鑽研明末農民戰爭的史事,比起其他大多數人從1977年才重新開始治學,在時間上多爭取了大約五年。這是值得慶幸的事。
1977年10月,在我的堅持下,外研所讓我回到歷史系。系總支書記景存玉同志要我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去,理由是該室缺人,正好我又懂英語(其實我的英語水平只能勉強閱讀)。我說:“我的專業是明清史,如果系裏一定要我去世界現代史教研室,那我還不如留在外研所。”她見我態度堅決,就笑着說:“你就說你的興趣是明清史,不要說專業。”意思是我並沒有專業,只是勉強同意我到中古史教研室工作。為了證明自己在明清史方面有一點基礎,我立即動手把我在李岩問題上探討的結果寫成文章,這就是《李岩質疑》。1977年年底,我把稿子送到《歷史研究》編輯部,該文發表在1978年5月號上。當時刊物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文章發表後反應頗為強烈,支持的人不少,反對者也甚多。因為歷來都認為李岩確有其人(只是清初河南文人鄭廉在《豫變紀略》中以親身見聞指出李岩為烏有先生;康熙《杞縣志》和康熙《開封府志》裏收有《李公子辨》一文堅決否認杞縣有李岩。但是即使在清初各種更加著名的相關史籍裏還是有多少不等的李岩“事跡”,可以說這是當時人的共識。到乾隆四年欽定《明史》頒佈以後,李岩的“事跡”被採入李自成傳,遂成定論。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以大量篇幅敍述李岩,且給以高度評價;這篇文章在延安被定為“整風文獻”,解放區各級幹部都得認真學習,李岩的故事得到了空前的傳佈)。1964—1965年,學術界曾就李岩評價問題展開過討論,一時頗為熱烈,發表的文章不少,一派認為李岩是李自成起義軍中正確路線的代表,另一派則認為李岩是地主階級分子,在起義軍中起了破壞作用;自然也有些折中的意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都發表了綜合報道,後來在香港結集出版,書名就叫《李岩評價問題討論集》。我的文章基本論點正是根本否定李自成起義軍中有過李岩這個人物,所謂的評價自然就毫無意義。我發表這樣的驚人之文,絕不是聳人聽聞,也不是僅據鄭廉和《杞縣志》的舊說;而是花費了大量時間查閱過有關史料,其中僅地方志就有千部以上,何況還有時人文集、檔案等資料;數量相當龐大,可是就是沒有一條能證明李岩存在的確切材料。1984年出版的《明末農民戰爭史》的附表前面有一段話:“過去在一篇關於李岩的拙稿中談到,我們現在對許多職位很低的大順政權文武官員都查得了可信的史料,為甚麼名聲僅次於李自成的‘核心人物李岩’卻始終未能找到一條真實材料?我願意藉此機會建議對李岩問題關心的同志多做一些史料的發掘和鑒別工作,不要在不分真偽的‘有史料依據’的水平上停滯不前。”現在,又過了十幾年,查閱的書更多,仍然沒有發現李岩的可靠材料。請同行學者想想,按通常的說法,李岩是崇禎十三年(1640)參加起義的,這正是李自成起義大發展時期,起義軍先後攻克的大城市就有洛陽、襄陽、西安、太原、大同、北京等地,李岩既是“制將軍”又是主要謀士,當時各方面的人都密切關注李自成起義軍的情況,再說李自成軍在北京停留了四十三天,在京的明朝官員就有兩千多人,其他識字的人還多得很,為甚麼就沒有人見過李岩並留下哪怕一條記載呢?至於野史中出現的大量李岩“事跡”,我在《李岩質疑》一文裏已經做了論證,是由小說的虛構情節混入史籍的。明朝後期黨爭和紳衿紛鬥非常激烈,編寫小說和傳奇作為鬥爭手段是常見的事,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清初。由“葫蘆道人”“懶道人”編寫的《剿闖小史》在1644年秋天就已經在江南書店內發賣了,這時弘光帝已經即位,所以書中寄希望於“弘光中興”,而且李自成也還在世,小說的編者除了收集一些廣為人知的大事外,還杜撰了不少情節以增加趣味並彌補自己見聞的不足,其中就包括了有關李岩的創作。入清以後,《剿闖小史》曾多次改名,如《定鼎奇聞》《新世宏勳》。康熙十年(1671)計六奇編成《明季北略》,其第二十三卷(補遺)就是以《新世宏勳》為底本刪改而成。此後人們以《明季北略》為史書加以引用,並未想到其中竟有小說家之虛構;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大量採用了《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以至李岩其人其事廣為傳播。1978年5月《李岩質疑》發表後,7月1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王賡武教授夫婦和美國耶魯大學鄭培凱先生來我校訪問,由何兹全教授和我接待。當時,我很少說話,到上午快結束的時候,鄭先生問我:“顧先生發表了甚麼文章?”我回答:“最近在《歷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他突然想起來問道:“是不是《李岩質疑》?”我說:“是的。”他回到美國後立即告訴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Buffalo)分校的戴福士教授(Prof.Des Forges)。戴福士教授研究的重點是河南省(史學界的一種分區研究方法),他閱讀過鄭廉《豫變紀略》等書後也對李岩的真實性表示懷疑,1977年冬曾來過中國訪問,找到上海的楊寬教授等人交換意見,可是這些人談的都是對李岩的評價,同他的本意不一致。於是,他回國後自己繼續研究,正在這時他因鄭培凱的推薦讀了我的《李岩質疑》,立即來信表示同意。不久,他就寄來了自己的長篇打字文稿The Puzzle of Li-Yen(《李岩之謎》),此文後來在美國刊物上發表。1978年年底,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召開了“文化大革命”後第一次史學界學術討論會,即中國農民戰爭史討論會,儘管條件較差,到會的各地代表卻非常踴躍。正是在這次會上認識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謝國楨、王戎笙、白鋼等八位先生,華東師大的謝天佑、王家範,蘭州大學的趙儷生,鄭州大學的高敏,山東大學的孫祚民,陝西師大的孫達人,河北大學的漆俠,當時在上海師大的王春瑜,還有很多同行,記不清了。會上討論得非常激烈,主要是圍繞着一些觀點爭論不休,自然是各持己見,得不出甚麼結論。會議發起單位華東師大還組織與會者在上海參觀了黨的“一大”會址、豫園,到蘇州遊覽了拙政園、虎丘、寒山寺;會議結束時成立了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選舉了第一屆理事會,我也當選為理事。在1980年代,農民戰爭史研究還處於高潮,兩年一次的年會頗受史學界的重視,由謝天佑、王家範主編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輯刊》和白鋼主編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論叢》不僅能順利出版,而且有相當影響。在這兩種刊物上,我發表了一批有關明末農民戰爭史的專題研究文章,澄清了不少問題。到1982年冬終於寫完了專著《明末農民戰爭史》,1984年該書才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印量達一萬六千冊,早已脫銷。
在明末農民戰爭史的研究上,取得的進展主要為:
一、明末農民大起義的背景。對明朝末年階級矛盾的極度激化,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農民除了奮起反抗別無生路,引用的典型史料頗能說明問題,從而論證了起義的正義性。
二、李自成早年當過放羊娃,參加起義前是米脂縣銀(圁)川驛驛卒(馬夫)。吳偉業《綏寇紀略》和《明史》等書說他同姪兒李過一道投入明朝官軍,後來在金縣起義的記載完全不可靠(參見《李自成起事考》)。
三、李自成參加起義後是在王左掛部下,編為八隊,綽號“闖將”。王左掛投降後,李自成即成為一支獨立的隊伍,人稱“八隊”。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種錯覺,以為“闖將”是“闖王”高迎祥部下的一員將。其實,“闖王”“闖將”“八大王”“闖世王”“點燈子”“鄉里人”等都只是參加起義的人為了避免暴露真實姓名以連累家庭和親屬而隨口起的綽號,一般不存在從屬關係。李自成也從來不是高迎祥的部將。根據明末殘檔,崇禎五年(1632)冬李自成(闖將)已在山西的各支起義軍中名列前茅,為明廷所關注。許多書上說,崇禎九年(1636)高迎祥被俘犧牲後李自成才“繼為闖王”,根本不對。據我的查考,李自成的綽號只有“闖將”,崇禎十五年(1642)為各部首領推舉為“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將軍”,次年在襄陽又被推舉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他自己並沒有稱過“闖王”;“闖王”的稱呼來自百姓。
四、李岩的問題,已如上述,不贅。
五、滎陽大會的問題。在許多史籍中都記載了所謂“滎陽大會”,據說崇禎八年(1635)起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會集於河南滎陽,決定“分兵定向”;李自成還在會上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講話,為許多史著甚至通俗讀物所引用。其實,這個重大事件完全不可靠,它出自吳偉業的《綏寇紀略》,卻同許多第一手材料相抵觸。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浙江方福仁先生就撰文首先指出“滎陽大會”純屬虛構(方文大概發表在《光明日報》上)。我完全贊同方福仁先生的論斷,並用當時任職兵部尚書張鳳翼的《樞政錄》、河南巡撫玄默的《剿賊圖記》、河南巡按金光宸的《兩河封事》以及清初《滎陽縣志》等第一手材料加以證實。
六、李自成起義軍大發展的經過。
七、李自成建立政權的經過:崇禎十五年冬在河南各地建立地方政權;十六年春建立襄陽政權(開始有中央機構);十七年(1644,即大順永昌元年)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同年大順軍佔領整個黃河流域(包括北京在內),從西北到山東沿海都派設了各級地方官員。
八、不同意所謂的李闖式“流寇主義”。
九、不同意把大順軍失敗歸因為進入北京後的“腐化變質,追求享樂”。
十、支持並補充論證了李自成犧牲於湖北省通山縣九宮山麓,認為李自成出家的說法根本不可信。
以上詳細論點見《明末農民戰爭史》及相關論文。
最佳賣點 : 本書重塑了明末農民戰爭的歷史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