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 作者 | 葉龍/ 編; 錢穆/ 講述 |
|---|---|
| 出版社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中國文學史:國學大師錢穆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罕見的通儒,一生著述超過80本,可是從沒有一本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後人僅從他散落的演講文章,及一些長篇散文中讀到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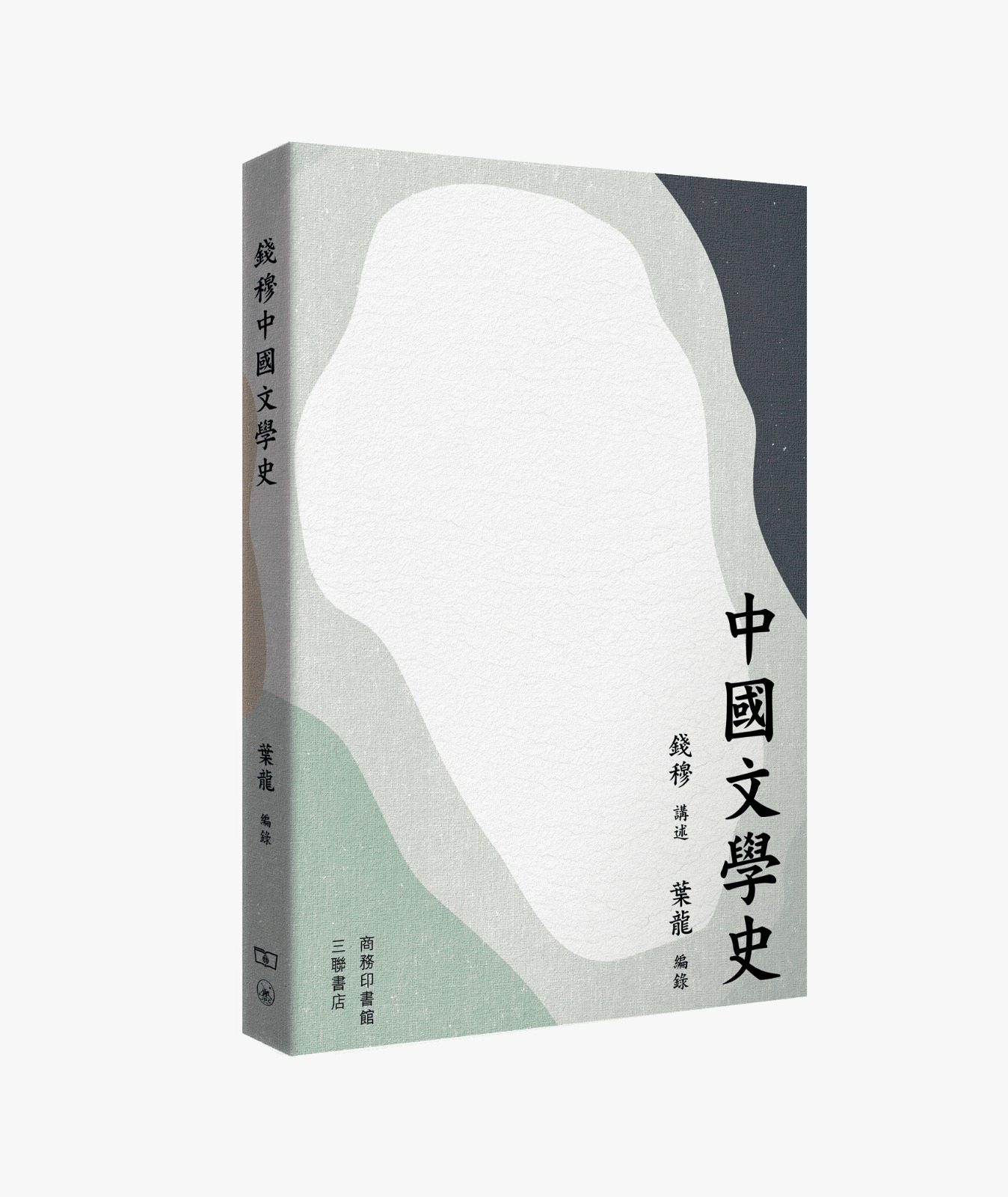
| 作者 | 葉龍/ 編; 錢穆/ 講述 |
|---|---|
| 出版社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中國文學史:國學大師錢穆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罕見的通儒,一生著述超過80本,可是從沒有一本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後人僅從他散落的演講文章,及一些長篇散文中讀到錢 |
內容簡介 國學大師錢穆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罕見的通儒,一生著述超過80本,可是從沒有一本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後人僅從他散落的演講文章,及一些長篇散文中讀到錢師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真知灼見。錢穆五十年代曾在新亞書院開授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整體系,惜始終未有機會將課程講稿整理成書。師從錢穆多年的葉龍,把60年前的課堂筆記加以整理,搜遺補漏並加上注釋,編成本書。全書三十多篇文章,由堯舜禹講至清末,體例以時間為序。錢穆以“史”及“人”的標準衡量文學,在講稿中針對具體朝代和文學流變,提出許多新創見,並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及誤解作出了考證和解釋。本書特色:(1) 錢穆對中國文學研究甚深,並曾開課教授學生,但多年來未有出版過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只有一些散落的演講文章及散文。本書由葉龍編錄,把課堂筆記整理,搜遺補漏並加上注釋,成為了一本較有系統的專著。(2) 講稿針對具體朝代和文學流變,提出許多新創見,並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及誤解作出了考證和解釋。(3) 本書以講稿為本,讀來行雲流水,字字珠璣,不如一般學術著作般沉悶,而且旁徵博引,講文學兼引用史料,看地理,貫通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是一部資料豐富多元的文學史書。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葉龍,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曾師從錢穆多年。後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文學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歷任中學及大專文史科教師,講述先秦諸子經濟思想、中國經濟史、史記導讀、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國佛教史等科目。著有《錢穆講學粹語錄》、《錢穆講中國經濟史》、《桐城派文學史》、《桐城派文學藝術欣賞》、《中國古典詩文論集》、《王安石詩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學研究》、《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等。葉氏課餘在報章撰寫散文,筆耕甚力。
產品目錄 駱玉明序 陳志誠序 葉龍序 第 一 篇 緒論.第 二 篇 中國文學的起源第 三 篇 《詩經》第 四 篇 《尚書》第 五 篇 《春秋》第 六 篇 《論語》第 七 篇 中國古代散文第 八 篇 《楚辭》(上)第 九 篇 《楚辭》(下)第 十 篇 賦第 十一篇 漢賦第十二篇 漢代樂府第十三篇 漢代散文 —《史記》第十四篇 漢代奏議與詔令(附書札)第十五篇 漢代五言詩(上)—蘇李河梁贈答詩第十六篇 漢代五言詩(下)—古詩十九首第十七篇 建安文學 第十八篇 文章的體類第十九篇 《昭明文選》第二十篇 唐詩(上)(初唐時期)第二十一篇 唐詩(中)(盛唐時期)第二十二篇 唐詩(下)(中、晚唐時期)第二十三篇 唐代古文(上)第二十四篇 唐代古文(下)第二十五篇 宋代古文 第二十六篇 宋詞第二十七篇 元曲第二十八篇 小說戲曲的演變第二十九篇 明清古文第三十篇 明清章回小說第三十一篇 結論跋
| 書名 / | 中國文學史 |
|---|---|
| 作者 / | 葉龍 編; 錢穆 講述 |
| 簡介 / | 中國文學史:國學大師錢穆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罕見的通儒,一生著述超過80本,可是從沒有一本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後人僅從他散落的演講文章,及一些長篇散文中讀到錢 |
| 出版社 /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620706868 |
| ISBN10 / | |
| EAN / | 9789620706868 |
| 誠品26碼 / | 2683016937003 |
| 頁數 / | 284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2.7x15.2 |
| 級別 / | N:無 |
自序 : 葉龍序
記得在二零一二年冬某日,在夏仁山學長的介紹下,有幸與新亞老校友黃浩潮、葉永生諸兄一同茶聚,談起我有一份業師錢穆賓四先生的“講學粹語”稿和二十多封錢師親筆函件,還有曾在香港《信報》連載的錢師講課的“中國經濟史”筆記和我本人的撰述,也曾在《信報》連載約有三十萬字的〈歷代人物經濟故事〉。上述多位學兄異口同聲的,都認為值得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因為有新亞歷史系的陸國燊校友及同時兼管商務業務的陳萬雄董事長也是校友。
不久與陸兄再次茶聚後,便帶同文稿邀我同車回商務見負責出版中文書籍的總編毛永波先生。到了商務總部,國燊兄把所有上述稿件全部交給永波先生審閱並由他作出決定。
由於永波先生是資深出版家,對兩岸四地的中文出版狀況瞭如指掌,由他即時決定先出錢師講的“中國經濟史”,然後再出“錢穆講學粹語錄”,於是 2013 年 1 月在香港出版了前者,後者於同年 6 月出版時,《錢穆講中國經濟史》在香港已第二次印刷,反應相當好。至於國內的簡體字版也於 2014 年 1 月在北京後浪書店發行,頗受各界人士的歡迎,本人也收到
該書店多套贈書,到了 3 月份已印刷達五次之多。可能因為發行網廣,幾個月前,有友人在新界大埔也已看到有書店在售賣簡體字本的“中國經濟史”了。
錢師的課堂經濟史稿之所以頗受歡迎,除了錢師講學有其獨特與精彩的見解以外,得加上國內經濟界名人林毅夫先生的作序品題,還有據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家丁望先生早前曾在香港《信報》撰文報導:有北京劉亞洲將軍對錢師加以讚揚,說錢師在經濟史和他的其他史著中,闡述分析中國古代執政者之所以不能戰勝常來騷擾的匈奴與羌人等民族,是由於我國北方與西北有大高原,而遊牧民族卻善用騎兵能征慣戰,而漢族人民以農耕為主,不諳騎兵作戰,以致常吃敗仗。直到漢武帝亦懂得養馬習騎,才把匈奴、羌等少數民族征服,國家才得統一。當然現在我國已是五十多個民族大團結,早已沒有遊牧與農耕之別。舊說農、工、商、學、兵,現在行業更多了,大家各自在其本位上努力着。
錢師講的“中國經濟史”造成了各方的轟動,連月來有北京的、成都的以及廣州和深圳的報刊記者來訪問我,有的還來了多次,並在上述各地報章大篇幅加以報導。在下在此衷心表示感謝,大家都是在同一目標下,為要把中華學術文化加以發揚光大,為要把錢師所擁有的滿腹經綸,讓沒有能在新亞書院聽過課的同胞都能得到分享。錢師一生絕不重視衣食住等各方面的物質享受,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他只希望我們每一位中國人能多讀一點中國的典籍,能多學習一些中國的歷史文化,讓我們知道中華民族是何等的偉大,他就於願足矣。
說實在的,錢師無論講哪一門課程,都有他精彩獨到的見解,他在新亞開的課據我記憶所及,有中國通史,還有中國的秦漢史、文化史、思想史、經濟史、文學史以及社會經濟史、論語、孟子和莊子等;至於在新亞研究所錢師還開了“韓(愈)文”與“詩經”,那是必修的。同時他在戰前北大等校,八年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聯大、武漢研究所諸校及抗戰勝利後在江南大學,以及在台北文化大學碩士、博士班等校授課,據我所知他尚有開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讀……等課。近日我重讀錢師講的“中國文學史”,覺得他對歷史地理也滾瓜爛熟,他還指出太史公因不熟悉歷史地理,把古人的著作寫對的當作寫錯來看。錢師是應該可以開“中國歷史地理”的。其實,錢師沒有把握絕不會開那麼多科目,錢師常說,一個人並非大學畢業就算是完成了,也不是讀了一個碩士甚至一個博士學位就成功了。
讀書是一輩子的事,做學問是終生的事業。錢師就是希望我們要向他學習,他用一生的精力,把中國的經、史、子、集都讀通了,所以他講任何一門課,必定有其獨特的見解。
近期友人常有勸我,尤其是唐端正學長及夏仁山學長多次敦促我把錢師講過的課堂筆記整理出來,好讓大家都可以讀。由於當年其他同學聽了錢師的課,雖然也有做筆記的,但都不夠詳細,首先使我想到的便是錢師 1955 至 1956年講的“中國文學史”。為甚麼呢?我雖有讀“哲學教育系”,讀新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是“孟荀教育思想比較”,但研究所畢業後,我留校擔任助理研究員,是錢師指導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多年,直至 1963 年錢師辭職前一年。雖然我又在1969 年新亞加入中文大學後重讀了一個主修中國歷史的榮譽文學士,但後來經錢師向羅慷烈師多次推薦,終於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而且都是主修中國古典文學。更湊巧的,當我獲得博士學位不久,香港佛教會的寶燈法師邀請我擔任能仁學院(按:此校在台北教育部立案)院長並兼哲學及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但當時台北教育部規定,副教授可擔任代院長,正教授才可任院長。我雖在新亞教過大一國文七年,但只是一個兼任講師,後來在 1972 至 1974年擔任嶺南書院中文系專任講師兼助理訓導長時,仍未得到副教授資格,於是港大的兩個高級學位正好派上了用場,我先是用港大博士論文,經台北審查獲通過得副教授資格。因副教授只能做代院長,而我的大專服務年資已夠長,於是再
將我尚未公開發表的碩士論文〈王安石詩研究〉,再送台北教育部申請升等,更奇妙的是,經嚴格審查通過獲升正教授,使我擔任了名正言順的院長。這裏得感謝羅慷烈師對我攻讀
碩士的悉心指導,並妥善安排我攻讀港大博士學位,終於順利完成,使我難忘師恩。
由於上述因緣,我先整理錢師的“中國文學史”講稿會比較輕鬆些。當我讀到這本筆記本第一篇“緒論”的最後兩行字時,內心感到高興,錢師以肯定的語氣說道:
“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
上述這段話,我當時如實記錄下來,沒有增添減少,其用字修辭甚至造句,絲毫沒有改動。使我高興的,是 1955 年9 月某日,錢師開講的第一天,他竟說出:“過去還沒有出現過一本理想的文學史。”因錢師一向是說話謹慎謙虛的,說出這句重話豈不是會得罪好多曾經撰寫並出版過“中國文學史”的學者或教授?無論如何,過去寫中國文學史的作者除非他心胸寬宏大量,不然,他們內心一定會感到不舒服的。
但是,錢師當時如此批評,實在少見。我和一羣同學多次在課餘時圍着聽錢師教誨:“你們讀了我的《國史大綱》,還可去多看些別人寫的‘中國通史’,可以作出比較,看看有甚麼不同的地方。”接着的一句大意是:“你們自己去選擇吧!”
這一類的話。但使我高興的,便是由錢師來講“中國文學史” 這門課,必定有它獨特之處,亦即是錢師所講,必定有他創新的見解,讓我們可把過去曾看過的其他“中國文學史”作出一些彌補。錢師並不是說,憑他個人講堂授課,可以把“中國文學史”講得十全十美,他是肯定的說:“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這裏錢師明明說並不是靠他個人可以力挽狂瀾,乃是要靠大家共同來努力,要靠大家一同來尋求,一同來創造,以達到成功之路。記得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有一次參加新亞研究所的師生月會報告,錢師也在場,他曾說:“世界上沒有一本著作是十全十美的。”但錢師在“中國文學史”有關重大問題上卻可作出自己的見解,這便是有益後輩。
舉例說,錢師是非常欽佩,可說是非常敬佩朱夫子(熹)的,不然,錢師也不會在晚年用他十年八載的精力來撰成《朱子新學案》,連他的知己好友羅慷烈教授也談到錢師的一生代表作時說:“錢先生,自從晚年完成《朱子新學案》後,他早先被譽為權威著作的如《先秦諸子繫年》、《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以及《國史大綱》等名著,都得讓位了。”錢師在講“中國文學史”的《詩經》時,雖然對朱子也有讚語,他說:“朱子解釋《詩經》有創新之意。”意即朱子有與前人不同的解釋,但錢師也毫不客氣的指出朱子有時解釋《詩經》也有錯失。因為朱子只用直指其名直敍其事的“賦”來解釋《詩經》,而錢師認為解釋《詩經》可有兩種方式,他為取信於聽眾,舉出中國文學史上三個不同時代和作者的文學作品來證明,使人無懈可擊,這就是錢師所持有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做學問態度。
錢師的著作,也不是沒有疏誤,他在向我們講“中國通史”時,多次講起他曾請呂思勉先生為其《國史大綱》校閱一遍,還請繆鳳林教授校正該書的疏誤,並在再版時一一加以訂正。錯就是錯,錯了就得改,沒有客氣講。錢師指出太史公司馬遷講到《離騷》時,他不識歷史地理,以為古人把地名寫錯了,還把原文對的反而改為錯。錢師指出我國古代的山名水名都有特別的意義,誓如“霍山”這個山名,在我國的安徽與山西均有霍山,小山為大山所圍叫“霍”,所以都有“霍山”,故“霍山”只是一普通名詞,並非專有名詞。又如“洞庭”這個湖名,並不限於只有湖南省才有,即是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的現象”者,都可以稱為“洞庭”,因湖南的“洞庭湖”通湘、資、沅、澧諸水;但太湖亦有洞庭湖之稱,因為太湖是通黃浦江、吳淞江等多條水,所以太湖也可稱“洞庭湖”。錢師說:太史公把《楚辭漁夫》篇所說的“寧赴湘流而葬江魚之腹中”一句,認為有誤,特改為“寧赴常流”,其實“湘流”並不錯,倒是改為“常流”卻是錯了。司馬遷以為“湘水”在湖南,怎麼人在鄂(湖北)卻會在湖南的湘水自殺呢!錢師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漢北時所作,所說之“湘流”,實是指“漢水”,而並非“湘水”。這就是錢師的博學而無所成名。講文學史亦得要義理、考據和辭章三者兼顧,不但要講其歷史演變、創作目的和字句修辭,而且還要了解歷史地理,懂得校勘學,所以讀書做學問真不容易,少一瓣就會出錯。
一部中國文學史,等於錢師平常所講的,它包括了唱的和說的文字,即包括原始詩歌和故事小說,還有做的文學如舞蹈戲劇,以及正式用文字寫成的文學,單是文字方面的作品,三千年來如此眾多的作品和作家,欲在一年的課程中來加以詳細闡析所有作品,當然並非易事,但錢師每逢遇着時代大轉變,而大家對某一類重要創作,在意見上有重大分歧時,他必定會作出明確的決斷,並提出有力論證,使人心服。
錢師做學問的一貫主張是:歷史應還其本來面目,不能曲解事實。不可貽誤後人。不過有一點可以補充說一下,錢師自己說曾在新亞時講過兩年文學史,但他校務冗忙,沒有把學生課堂筆記本加以整理改定。我聽錢師這門課是在1955年秋至 1956 年夏,錢師還查閱過我們的筆記,兩次是由助教查看,給了我高分。一次是錢師自己查閱,只用紅筆寫了“五月四日”。如果當時錢師欲改定筆記本,很可能會取用我的筆記本,因為只有我全懂他的無錫國語,可惜他當時忙不過來。錢師還說曾講了兩次,我又在 1958 至 1959 年 4 至 6 月這段時期聽錢師講宋元明清時代的文學史,那正是我攻讀研究所時期,有空就去聽,約有十多次,也記下了些筆記。最後,我把錢師親自擬的兩次文學史考試題目,都附錄於後,一次是 1956 年 6 月期終考試題目;一次是同年畢業考試試題,如果我們能夠根據錢師全年所講的,溫習後圓滿作答,那也是錢師希望我們學習的(當然我們能多看參考書最好),那我們對中國文學史也可以明瞭得一個大概了。但錢師說過,研究文學史是一輩子的事,希望吾人來共同尋求與創造。同時,本記錄稿難免有疏失之處,文責應當由筆錄者來負。尚祈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最佳賣點 : 全書三十多篇文章,由堯舜禹講至清末,體例以時間為序。錢穆以“史”及“人”的標準衡量文學,在講稿中針對具體朝代和文學流變,提出許多新創見,並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及誤解作出了考證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