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 (導讀版)
| 作者 | 張蔭麟 |
|---|---|
| 出版社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中國史綱 (導讀版):《中國史綱》是張蔭麟先生短暫一生留下的惟一專著,原爲作者受聘編寫的高中歷史教材的一部分。作者依據自己的歷史觀對東漢前的中國史實作了較爲嚴格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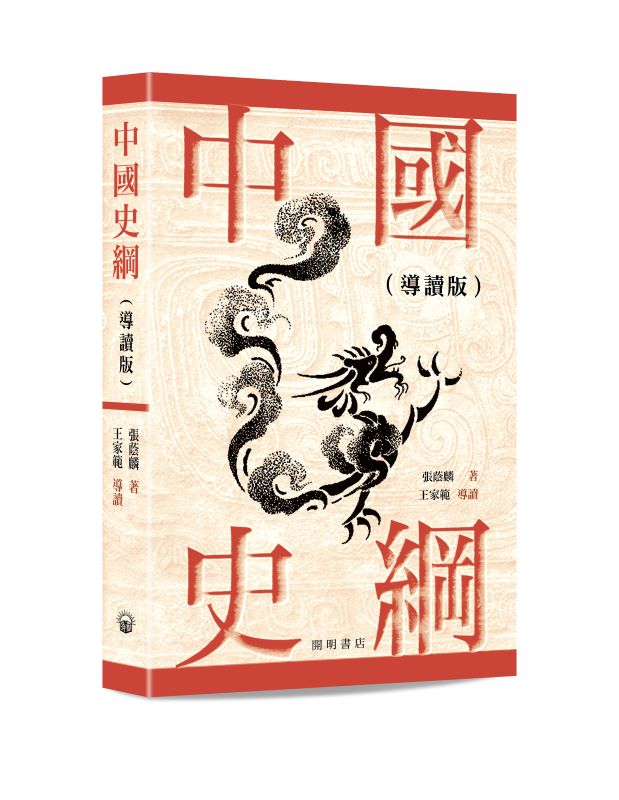
| 作者 | 張蔭麟 |
|---|---|
| 出版社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中國史綱 (導讀版):《中國史綱》是張蔭麟先生短暫一生留下的惟一專著,原爲作者受聘編寫的高中歷史教材的一部分。作者依據自己的歷史觀對東漢前的中國史實作了較爲嚴格的 |
內容簡介 《中國史綱》是張蔭麟先生短暫一生留下的惟一專著,原爲作者受聘編寫的高中歷史教材的一部分。作者依據自己的歷史觀對東漢前的中國史實作了較爲嚴格的選擇和取捨,把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玩索所得」融會貫通,用講故事的方式寫出期間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章節安排簡要得當,文字技巧活潑動人,思想智慧透徹通達,隨時流露出作者的才情與用心。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張蔭麟(1905—1942),號素痴,亦常作筆名,廣東東莞人。著名學者;歷史學家。1923年考入清華學堂中等科三年級肄業,以「史、學、才」三才識為人稱道。後赴美留學,歸國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等任教。學貫中西,兼通文史哲,後專門從事歷史學教授研究,多有創見。
產品目錄 導讀自序一自序二自序三自序四第一章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第一節 商代文化第二節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第三節 周朝的興起第四節 周代與外族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會第一節 封建帝國的組織第二節 奴 隸第三節 庶 民第四節 都邑與商業第五節 家 庭第六節 士第七節 宗 教第八節 卿大夫第九節 封建組織的崩潰第三章 霸國與霸業第一節 楚的興起第二節 齊的興起(附宋)第三節 晉、楚爭霸第四節 吳、越代興第五節 鄭子產第四章 孔子及其時世第一節 魯國的特色第二節 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第三節 孔子與其時世第四節 孔子與政治第五節 孔子與教育第六節 孔子的晚年第五章 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第一節 三晉及田齊的興起第二節 魏文侯、李克、吳起第三節 秦的變法第四節 經濟的進步與戰爭的變質第五節 國際局面的變遷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第一節 新知識階級的興起第二節 墨子第三節 墨子與墨家第四節 孟子、許行及周官第五節 楊朱、陳仲、莊周、惠施、老子第六節 鄒衍、荀卿、韓非第七章 秦始皇與秦帝國第一節 呂不韋與嬴政第二節 六國混一第三節 新帝國的經營第四節 帝國的發展與民生第八章 秦漢之際第一節 陳勝之起滅第二節 項羽與鉅鹿之戰第三節 劉邦之起與關中之陷第四節 項羽在關中第五節 楚漢之戰及其結局第九章 大漢帝國的發展第一節 純郡縣制的重建第二節 秦、漢之際中國與外族第三節 武帝開拓事業的四時期第四節 武帝的新經濟政策第十章 漢初的學術與政治第一節 道家學說的全盛及其影響第二節 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第三節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響第十一章 改制與「革命」第一節 外戚王氏的專權第二節 哀帝朝的政治第三節 從王莽復起至稱帝第四節 王莽的改革第五節 新朝的傾覆第六節 東漢的建立及其開國規模附 漢帝國的中興與衰亡(一)(二)附錄一 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附錄二 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附錄三 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 書名 / | 中國史綱 (導讀版) |
|---|---|
| 作者 / | 張蔭麟 |
| 簡介 / | 中國史綱 (導讀版):《中國史綱》是張蔭麟先生短暫一生留下的惟一專著,原爲作者受聘編寫的高中歷史教材的一部分。作者依據自己的歷史觀對東漢前的中國史實作了較爲嚴格的 |
| 出版社 / |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624592702 |
| ISBN10 / | |
| EAN / | 9789624592702 |
| 誠品26碼 / | 2682602672007 |
| 頁數 / | 338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1x13.5 |
| 級別 / | N:無 |
導讀 : 導讀
王家範
百年來在新史家裏頭,關於「通博」與「專深」,確實歷來都有不同的看法。傅斯年是代表了一種意見。他認為應該先從斷代史做起,其潛台詞便是只有斷代史做齊、做成功了,才可能有像樣的通史出來。我想這個意思,直到今天,史學界的絕大多數同人仍會有同感。斷代史、專史沒做好,再有本事,能做出好的通史嗎?
但問題跟隨着又出來了:通史是不是只需要把斷代史「接龍」接起來就成了?後來的實踐已經告訴我們,斷代史出得也不少,也有嘗試大規模「接龍」工程的,但也很難理想。記得1941 年當張蔭麟出版他的《中國史綱》第一冊時,就在他的《自序》裏說:「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指20 世紀30 年代)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它們結集,把它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說得多好!然而,冷不防,在分別一一說明了他剪裁調度通史主張的五條選擇標準後,突然插上一句:「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句大實話。
通史不容易寫好,不容易寫得使多數人滿意,原因很多。從實際的操作層面上說,「通」是專的綜合。通史的寫作者必得「通博」,對個人來說,這是極難做到的。雖然他完全可以藉助現有的成果,但在個人精力方面必會遇到許多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所不知」是不可能的,「歸納」總是先天地具有「不完整性」。所以,百年裏,有好幾部個人的通史是沒有寫完的,而且沒有一部通史能完全經得起專家的仔細挑剔。正因為如此,才有集合各方面專家集體協作的念頭。這樣做,在「專、博」方面的矛盾或許可以緩和些,卻引來另一個大缺陷:通貫始終的「氣」沒有了,我把這叫作「氣散神消」。因眾多作者各自操作,難以相互關照、前後呼應,缺乏一以貫之、整體理解的精神氣質,是預料之中的事。即使像《劍橋中國史》那樣,採取「專題集合」的形式,且有一主編總領其「精神」,「神散」的先天性弱點還很明顯地存在。
無論怎樣說,通史真正的難,還是難在史識,那種能居高臨下,「一覽天下眾山小」的把握能力,即「識大而不遺小,泛覽而會其通,達人情,明事變,洞幽賾,晰條理」(徐哲東讚呂誠之先生語,見《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這種能力或許需要某種不同尋常的稟賦。但有一點是可以從比較成功的通史寫作中得到體驗的,這就是:此種能力的獲得,僅僅有具體史實的資源供給一定是遠遠不夠的。它更需要作者對人文領域更廣闊的知識背景和深入的體驗,對人類,對社會,對世界方方面面多視角的體察。這時,我領悟到了呂思勉先生特地把一句俗話加以強調的意義,這就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我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出版的1945年以前,大約已有42 部通史(不包括史話一類,據《1900 — 1975年:七十六年史學書目》)。到今天,究竟總共出版了多少通史?我沒有統計,或許已不下百部。這只要看近二十年各地編通史教材成風,就可知數字一定很壯觀。
時間作為一種特殊的過濾器煞是無情。大江東流不止,潮起潮落,風行的未必就能傳承,精萃遭遇冷落亦時或有之。所幸時光似水,反覆沖刷篩洗,是沙礫是金子總會逐漸分明。真正的金子,即使因緣種種不幸遭際,被塵土無辜掩埋了,或遲或早都能再見天日。這是事理所使然,強制不得的。陳寅恪、呂思勉、錢穆、蔣廷黻等等不都是如此?!
這裏,將要向大家推薦的,張蔭麟教授(1905-1942)短暫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中國史綱》,也屬於數十年後重新發光的一個事例。
為學貴自闢,莫依門戶側
這部《中國史綱》,是當時教育部計劃出版的高中歷史教材《中國史綱》的第一部。1935 年,張蔭麟已從美國留學歸來二年有餘,任清華大學歷史、哲學兩系教授。受部聘後,他當即放下手裏的其他科研課題,「遍諮通人」,潛心策劃《史綱》體例和細目。還特別向清華請了長假,專致筆耕其所負責的先秦至唐以前部分。其餘部分原計劃邀請吳晗、千家駒、王芸生等分任。
未及二年,「盧溝橋事變」突發,國難當頭,蔭麟被迫離京輾轉南下浙大、西南聯大,其事遂不如願。經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將此前已完稿的八章,加寫《自序》,遂由他改教的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貴州遵義面世。原初題名《中國史綱》第一輯(此據張其昀《張蔭麟先生的史學》,筆者尚未見原本),時為1941 年春夏之間。初次印行匆促,著者名還曾誤植為楊蔭麟,蔭麟也不在意。又據《初版自序》、《再版自序》,知次年再版,始增入九至十一章(前據吳晗《記張蔭麟》,後一點吳文回憶則有誤)。此後,先生興奮中心轉移,改攻兩宋史,僅撰寫三章(第三章未完),就因病撒手西歸,終年37 歲。如天假以年,從其已發表的宋史成果預測,《中國史綱》的宋史卷必將更為光彩奪目─想到至今尚沒有一部能與張氏風格相匹敵的兩宋史,對他的英年早逝怎不叫人傷感倍至?!
讀過《中國史綱》的,多會驚羨它的文筆流暢粹美,運思遣事之情深意遠,舉重若輕,在通史著作中當時稱絕,後也罕見(唯錢穆《國史大綱》可相匹敵)。全書沒有累贅冗煩的引文考證,不故作深奧高奇,史事都以「說故事」的方式從容道來,如行雲流水,可令讀者享受到一口氣讀完不覺其累的那種爽悅。也因為讀來悠然輕鬆,據我個人的觀察,讀者很容易輕忽了對著者構思和寓意的細心體察;一不經意,書中潛心涵泳所得的精警見地,屢屢就從眼皮下滑過。為此,我想先從著者的人格、學術風貌說起,或許對讀者進一步體會本書不無幫助。
離蔭麟去世才四五年,謝幼偉博士著文懷念故友,就不無憂慮地說:「這一位天才學者,俗人不必說,即學術界中也許已忘記了他。他的著作以報章雜誌發表的短文為多。這些短文到現在還沒有集合出版,整部的著作有《中國史綱上卷》,而這也只有浙江大學史地研究室的石印本。所以在某一時期內,他雖曾驚動我國的學術界,到目前他卻很可能為學術界所遺忘。但他是最不應遺忘的一人。」此後,情況雖然還沒有到謝氏杞憂的那麼糟,文集、《史綱》海峽兩岸還都出版或重印過,但流傳不廣。世俗總多勢利和健忘,也是無可如何的。張蔭麟的名字,對今日大多數學人恐怕都會感到陌生。然而,恰如謝氏所說,回溯到三四十年代,蔭麟名聲不小,曾被學界譽為奇才,受到了前輩和同齡學者的普遍敬重。1929 年夏與蔭麟同船赴美留學的謝幼偉博士,更是熱情讚美蔭麟為天才,在長篇的紀念文章裏說道:「張君是天才,這是無疑問的。他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曾寫過一篇《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見本書附錄一),寄到《學衡》雜誌,《學衡》的編者認為是一位大學教授的作品。這一點即可證明張君的聰穎是遠在一班學人之上的。所以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先生遇到了這一位年輕學生,也不能不特別注意,不特別賞識。」(《張蔭麟先生言行錄》)
蔭麟來自廣東東莞,自幼喪母,家境貧寒。1923 年秋季考入清華學堂(時為留美預備學校)中等科三年級,直至1929 年大學畢業,經歷了清華學校改制的全過程。入學伊始,即如上述所記,不足18歲的蔭麟,已經著文向老師梁啟超挑戰「老子出生」說,且考辨精細,徵引經典鑿鑿有據,名驚京華。在繼後的兩年裏,他在《清華學報》、《學衡》、《東方雜誌》等一流刊物上發表的學術文章不下十餘篇,涉及經學考據、中外交流史、科技史等多項領域,還參與了當時正轟動學界的(顧頡剛)「古史辨」論戰。今天,重讀這些論文,我們簡直不敢相信,一個20 來歲的學生,學術水準竟可以令當下有些大學教授汗顏。其中《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不僅大大擴充和修正了乃師(啟超)關於這個論題的史料,而且對西學輸入的影響以及清代並未因此而改變「科學(思想)不盛」的原因發表了精警見解;《張衡別傳》和《宋盧道隆吳德仁記里鼓車之造法》兩文,則更應該看作首開我國古代科技史研究風氣的力作,具里程碑意義(劉仙洲先生即如是說)。據不完全的統計,去美留學前的六七年時間內,已積有學術成果(包括譯文)40 項。怪不得謝幼偉博士終發為「天才」的讚歎。
蔭麟自號「素癡」,常用作文章筆名。我以為,無論從哪方面看,例如對學術的癡情專注,孤傲內向,不通人情世故,不易適存於現社會(友人謝幼偉、張其昀、賀麟、吳晗等回憶他的個性),以及治學「神解卓特,胸懷沖曠」(熊十力讚其學術境界),也包括過早地夭折,難享永壽等等,蔭麟都很符合天才學者的特徵。然而,如若只從個人天賦角度去理解,那很容易忽略了今天重新認識蔭麟先生的許多更有價值的啟示。
近代以來,人才成羣,風湧而起,明顯有過兩個突出的高峰時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間,以曾、胡、李、左、張以及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幕僚文士為代表。是時人才濟濟,不拘一格,政壇文氣之盛為中古以來所未有。其中能集道德、事功於一身如曾、胡者雖鳳毛麟角,但在經世致用一隅有卓識奇功,建樹不凡的可以數出一大羣。稍後在他們的影響下,還走出了一批最早通達世勢、熟悉「洋務」的新人。二是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具現代意義的各種學科相繼濫觴,「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一代溝通中西的學科權威名家大抵成形於這一時期。假如說上一高峰「事功」派佔盡風光,許多人物多似電閃雷鳴般倏然過眼,有力度而少餘韻;那麼第二個高峰承上輩及其時代的恩澤,別開新天地。是時激盪過後,「朝野」尚稱「苟安」,中西文化教育往來更密。淡出「事功」的「學問」派那厢真現獨好風景,其山高水長,遺澤後世且深且厚,更堪百年後回味不已。
蔭麟生而有幸,及時親逢學問盛世的文化滋潤,並能以新秀的身份參與其間。他天性聰穎,造化把他從嶺南送上京華,進入風雲際會的文化中心,後來又留學西洋,確是時勢造就了他天才有為。那時,「五四」個性解放、自由探索的新風吹拂神州,學術報刊似破土春荀湧出,自由討論風氣極盛一時。蔭麟又直接生活在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胡適、陳寅恪、吳宓、傅斯年、錢穆、顧頡剛(其中最年輕的,也比蔭麟長十幾歲,均屬老師輩)等等一羣知名學者輝映的人文光環下,猶魚得水,遨遊自如,才有了上面「少年英發」動人的一幕。讀蔭麟的傳記,最令我感動甚至妒忌的,是那個時代學者的氣度和學術自由討論的文化氛圍。同在清華,哲學家賀麟比蔭麟高三級,兩人很快就成為終生摯友。據賀麟的回憶,蔭麟給他的第一印象是:一個清瘦而如飢似渴地天天在圖書館鑽研的青年。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國文化史演講班上,梁任公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來,向聽眾中問哪一位是張蔭麟。蔭麟當即起立致敬。原來是蔭麟寫信去質問老師前次演講中的某一點,梁先生在講台上當眾答覆他。這事發生在蔭麟已於《學衡》著文與先生商榷之後。他倆常去聽梁任公的演講,可見對先生的仰慕。但蔭麟的脾氣向不願意拜訪人(終生不改,時人稱其為「怪」)。1926 年夏,被賀麟拖着才第一次拜謁梁任公。先生異常歡喜,勉勵有加,當面稱讚蔭麟「有作學者的資格」(另據王煥鑣《張君蔭麟傳》,說「梁任公得其文歎曰:此天才也」)。此後二三年中,他卻從未再去謁見過梁任公。他很想請梁任公寫字作紀念,也終於沒有去請(見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載《思想與時代》第20 期,1943 年3 月)。還值得補一筆的是,1929 年初,蔭麟正在撰寫長篇學術論文《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鞫》,針對梁先生燕京大學演講《古書之真偽及其年代》而發。論文在《燕京學報》刊出時,梁任公已病逝。蔭麟在文末特別有一段附語,說「此文初屬草時,梁先生尚在世。本當重校付印,先生已下世,竟無從請問以決所疑矣。作者極不願意於此時舉其素所尊敬之學者之旨為錯誤之例。惟以愛真理故無法避免耳。」(台灣1956 年版《張蔭麟文集》,全文長48 頁)
有這樣的老師和這樣的學生,氣度、風範盡在不言中,這正是那個時代的驕傲。蔭麟與同時代學者多有評論商榷的文案往來,不獨對梁任公。本着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則,對其他師輩如周樹人、陳寅恪,年長而剛負盛名如顧頡剛、馮友蘭,他的評論也總是「是則是,非則非,毫不掩飾,毫不客氣」,而被評論者都豁達大度,師長更以獎掖新進的態度深許之,至少也不會像現在那樣,弄不好就扯到別的地方去。不信,可以去讀寅恪先生詩:《輓張蔭麟二首》(載《陳寅恪詩集》第31 頁)!
蔭麟一生信奉恪守的治學格言,是「為學貴自闢,莫依門戶側」(《致賀麟留美贈別詩》)。蔭麟在他光采而短暫的一生中,這種個性氣質實在是太強烈了,因此也特別地感人。誦讀他的學術論著(也包括教材的編寫),我們處處都能觸摸到那種不甘因循剿襲,勇於求新求突破的自由創造精神。這再一次證明,寅恪先生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決非義寧一人所獨執,而曾經是沐浴了「五四」精神那代人的真誠追求。那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話很流行,沒有任何權威偶像是碰不得,不可說不的。這樣的氛圍不可復得,方有「壁立千仞」之說。唯其如此,優秀學者於「五四」後一二十年內成羣成團地噴湧而出,才可以被通解、被體認。
這種不依門戶、自由創造的風格,決非世俗常見的那種無端狂妄,藉淺薄挑戰名家以求一搏。蔭麟從心底裏尊敬一切有學術成就的前輩和師友,細微地體察汲取一切有價值的學術創造,治學厚實而見地敏銳,執著底定而鄙薄趨俗。據說他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對梁任公表面上「敬而遠之」,再而三地「挑戰」,內心實則一往情深。熟悉他的朋友說,蔭麟最欽佩任公文章「筆峰帶有情感」,「張君的文章頗受任公的影響,一篇之中總含有多少任公的筆調」。
那時,剛從經學考據的桎梏中叛離不久,國學的根子依然深扎在一代新學的底部,欲連根鏟除(也畢竟鏟不盡)那是幾十年後的事。蔭麟的學術是以考據起家的,很見功力。對太炎先生服膺至深,即是明證。有人統計,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都涉及考辨,學問有根據而不流於空疏。然而,蔭麟可貴的是,承傳而不因循,勇開風氣敢為先。蔭麟曾對謝幼偉坦言:「寫考據文章是很容易的。」言之似極輕鬆。反之,為了《中國史綱》,他卻喟歎:「寫這種文章是很費苦心的。」一輕一重,其味無窮。
在闡明這輕重內涵之前,我先得把蔭麟對任公的紀念文章拿出來,一則彰揚他對老師真誠而不帶一絲虛假的愛(這是最有價值的尊師),一則為理解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提供一份證據。據現在掌握的材料,梁任公剛去世,「全國報章雜誌,紀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無聞」。蔭麟在甫將赴美前夕,即草寫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首次從學術史演進的角度,將老師一生智力活動劃分為四期,分別評估他在各時期的「特殊貢獻與影響」,客觀公允,敬仰之情含而不露(載《學衡》第67 期。賀麟所述赴美後一文,已是第二篇,記憶有誤,不贅)。十多年後,他所參編的《思想與時代》特地刊登了張其昀錄存的任公未刊遺札中數十事為《梁任公別錄》,蔭麟親為之跋。文章起首即聲情並茂:
此時為此文,不禁起予空谷足音之感也。方戊戌前後,任公之在文界,何啻如旭日中升?一篇之出,百數十萬人爭誦。曾不四十年,後生已罕或能舉其名。其一知半解者,甚且為蚍蜉之撼。「或榮譽若天仙光寵,消逝時迅越流星」,歌德之詩,可為任公賦矣。
接着大段論述任公與政的種種曲折,反駁攻擊者,並檢討自己十年前「年稚無知,於(先生)民國後之政治生涯,妄加貶抑」,評析平恕允直,可與寅恪先生《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對讀,此處略過。筆峰轉至學術,蔭麟說道:
以言學術,世人於任公,毀譽參半。任公於學,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學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為其考據之作,非稗販東人,則錯誤百出,幾於無一篇無可議者。實則任公所貢獻於史者,全不在考據。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鶩博,最不宜於考據。晚事考據者,徇風氣之累也。雖然,考據史學也。非史學之難,而史才實難。任公在「新漢學」興起以前所撰記事之巨篇,若《春秋戰國載記》,若《歐洲戰役史論》,元氣磅礴,銳思馳驟,奔磚走石,飛眉舞色,使人一展復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史學之林,以質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麥可萊、格林、威爾斯輩,皆瞠乎其後矣。(《跋梁任公別錄》)
此跋的文風,酷肖乃師,磅礴之勢不減。活潑潑的蔭麟就是這樣:對自己素所尊重的老師,他不諱言其短,「才大工疏,事繁鶩博,最不宜於考據」,寥寥幾筆,可謂彈無虛發,正中鵠的。而於先生史才、史識之長尤三致其意,領悟深得精髓,亦屬「就有道而正焉」。我作教師的有經驗,百依百順的,盡說好話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學生。還是賀麟說得極有餘味:「那知這位在學生時代質問梁任公批評梁任公的蔭麟,後來會成為梁任公學術志業的傳人。」梁任公是個大忙人,晚年轉而治史已時不待我。蔭麟靠着他對前輩史才、史識的獨具慧眼,《中國史綱》的創製獲得了非凡成功,而這便是對老師最好的回報。
從上文即可讀得蔭麟的心聲。他絕對不是故意看輕考據。考據是很苦的事,是一種特別的工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實在的成績。然而,不以考據為底止,注重推出義理,這才是蔭麟治學的個性特色。而且,這義理也是經過改造,充實了新的內涵的。他的治學理路,在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寫給張其昀的信中說得最明白:「國史為弟志業,年來治哲學社會學,無非為此種工作之預備。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海峽兩岸《文集》均有載錄)。所以,他對謝幼偉說的一易一難,決非故作危詞,內中大有深義存焉。這實際關聯着一個時代大話題,就是:考據與義理的關係。
我以為謝幼偉的確算得上是蔭麟的鍾子期了。蔭麟選擇對謝氏發此駭俗之論,亦可謂「擇其善鳴者而鳴之」。蔭麟死後五年,謝氏在紀念蔭麟的文章中作了如下的發揮:「寫通史是需要思想,需要有很高的識解的。有人認為專門弄考據的人是思想上的懶惰者,這雖不見得完全正確,但若在考據上兜圈子而不能有進一步的工作,則至低限度,這種人是難得有什麼思想可言的。考據必進至義理,必以義理開拓其心胸,然而是考據不落空。一位良好的歷史學者不能光是一位考據家。不管他的考據做得怎樣好,然只是史料的提供,不是史學的完成。史學的完成,有待於史學家理解的深入和同情的洞察。這一點又須待史學傢具有史學的修養。治史學的而不兼治哲學,這是一種缺陷。」(《張蔭麟先生言行錄》)
蔭麟在新史家羣雄紛起的那個年代,能夠獨樹一幟,特具風骨,確實應該歸諸他不滿足現狀,不隨眾亦步亦趨。眾史家中,他是最先覺悟到史學的改造創新,應該藉助哲學革新理論觀念和思維方法,藉助社會學認識歷史上的社會構造和社會變遷,以滋補舊史學義理的「營養不足」。可以這樣說,在史家中,對西洋哲學和西方社會學了解的廣度和深度,當時無人可與之倫比,獨居翹楚。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可能性」是什麼》、《論同一》等文來看,世紀初西方一些哲學新潮已進入他的視野,如柏格森、羅素、懷特海、斯賓格勒;特別是現象學剛興起,蔭麟就注意到了,這在中西哲學交流史上也值得記一筆。
當時,編著中國通史蔚然成風,因為學識才華的特殊,學者普遍對蔭麟都期望很高。錢穆在1942 年底,把他的《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一文作為對蔭麟的悼念,發表在《思想與時代》雜誌上。文末即說:「故友張君蔭麟,始相識於民國二十三年春夏間。時余與張君方共有志為通史之學。當謂張君天才英發,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諸科,學既博洽,而復關懷時事,不甘僅僅為記註考訂而止。然則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豈期天不假年,溘然長逝。」史家偏好經驗事實,一般很少像蔭麟那樣深陷於哲學沉思。因此,熊十力耐不住破門而出,說道今之言哲學者,或忽視史學;業史者,或詆哲學以玄虛,二者皆病。特讚張蔭麟先生,史學家也,亦哲學家也。其為學規模宏遠,不守一家言,使天假之年,縱其所至,則其融哲史兩方面,而特闢一境地,恢前業而開方來,非蔭麟莫屬(《哲學與史學─悼張蔭麟先生》,1943 年)
蔭麟天性聰穎,但他從不自恃天賦而學點偷懶。束書不觀,空談義理,天才成為無知淺薄的狂漢,蔭麟是不愿為之的。蔭麟治學的勤奮幾乎近於顛狂。每寫一篇文章,精神高度集中,老是幾晚不睡覺,直至文章一氣呵成時,然后才大睡幾天,大吃幾頓。寓所裏滿地滿牀的書,東一本,西一本,凌亂狼藉得不成樣子,他也無所謂。到病重的時候,他開玩笑地對友人說:「我從今后要學懶了」。可他還是做不到,連勸他改讀點輕鬆的小說,改不了習慣,依然捧起哲學書,手不釋卷,直至臨終。因為讀的書極多極廣,著文不論古今中西,隨處觸發,總見火花。他的時評也寫得極犀利明快,有時惹得當局十分惱怒。在史學、國學、哲學、社會學四方面所積功底,使他可以和當時任何一門專家對話。然而,通博並不是他的真正驕傲。蔭麟對社會、對歷史那種全局統攬和深刻洞察的獨特把握能力,在當時才是出類拔萃,最具價值的。
在我看來,蔭麟《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兩文,代表了他那個時代史學理論認識的制高點。有些觀點后來不僅未有超越,甚至有所倒退。關於這個話題,將留在下一段落再作討論。最後,還想特別要說說他的一篇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短文:《玩「易」》。1956 年台灣版《文集》就因疏忽(或別的什麼原故?)而漏收,實在不應該。因為,這代表着他關於社會進步一種獨特的歷史思考。
這篇短文寫定於1933 年9 月。從文內「異國晚秋」字句推測,寫作的時候人還在美國。蔭麟借發揮《易經》的哲理,實際談的主題是社會變遷和「革命」。這麼一個很深奧的社會哲學問題,他卻幾乎是用了散文詩的形式來表述,很含蓄,也很深沉。短文直指《易經》的着眼處在生命,故曰:「生生之謂易」。而近世流行的「革命」一詞又恰好是從《易經》「革卦」裏推演出來的。與時潮最不同的是,文內反覆申述,要把「易」應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會秩序原是活的,原是一個活的有機體。所以革命的「命」要當生命解。只有創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舊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於尋死。他極為感慨地說道:「創造新的生命,以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易一個舊的,那豈是病夫易室,貴人易妻那樣容易的事,而急促得來的?」用不着我多加饒舌,熟悉百年來思潮變遷的學人,都能掂出這些話的千鈞份量。這才是真正經得起百年歷史檢驗的義理。我要補一句的,這裏反映出了蔭麟對孔德、斯賓塞以來的社會學基本學理的圓熟運用,而且妙在不着痕跡,極似寅恪先生的風格。所以他對歷史的考察,往往側重社會層面,在制度的創設和功能演化方面,非常用力,頗多新的洞見。這種史識后來被應用到對歷史上農民起義和改革、改制的全新詮釋上,極其成功,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一失敗之均產運動)》、《南宋亡國史補》和《中國史綱》第十一章《改制與「革命」》。行內人讀了多能體會這些文篇在史學史上的特殊價值,但一般讀者則未必。尤其是前兩篇,形似考辨之作,更不合現在讀者的口味。除專門理論探討文章外,蔭麟的史學論述風格,是從不脫空搬弄理論概念,橫插大段議論,義理即寓於史事鋪敍之中,偶有一二句點睛之筆,亦淡淡而出,極容易被放過。或許這就是中國史學的傳統,所謂《春秋》筆法。讀者宜多加咀嚼,細細消化才是。
最佳賣點 : 張蔭麟——一代史學天才
舉重若輕——大家手筆的歷史小書
經典再現——堪稱絕唱的中國通史
真正生動的,真實的通史,大有讀頭,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