弔詭與共在: 莊子無用政治學的跨文化對話
| 作者 | 鍾振宇 |
|---|---|
| 出版社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弔詭與共在: 莊子無用政治學的跨文化對話:本書呼應近十年來台灣跨文化莊子學研究思潮之問題意識,探討道家哲學(主要是莊子)如何回應現代性之問題。透過跨文化哲學的方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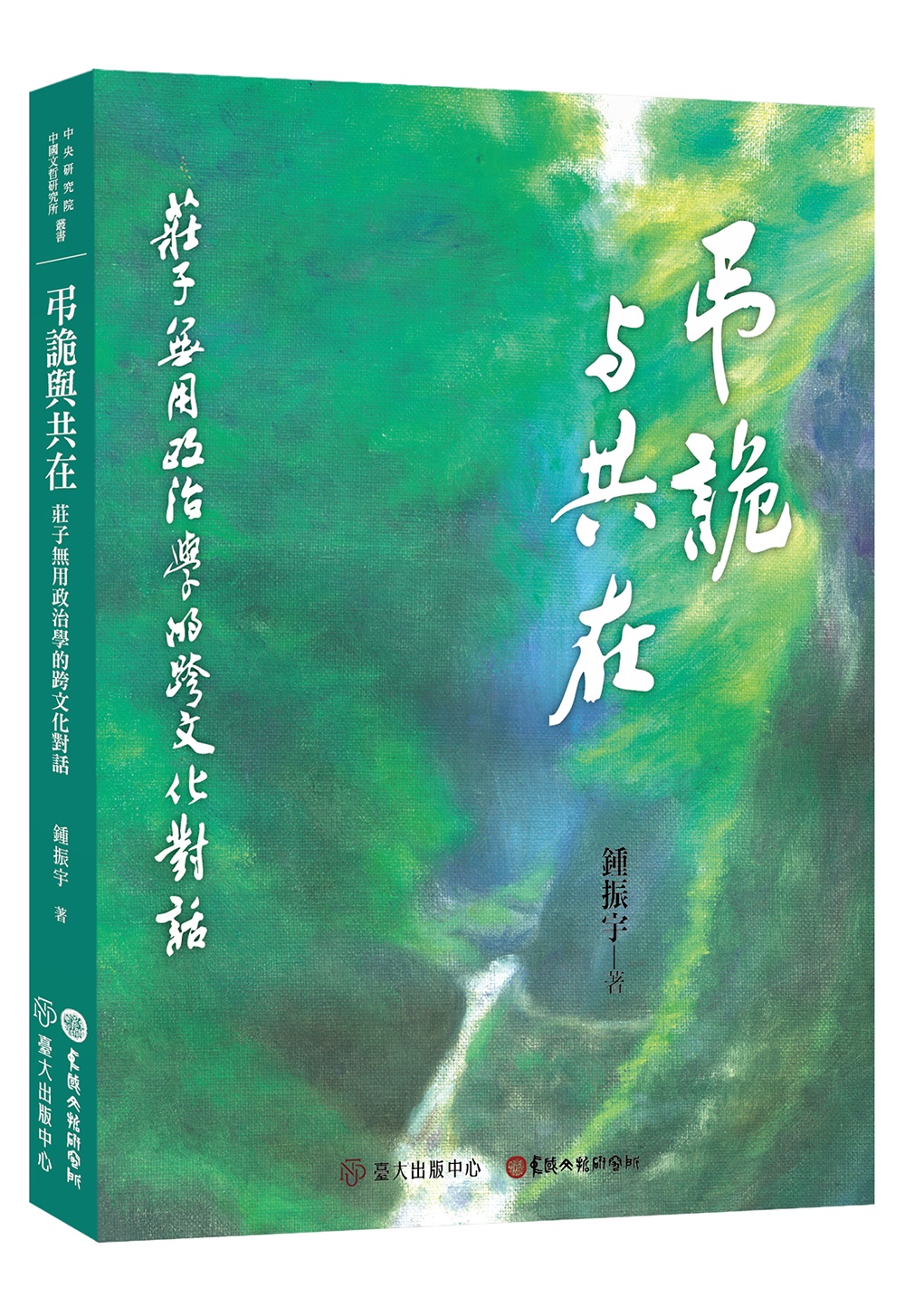
| 作者 | 鍾振宇 |
|---|---|
| 出版社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弔詭與共在: 莊子無用政治學的跨文化對話:本書呼應近十年來台灣跨文化莊子學研究思潮之問題意識,探討道家哲學(主要是莊子)如何回應現代性之問題。透過跨文化哲學的方法 |
內容簡介 本書呼應近十年來台灣跨文化莊子學研究思潮之問題意識,探討道家哲學(主要是莊子)如何回應現代性之問題。透過跨文化哲學的方法,本書比較莊子與西方哲學家(如海德格、孟柯、鄂蘭、南希等)對於「弔詭」與「共在」的討論,使得本書具有國際研究的視野。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弔詭」探討存有論與政治之間的關聯性,回應當代哲學家牟宗三以「辯證」方式連結存有論與政治,本書試圖提出「弔詭」的模型超克之。第二部分「共在」透過與西方哲學的對話,試圖開創莊子哲學的社會性。透過本書,筆者希望打開莊子哲學的政治社會向度,以補充傳統上對於道家新外王討論的空缺。
作者介紹 鍾振宇德國Wuppertal大學哲學博士,專長為道家與海德格哲學的比較,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著作有《道家與海德格》、《道家的氣化現象學》。
產品目錄 導論 一、無用政治學:存有論與政治之間 二、弔詭的之間:無用與有用的弔詭 三、無用政治學的開展:規範、技術、政治 四、無用政治學的開展:社會共在第一部分 弔詭第一章 後設政治學三形態:牟宗三與海德格論「存有論與政治之間」 一、牟宗三的後設政治學:存有論與政治之關聯 二、海德格的後設政治學 三、兩位哲學家構想之比較 四、辯證、弔詭、之間:後設政治學的三種基本形態 五、結語第二章 無用與有用的弔詭:莊惠之質與海德格「用的差異性」 一、海德格論「無用與有用的差異」 二、莊子對於惠施思想的超克:惠施如何作為莊子的最佳對手 三、莊惠之質與無用政治學 四、結語第三章 無用與規範的弔詭:孟柯力量美學的啟示 一、孟柯的力量美學 二、道家與孟柯的比較 三、孟柯學說的討論 四、孟柯的回應與進一步討論第四章 無用與技術的弔詭:海德格對機心的闡發 一、海德格與莊子的無用 二、海德格與莊子的機心:海德格論現代技術的本質 三、無用與機心的弔詭:對待技術的適當態度 四、結語第五章 無用與政治的弔詭:章太炎的中道政治學 一、齊物哲學的背景: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中道觀 二、齊物哲學的批判對象:權力批判 三、齊物哲學:不齊之齊 四、齊物哲學的當代意義:現代性的超克 五、齊物哲學與無用政治學 六、結語第二部分 共在第六章 無用與共在:莊子、海德格、鄂蘭論社會性 一、莊子的共在:以〈養生主〉為中心之探討 二、莊子與鄂蘭論公民的共是 三、結語第七章 無用的共通體:楊儒賓「形氣主體」的啟發 一、形氣主體 二、交互主體性:勞思光的說法 三、共通體:南希的共在存有論 四、莊子的共通體 五、莊子無用政治學的「形氣共通體」第八章 無用的民族:海德格論「民族」共同體 一、1927年《存有與時間》中的民族與政治 二、1930年代的「民族」概念 三、1945年「無用的民族」結論徵引書目索引
| 書名 / | 弔詭與共在: 莊子無用政治學的跨文化對話 |
|---|---|
| 作者 / | 鍾振宇 |
| 簡介 / | 弔詭與共在: 莊子無用政治學的跨文化對話:本書呼應近十年來台灣跨文化莊子學研究思潮之問題意識,探討道家哲學(主要是莊子)如何回應現代性之問題。透過跨文化哲學的方法 |
| 出版社 /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6267768136 |
| ISBN10 / | |
| EAN / | 9786267768136 |
| 誠品26碼 / | 2682965531003 |
| 頁數 / | 360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7×23×2 |
| 級別 / | N:無 |
| 重量(g) / | 619 |
| 提供維修 / | 無 |
導讀 : 導論(摘錄)
筆者在2016年出版了《道家的氣化現象學》一書,主要是希望能夠由存有論與現象學的角度重構道家哲學。筆者的淺見是,對於中國哲學來說,現象學所追求的實事(Sache)不是胡塞爾(Edmund Husserl)所說的「意識」,也不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說的「存有」,而是「氣」。該書是由氣化哲學的角度重新探討道家哲學的當代意涵。
然而,自2014年開始,筆者的研究領域已經開始由長達十六年的存有論研究,轉向到比較具體性的政治社會哲學向度。在《道家的氣化現象學》中已經有兩章接觸到此一道家新外王的領域(第七章〈批判的氣論〉與第八章〈莊子與當代批判〉);然而,這兩章牽涉到的比較是偏向「批判、解構」的部分,對於外王的建構部分探討較少。本書則是筆者2014至2024十年間,對於道家新外王「建構」面的思考。所謂的建構,主要是指與現代性相關的領域之開展,例如有用、政治、規範、技術、社會共在等方面。
首先說明本書的歷史背景。現代性是一地球性的事件,撼動星球上各國,至今仍餘波盪漾,仍是一未竟的事業。面對此一地球性事件帶來的壓力,保守主義哲學家思考如何由傳統智慧中開展出現代性價值。筆者寫作本書的核心關懷,即是百年來困擾各國哲學家的「傳統思想與現代性的關係」這一問題意識。在面對現代性時,保守主義哲學家如德國的海德格、中國的新儒家學派(如牟宗三)、日本的京都學派(如西谷啟治)試圖由西方哲學、儒學、佛學等傳統思想,探討傳統思想開出現代性的可能(晚期海德格也受道家影響)。在1930年代,三位保守主義哲學家幾乎都有後設政治學(Meta-Politik)的思考,亦即思考存有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本書第一章即探討海德格的「直通說」與牟宗三的「曲通說」(坎陷說)。牟宗三稱此為「新外王」之議題,意指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對西方文化在政治社會方面的優勢,中國文化如何開展出此時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民主與科學之問題。對此,牟宗三以「良知坎陷說」(或稱「民主〔科學〕開出說」)來回應。其後,學者續有努力,就儒家的新外王而言,鄧育仁《公民儒學》嘗試由現代公民哲學的角度開展儒學。就道家的新外王而言,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提出人文建構型的莊子,並提出「形氣主體」來建構莊子哲學的政治社會向度。本書對於新外王問題意識的開展,大抵是回應牟宗三以降諸位哲學家對於新外王議題的展開(尤其是道家方面),並希望在存有論與現代性之關係的議題上能有些微的推進。
本書的問題意識源自保守主義哲學家的新外王思想,本書的解決模型則源自另一思想資源,此即跨文化莊子學。約一百年前民國初建時,章太炎發表了〈齊物論釋〉,加上嚴復的老子研究,道家的「平等(不齊之齊)」、「自由」等概念,初步開展了現代化新外王與跨文化面貌。當然,那時候由於初步接觸西方哲學,跨文化的研究仍處於初創的階段。例如章太炎主要仍是以佛學為解莊基礎,而不是康德(Immanuel Kant)或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西方哲學。到了牟宗三、唐君毅這一輩新儒家學者,藉由英文閱讀西方哲學原典,跨文化的研究才慢慢有了新的開展,如牟宗三以康德作為中西哲學的橋梁。1980年代以降,留洋學者逐漸回國,對於西方哲學的吸收,漸漸進入可以以德、法原文研究的階段,對於儒家、道家的跨文化研究,也有了更廣闊的面向。時至二十一世紀,跨文化的莊子研究有了新的發展,楊儒賓稱之為「第三波莊子學」。此波的莊子研究,主要特點是以西方哲學為對照與概念資源,開展莊子思想的時代意義。其主要推手何乏筆於2005年開始,在中研院文哲所舉辦了一系列跨文化莊子研究工作坊,為臺灣引介法語莊子研究的思想。其主要焦點是莊子哲學如何與當代哲學思潮對話(如現象學、法蘭克福批判理論、歐洲漢學莊子研究等)。以何乏筆為中心所形成的跨文化哲學共通體,引入了畢來德(Jean F. Billeter)、孟柯(Christoph Menke)等關於莊子與新外王研究的資源,促成筆者得以完成本書。
筆者的新外王工作,主要是要連結存有論與現代性,或說是連結哲學與政治。畢來德提出兩種驚奇:哲學驚奇與政治驚奇。哲學是關於單一人沉思的存有論(以海德格為代表),政治是關於複數性群體的行動(以鄂蘭為代表)。畢來德的莊子研究強調莊子思想中的個人與新的主體性範式,傾向於高舉政治與人的複數性,而貶低哲學,此與筆者相異。筆者既未貶低政治,也不貶低存有論,而是希望能夠溝通兩者,尋找兩者的弔詭關聯。
關於現代性的議題,本書並無法關注所有的面向。本書分為「弔詭」與「共在」兩部分,但其實兩部分的內涵都牽涉到現代性。第一部分「弔詭」主要探討現代性中「有用」(第二章)、「政治」(第一章、第五章)、「規範」(第三章)、「技術」(第四章)等向度。第二部分「共在」則是關於現代性中的「社會」向度,闡述莊子哲學如何回應現代性共同體的問題。總的來說,這兩部分探討的是海德格所說的存有場所(polis)所包含各種文化領域在現代性中的展現。因此,本書可說是莊子哲學對於現代性政治社會議題由存有論出發而來的回應。
一、無用政治學:存有論與政治之間
本書名為「弔詭與共在:莊子無用政治學的跨文化對話」,其思想核心是莊子的「無用政治學」。「無用政治學」並不是經驗性的政治科學,而是類似海德格所說的「後設政治學」,探討的是存有論與政治的關係。
何謂「後設政治學」?此詞由海德格所提出,在1930年代初納粹興起之後,海德格領悟到《存有與時間》中的「此在」(Dasein)仍是太過於個人的,透過個人的決斷(Entschlossenheit)能夠達到本真性。此階段他歷經思考的轉向,也就是由個體轉向群體,思考國家、民族等集體之優先性,強調透過民族的決斷來達成民族的本真性。「此在」概念也由「個體的此在」,轉變為「民族的此在」。在海德格的遺稿《黑皮書》中,他於1932年首次提出「後設政治學」的構想(GA94, 124)。
海德格認為政治應該有存有論向度,而不僅是世俗的權力政治(Machtpolitik)或黨派政治(Parteipolitik)。「後設政治學」期待的是「存有的時代」之來臨,此「存有的時代」也稱為「另一開端」(anderer Anfang)。存有歷史是由第一開端(erster Anfang)到另一開端的歷程,形而上學必須深化為「歷史的民族之後設政治學」(Metapolitik des geschichtlichen Volks)(GA94, 124),也就是由第一開端到另一開端的具體實現過程。希臘人是第一開端,德國人則是另一開端,中間有羅馬人、猶太人、美國人、俄國人、中國人等集體概念。德國人所必須完成的歷史使命,即是透過革命而達到另一開端,國家社會主義則是完成這一使命的一種可能性。
後設政治學規劃德意志民族與國家的未來理想,也就是一種「精神的國家社會主義」(Der geistige Nationalsozialismus),「精神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之「庸俗的國家社會主義」(Vulgärnationalsozialismus)不同。海德格於1939年寫道:「在1930至1934年間,就存有歷史的觀點,我認為國家社會主義是通往『另一開端』的過渡階段。」(GA95, 408)這是海德格沉迷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因,因為這是實現理想的存有時代之必要階段。海德格的後設政治學是透過哲學革命去影響政治,這與柏拉圖的理想國當然很類似。為了「後設政治學」的政治理想,海德格認為必須透過國家社會主義者來進行民族革命,這也是海德格1933年投入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因。首先要有國家社會主義,才能產生一個新的德國。
後設政治學認為政治應該有存有論向度,海德格也用古希臘的polis概念去說明後設政治學之領域與層次:「屬於polis的有諸神和神殿、慶典和遊戲、統治者與元老會議、人民集會場與軍人、詩人與思想家。」(GA53, 101)Polis 不是現實具體的國家、城邦,而是人之歷史地居留之場所(乃至於一個民族的歷史性場所)。Polis不是某個文化領域(如一般與經濟、技術等並列之政治領域),而是「存有」,polis在此似乎就是存有的另一種稱呼。「政治場所」(polis)不是與國家機構、權力政治相關的,而是與存有相關的「存有場所」。海德格甚至認為自己是當時唯一的「政治家」(後設政治家),當然,這種政治是存有論的政治,而不是現實中的黨派政治、權力政治。
但是後設政治學這種連結存有論與政治的方式,認為存有論可以指導現實政治,最終卻遭到現實政治的否定。二戰之後,海德格不再堅持精神的國家社會主義,而轉向「無用的民族」之後設政治學。因此,海德格對於後設政治學的思考經歷兩個階段:中期的「精神的國家社會主義」階段與晚期的「無用的民族」階段。可以說,「無用的民族」是海德格對於「後設政治學」的最後話語。在中期精神的國家社會主義階段,海德格更關心政治領域;而到了晚期無用的民族階段,他轉而關懷現代技術之領域,較少關心政治,這與他中期在政治上的挫折相關。此階段海德格只能繼續期待德意志民族成為無用的、等待的民族,以此來駁斥納粹之有用性以及洗清自身的納粹疑慮,並且對當代世界的技術化傾向進行後設政治學之批判。本書的核心思想「無用政治學」,部分內容可以說是繼續闡發晚期海德格之「無用的後設政治學」(無用的民族)所欠缺的政治領域之討論。
探討完「後設政治學」的內涵,可進一步說明何謂本書的核心思想―「無用政治學」或「無用的後設政治學」?首先說明「無用」。《莊子》中有許多討論「無用」的段落:〈逍遙遊〉末段惠子與莊子辯論大瓠(大葫蘆)與大樹的無用,〈人間世〉匠石與大樹在夢中進行關於無用的對話,〈外物〉「黃泉故事」有莊惠之相關辯論:「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這段話明確地說明了無用如何作為有用的始源(Ursprung),也曾經被海德格寫下送給妻子。莊子之強調「無用」,與其時代氛圍之強調有用性密切相關。在戰國時期,「有用」成為時代總動員(Mobilmachung)的力量,這個力量擴散到當時各個空間,成為一種世界觀(Weltanschauung),例如知識分子的言論若沒有用(子言無用),等於被時代所放棄。《莊子》首篇〈逍遙遊〉最後的段落、若可以合理地將之視為全篇,甚至全書的主旨,即是莊子與惠施關於有用無用之辯論,「逍遙」作為「無用」(「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可以說是針對惠施「有用總動員」而提出的。莊子於全書之首篇即提出「無用有用之區分」,可見此一區分的關鍵性。關於莊子的「無用」思想,學界著墨已多,此處不贅述,轉而由海德格的角度說明無用與現代性的關聯。
最佳賣點 : 本書呼應近十年來台灣跨文化莊子學研究思潮之問題意識,探討道家哲學(主要是莊子)如何回應現代性之問題。透過跨文化哲學的方法,本書比較莊子與西方哲學家(如海德格、孟柯、鄂蘭、南希等)對於「弔詭」與「共在」的討論,使得本書具有國際研究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