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作為前瞻: 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
| 作者 | 陳恒安 |
|---|---|
| 出版社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抵抗作為前瞻: 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若歷史學無法獲得社會支持,那麼身處於記憶膨脹且意義紛歧的時代,我們是否能憑藉歷史學中的科學性來指引未來的記憶與遺忘政治?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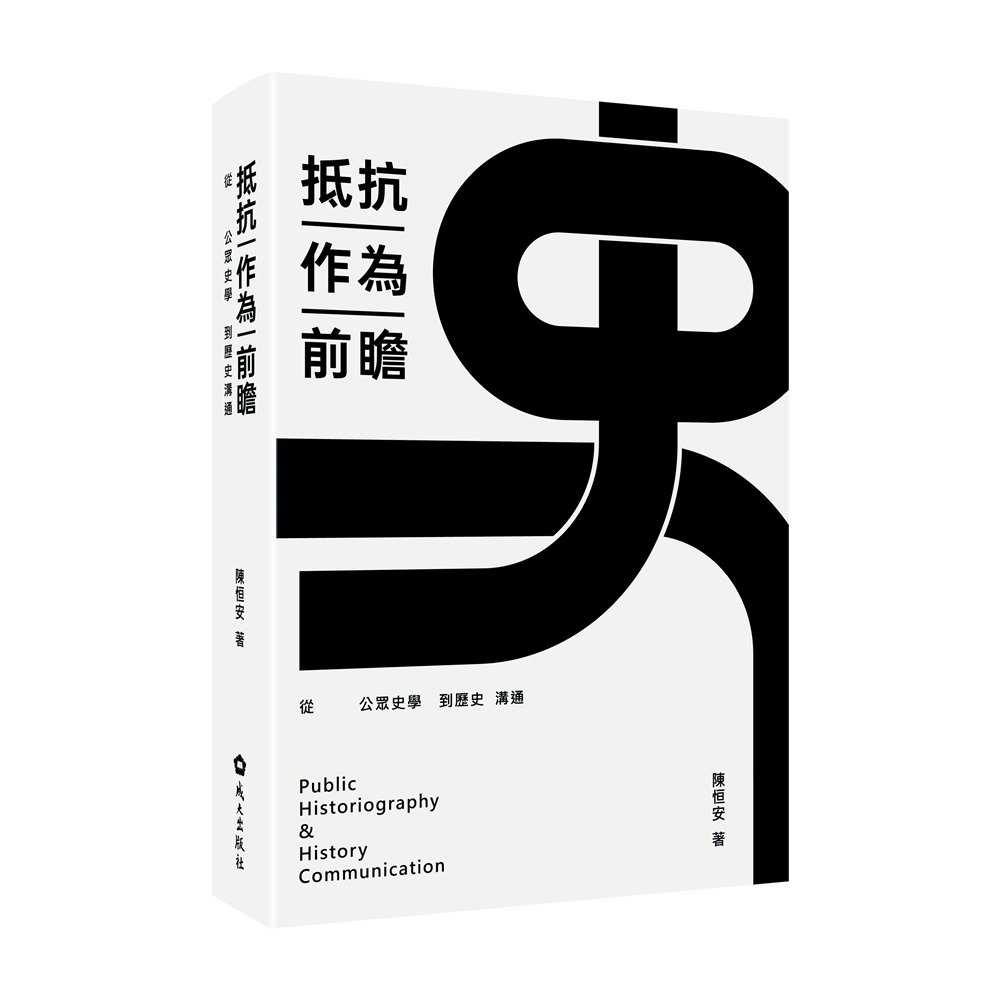
| 作者 | 陳恒安 |
|---|---|
| 出版社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抵抗作為前瞻: 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若歷史學無法獲得社會支持,那麼身處於記憶膨脹且意義紛歧的時代,我們是否能憑藉歷史學中的科學性來指引未來的記憶與遺忘政治?社 |
內容簡介 若歷史學無法獲得社會支持,那麼身處於記憶膨脹且意義紛歧的時代,我們是否能憑藉歷史學中的科學性來指引未來的記憶與遺忘政治?社會大眾究竟該擔心記得不夠多,還是記得夠不夠好?人們之所以叩問過去,正是期待從經驗中提煉出得以想望未來的素材。抵抗作為前瞻,意指我們應勇於嘗試將歷史學思考過去的方式,運用於前瞻個人、社會與世界的未來。對於歷史人而言,前瞻自身學科未來,更是責無旁貸。
作者介紹 作者陳恒安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系、生物學研究所、德國慕尼黑大學科學史研究所畢業。目前服務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近年研究興趣環繞在科技與社會研究、科技史、公眾史學、史學理論、科技溝通,以及博物館學相關領域。近年開設課程包括科學革命、達爾文革命、生態學與環境運動史、科技與社會研究、公眾史學等。
產品目錄 "推薦序走出歷史的活路:讀《抵制作為前瞻: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郭文華 建構批判、溝通與前瞻的臺灣公眾史學/張隆志歷史為何有大用的解謎書/謝仕淵致謝第壹章 導論一、前言二、研究問題的背景與任務三、問題與待解難題四、各章安排五、結論第貳章 公眾史學的發展:從科普、史普到知識溝通一、如何藉普及歷史知識以強化歷史學者社會參與二、公眾歷史學1. 英語與德語世界的進路2. 美國的發展與邁向國際3. 德語區的發展三、記憶膨脹下的歷史1. 記憶所繫之處與歷史的差異2. 歷史文化與記憶文化四、公眾史學在臺灣的初探1. 貝克〈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家〉與臺灣的公眾史學(1)臺灣的「貝克迷思」現象(2)關於貝克在史學史中角色的補充(3)貝克與英語世界公眾史學的關係2. 歷史學界的回應:課程、系所與學會3. 社會渴望歷史五、結論附論 今日,歷史學就是科學,不多也不少一、前言 二、歷史學與科學三、以當代為導向的科學史研究四、萊因貝格爾的嘗試五、萊因貝格爾的可能影響六、結論:萊因貝格爾與呂森第參章 博物館歷史學的知識論及方法論一、博物館歷史學1. 博物館的特色與功能2. 博物館中的「物」3. 博物館歷史學不可迴避的責任與主題4. 博物館歷史學如何落實於博物館二、行動中的地方文物館1. 「行動者網絡理論」與「交易區」的視角2. 從地方博物館與文化館到管地方文化3. 行動者網絡理論4. 「交易區」、「邊界物」與「互動型專家」5. 從「在地」到「再地」再到「在地」6. 一些地方案例的討論三、STS 與家鐵道博物館共創的嘗試1. 公共性作為天命2. 鐵道技術文化生態系3. 液態博物館的起始工作4. 充滿隱喻的鐵博Logo四、結論 第肆章 集體或採集的記憶:大學博物館中的大學歷史一、大學博物館中的校史展示:歷史行銷與歷史教育1. 校史與大學史的書寫與研究2. 從歷史行銷、大學社會責任(USR)到大學歷史責任(UHR)3. 從企業史再回到校史與大學史4. 大學博物館校史展場中的歷史溝通案例:成功大學博物館「成功的原點」 5. 從培養歷史的債感開始二、大學博物館中的歷史:殿堂或「歷史實驗工坊」?1. 歷史學實驗工坊:成大歷史文物館2. 我來、我見、我征服?北門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與醫療史3. 誰的記憶比較重要?從博物館到校園文化資產4. 不易面對的沉重歷史:歷史策展與歷史書寫的倫理三、結論:博物館中的「歷史正確」與其層次第伍章 具可讀性校史的書寫實踐與反省:以國立成功大學大學法人化與大學自主治理案的推展歷史為例一、校史書寫者的倫理困境 二、法人化與五年五佰億計畫的結合三、 從大學法人化(incorporation)轉為大學自主治理(self-governance) 四、大學自主治理的推展與結束五、鴨子划水到最後的投票六、結論:未來的希望形上學附錄:成功大學推動法人化與自主化歷程附論 校史書寫行政上的難題第陸章 黃金大稻埕:從「金瑞山」談個人記憶、家族記憶或公眾的歷史一、前言二、歷史的債感與情感三、記憶熱潮四、為什麼要寫金瑞山?五、稻江金商:金瑞山銀樓以及「金子案」1. 金瑞山的建立與「金塊密輸出案」(第一次金子案)2. 第二次「金瑞山金子案」3. 金瑞山與大稻埕的日常生活(1)金瑞山的宗教生活與寺廟的關聯(2)食阿片與戒阿片(3)金瑞山的日常生活軼事六、結論 第柒章 結論一、抵抗宣言二、歷史前瞻三、公眾歷史1. 說故事與說歷史2. 歷史中的情感四、歷史溝通1. 歷史溝通者:互動型專家2. 博物館作為「概念方法」(conceptual methodology)3. 大學史與校史4. 家族史五、結論1. 每個人必須是他自己的史家2. 理論化之必須參考文獻索引"
| 書名 / | 抵抗作為前瞻: 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 |
|---|---|
| 作者 / | 陳恒安 |
| 簡介 / | 抵抗作為前瞻: 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若歷史學無法獲得社會支持,那麼身處於記憶膨脹且意義紛歧的時代,我們是否能憑藉歷史學中的科學性來指引未來的記憶與遺忘政治?社 |
| 出版社 /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6269862726 |
| ISBN10 / | |
| EAN / | 9786269862726 |
| 誠品26碼 / | 2682613909000 |
| 頁數 / | 488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1*15 |
| 級別 / | N:無 |
| 提供維修 / | 無 |
推薦序 : 推薦序
走出歷史的活路:讀《抵抗作為前瞻: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
郭文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看了書稿最後的樣子,覺得只有你能寫序,可以嗎?」數個月前恒安來訊說起他的新書《抵抗作為前瞻: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以下稱《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邀我寫些感想,我受寵若驚。
恒安的說理功力早有定評。他是國科會《科學發展》月刊「科技與社會」專欄(2020 年配合刊物轉型停刊)的「長工」,近二十年來處理編務瑣事,不時還得自己跳下來救火,下筆又快又好。他也主持《成大校刊》,「主編的話」是我的愛讀。在裡面恒安時而發抒、時而沉思,文史哲文獻信手拈來毫不費力,科學新知也難不倒他,讓這本校園刊物卓然不群,與其服務的頂尖大學毫不遜色。我一方面為能先睹為快這部作品感到榮幸,同時也湧起我們共同的學習背景與歷程。或許作為這段跨域實踐的見證,是這篇小文的因緣吧。
恒安與我不算典型的人文社會人。我們出身生醫,在醫學史交會,回國後各自開展生涯,在高教體系安身立命。恒安進入臺灣最老的國立大學之一,在最傳統的人文科系中培育人才。我回到母校,側身全台唯一,標榜跨域、最新最潮的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的研究所,從科技體制出發,反省與展望它與社會的型塑。像我與恒安這樣隨順漂流,演化成不同學術物種的歷程,有種說法是「棄 X 從 X」,但我們都清楚是那個時代造就了我們,一個轉校、換系、串聯讀書會不稀奇,街頭「上課」不突兀,人人期待改變,視野遠大,自許成為既抵抗又前瞻的公眾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解嚴世代。
話說回來,恒安與我畢竟一路平順,有危機也化為轉機,是務實的夢想家。我們沒陷在文理分家,各走各路的糾葛中,也不想被輕易安上「棄 X 就 X」的高帽。於是,在跨領域口號尚未如此浮濫的世紀末,我們著陸於通識中心,見證自由派先行者、校長,與有志之士所領導的大學改革。在標榜不破不立的學術刊物如《當代》、《島嶼邊緣》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及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社區大學之間,通識是體制內的學術實踐場域。以「通」為名,它是科技與人文社會的「交易區」(trading zone),科會「科技、社會與傳播」學門召集人,這樣看似不搭嘎的守備位置。
《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要從這樣的跨域背景來理解。它引經據典,知識含金量毋庸置疑(特別是國內較少介紹與討論的德語文獻),但它並非象牙塔的產物,只想與歷史學界對話。這本書體現作者的學術實踐歷程,訴求的是下一代的歷史人:不管他們是正迷失在專業之中,或者猶豫在文理之間,抑或是將跨出大學舒適圈,惶惶於畢業即失業。這樣說,《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不是鼓吹歷史多好多棒的同溫層作品,而是教戰手冊,以作者親身經驗為基底,分享作為志業的歷史要如何走下去。
這個特色從其書寫便可看到。《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文字清晰明朗,但篇篇長篇大論,擲地有聲。多數章節為成果報告,是學術生產體制下的產物,但細究內容,會發現作者沒有因此偷工減料或減少力道,文筆生猛直率。本書有作者執行相關計畫,與大學、教育部或國科會互動的歷程,更循循善誘,隨處註解學術討論與參考資料(比方說接在第二章後面很長的附論),翻轉在跨域計畫下人文學者並不是只能「take it or leave it」,而有迎接挑戰,發揮創意的空間。《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既是研究的歷史,也是 STS 的論述。它並非要歷史工作者無所不能,而是演示在既有知識社會體制下要如何想問題、找解方。
也因此,本書重點不是看作者講了什麼,而是他為歷史工作「翻轉」出什麼,以下分享所見所得。首先是立場。透過近年學界討論的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作者由「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家」的提問(纏繞在歷史相對主義的「貝克迷思」),提出用「知識溝通」(knowledge communication)解放歷史研究,進而自我脫困(見第一章)。如其堂堂正正的宣示:
其實,無論未來的工作場域在哪裡,或者工作的性質是什麼,歷史學系的畢業生都應該首先是一位稱職的「歷史溝通者」(history communicators),只是所處職場、任務與使用工具不同而已。如果這麼想,有許多過去大學歷史學系或許未曾留意的事情就成了未來可多關注的利基。例如:地方史、企業史、家族史、校史、機構史、歷史小說、歷史電玩、文史旅遊企畫等的廣義書寫。歷史溝通者可為這些單位機構萃取文化歷史中的關鍵精神,促進認同歸屬,創造機構品牌特色。或者,作為歷史溝通者更可參與政策研討、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文化資產,甚至歷史療癒等工作。當然, 歷史行銷(history marketing) 與歷史娛樂(histotainment)更與所謂的產業及就業有更直接的關聯。
以上不是「就業輔導」,勸歷史系學生放下身段混口飯吃,而是點破他們要透過貼近社會脈動來反省本身的專業。他進一步說明:「在一個寫歷史不需證照的世界,難道歷史系/學不該反思自己賴以為基礎的一切?否則,如何自我辯護?難不成每當社會有人質問歷史是什麼,或唸歷史學系有什麼用的時候,歷史系/學只能老話重提,不斷述說人文很重要,忽視人文價值多不符合文明社會的理想等。」
在標舉公眾與溝通後,歷史研究的「what」重心也就轉進成更深沉的「how」與「why」的思索。《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並未抽象演繹這些問題,而是具體用三個實踐場域,呈現歷史工作者在科技史研究(第二章)、博物館研究(第三與第四章)與大學史書寫(第五章)的第一手衝撞經驗,有掌故、有分析,旁徵博引,讀來很過癮。
第一個是作者從科普書寫來切入的「歷史普及」場域。從局外人的角度看,作者指出一個歷史學的弔詭情境:歷史本以說故事見長,但竟要向科普取經,才能理解「史普」的意義?如果要為此辯護,或許有人會提到過去的《歷史》月刊,現在的「故事」或者是「歷史學柑仔店」的平臺,說歷史學並未偏廢普及。但作者用更上位的「歷史記憶」與「歷史文化」,指出如何讓歷史知識流動,透過書寫與閱讀產生溝通,才是重啟歷史文化的起點。
這裡有概念的轉換,也有戰略的思考。這樣說,科普在國內沒有專業系所,必須不斷透過論述與實作建構必要性。因此,雖然這些年臺灣科普的推動有許多困難(一部分與歷史學類似),但在此之間的各種嘗試卻已足夠給歷史界不少有用的理論根據與策略,比方說作者所引述張隆志教授以「知識民主化、學術研究公共化,以及提升公民歷史素養」為宗旨的公共史學。如此,這個打破專家與常民邊界,活潑的歷史,就不再拳拳交由學者操刀,「以宣示、背書與撰述美好未來的許諾形式出現」,而是如科學一樣,可討論、可展開,「相互撞擊、激發對話進而產生各種意見」。這也是打造「創造中的歷史」(history in the making),對歷史公民的邀請。
第二個實踐場域是博物館。博物館兼具展示與教育功能,本身也是觀看與玩賞的空間,是歷史界相對陌生,但在科普與科教領域長期關注的場域。在《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中作者顯示他在國內外博物館的田野功力,帶領讀者思考「博物館的歷史學」或者更具體的「博物館作為方法」。有別於博物館學或歷史學的論述, 作者以物件為中心, 用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的物政治(Dingpolitik) 與邊界物(boundary object)切入,指出物件在翻轉博物館公眾敘事的角色,值得我們重視。
這裡補充一個案例。以國立歷史博物館 2024 年的重開幕來說,該館是「南海學園」的一部分,也是許多五、六年級生的回憶。2018 年起該館進行整修,歷時六年,但迴響卻不如預期,有指出展示定位不清者,有質疑文物種類貧乏者,有批評動線與配置混亂者。這裡且擱下這些批評,從博物館的歷史學看,有兩個展示有翻轉意義,但較少為人著墨。第一是建築物。國立歷史博物館是戰後的產物,但其建物可追溯到 1916 年因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所興建的迎賓館,隨著國民政府 1955 年沿用創立文物美術館,即歷史博物館的前身起,這棟建築物如變形金剛一般逐步改頭換面,從日式會堂轉化成中式宮殿建築。在展覽中,參觀者不但從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印象裡的歷史博物館,更可以看到館舍整修的一大亮點—屋瓦。從顏色到式樣到鋪設,這個修復重現傳統工藝,也是戰後技術史的縮影,更是精彩的文物展示。
第二是「中華文物箱」。這是 1969 到 1986 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承接的企劃,挑選與製作文物複製品與徵集當代書畫,以配合在國外宣揚中華文化。這些「類文物」一方面呈現戰後臺灣徘徊在國際政治與定位的糾葛,一方面這些物件的創造(如何複製與仿舊)與流通(如何使用與詮釋)本身也成為歷史,值得繼續探究。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在書中指出的「用博物館寫歷史」,充分地為這兩個用心的展覽做註腳,如其所言:博物館歷史學「必須更有意識地,亦即更主動地引領社會面對困難的過去(difficult pasts),不受歡迎的遺產(undesirable heritage),甚至明知觸碰即會引發爭議的危險的過去(dangerous pasts),以及因分享權威(shared and sharing authority)之後所帶來的多元爭議,並致力開啟並維護知識民主之後的溝通對話機會。」
第三個實踐場域是大學。對有行政經驗的我來說,這部分牽涉知識溝通的學理與實踐,更有組織倫理的考量,讀來特別有感。順著公家單位限制下歷史工作者如何取捨物件,調整步伐,克制所謂的「知識傾倒熱情」,作者在這個場域的反省是做為歷史教授、博物館一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多重實踐。比方說,如果博物館的展示目的是呼召與邀請參觀者,那國立大學校史的收藏標準為何?呼召對象是誰?目的為何?當然,臺灣的校史單位大多人才不足、經費短缺、展示乏善可陳,但就算歷史悠久的大學的博物館,硬體看起來四平八穩,但展示稍嫌平淡,無法匹配它們在臺灣高教的地位。而一些大學的校史則以宣傳政績為導向,敘事浮誇虛矯,談不上深度,格局更不用說。
這樣說,在通識改革風起雲湧的九○年代,大學是社會改革的重心,常見到像「大學之理念」這樣的期許。相對於此,現在的大學將社會責任與永續朗朗上口,但似乎少了些自我要求的動力,隨國際排名與指標亦步亦趨。對此,作者並沒有「事不關己」,以教授的高姿態哀嘆大學的淪喪,而是正視大學的經營現實,以「入世」態度活用大學社會責任,讓校史既是歷史行銷(historical marketing),也是歷史教育。作者並非光說不練;第四章後半他出入策展人與歷史學家兩個角色,分析他所參與的「成功的原點」展覽,展現精彩的博物館歷史學演練。第五章聚焦大學法人化與大學自主治理案的論爭經緯,不但為本世紀的成大留史存真,更讓這段過往超越單一學校論述,對爭取國際一流與頂尖卓越經費的國立大學,甚至對近二十年高教體系的發展都有啟示。筆者在擔任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長期間承接校史業務,之後規劃相關專書,對學校特性、創校使命與時代意義等有過一番摸索。這次有機會在研討會與個別請益之外,更全面地了解作者對大學的「全方位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十分欽佩。此外,筆者在圖書館服務,對附論的「校史書寫行政上的難題」也深有所感,期待未來作者對此繼續深論。
《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的最後一章看似獨立,是作者陳恒安的家族過往,但放在歷史工作者自我脫困與呼召歷史公民的脈絡中,理論意涵油然而生。恒安不掉書袋談納粹記憶與世代轉型正義,而是透過現在沒有太多人知道的大稻埕金瑞山銀樓案,因被當局指控「操縱委託黃金,意圖私利致亂金融」而停業逾一甲子的知名銀樓來示範公共史學實作,也為本書畫龍點睛,演示來自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方向上「說自己故事」的重要。
當然,現在已經有許多懷舊社群網站,人們透過分享故事互動,但恒安想說的更多。他以「歷史的債感與情感」的制高點,論證個人史不是將自己的事寫下就算,取材方式與下筆輕重都攸關歷史的實作倫理。以金瑞山銀樓案來說,恒安不算事主,也非純然的「公親」,因此在專家常民的劃界工作(boundary work)外,恒安以「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的位置,完成這個敘事。其中,歷史工作者介入的原因不只是「尋求真相」的抵抗,也是留下集體記憶的前瞻,是「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意義。這並非孤例。有識者挺身面對德國的世代差異與誤解,齊邦媛不願父親被說成遁逃至臺的「巨流河」敗戰者,恒安不忍看到金瑞山案當事人的苦情遭人遺忘,都證成作為社會行動的多元歷史的必要性。
這也讓我想起我關注的安寧課題。幾次與恒安走在舊台北市區,所謂的「三市街」時,恒安有時若有所思,冒出「知道這裡過去是哪裡嗎?」之類的感嘆,令人摸不著頭腦。直到讀完這本書,才讓我以讀者身分進入恒安先前欲言又止,或者一言難盡的過往。作為專業歷史工作者,恒安的「困學」與「治史」是一體的兩面。歷史書寫不只是為了滿足學術興趣,也是自我療癒與超越,更是歷史文化的基礎。近年來由於 STS 研究者的引介,兼顧可行性,從臨床湧現的「照護的邏輯」(logic of care)呼聲四起。但嚴肅地說,要讓醫病放下各自身段,成就有意義的決策共享(shared decision making),需要更廣褒的醫療文化與生死素養來支撐。對此,從《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啟發的善終普及與知識溝通,似乎開出一條通貫醫學教育與職涯發展,不勉強的脫困之道,值得我們深思。
終究,多年跨域後我與恒安這兩位「轉學生」在此會合。謹以此小文攀附驥尾,也希望讀者們在書中找到各自的脫困心法,走出活路,在知識大海中悠游自在。
最佳賣點 : "若歷史學無法獲得社會支持,那麼身處於記憶膨脹且意義紛歧的時代,我們是否能憑藉歷史學中的科學性來指引未來的記憶與遺忘政治?社會大眾究竟該擔心記得不夠多,還是記得夠不夠好?
人們之所以叩問過去,正是期待從經驗中提煉出得以想望未來的素材。抵抗作為前瞻,意指我們應勇於嘗試將歷史學思考過去的方式,運用於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