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lobal In the Local: A Century Of War,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 作者 | 張信 |
|---|---|
| 出版社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全球變化與鎮江: 近代中國的戰爭、商業與技術:本書以長江下游的城市鎮江為例,深刻剖析中國地方社會在1830年代~1930年代這一百年間,如何與全球三大變革的互動:包含鴉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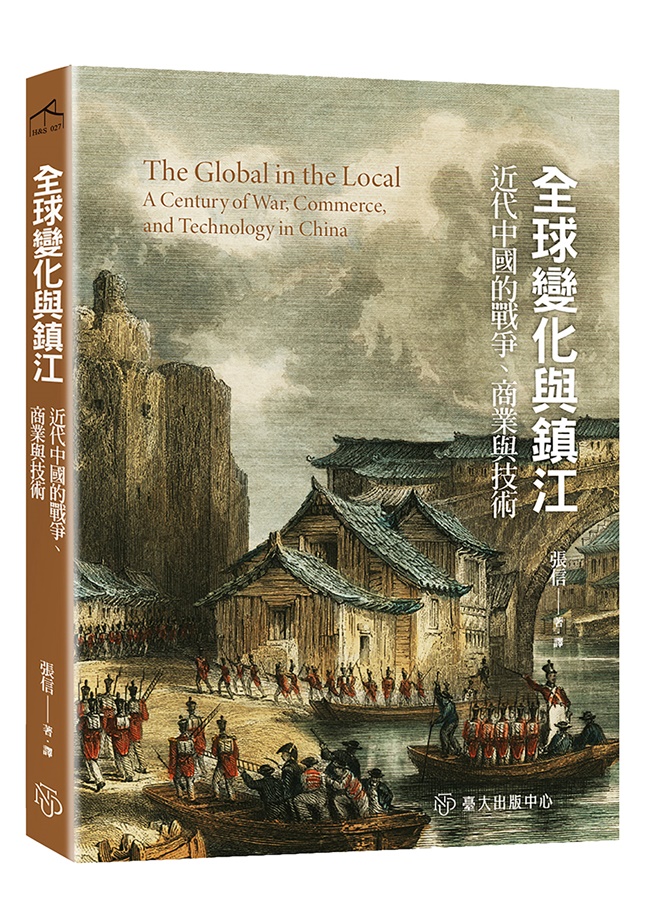
| 作者 | 張信 |
|---|---|
| 出版社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全球變化與鎮江: 近代中國的戰爭、商業與技術:本書以長江下游的城市鎮江為例,深刻剖析中國地方社會在1830年代~1930年代這一百年間,如何與全球三大變革的互動:包含鴉片 |
內容簡介 本書以長江下游的城市鎮江為例,深刻剖析中國地方社會在1830年代~1930年代這一百年間,如何與全球三大變革的互動:包含鴉片戰爭的爆發、以上海為中心的商業網絡的形成,以及蒸氣航行技術的引入與應用。這些變革不僅對當時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深刻影響,也對中國地方社會提出重大挑戰,重塑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本書從常民的視角呈現鴉片戰爭的衝擊、中國貿易體系的轉變,與蒸氣航行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改變。本書旨在深入研究全球和地方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最終如何交融成一段相生相長的歷史變遷過程。
作者介紹 張信1977年通過中國全國高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1984年在美國新墨西哥大學任教一年,隨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主修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分別獲碩士和博士學位。現任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講授中國史、全球史和亞洲史。中英文專著包括: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Henan、《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The Global in the Local: A Century of War,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以及《地方視野中的全球變遷》。
產品目錄 致謝中文版序導論第一章 日漸成形的全球與十九世紀前的中國第一部分 戰爭是負面接觸的方式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的鎮江第三章 鎮江之戰第四章 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第二部分 跨區域貿易和亞洲貿易網絡第五章 十九世紀的貿易體系轉型第六章 連接南北貿易第七章 上海貿易網絡第三部分 中國社會與西方技術第八章 蒸汽航行與西方經濟擴張第九章 小蒸汽船時代第十章 外來技術與地方社會結論主要原始資料引用書目索引
| 書名 / | 全球變化與鎮江: 近代中國的戰爭、商業與技術 |
|---|---|
| 作者 / | 張信 |
| 簡介 / | 全球變化與鎮江: 近代中國的戰爭、商業與技術:本書以長江下游的城市鎮江為例,深刻剖析中國地方社會在1830年代~1930年代這一百年間,如何與全球三大變革的互動:包含鴉片 |
| 出版社 / |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3508137 |
| ISBN10 / | |
| EAN / | 9789863508137 |
| 誠品26碼 / | 2682555986008 |
| 頁數 / | 320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4.8×21×1.7 |
| 級別 / | N:無 |
| 重量(g) / | 440 |
| 提供維修 / | 無 |
自序 : 中文版序(摘錄)
社會學家邁克爾.布拉沃伊(Michael Burawoy)曾呼籲我們去研究「全球民族誌」,去瞭解全球變化過程中,人們真實的生活體驗和經歷。我的研究是對這一呼籲的回應,但不同於布拉沃伊僅關注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後現代世界」,我將目光投向中國社會,研究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普通人的生活,以此來揭示在這一時期全球變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是如何與中國地方社會的變化交融的。
我的主要目的是捕捉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變化的動態。我認為這些變化本身,是在全球範圍內歷史變遷與中國地方社會內部變化相互交融的基礎上滋生的,而這些地方社會的變化又以中國文化為背景。在本書中,我不僅會闡述中國社會如何在全球變遷中發展,還會展示各階層人們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與全球變化磨合。在這一磨合過程中,他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來推動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
這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中國地方社會在1830年代至1930年代這一百年間,如何與三個主要的全球變化互動。這三個變化為近代帝國主義(modern imperialism)的興起、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速,以及西方國家機械化技術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傳播。在中國,這些變化以以下幾個形式呈現:西方工業化國家發動的鴉片戰爭;以上海為中心的亞洲貿易網絡的形成,從而引發了中國內部跨區域貿易的轉型;和西方蒸汽船技術的引進和應用。這些變化與同一時期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的情形相呼應,其中包括西歐國家、美國和日本爭奪對亞洲(中亞和東亞)、大洋洲和非洲領土的直接控制權,東亞貿易網絡的崛起並向亞洲其他地區擴張,以及蒸汽船在大西洋、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尼羅河沿岸的運用。這些變化不僅給中國地方社會帶來了一連串挑戰,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熟悉的生活環境,儘管在某些情況下為普通人帶來了新的生活機會。本書旨在探討這些全球變化如何與中國地方社會內部的變化結合,以至於最終凝聚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變遷過程。
這項研究基於我對全球和地方關係的理解。我認為全球和地方是一個整體,而全球變化是透過地方社會的變化來實現的。全球變化源於每個地方社會內部,既作為地方社會變化的一部分,也存在於「全球與地方聯繫的多樣性、重疊性和在各領域內的延伸」中。只有當全球變化納入地方變化時,全球變化才真正成為「全球性」的。作為十九世紀全球變遷的一部分,包括近代帝國主義的興起、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和西方工業化技術的傳播,全球變化的結果是使各地區和個人之間,以及不同文化、社會和遙遠的地方之間互聯、互通和互動的增加。這些變化既不源於西歐國家,也不基於歐洲文化。
同時,我也認為全球和本地之間的互動既不是全球接管本地(如喬治.里策﹝George Ritzer﹞認為的那樣)導致不同地方社會同質化,也不是不同地區之間衝突日益加劇(如塞繆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認為那樣),導致所有地方社會的異質化。這種互動是全球變化和地方社會之間的磨合過程。在這個磨合過程中,全球變化會逐漸滲透到每個地方社會,而每個地方社會也會在與之積極互動中逐漸成為其一部分。最終,兩者會融為一體。也就是說,當全球變化改變了人們原有的生活狀態並對其造成破壞時,人們為了生存會做出各種努力,規避這些變化帶來的困難,同樣也會利用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機遇來改善自身處境。因為在每個全球變化的表面下,存在著人們求生存的本能和改善生活的願望、努力和能力。這些本能、願望和能力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驅動力。在這驅動力下,人們透過改變每個地方社會而最終改變全球。
因此,我不同意包括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在內的混合化理論的倡議者的觀點,因為他們往往將地方社會視為全球變化的「適應者」,或者說在將全球變化納入人們生活的過程中,起到「適應性」角色的社會。相反,我認為人們是全球變化的積極參與者。在這方面,我贊同拉尼.魯布迪(Rani Rubdy)和阿爾斯古夫.盧布納(Alsagoff Lubna)對混合化理論的批評。和他們一樣,我也認為人們有能力「根據他們自己的本地框架和傾向」,根據自己的需求、欲望和利益創造性地參與全球變化。
我根據以上概念來理解全球和地方之間的共生(symbiotic)關係。我把它們看成是一個連續體,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分割和對立的二元體。12我是基於對全球和地方之間關係的這種理解來體會羅伯遜所說的「全球只體現在地方」的涵義。
最後,關於全球變化的結果,我和瑪律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以及大衛.赫爾德(David Held)及其同事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們都認為全球本身「體現了社會關係和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空間組織的轉變」。但是,我強調全球變化對人們之間的經濟、技術、政治、文化和社會聯繫產生了特定的影響,不僅在一個特定地理位置內部,而且在每個地理位置的內外之間。同時,我不像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那樣,將全球化視為現代化的完成。相反,我認為全球變化是長期歷史變遷的一部分,始於世界各地,並在每個地方社會中發生。
為了瞭解中國地方社會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如何與全球變化交融,我著手了以下研究。在這一時期內,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演變。我想向讀者展示中國老百姓是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生存下來的。他們不僅面對挑戰,而且成功地駕馭全球變化所帶來的機遇,改變自己所處的地方環境,並由此使整個中國社會走上了其獨有的近代化道路。為了更好地讓讀者理解我這本書的理論立足點及其意義,我在此書的中譯版中增加了這一序言。在此,我將梳理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近幾十年的發展軌跡,讓我的讀者們看到近些年,西方學者如何透過各種努力最終擺脫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觀,並因此讓我有機會從全球和地方的雙重角度來探討中國歷史。
內文 :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的鎮江(摘錄)
在開始研究鎮江戰爭之前,讓我們先簡單瞭解一下鎮江的歷史和居民。我們會發現,鎮江不僅在十九世紀前的九大宏觀區域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一個歷史悠久、充滿生氣的居住地。可是,近代帝國主義的出現卻使得這一切遭受到毀滅。現在,讓我們從鎮江作為一個渡口的歷史開始敘述。
作為海之門的渡口
鎮江是位於長江下游的一個城市,位於當今江蘇省的西南部。隨著跨區域貿易的發展,它與長江沿岸,特別是長江下游的其他城市,幾乎同時出現。雖然在十九世紀之前,這些城市中的大多數仍然是小型或中型城市,但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鎮江、揚州和南通等城市在規模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長江是世界第三長的河流,橫貫中國,西起今天的青海省,東至上海市。它的上游是從其發源地至宜昌(在湖北),中游在宜昌和湖口(在江西)之間,而下游則從湖口一直往東流到太平洋。儘管西方人通常稱之為「揚子江」,但大多數中國人稱其為長江。
鎮江位於長江下游,這個地區本身是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地區之一。該地區大約在西元220年的東漢末年開始發展,並在宋朝時期成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中心。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它不僅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也是「城市化最明顯的地區」。直到晚清時期,長江下游仍然是全國商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
在中國,人們通常稱這地區為「江南」。1645年,清朝在該地區建立了江南省,並於1665年將其一分為二,分別成為安徽省和江蘇省。從那時起,「江南」一詞所指的就是包括今天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上海、嘉興、湖州和杭州等城市的地區。透過東漢和北宋之間發生的三次從北向南的人口大遷徙,該地區成為這些北方移民的主要居住地。這幾次遷徙不僅使江南的人口增加,還為該地區注入了新的生活方式、農耕技術和各種文化元素。例如,新的移民促進了江南原有耕作方式的改變,從而將粗放式耕作轉變為集約式耕作,並因此極大地提高了水稻產量。
在春秋戰國時期,鎮江以東的長江下游一段呈傾斜的V字形,向東通向中國海,這個地方被稱為「海門」。這個V字形正好處在河流和大海的交匯處,因此被視為重要的地理位置。西元1300年左右,長江上游淤泥的堆積使得海門變窄,並逐漸向東移動。
在西周時期,現在的鎮江是周朝王室的一個分支設立的駐軍地。在秦朝和西漢之間,連接長江下游南北的唯一通道是長江南邊的「京口」和北邊廣陵之間的渡口。因此,京口成為南北方向過江的必經之地。三國時期,孫權在京口的北固山前建造了一個類似金屬容器形狀的城池,據稱這座城池是現在鎮江市的前身。
隋朝修建大運河,顯然提升了鎮江在王朝眼中的地位。隋朝第二位皇帝隋煬帝修建運河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能夠巡視南方並將穀物從經濟發達的南方運到新的都城洛陽。為此,他決定疏浚現有的運河並開發新的部分,最終將整個運河從今天的北京一直延連接伸到現在的杭州。
大運河分為四個主要部分(這些部分不包括連接長安和黃河的獨立運河)。京口坐落在其中一個部分——江南運河的入口處,而江南運河可以容納長200尺、寬50尺、高45尺(1尺等於37.1475公分)的船隻。由於大運河連接了當時全國的五大河流——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鎮江成為全國最廣泛的水路網絡的一部分。鎮江位於長江和大運河的交叉口,因此顯然處於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真正使鎮江成為長江上一個繁忙城市的是漕運的開始。
鎮江的崛起和漕運
雖然在之前每年春秋兩季都有貢糧運輸,但直到大運河修建後,大部分貢糧才透過水路運往王朝的首都。在隋朝和唐朝初期,鎮江成為漕運的第二大轉運中心。然而,漕運在唐朝末年衰落,並在五代十國時期因各方勢力的紛爭而暫時停止運作。
北宋繼承了唐朝的貢糧運輸方式。在重新規劃河流和運河的運輸路線後,北宋王朝很快恢復漕運,並開始將貢糧和其他商業物資透過大運河從長江下游地區運往國都汴京(今開封)。透過這個運輸系統,來自東南地區的貢糧首先在長江以南的各個地點聚集,然後透過大運河到達北方。雖然當時鎮江並不是各路商家的貨物採集點,但它是江南漕運船隻直達大運河北端的必經之地。正因為如此,鎮江成為漕運的繁忙之地,以至於當地官府不得不建造一條單獨航道,以緩解船隻從城市進入大運河所造成的壅堵。
北宋末期,由於金朝(中國東北女真族所建)不斷騷擾導致長江以北的大運河中斷,揚州在漕運中失去原有的地位。但是,這反而增強了鎮江在漕運中的地位,因為鎮江位於長江南岸。特別是南宋時期,隨著王朝水路運輸的重組和新首都臨安(今杭州)的建立,宋朝開始依賴江南運河向首都運輸貨物。江南運河因此成為連接臨安和長江上下游地區的重要紐帶,而鎮江則是長江下游地區漕糧運輸通往臨安的必經之地。鎮江因此成為長江下游地區最繁榮的城市之一。
元朝在大都(今北京)建都,因此放棄了修建大運河的初衷:將貢糧運往開封或洛陽。為此,元朝將運河改道,使其直接從東南向東北延伸,而不是往西北方向。可是,隨著時間推移,會通河變得越來越淺,其中有幾段已被淤泥完全封閉。因此,元朝開闢了一條海路,讓漕船由黃海和渤海到達首都。由於海路開通,鎮江不再是漕運的必經之路,因此在漕運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明朝初期,當海上貿易被禁止時,鎮江曾有機會重新恢復其在漕運和大運河南北貿易中的地位。但是,明太祖將首都遷至應天府(今南京),使得透過南北運河運送漕糧不再必要。因此,沿著南北運河的貿易活動也減少了。此外,由於運河長期未經修繕,長途販運商人開始選擇其他貿易路線。這兩個因素共同導致了鎮江重新崛起的推遲。
當明成祖將首都遷至順天府(今北京),並將運河運輸漕糧作為王朝首要事項之一時,鎮江的情況立即發生變化。明朝皇帝考慮繼續採用前朝的方式,將海路與大運河結合起來。但是,由於日本海盜對海上旅行造成危險,他放棄了這個想法。對他來說,唯一的選擇似乎是重建大運河。因此,大運河再次成為自明成祖以來漕運的主要依靠,這一舉措使運河得以延續多年。即使在黃河累積大量淤泥、航道經常變化、河岸需要不斷修復的情況下仍是如此。
在這些變化中,鎮江恢復了在漕運中的原有地位。由於瓜洲渡口在鎮江和揚州之間更為安全、方便,大多數運輸船隻透過這個渡口渡江,直到多年後瓜洲渡口的水位變得太低,無法通過為止。因此,鎮江開始在明朝中期以降的中國跨區域貿易中扮演南北連接的重要角色。
跨區域貿易中的南北連接
明朝禁止海上貿易時,中國已經開始出現大規模商業化,而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這種商業化基於宋朝早期的經濟擴張,以長途貿易體系為主導。這種貿易體系使得不同貿易區域間的糧食、穀物和奢侈品交換成為可能。其興起受益於交通條件的改善、國外白銀的湧入、紡織業的出現,以及王朝對市場控制的鬆動。同時,農民經濟也逐漸脫離自給自足的形態,開始依賴市場交換以滿足生活需求。這一切為鎮江提供了成為南北跨區域貿易關鍵環節的機會。
對鎮江的商業化產生極大影響的是經濟作物種植的崛起,其推動了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據估計,到明朝中期,廣東有40%到70%的農民已經將他們的農業生產投入到甘蔗種植中。在北方,棉花種植占據20%到30%的農田,從而取代糧食。北方很多地區也因此成為全國最好的棉花生產地之一,僅次於江南地區。到十八世紀,水果和菸草成為廣東和福建的主要經濟作物。但最突出的商業轉型是江南開始大量生產絲綢和棉花。
以往的江南是一個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區域。自唐朝起中國的經濟中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後,江南一直是最重要的貢糧產地。江南的稻米主要透過大運河源源不斷地被運往首都。這一切在明朝中期後開始發生變化。儘管蘇州仍然是全國稻米貿易的中心,江南則開始逐漸失去其稻米產區的地位。相反,儘管那裡的貢糧仍然繼續被輸往首都,江南地區自己卻不得不從四川、湖南、安徽和江西等地進口稻米以滿足當地人口所需。其中最主要的成因是:經濟作物的生產產生了大量的收益,因此促使大多數農民從稻米種植轉向絲綢和棉花產品的生產。
江南這一變化所產生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波及了整個中國。由於全國各地在商業化過程中的財富累積,特別是對絲綢和棉花產品需求的擴大,使得在江南地區生產絲綢和棉花產品比種植水稻更有利可圖。為了應對市場對絲綢的高需求,該地區的農民轉向養蠶。他們利用此所得的高額利潤購買了化肥、優質蠶繭、桑樹苗以及養蠶和繅絲用的木炭,以提高絲綢產量。就此,江南很快成為全國絲綢和棉花的生產中心。但隨之而來的是,在出現紡織業的同時,江南以純水稻種植為本的農業則喪失殆盡了。
與此同時,由於經濟作物生產的強化和人口增長,江南成為一個從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四川、湖南和江西進口稻米的主要地方。明清兩朝似乎都深刻認識到江南的變化,因此鼓勵這些地區向江南出售稻米。這些地區也經過自己的農業生產和長途貿易的改變來適應江南地區對稻米的需求,因為江南地區需要養活的人口比全國其他任何地區都多。
其直接結果是在清朝中期出現了一些稻米轉運中心:重慶、漢口、九江和長江邊的蕪湖。這些城市成為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等省與江蘇、浙江、廣東和福建進行貿易的貨物聚集中心和聯繫紐帶。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鎮江成為江蘇北部的稻米集散地,然後逐漸變成江南與長江中上游的樞紐。幾乎所有從長江中上游前往江南的稻米在進入大運河之前都會首先到達鎮江,然後透過江南運河到達蘇州。清朝時期,福建和廣東在蘇州市場上購買的大量來自長江中上游的稻米都是從鎮江採購來的。
鎮江能夠在稻米貿易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主要得益於清初長江中上游地區的經濟發展。長江上游地區在中國歷史上一向以生產稻米著稱,包括所謂的「天府之國」,即今日的四川成都,儘管該城市並不坐落在長江上,而是透過岷江與長江相連。在清朝之前,人們很難步入長江上游地區,因為船隻沿川江(通往長江中下游的主要通道)而下很危險,此地幾乎是遙不可及。正因如此,四川在歷史上一直與其他地區的貿易脫節,商人們只能運輸少量的產品,如茶葉和絲綢。
自奠定江山以來,清朝為振興長江上游的經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透過官府補貼和鼓勵移民,促使了長江上游從清初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的經濟復甦。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大量的移民不僅增加土地開發的數量,而且還引進先進的耕作技術,因此大大提高了農作物產量和各種商品的數量。長江上游地區因此成為全國跨區域貿易的一部分。來自川江支流的稻米、糖和鹽在宜賓、瀘州和重慶聚集,然後順著長江到達其他地區。到了十八世紀末,長江上游地區已經「比任何其他周邊地區更好地融入國民經濟」。
長江上游經濟復甦之際,長江中游地區的經濟也突飛猛進。明末,滿族入侵導致該地區部分荒蕪。但到清初,清王朝鼓勵人們遷徙到長江中游,特別是漢江地區的高地荒蕪之處。雖然此舉未能完全成功,但該地區仍有不少經濟發展,例如陝西南部的山區和湖北北部的丘陵地區。這使得漢江上的貿易恢復了活力,該地區很快成為中國主要的稻米供應地之一,也因此被重新納入全國糧食交換市場。長江上游和中游地區的所有貨物都透過長江下游被運往江南。雖然長江中游地區也有通往其他地區的河道,如贛江、湘江和西江,但穀物、木材、棉花、絲綢、茶葉和稻米等貨物都透過長江下游向東運輸。
就是這條連接長江中上游地區和江南的主要貨物流動路線,使得鎮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鎮崛起成為在全國跨區域貿易中占據一席地位的重要城市。在明末和清朝大部分時期,除漕糧外,大量商品貨物都透過鎮江運往江南,並被銷售給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例如,江南地區所使用的來自北方的棉花中有很大一部分透過鎮江運輸。同時,來自蘇州、杭州和湖州的絲綢產品也透過鎮江運往新疆,成為邊疆貿易的一部分。四川、湖南、雲南和貴州的木材也沿著長江先到達鎮江,再被運往蘇州。因此,在十九世紀之前,鎮江已經成為南北跨區域貿易的樞紐。
最佳賣點 : 本書以長江下游的城市鎮江為例,深刻剖析中國地方社會在1830年代~1930年代這一百年間,如何與全球三大變革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