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の祭
| 作者 | 柳田國男 |
|---|---|
| 出版社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日本的祭典: 那些形塑社會與信仰的日常儀式:—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揭示神人共感的祭典精神與文化記憶—從古至今,祭典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不僅是對神靈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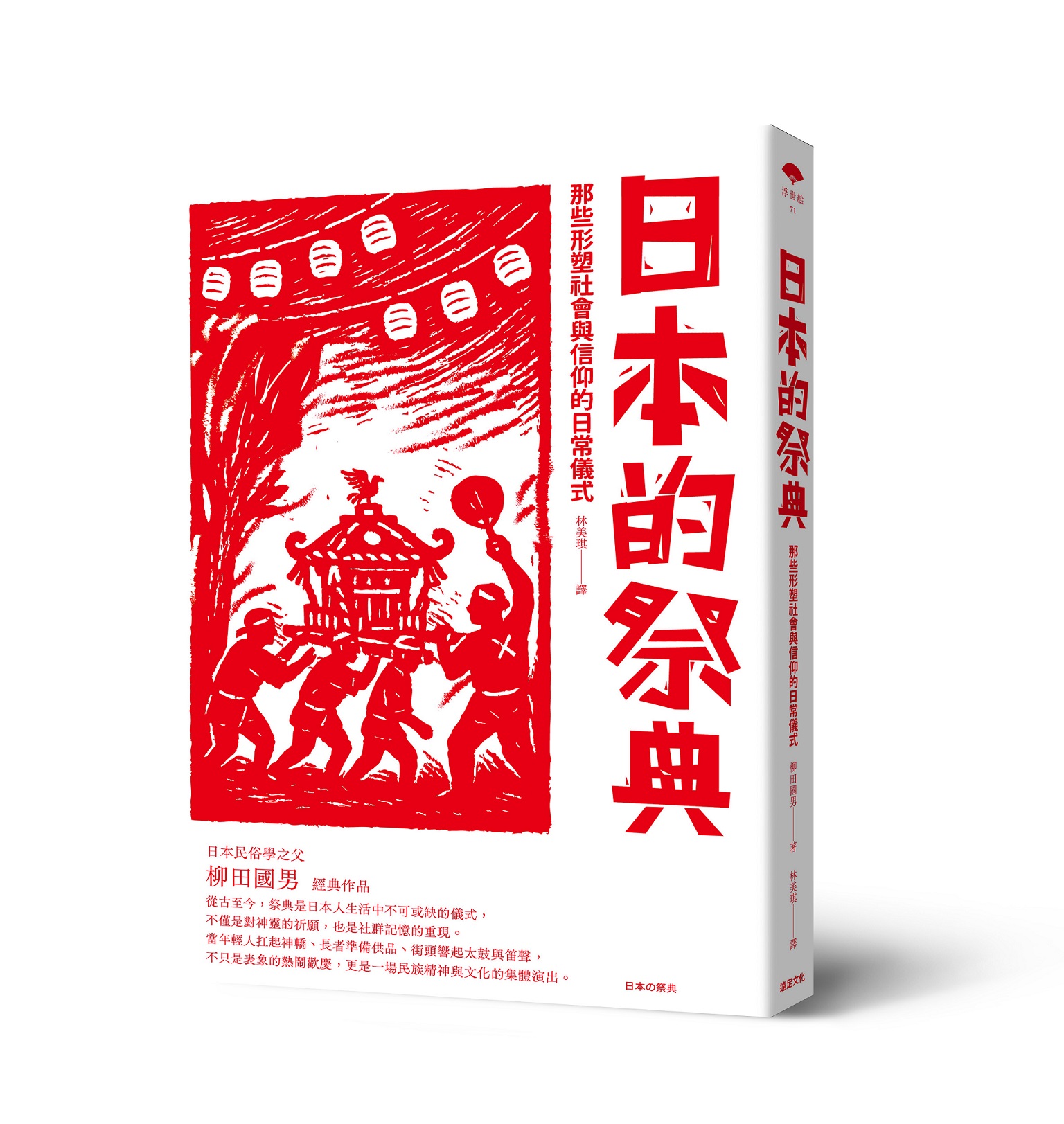
| 作者 | 柳田國男 |
|---|---|
| 出版社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日本的祭典: 那些形塑社會與信仰的日常儀式:—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揭示神人共感的祭典精神與文化記憶—從古至今,祭典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不僅是對神靈的 |
內容簡介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揭示神人共感的祭典精神與文化記憶——從古至今,祭典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不僅是對神靈的祈願,也是社群記憶的重現。當年輕人扛起神轎、長者準備供品、街頭響起太鼓與笛聲,不只是表象的熱鬧歡慶,更是一場民族精神與文化的集體演出。------------祭典,是日本人生活中最具象徵性的日常儀式,深植於四季更迭與土地脈動之中,承載著古老信仰、社群關係與民族精神的深層記憶。祭典,也是連結可見現實與不可見世界的橋樑,從神話中的「山之神」、「海之神」,到祭典前「物忌」與「精進」的莊嚴準備,引領人們進入超越日常、與神靈共感的聖域。柳田國男透過細緻的田野觀察與深刻的歷史意識,引導我們回望那些看似尋常卻蘊含深意的信仰行為。本書原是他在大學講授的課程,描繪祭典從淵源、儀式、場域標誌到供品與神職的諸多細節,揭示其如何形塑日本人的思想、道德與社會秩序。這是一趟探索日本文化根源的旅程,讀者將重新思索何謂「常識」、何謂「信仰」、何謂與土地共生共鳴的生活哲學,並感受代代相傳的生命韻律與精神之光。
作者介紹 柳田國男1875-1962。日本民俗學者、詩人。「大日本帝國憲法」時代,歷任農務官僚、法制局參事官、宮內書記官、貴族院書記官長、樞密顧問官。日本學士院會員、日本藝術院會員、文化功勞者,國內外數度受領頒勳,勳等敘至「正三位.勳一等」。生於兵庫縣,原姓松岡。幼時與家人一眾共居,家屋窄仄對生活相當壓迫,使其對於「家屋的構造」產生探究的興趣,間接植下以民俗學為志的種子。11歲那年寄居三木家豪邸,因而得以博覽群書,記憶力可稱非凡。其後居所輾轉各地,成長過程手不離卷。1900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科畢業,論文選題為三倉(社倉、義倉、常平倉)研究,乃其探知「民眾史」的契機。1901年成為柳田家養嗣子,改姓柳田。1908年於自宅展開「鄉土研究會」,隔年的東北旅行,為其首度探訪「遠野」。1910年,「鄉土會」開始運作,擔任幹事。1913年,與高木敏雄合力發行雜誌《鄉土研究》。1920年,於《東京朝日新聞社》客座專欄,並展開全國各地的調査旅行。1921年赴歐,就任日內瓦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委員;辭任返國後,1924年於慶應大學擔任文學部講師,授課科目為「民間傳承」。1934年,與民俗學者宮本常一會面,倡議推進民俗學的研究。1939年,成為財團法人民間學術協會創會會員。1941年,以對於民俗學的建構與推廣之貢獻,獲頒朝日文化獎。1947年於自宅成立「民俗學研究所」。1951年獲頒文化勳章。1962年因心臟衰竭辭世,亡故後時任首相池田勇人追贈旭日大綬章。柳田國男的「鄉土生活研究法」,具有濃烈的「現地調查主義」色彩,對於許多同代與後續的研究者產生極大的影響,其個人也對歷史學、日本國語教育、社會科教育等做出相當大的貢獻。於民俗學研究領域具開創建置的始祖地位,更被尊為民俗學之父。著述豐廣,主要著作有《遠野物語》、《日本的民俗學》、《桃太郎的誕生》、《蝸牛考》、《妖怪講義》、《日本的傳說》、《日本的昔話》等。譯者簡介林美琪於出版界工作多年,現為專職譯者。對翻譯工作一往情深,嗜譯小說、散文,樂譯勵志、養生等實用書,享受每一趟異國文字之旅,快樂筆耕。譯作百本,歡迎賜教:[email protected]
產品目錄 序學生生活與祭典從「祭」到「祭禮」祭典會場的標誌「物忌」與「精進」神幸與神態供品與神主參詣與參拜編按
| 書名 / | 日本的祭典: 那些形塑社會與信仰的日常儀式 |
|---|---|
| 作者 / | 柳田國男 |
| 簡介 / | 日本的祭典: 那些形塑社會與信仰的日常儀式:—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揭示神人共感的祭典精神與文化記憶—從古至今,祭典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不僅是對神靈的 |
| 出版社 /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5083748 |
| ISBN10 / | |
| EAN / | 9789865083748 |
| 誠品26碼 / | 2682972538002 |
| 頁數 / | 320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2.8*18.8*1.7cm |
| 級別 / | N:無 |
| 重量(g) / | 338 |
導讀 :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秋天,東京某大學設立了「全學會」,在這個全校共同參與的學術活動中,我受邀到教養部為學生講授一場名為「日本的祭典」的課程。台下坐著的,多是來自理工、農學與醫學院的學生,文學院的學生反而不多。正因為如此,我特別思考了講話的方式,希望能讓這些平時較少接觸這類主題的年輕人,也能產生興趣並有所收穫。
在現代的日本,從小學到大學,幾乎沒有機會聽到這樣的講座,甚至有機會把「祭典」當作一個探討課題去思考的人也非常少。然而,我始終相信,不久的將來,這將成為全國上下共同研究的重大課題。因此,讓這些年輕人現在就開始培養健全的常識,是非常重要的準備工作。而且他們是最理想的聽眾,因為年輕的頭腦充滿推理的敏銳與求知的熱情,更保有一張如同白紙般純淨的感受力。
其實,「日本的祭典」並非向來無人關注。除了專責管理祭典的神職人員之外,民間的紀錄也越來越詳盡。像是肥後的《宮座的研究》,以及同時期,山城地方的井上賴壽在《京都古習志》中詳盡描述京都村落的古老習俗,而大和地區的辻村好孝更將他的田野調查連載在雜誌《磯城》上,並且即將彙整成書。此外,播磨與但馬地區的西谷勝也以及越前的齋藤優,也都陸續發表了不少寶貴的採集報告。這些研究大多從過去的文化中心地區開始,逐步擴展到更遠的地方,這樣的趨勢真是令人欣喜。
如果有志於研究這個領域,光是翻閱過去的紀錄,就會發現資料豐富得超乎想像。近年的雜誌,如《民俗藝術》或《旅行與傳說》,裡面都有非常可靠的報導;而松平齊光主編的專業期刊《祭典》也已經發行了,更不用說,地方的郡誌與町村誌裡,幾乎都會記載至少一則與祭典相關的紀錄。當然,若與全國各地無數的神社數量相比,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但單從資料的累積來看,已經相當可觀,足以讓人感受到它的豐富與多樣了。
將這些資料加以整理分類,進而揭示日本祭典的現狀,本來就是專家的工作。而要讓未來活躍於其他各領域的人們,對於國家固有信仰擁有基本的認識,就得準備一份充分且精煉的概要。這份概要,理想上應該是只要聽過一次就能記住並加以思考的內容,也必須是值得記住、值得深入思考的內容。
如果只是堆積大量資料,反而會澆熄這些人原本的求知欲,甚至讓他們感到無從下手。正因如此,我一直擔心這篇文章會不會已經太過冗長了。同時,我也不免自問,這樣的內容究竟是否符合一份「概要」應有的條件呢?
當專家想要分享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往往不自覺地將自己所知的一切全盤傾出,卻忽略對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這樣的風氣在學術界並不罕見。或許一方面是因為,專家誤以為「這種程度的事情,應該隨便講講就懂了吧」,這是將自己的知識水平當成對方的基準而犯下的錯誤;另一方面,或許也是出於好意,想讓對方多學一點,哪怕只是多一分都是好的。然而,最主要的動機,恐怕還是想讓對方感到安心,覺得自己面前的這位專家果然可靠,於是毫不懷疑地接受他所說的一切。這種帶點學者特有的虛榮心作祟,確實不容否認。
而我呢,至今不過是個單純熱愛民俗文化的普通人,既沒有什麼非得向世人宣揚的堅定主張,也總是帶著困惑在摸索。因此,面對年輕人時,我的態度向來是:「從大量最可靠的事實裡,大概只能歸納出這樣的結論吧?你們覺得如何呢?」這種帶著問號的語氣,或許反而更適合與年輕人對話。因此,在這本書裡,我也反覆強調:「這只是一種看法而已,千萬別輕易照單全收喔。」甚至刻意重複到讓人覺得有點好笑了。
我真正想傳達的,只是希望大家能意識到,這是我們整個民族都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而只要我們願意認真面對,積極思考解方,所需的知識與方法其實已經具備得差不多了。只要時代繼續推動,這門學問也一定能不斷向前發展。然而,這樣的目的究竟達成了沒有?老實說,我的心意雖然真誠,卻深感自身能力遠遠跟不上理想。
特別是最後的兩個章節,原本預定要公開講演,卻因故臨時取消,最後只能將事前準備的講稿重新整理,潤飾後收錄其中。因此,或許在說明上仍有些不夠周全之處,這點我自己也有些遺憾。
昭和十七年十一月
柳田國男
內文 : 祭典會場的標誌
一
祭典時必定立木,這是貫穿日本神道古今的一大特徵。然而,這一儀式的形式卻在不斷變化,變化之廣、之深,幾乎無窮無盡。僅憑一兩個零碎的事例便試圖推測它的根本思想,不僅不可能,而且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因此,我們必須盡量廣泛地觀察現存的各種形態,即使無法窮盡所有細節,至少應該先承認它的變化繁多。這種態度不僅適用於探討祭典問題,更是理解一切國民生活現象所應當抱持的基本原則。而在日本的祭典研究中,這一點尤為重要。
我們常說,只是依賴書本的話,很難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因此,即使對祭典問題不特別感興趣的人,依然可以從我的講述中獲得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不過,如果一直說「祭典變化繁多」,只會讓人覺得麻煩,甚至失去興趣。因此,我試著進行分類,整理出一個脈絡,並思考這些演變是否都源自某個共同的基本法則,或是因為何故而產生分歧。為了做出合理的回答,我也會盡力釐清可能存在的阻礙與疑問。至今為止,我始終抱持這樣的態度進行研究,而幸運的是,我尚未遇到完全出乎意料的例外。
進行分類時,當然應該從最簡單的方式開始,例如數量或大小的差異。
同樣是為了祭神而豎立旗幟,近年來在個人祈願時,常見的做法是使用「千本幟」。這是一種細長如筷子的木棒,上面貼著紙條,寫上神明的名號、祈願者的姓名與年齡,然後在參詣路旁密密麻麻地插上數十根。不過,在村莊的祭典上,通常只會豎立兩根旗幟,卻高聳入雲,上面用濃墨大大寫著富吉祥意味的文字,氣勢恢宏。
同樣是御幣,我們熟悉的通常是長度約二尺(約六十公分)或三尺(約九十公分),於神前正中央豎立一根,供人朝拜。但在東北地區,這種御幣稱為「御指棒」,而在近畿到山陰一帶,則有一種名為「御幣樣」的御幣,每逢祭典便重新製作,高度可達一丈以上,甚至會立上四根、八根之多。
儘管名稱不同,但從外觀來看,沒有人會認為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傳統。但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這些御幣的製作方式與形狀略有不同,甚至在相鄰地區也未必完全一致,反而是在遙遠的地方,時常能見到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樣的變化,必有其背後的歷史與原因。對此,我相信總有一天,我能夠逐步解開其中的謎團,為這些傳統的流變找到合理的解釋。
二
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差別,甚至可能讓後人誤以為起源不同的差別,在於有些祭典是豎立活生生的樹木或樹枝,而有些則是使用經過削製的木柱或木棒。兩者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是在祭典當日豎立於祭典會場上,作為儀式的一環。至於選擇哪一種方式,通常是受到當地風俗的影響,或許當中隱藏了一些我們還沒發現的地方特色。
也有一些地方的做法是介於這兩者之間。例如,有些地方會採集新鮮的樹枝,裝飾在削製過的木柱或木棒頂端;又如四月八日的「天道花」,就是將杜鵑或石楠的花枝綁在長竿上,高高豎立於空中。
此外,還有一種更為特殊的儀式,民間俗稱「梢付塔婆」,是一種紀念亡者的習俗,也稱作「祭奠」或「弔祭」。這是一種在亡者逝世五十年或三十三年後舉行的最終法事,象徵亡靈即將正式昇華為神靈,人們會在墳墓上豎立一根木柱。全國各地都有這種木柱,通常是使用新鮮的杉木,四面削白,上面書寫戒名或佛教經文,唯獨頂端保留生長中的枝葉,因此,這種塔婆也稱為「活塔婆」,如今已被視為一般供養用的墓標。如果亡者是神職人員或巫女的家人,也有可以縮短「亡者成神」年限的習俗,例如在土佐 地區,相傳有亡者去世滿六年即可奉祀為神靈的說法。這些或許原本就是日本自古以來的傳統習俗,也可能在佛教傳入日本之前就有慣用的名稱了。
如今,墓地中豎立的木柱普遍稱為「塔婆」,但關西與東京近郊的習俗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在東京一帶,親族及友人會各自帶一根塔婆來,因此年長者去世後,墓地上往往塔婆林立,形成一道獨特的景觀。某些地區甚至會直接種植松樹或榊樹 作為墓標。在上總 沿海地區,人們種下的樹木一年一年朝天空伸展,最後與新舊墓地的樹木交織成靜謐的林蔭,宛如一座生生不息的森林。在我看來,或許這才是最貼近自然的悼念方式。而如今的「梢付塔婆」,那種只留下杉樹頂端枝葉的形式,應該也不是跟這種傳統毫無關聯。事實上,確實流傳著一些塔婆扎根於地,最終長成參天巨木的傳說。
三
在日本這樣的國家,要判斷最早是使用「立柱」或「活樹」並不困難。過去,我國的山野到處林木茂密,杉樹、樅樹與梅樹 等大樹直衝雲霄,松樹也昂然傲立,十分壯觀。在這樣的環境中,要刻意去挑選出一棵最厲害的樹作為神靈降臨之木,反而費時費力。因此,當時應沒必要刻意砍伐樹木、削製成柱,加工成反倒容易腐朽的標誌。後來人們開始使用立柱或木棒,想必是出於新的需求與環境變遷所致。
如果是一望無際的沙漠之國,或是遼闊無垠的草原民族,他們或許會逐漸遺忘最初的起源,只重視柱子的狀況,甚至改以石柱或金屬柱取代。而日本人自古便與樹木共存,離不開森林生活,且這片土地也很適合樹木生長,因此,我認為一開始,人們透過大自然中的樹木便能輕易與靈界溝通。
不過,要進一步探討為何後人開始使用旗幟、御指棒或梢付塔婆等木製高竿來代替活樹,就會牽涉到更廣泛的民族文化交流與習俗的變遷。簡單來說,祭場的選定,亦即因應人們的意願而必須某個程度改變迎請神靈的場所後,經歷了幾個小幅的演變,才逐步發展成今天的樣貌。
促成這一段演變的,正是日本人長久以來的遷徙與開墾歷程。從上古史的角度來看,這個趨勢可追溯至遠古時代,但在今天仍然可見它的痕跡。無論是朝鮮、滿洲,還是南方群島,每當國人進入新的環境,便會重新感受到這種需求。最初,人們只是接受神明的指引,在某地進行祭祀;後來,開始詢問是否可以在此供奉神靈;再進一步,則是認為必須在潔淨之地建造神社以供奉神明。就這樣,漸漸發展出不同的祭場標誌方式。
也就是說,日本人的信仰,在始終不違背神意的前提下,經歷了這樣的演變。這種演變的每個階段都鮮活地留存至今,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四
根據歷史記載,以竿柱代替樹木的習俗由來已久。例如,《日本書紀》中記載了一則關於「大柱直」的故事:推古天皇 二十八年,群臣在檜隈 的山陵外塚上立起一根柱子,其中有一根特別高聳,因此賜予了「大柱直」這個姓氏。雖然在塚上立柱可能與祭祀相關,但這點仍有待考證。
更具代表性的是,《延喜式》 中的祝詞慣用語中提到:「於底津磐根 上,穩固地立起宮柱……」其中的「宮柱」一詞,或許會讓人聯想到今日神殿四周的柱子,但如果這些宮柱只是一般建築的支撐柱,它就不會被視為具有神聖意義的象徵物,自然也不會成為信仰的核心。神社建築歷經世代發展,非專家難以詳述古今差異,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古老的祭祀傳統中,始終有一根特別重要的柱子受到相當的重視。
以伊勢神宮為例,在中世以後,人們開始稱其中的一根柱子為「心柱」或「心之御柱」,賦予它深奧的宗教意涵。我雖然才疏學淺,沒能完全理解其中的神秘,但可以推測,這根柱子與佛寺塔內的「心柱」不同,它是從眾多社殿的柱子中選定出來的,且在豎立時會舉行特別的儀式,例如在柱根下埋藏某些物品等。這顯示出自古以來,即使是國內最為尊貴的宮殿與神社,依然保留著立柱祭祀的傳統。
而更為人所熟悉的便是諏訪的御柱祭。這項祭典的儀式古樸純粹,或許正是古老形態得以保存至今的實例。即使到了今天,依然每隔六年便舉行一次,人們從深山中砍伐高大的樹木後拖運到神社,豎立於社地的四個角落。這四根御柱的高度還有特定的順序,據說正面左側的御柱最高。豎立新的御柱時也會舉辦平時難得一見的盛大祭典。
在信州地區,許多神社仍保留著類似的立柱祭。有些神社會在次年將諏訪本社前的御柱迎入社中豎立起來,有些則會自行豎立自己的御柱。然而,無論形式如何變化,這些祭典無一例外都是當地最隆重的儀式之一。
直到近年,我才知道除了信州之外,東北地區也有許多神社雖然不會豎立如此高聳的柱子,卻仍然遵循古制,立起兩根或三根柱子並舉行祭典。此外,關東地區某些地方,直至不久前仍保留著名為「柱舞」的祭典,特色是豎立一根高柱,並讓人攀上頂端舞蹈,因而聲名遠播。
有人認為,諏訪的御柱祭因為豎立四根柱子,所以可能與建築結構有關,但事實上,諏訪神社本就以「沒有神殿」為特色,因此不可能只是單純的建築構造。或許,這種儀式可由伊勢神宮每隔二十年依原型重建神宮本殿這個「式年遷宮」制度類推而來,但如果兩者確實相關,那麼這種聯繫必然更為深遠。
如今,諏訪的御柱祭給人的印象是「因為立御柱而舉辦祭典」,但我認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要舉行六年一度的盛大祭典,才有了立御柱的習俗。這與其他地方的祭典相似,都是透過豎立這些神聖的柱子來標示祭典的場所,宣告這裡是迎接神靈降臨的清淨之地。我想,無論是高大的御柱,還是各種不同大小的神木,應當都承載著同樣的意義。
五
在祭場四周豎立樹木以隔絕外界的不潔之物,這必須是極為隆重的祭典才做得到,不過,也有幾個祭典是以「立木」作為儀式的核心或特色。
例如,紀州 岩出村的岩出大宮,古時稱作「總社權現」,是根來寺地主神所鎮守的神社。這裡流傳著一種俗稱「齋刺神事」的儀式。《那賀郡誌》記載,每年八月初一的夜晚,在漆黑的夜幕下,村民會抬著榊樹前往村子的東西兩端,然後豎立起來。途中,隊伍會拖著鐵棒以示警戒,並在行列的前後左右灑水祓禊。據說,榊樹的葉子蘊含神聖的力量,許多人尾隨隊伍只為能摘得一片葉子。
「齋刺」意指將帶有神聖氣息的樹木插於邊界之地。一旦豎立起來,內部便成為適合舉行祭典的潔淨之地。可是,用這種方式圍繞整個村莊,由於範圍過於遼闊,反而會納入某些不潔之物。即使如此,也有許多村莊在祭典時,不是將旗幟立於神社入口或頭屋的家門前,而是豎立於村中道路的兩端,這或許也是昔日整個村莊同心協力,共同遵守齋戒的遺風。
信州的穗高神社也有類似的「境立」儀式,這是在神社四周各十町(約一公里)的邊界處豎立榊樹。《南安曇郡誌》記載了這項儀式的詳細內容,但如今只會在神社重建之年才舉行。要將十町四方這樣廣闊的區域劃為神聖之地,並在立木之後杜絕一切穢物進入,在現代社會恐怕難以每年執行。但在過去,這樣的儀式或許曾經年年舉行,或者當時的範圍比今日所記載的更小。如果能親自赴當地調查,應該還能發掘出更多的線索才對。
在九州,宇佐八幡宮至今仍會舉行名為「柴指」的祭祀活動。這項儀式於每年二月與十一月初卯日的大祭前七天、也就是酉日的深夜兩點左右舉行。儀式中,人們會在各個特定地點插下四十五根名為「齋柴」的榊樹枝條,而在正式的文獻中,這一儀式稱為「致齋」,表示即將展開一段嚴格的齋戒期。
這些齋柴所插立的地點自古以來便是固定的,其中三根設於神社境內的特定位置,而那裡本來就有榊樹,因此,齋柴或許是被掛在原有的樹枝上。其餘四十二根則是安置在本社與末社的主要入口,不會影響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不過,當其他地方的居民聽說神聖的齋柴已經插上去時,虔誠的信徒便會自我警醒,端正身心,努力遵守祭典期間的清淨戒律。這樣的習俗,或許正是昔日人們恭敬慎行的傳統表現。
六
在九州的南部農村很常聽到「柴指」一詞,意思是大型祭典的開始。這個儀式本質上與紀州等地的「齋刺」相似,它的核心概念在於以「忌柴」標示神聖之地。在這一天,家家戶戶從山中折取樹枝,插在門口或屋簷下,與正月立松、五月懸掛菖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奄美大島及其周邊諸島,「柴指」的舉行日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定於舊曆八月的第一個壬日,有些地區則是選擇舊曆的八月十一日。不過,這裡的「柴指」與宇佐八幡宮的祭典活動有所不同,主要是為了祭祀祖先,而非神社的祭典。儀式中,人們在房屋四周或籬笆上插上新鮮的蘆葦葉,表示這戶人家正在舉行祭典。這與南九州的「柴指」本質相同,只是範圍有所差異——宇佐八幡宮的「柴指」僅限於神社入口或神職人員的住宅,而南方島嶼則是全村家戶都舉行這個儀式。
這種習俗的存在,或許揭示了日本祭典演變的一個重要軌跡,也就是說,正月、節句 等家家戶戶的年中節慶活動,與村莊神社的共同祭典本來是一體的,後來才逐漸分化為兩種不同的形式。其中,頭屋制度便可視為這兩者之間的過渡形態。有些地方的頭屋會立標誌來表示正在舉行祭典,這與「柴指」的功能相似。頭屋制度本身在各地有不同的形態,因此我們仍能追溯它的演變過程。
對於只熟悉自己家鄉祭典的人來說,或許難以察覺這些變化。但在各地的祭祀習俗中,仍能見到幾個不同層級的祭典,例如由家戶主導的儀式,到神職專管的大型祭典,以及位於兩者之間的「頭屋祭」等。在中國地方的東部地區,除了村落的氏神祭之外,居民會輪流擔任頭屋,負責舉行特定的祭典。這些祭典有時邀請神職人員主持儀式,但基本上是與神社的例行祭典分開的,主要在秋收後或春耕前舉行。關東東部的「步射」儀式,近江 東部到越前 地區的「御構内」,以及遍布全國的「日待」或「二十三夜待」,都與這種祭典相類似。這些儀式雖然被視為祭典,但其實更接近每年的例行節慶活動。
另一方面,有些地區的頭屋會被選定為村中神社大祭的奉仕者,不僅要負擔祭典供品與費用,甚至要提供自己的宅邸當作「神宿」,供奉神靈。東京市內仍然保留著這類頭屋制度,雖然只是單純地履行信仰義務,但在古風純樸的地區,頭屋的職責往往比專業神職人員更加繁重,在某些情況下,頭屋主人會自己擔任一整年的神主,不假外力。從名稱的一致性來看,這些祭典並非各自獨立發展,而是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而發展出不同的形態。因此,我們不得不探討它們的共通點以及最初的原型。
最佳賣點 :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揭示神人共感的祭典精神與文化記憶—
從古至今,祭典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
不僅是對神靈的祈願,也是社群記憶的重現。
當年輕人扛起神轎、長者準備供品、街頭響起太鼓與笛聲,
不只是表象的熱鬧歡慶,更是一場民族精神與文化的集體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