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 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
| 作者 | 趙善軒 |
|---|---|
| 出版社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 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貨幣的流轉,不僅記錄著市場交易的軌跡,更映射出國家治理、社會變遷與思想演進的深層脈絡。從漢代五銖錢到清代銀本位,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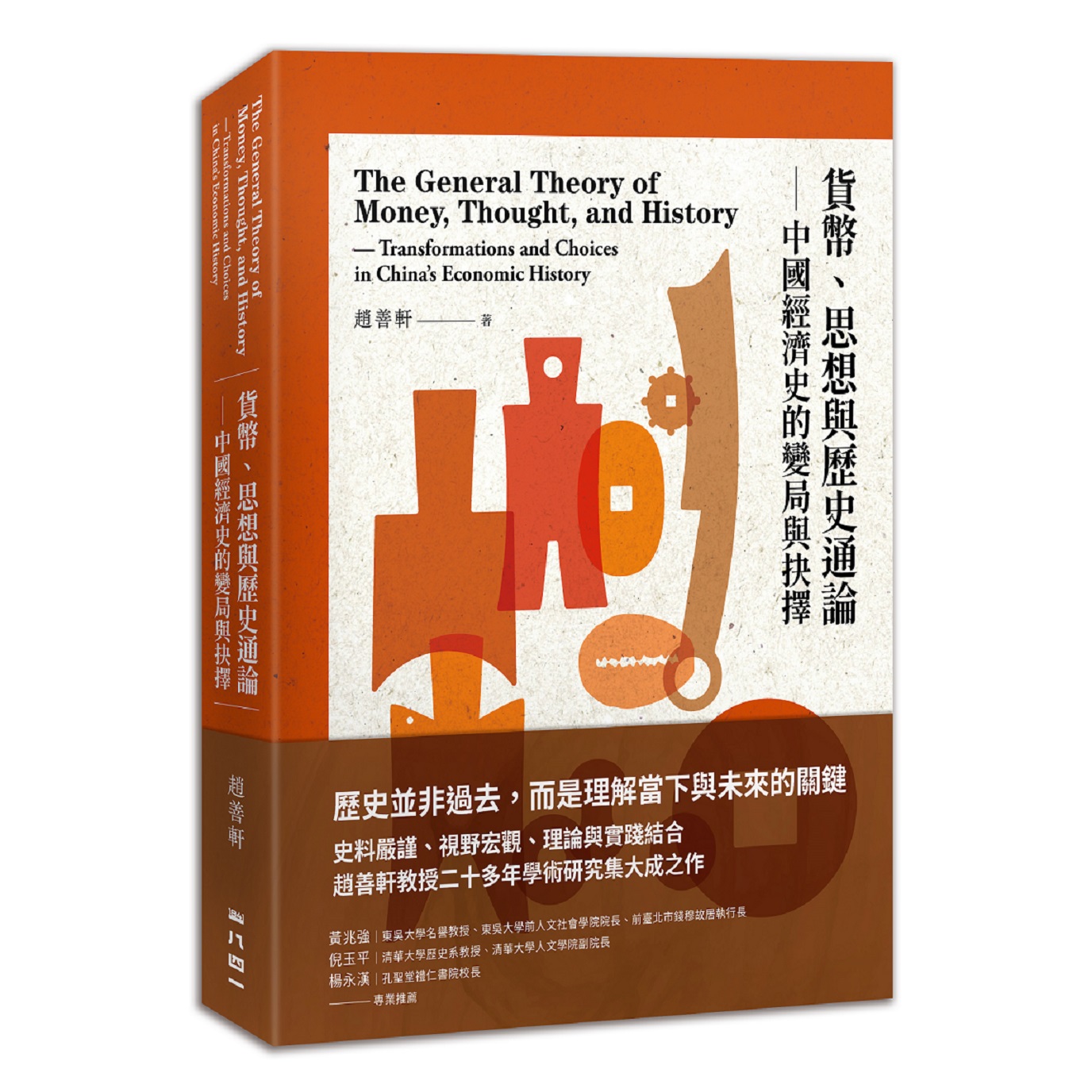
| 作者 | 趙善軒 |
|---|---|
| 出版社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 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貨幣的流轉,不僅記錄著市場交易的軌跡,更映射出國家治理、社會變遷與思想演進的深層脈絡。從漢代五銖錢到清代銀本位,從 |
內容簡介 貨幣的流轉,不僅記錄著市場交易的軌跡,更映射出國家治理、社會變遷與思想演進的深層脈絡。從漢代五銖錢到清代銀本位,從唐宋交子到近代信用貨幣,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制度不僅影響了市場,也塑造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模式。本書核心關注中國經濟史中的關鍵問題:.貨幣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循環模式——為何中國歷史上貨幣經濟與自然經濟反覆交替?.「全漢昇難題」:盛世物價低廉之謎——為何唐代前期物價低廉,卻仍被視為昇平盛世?.政府干預與市場運作的權衡——從鹽鐵專賣到明代大明寶鈔,政府對貨幣的控制是經濟繁榮的保障,還是衰退的根源?本書特色:.史料嚴謹——大量引用出土文獻、清代刑部宗卷、明清財政文獻、盛宣懷檔案等、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等一手史料,還原貨幣制度與歷史發展的演變過程。.視野宏觀——融會古典經濟學、貨幣史、經濟思想,探索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理論與實踐結合——透過歷史比較分析,討論現代經濟政策的可行性與挑戰。本書是趙善軒教授二十多年學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適合對中國經濟史、貨幣制度、政治經濟學感興趣的讀者,亦可作為學術研究、政策制定的參考讀物。歷史並非過去,而是理解當下與未來的關鍵。
各界推薦 黃兆強(東吳大學名譽教授、東吳大學前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前臺北市錢穆故居執行長 )倪玉平(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楊永漢(孔聖堂禮仁書院校長)
作者介紹 趙善軒,一九八一年出生於香港。二○二四年當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副院士。二○一八年,榮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現任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客座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於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獲榮譽文憑和榮譽文學士學位,後在新亞研究所取得臺灣教育部授予文學碩士(史學)學位,廣州暨南大學獲文學博士,並在新亞研究所完成博士後(史學)研究。專治中國經濟史、政治經濟思想史。曾供職於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布萊恩特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學府。歷任客座教授、副教授、研究員、高級訪問學者。現居英國倫敦泰晤士河畔。二○一八年創建了「趙氏讀書生活」YouTube頻道,通過該平台分享歷史知識,頻道訂閱人數超過三十八萬,每月平均觀看人次達到三百萬。
產品目錄 〈自序〉 倫敦泰晤士河畔談 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代序〉「成一家之言」的意義 劉志輝 編者說明第一篇 貨幣與經濟思想 第一章 | 《管子》其書其人與現實主義精神 第二章 | 漢文帝放鑄政策的經濟影響第三章 | 黃老學說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第四章 | 《史記.貨殖列傳》的生產行業第五章 | 《史記.貨殖列傳》的國家經濟史論述——司馬遷選材取向分析第六章 | 司馬遷的「求富尚奢觀」——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太史公的經濟思想第七章 | 司馬遷為商人立傳的尺度 第二篇 政府干預與市場經濟第八章 | 專賣、選士與路徑依賴下的司馬遷經濟思想第九章 | 從英譯《史記》說起——司馬遷「因善論」釋義第十章 | 漢官秩若干「石」定義考第十一章 | 干預主義與反干預主義——《鹽鐵論》中的經濟思想第十二章 | 《老子想爾注》的反欲思想——兼論與《史記》之比較第十三章 | 從《二年律令》看漢初自由經濟——兼論荀悅「上惠不通」說.第三篇 貨幣體制與經濟變遷第十四章 | The Monetary Thought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D 220–280) 第十五章 | 兩漢三國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之角力——從貨幣思想探究「中古自然經濟」之形成 第十六章 | 唐玄宗時期貨幣非國家化的辯論 第十七章 | 盛世物價低賤的困惑——讀全漢昇先生物價史札記第十八章 | 北宋長江農業與政府之稅入 第十九章 | 反格雷欣法則下的大明寶鈔第二十章 | 明末清初的關稅收入——讀倪玉平《清代關稅:1644 - 1911年》札記第二十一章 | 從人口、物價、工資看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國民生活水平 ——《清朝乾嘉之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導讀 第二十二章| 包世臣的貨幣思想研究 第四篇 企業史與經濟倫理第二十三章 | 一八七○至一八九○年上海機器織布局與輪船招商局的尋租行為第二十四章 | 鄭觀應「專利經營」建議及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實踐 第二十五章 | 替代理論的中國經驗——以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為例 第二十六章 | 華人商業倫理的交易費用——近代企業管理的考察 第五篇 學術與思想史 第二十七章 | 評宋敘五《西漢貨幣史》第二十八章 | 饒宗頤、三杉隆敏與海上絲路考 第二十九章 | 何炳棣與中央研究院斷交考——兼論海外華人的政治認同轉向
| 書名 / | 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 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 |
|---|---|
| 作者 / | 趙善軒 |
| 簡介 / | 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 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貨幣的流轉,不僅記錄著市場交易的軌跡,更映射出國家治理、社會變遷與思想演進的深層脈絡。從漢代五銖錢到清代銀本位,從 |
| 出版社 /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6269969760 |
| ISBN10 / | |
| EAN / | 9786269969760 |
| 誠品26碼 / | 2682945484008 |
| 頁數 / | 432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7*23*2.2 cm |
| 級別 / | N:無 |
| 重量(g) / | 730 |
推薦序 : 代序:「成一家之言」的意義
劉志輝
年初,收到善軒的邀請,替其大作《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寫序,深感榮幸之餘,也不禁有點苦惱。其一、經濟史實非我所長,故不敢妄言置喙。其二、礙於與作者相識多年,恐怕「好惡亂其中」,讓自己下筆不夠客觀和理性。左思右想下,決定以「『成一家之言』的意義」為題,藉此反思獨立心靈對歷史學者的重要性,並兼論歷史學者任務與意義。
一、 成一家之言
善軒少立大志,自攻讀歷史始,已定下「成一家之言」的期許。所謂「成一家之言」,就是歷史學者在解釋歷史現象時,能將獨特見解在自成體系的論著內呈現。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叛降,全家當誅。其時,四十七歲的司馬遷受牽連下獄,受宮刑。出獄後,太史公任中書令,並在《報任少卿書》道出寫《史記》的心跡:「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的宏願,也是每一位歷史研究者對自己的期許。要「成一家之言」,必須透過「究天人之際」和「通古今之變」方能成事。若粗言之,「究天人之際」是考究歷史發展的「非人為因素」;「通古今之變」則是縱橫古今,並透析影響史事發展的一切「作用力」,並「復現」隱含在變化萬千的歷史現象裡的「道」。[1]而關於「成一家之言」的精髓,則可借清代史家章學誠的說話作闡釋: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傴事具本末、
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
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
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
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
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2]
有論者謂,「究天人之際」和「通古今之變」屬於章學誠所說的「史意」層次,也是歷史精神的問題。史家必須掌握到史意或掌握到歷史精神,他的史著才可以成為「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亦即「究天人之際」和「通古今之變」是「成一家之言」的核心內涵。凡「成一家之言」者,必會「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這是技術層次問題,是取材、編次等方面的問題。縱使在這四項史法上有很不錯的表現,仍未必可以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個目的,而使該史家「成一家之言」。這四項史法,只能說是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門檻。只是邏輯上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而非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s),更非充要條件(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章氏認為史家必須在掌握了四項史法處理史料,並進一步藉以達到「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之後,還必須運用一己獨斷的心靈,即「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方能對天人之際、古今歷史難以掌握的機微處,做出獨立判斷,才夠格去「成一家之言」。[3]
綜而言之,若說史家的專業技藝對「成一家之言」是不可或缺的,惟獨立判斷的心靈,對史家來說更是重中之重。在此,必須事先聲明,筆者只是欲借章學誠之「以獨斷於一心」,表明獨立之「心靈」或「精神」,對史家而言的重要性,是優於於技藝之存在。本文並無討論「獨斷於一心」之內涵或意義之意圖。
二、 「記往知來」——歷史學者的任務
相對於其他專業而言,歷史學家的工作是充滿「不確定性」的。誠如莎拉.瑪札(Sarah Maza)所言,歷史學家的工作,看似不證自明,不過一旦你開始思索,就會發現這其實出人意料地難以定義。大多數人會描述歷史學為「對過去的研究」。但是「過去」是一個龐大的集合,大多數的人文學科研究都涉及到人類的過去,許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所使用的素材,也都可以追溯到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前,那麼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有何獨特性呢?莎拉告訴我們,歷史學研究在理想上有兩層意義:解釋過去的變化如何展開,以及在讀者眼前重現過去的人們和場景。所以作為傑出的歷史學家,必須要具備記者的技巧,也要有小說家的技巧(所指的是源源不絕的想像力)。簡言之,歷史學家是社會中最優秀的故事編織者。[4]惟在中國歷史書寫的語境中,歷史學者研究者所肩負的任務遠非如此。
在二○一六年,余英時先生曾借章學誠對史籍的分類法,說明錢穆先生《國史大綱》與一般通史之分別。按章氏對史籍的劃分,史籍可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
閒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
余先生認為,根據上述的分類,《國史大綱》顯然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史家所寫的通史則大致應該歸類於「方以智」的「記注」。[5]此外,余英時先生又引錢先生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提及的「新通史」的三大條件:一、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二、新通史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三、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6]簡言之,「簡而扼要」與「記往知來」是錢穆先生撰寫《國史大綱》時所持守的基本原則。而「記往知來」四字,亦可概括歷史學研究者的主要任務所在。
若引用錢穆的說話,所謂「記往」是讓「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而「知來」則是「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愚以為作為歷史學研究者,既是一位好的說故事者,也必須是一位有益於現實世界,能幫助讀者「解釋」社會現狀,並發掘社會、國家、民族問題癥結所在的先覺者。作為「先覺者」,除嫻熟的歷史方法學技藝之先,還必須要具備「獨立判斷的心靈」,或謂之「獨立判斷之精神」。
三、 獨立判斷精神之重要
提到「獨立判斷精神」,或許我們第一時間會想到「客觀」二字。作為歷史學研究者,「客觀」固然重要,但誰都明白,在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中,絕對的「客觀」並不可能存在。而本文所謂「獨立判斷精神」不是源於自然科學,而是源於一種陸王式的「道德實在論」,或可稱為一種「道德客觀主義」。[7]行文至此,我們不妨引用一段陸象山的說話,作討論之資: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調自得,禍福無不自巳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8]
筆者在此借用陸象山語,解釋「獨立判斷精神」之內涵。所謂「獨立斷精神」,換句話說就是一種「自作主宰」的精神。如陳來所言,陸九淵特別反對道德上缺乏主體性的意識,即「自暴自棄」,所謂「自作主宰」也是要人樹立起道德主體性。因為道德實踐的成敗取決於自我的意志,人只有開發出自我本來涵具的資源,並堅決地確信人的內在資源,是人的自我實現的充分基礎和條件,才能在成聖成賢的道路上達成目標。[9]
那應史學家要成聖成賢嗎?若非如此,「自作主宰」對史學家而言有何重要性?筆者認為,既然史學家的任務是透過嫻熟的技藝,依據各種時間性和因果關係的理論,向讀者揭示與闡明歷史事件的關係和歷史發展的軌跡。我們首先要「先立其大者」,有一個超越的,高尚的,為他的根基。只要有能「自作主宰」,能「自成其誠」,方可以為來者留下一個「可供參考」的,有流傳價值的歷史論述。這樣一來的「成一家之言」便更具有其現實意義。下筆至此,慨然有懷,惟念善軒學術益精,亦可聊以自慰。
乙巳年,春,書於香江
[1] 關於「究天人之際」的內涵,實是比較含糊的。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對於「天」在歷史中扮演了甚麼角色,司馬遷是語焉不詳的。惟司馬遷在《史記》中所稱的「天」,可能包括人力的集體作用,但也可理解為含糊的「非人力量」。這種「非人力量」可簡稱為「勢」。余英時:〈中國史學思想反思〉,見氏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市:聯經,2008),頁608-609。
[2] 見(清)章學誠:《新編本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上》(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9月),頁138。
[3] 見魏聰祺:〈以《史記》印證章學誠所說「成一家之言」的史法特色〉,刊見《育達人文社會學報》,第7期(2011年7月),頁284-285。
[4] 莎拉.瑪札(Sarah Maza)著,陳建元譯:《想想歷史》(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頁17-22。
[5] 余英時:〈《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見氏著:《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新北市:聯經,2022),頁15。
[6] 同上註書,頁16。
[7] 有關「道德主義」是指道德真理的條件無須參考任何人的作風或風俗,道德事實是屬於世界的事實,並不是由人類建立或建構的。相關論述可見劉紀璐著,江求流、劉紀璐譯:《宋明理學——形而上學、心靈與道德》(新北市:聯經,2021),頁211。
[8] 陸九淵著,王佃利,白如祥譯注:《象山語錄》(山東: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頁149-150。
[9] 陳來:《宋明理學》(臺北市:允晨文化,2010),頁234-235。
內文 : 自序:倫敦泰晤士河畔談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
初入門徑
我從事經濟史研究,始於師從宋敘五(一九三四-二○一六)教授。當時,我仍是香港樹仁學院(現樹仁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生,跨系選修了宋教授在經濟系開設的「中國經濟史」課程,並旁聽了他的「西洋經濟史」與「比較經濟制度」兩門課。宋教授來港多年,口音依然濃厚,班上的同學大多不適應,但我卻沉迷於他縱橫古今中外的精彩講解。宋教授於一九四九年自北方避亂南下,是新亞書院經濟系的早期畢業生,後在香港大學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專攻清代學者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的「人口與經濟思想」及嘉慶年間(一七九六-一八二○)包世臣的「經濟思想」。一九七一年,宋教授獲得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資助,該學社成立於一九二八年,並於中文大學出版印行《西漢貨幣史初稿》出版後,該書因內容精湛而在臺灣被盜印,後於二○○一年易名為《西漢貨幣史》,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再版。一九八一年,宋教授應鍾期榮校長之邀,於樹仁學院經濟系任教,秉承古典經濟學派(Classical School of Economics)的學術思路,致力於經濟史的研究與教育。
我曾撰寫一篇學期作業,後投至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雜誌,刊出於該刊第八十一期(二○○四年二月),並轉載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三十七期(二○○五年四月)。該文即本書所收錄的〈評宋敘五〈西漢貨幣史〉〉,指出宋師著作的重要性:因其深度剖析了西漢貨幣問題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影響。本文認為此書有三大亮點:
一:清楚說明西漢貨幣政策多次變革所塑造的中國傳統貨幣思想獨特性。
二:以現代經濟理論解釋西漢的歷史發展,揭示中國歷史上的主流貨幣觀念正源於西漢。
三:闡明「反貨幣思想」的形成及其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
此外,宋師對經濟制度的深入探討亦極為可貴。他的論斷精闢,可準確描繪出西漢貨幣政策的演變,以及其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深刻影響。宋師原本是新亞書院歷史系的學生,師從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和牟潤孫(一九○九-一九八八)兩位大師,但後來發現自己對經濟史更感興趣,於是轉到經濟系繼續深造。隨後,全漢昇(一九一二-二○○一)先生從臺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轉職至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宋師長年旁聽全先生的課,並受其影響頗深。後來,宋師成為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著名經濟學家張丕介(一九○五-一九七○)先生的助教。因此,宋師在經濟史研究中更多採用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但也未完全脫離傳統史學的進路。在史學界與經濟學界,他的研究方法都是一種「異數」。
我跟隨宋師學習,並在他的悉心指導下與他合著了《清朝乾嘉之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宋敘五、趙善軒,香港:樹仁學院出版社,二○○四年五月)和〈包世臣的貨幣思想〉(宋敘五、趙善軒,新亞研究所:《新亞學報》卷廿三,二○○六年二月)。當時,我便深受他的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影響,這種方法成為我研究的基礎。古典經濟學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等人的自由市場理論為根基,強調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然而,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傳統方法多傾向於社會經濟結構分析或制度史視角,較少採用純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因此,宋師的研究方法,在當時學界顯得尤為獨特,這種方法也影響了我日後的學術取向。
《清朝乾嘉之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是我首部參與撰寫的學術著作。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曾介紹此書,稱:「宋敘五與趙善軒合著的《清朝乾嘉之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對乾嘉時期的中衰提出了新的看法,值得參考。」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兼前系主任呂元驄先生在序中指出:「本書的兩位作者嘗試從現代經濟學與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解釋清代中葉以後國勢衰退的原因。傳統看法認為,清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間達到了鼎盛,但作者指出,經濟衰退已在社會中產生影響,人民的生活正逐漸陷入貧困。書中還對清代人口急增與社會貧窮的關係進行了重新分析,讀者定會耳目一新。雖然本書並未全面探討所有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因素,但其提出的論點仍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恩師余炎光教授在序中也曾提到:「我個人一直認為,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論,應本著『世事無絕對』的觀念。如果只讚賞『康雍乾盛世』的興盛一面是不夠的,還應當看到背後的『陰暗』與『不足』。宋教授的這本書對此提供了重要啟示。宋教授是我在樹仁學院的同事,是中國經濟史的專家,我對他在清朝經濟史方面的研究一直敬仰有加。趙善軒是我的學生,同時也是宋教授的學生,他對這項研究的貢獻亦不容忽視。師徒二人能合力完成這一壯舉,實在可喜可賀。當然,本書並非完美無缺,仍有討論的空間,期待日後有更多的交流與探討。」
當年為了查閱原始檔案,我在廣州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的指引下,拿了他的推薦信,隻身前往北京故宮第一歷史檔案館,閱讀了清代刑部的宗卷資料,專注於工資糾紛的官司,從中了解了清中葉時期工資變動的情況。這段經歷讓我得以深入研究當時社會各階層的經濟狀況。隨後,我攜帶幾封恩師余炎光教授的推薦信,得到了尚明軒教授與錢遜教授(錢穆先生的兒子)的協助,得以前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數年後,我便補寫了〈康雍乾盛世的國民生活水平〉一文,該文於二○一一年三月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雜誌。
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清代的這段盛世百年間,不論是旗人、官兵還是宮廷工匠,各行各業的工資都未隨通貨膨脹而增加,而米價卻一路上漲。換句話說,乾嘉時期受薪群體的購買力逐步下降,生活壓力加劇。這或許也是嘉道年間民怨沸騰、民變四起的原因之一。書中一個特別有趣的發現是,我們引用了人口學家卡斯特羅(José de Castro)在《飢餓地理》(Geopolitical Famine)中的觀點,指出當人類的食慾無法滿足時,性慾會成為替代,貧窮反而導致出生率上升。加上清朝前期的政治穩定使死亡率驟減,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清代人口的爆炸性增長。
這個研究不僅依託傳統的朝廷檔案、刑部宗卷(勞資糾紛的工資紀錄)等一手資料,也從微觀經濟視角重新審視所謂「盛世」背後的受薪階層現實處境。一方面,我結合通貨膨脹、工資停滯與人口增長等多項關鍵因素,將之與清代特定時期的政治穩定性進行串聯;另一方面,透過參考卡斯特羅有關「食慾—性慾替代」的跨學科理論,為清代民怨、高出生率與社會結構轉變之間的關聯,提供更具體的解釋。此種「自下而上」的材料比對與理論接軌方式,補足了傳統「康雍乾盛世」論述的不足,也使得我們更能理解近代中國社會在經濟、人口與社會動態間的複雜交織。
然而,這些經歷也使我第一次在投稿時遇到了挫折。經濟史研究往往傾向於使用考證和綜合方法,而非過於偏向分析的研究方法。我曾協助宋師撰寫並聯名發表〈包世臣的貨幣思想〉一文,討論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導致物價上漲、銀貴糧賤的情況,進而對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產生了負面影響,甚至威脅到了政治穩定。包世臣作為地方官員的幕僚,提出了需要改革貨幣制度的主張,特別是行鈔的提議。他試圖用紙幣取代白銀作為貨幣,以解決當時的貨幣短缺問題。然而,由於他的行鈔主張缺乏兌現的保障,實踐起來面臨巨大困難。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等人反對紙幣的主要原因正是其缺乏兌現性,而唐朝與宋朝的紙幣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其兌現機制健全,這也表明兌現性是紙幣成功的關鍵因素。
這篇文章最終未能順利發表,審稿人指出應該投稿至經濟學期刊,而非歷史學期刊,並對史料使用和參考文獻提出了多方批評。宋敘五教授所採用的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與當時已逐漸數理化的經濟學研究趨勢相背離,尤其是數據模型的缺乏,使得我們的文章難以符合經濟學期刊的要求。最終,我不得不妥協,按照審查意見刪減了論文中的分析部分,僅將部分分析內容保留在註腳中,而正文則依照傳統史學的表述方式進行修改。經過大幅度的修改,文章最終在《新亞學報》上發表,但內容已與初稿有很大不同。由於此文是與宋教授合撰,而宋教授已故多年,此次出版則以原文收錄,以作紀念。
在宋教授安息後,我為紀念恩師,編纂了《經濟史家宋敘五教授紀念論文集》(楊永漢、張偉保、趙善軒主編,臺北:萬卷樓,二○一八年八月)。該論文集整理了宋教授未發表的碩士論文章節,並邀請了多位學者撰稿,以報答多年的師恩。
碩士畢業
碩士畢業後,我逐漸體會到傳統史學與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之間的矛盾。在新亞研究所攻讀碩士期間,我的指導老師是張偉保教授。與張師的初次見面是在樹仁學院圖書館,那時我仍是本科二年級生,曾在校刊上見過他的照片,便上前打招呼,表達自己對經濟史研究的興趣。張師隨手在紙上寫下幾本書籍和數位學者的名字,囑咐我深入學習。
張師早年畢業於新亞研究所,師從著名經濟史學家全漢昇,後來以明代江西役法為題完成碩士論文,之後轉攻近代工礦史,並以此撰寫博士論文,博士後階段專研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計劃。楊聯陞(一九一四-二○○三)曾贈詩給全漢昇:「妙年唐宋追中古,壯歲明清邁等倫。經濟史壇推祭酒,雄才碩學兩超群。」全先生曾擔任臺灣大學經濟系系主任,期間培育出趙岡(一九三一-二○一三)、王業鍵(一九三○-二○一四)等知名學者。但他大半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晚年當選中研究院士,其研究仍以實證主義與史料考證為主,並影響了後來許多華人經濟史學者的學術取向。
在張師的指導下,我完成了新亞研究所史學組的碩士論文,題目為《上海機器織布局(一八七八-一八九三年)發展史研究》。張師屢次提醒我,史料乃學術研究之基石,這使我改變了以往寫作中的浮躁態度。最初,我曾計畫在文章中融入部分經濟學與管理學理論,因這畢竟是企業史的題目,本文認為適當的理論工具有助於更深入的分析。然而,為了確保論文能夠順利通過評審委員會,我選擇將重心放在史料分析之上。
〈鄭〉文最初投稿至臺灣的一本史學期刊,但遭退回。編審的主要理由是,我在文中指出鄭觀應(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利用與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一)的密切關係,為上海機器織布局申請了長達十年的專利,這一政策限制了潛在市場競爭者的進入,進而延緩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然而,審稿專家認為此論點欠缺合理性,因為上海機器織布局屬於大型投資項目,若缺乏專利保護,投資者或因風險過高而卻步,因此專利制度的存在具有其經濟合理性。
後來,我將文章投稿至大陸期刊,並基本保留了原初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該期刊的審稿專家普遍持干預主義立場,認為史學論文不應以自由主義視角「非議古人」。但在我看來,這些討論並非以今度古,因為即使在晚清時期,已有不少人意識到專利保護可能帶來的弊端。例如,司馬遷(前一四五/一三五-前八十六年)在《史記》中早已指出,政府與民爭利往往導致經濟失衡。換言之,專利保護應當僅針對重大技術創新與高風險投資,而非像李鴻章所推動的官督商辦企業,利用政府影響力壟斷市場。回顧當時撰寫的〈鄭〉文,相較於同時期的研究,確實顯得論證不夠周全,部分觀點尚有待補充與修正。最終,這些研究成果後來均收錄於《經濟與政治之間:中國經濟史專題研究》(張偉保、趙善軒、羅志強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二○○九)。
二○一七年十月,招商局召開成立一百四十五周年國際研討會,我與張偉保老師受邀參加。會上,日本籍經濟史學者濱下武志先生亦在場,他的碩士論文早在三十多年前即已研究上海機器織布局,但彼時所能掌握的史料與今日相比已有極大差異。此外,已故的黎志剛教授(一九五五-二○二一)也出席了此次會議。他曾多次自澳洲昆士蘭大學致電鼓勵我繼續深入研究,我們也時常透過書信與電話暢談學術。
會議期間,我在深圳蛇口招商局總部宣讀了〈上海機器織布局與輪船招商局(一八七○-一八九○年)的尋租行為〉一文。文章詳細分析了這兩家企業的尋租行為,涵蓋了它們與政府的政治聯繫、政策支持下的市場壟斷優勢,以及如何在商業競爭中維持既得利益。此外,該文還探討了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角色,以及國家與商業資本如何透過相互博弈影響中國近代化的發展進程。這項研究進一步揭示了晚清中國,特別是在洋務運動(一八六○-一八九○年代)背景下,政治與經濟結構之間的複雜關係。
宣讀論文後,與會學者隨即展開熱烈討論。許多人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初入學界的經歷,彼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九七八年起),當時的學術研討會多聚焦於國有企業與官督商辦企業,研究重點在於揭示其弊端與汲取歷史教訓,以期為市場經濟轉型提供參考。然而,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的聲音日益高漲,學術界的風向亦隨之轉變。過去對國有企業的批判性研究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對其「歷史價值」的肯定與吹捧,彷彿所有歷史研究的目的,最終都應服務於當代的政治需求。由於我不願大篇幅修改此文,最終沒有被收入招商局的紀念文集一書。【編者注:官督商辦,即政府監督與資助,但由民間資本負責經營的企業模式,興起於洋務運動(一八六○-一八九○年代),典型案例包括輪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創立)、上海機器織布局(一八七八年創立)等。此制度在維持一定市場活力的同時,也為官僚體系提供了尋租機會,成為晚清經濟結構中的一大爭議點。】
這一學術風向的轉變不禁讓我感慨,許多學者甘於順從權力,不顧學術誠信,甚至毫不猶豫地「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這樣的趨勢使得獨立批判性的研究愈發邊緣化,許多歷史問題的討論逐漸流於政治正確,而非真正的學術探究。我的研究則恰恰相反,試圖揭露晚清時期公權力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與侵害,強調公權力的本質是以權謀私,若無有效的制度約束,這種侵害只會變本加厲。我在論文中詳細剖析官督商辦制度的內在缺陷,並指出此模式雖能暫時促進工業化發展,卻同時滋生了尋租腐敗與市場壟斷,最終限制了中國自主經濟發展的空間。然而,在當前學術環境下,這類研究似乎顯得過於不合時宜,甚至與某些學界主流論述格格不入。
(節錄)
最佳賣點 : 貨幣的流轉,不僅記錄著市場交易的軌跡,
更映射出國家治理、社會變遷與思想演進的深層脈絡。
從漢代五銖錢到清代銀本位,
從唐宋交子到近代信用貨幣,
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制度不僅影響了市場,
也塑造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