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山
| 作者 | 余杰 |
|---|---|
| 出版社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香草山:《香草山》透過書信與日記的形式,展現一對年輕戀人對時代和極權的思索。他們在長輩的沉默與書籍的隻字片語中,觸及那場浩劫的一角,未曾親歷過的時代巨影,時刻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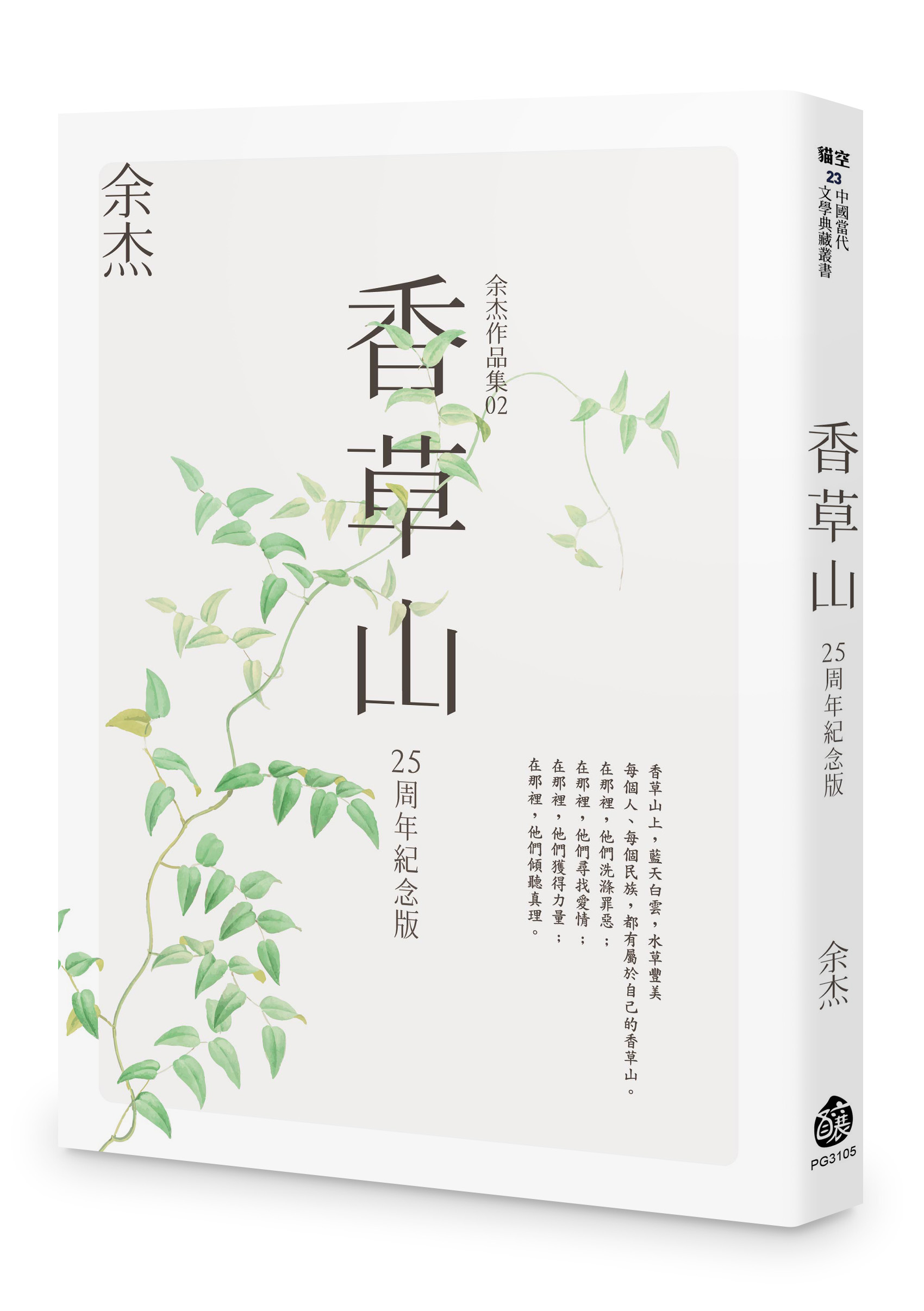
| 作者 | 余杰 |
|---|---|
| 出版社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香草山:《香草山》透過書信與日記的形式,展現一對年輕戀人對時代和極權的思索。他們在長輩的沉默與書籍的隻字片語中,觸及那場浩劫的一角,未曾親歷過的時代巨影,時刻籠 |
內容簡介 《香草山》透過書信與日記的形式,展現一對年輕戀人對時代和極權的思索。他們在長輩的沉默與書籍的隻字片語中,觸及那場浩劫的一角,未曾親歷過的時代巨影,時刻籠罩在兩代人身上。在交流與書寫之間,悲嘆一個個小人物的際遇,交流拼湊那段歷史的一角。 這不只是關於愛情的故事,更是一場探索與反思歷史的旅行。當個人經驗與家國歷史交錯,他們在理解與質疑間前行,試圖從過去的斷裂中尋找連結,從歲月的縫隙中看見希望。 歷史不再只是課本上的文字,而是一代代人的傷痕與遺緒。《香草山》中兩個青年人熱烈又真摯的筆觸,帶領讀者窺探血色歷史的一隅。
作者介紹 余杰 美籍蒙古裔作家、政治評論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2025年任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駐校作家及訪問學人。 1998年出版散文評論集《火與冰》,在世紀之交死水般寂靜的中國掀起旋風,短短數月間暢銷百萬冊,被評論界譽為八九後青年一代追求自由和獨立的最強聲音,隨後遭到中共政權殘酷打壓多年。2012年1月11日攜妻兒赴美定居華盛頓郊區,潛心著書立說。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著作多達近百,涵蓋當代中國政治、東方極權主義、近代思想史、民國史、台灣民主運動史、美國政治、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領域。致力於用文字顛覆馬列毛習極權主義、解構中華大一統觀念、批判西方左派意識形態,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秩序與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即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以臺灣為第二故鄉,近年來在臺灣出版各類著述,包括《大光》三部曲、《一九二七》三部曲、暴君習近平三部曲等。
產品目錄 只是公開地向你說著我的私房話──《香草山》二十五周年紀念版序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讓自己發光──《香草山》從未刊載的初版序言 第一章 信 (那封信, 像一顆小石子一樣擊中我的心) 第二章 智齒 (那顆智齒, 讓我們一起疼痛) 第三章 葡萄園 (你如同一棵鳳仙花, 來到我的葡萄園) 第四章 蝴蝶 (蝴蝶沒有死去, 只是隱沒在夜色中) 第五章 水井 (從幽暗的水井中, 打撈滿滿一水桶的星星) 第六章 蘆葦 (壓傷的蘆葦, 它不折斷) 第七章 睡蓮 (此刻,你的身體和靈魂, 像睡蓮一樣緩緩向我綻放) 第八章 泉水 (愛情像泉水一樣流淌, 從此不再有死亡) 第九章 蜂蜜 (你從遠方來, 我們一起採蜜築巢) 我是冰,我等待火──中國最大的讀書網站豆瓣網讀者關於《香草山》的讀後感
| 書名 / | 香草山 |
|---|---|
| 作者 / | 余杰 |
| 簡介 / | 香草山:《香草山》透過書信與日記的形式,展現一對年輕戀人對時代和極權的思索。他們在長輩的沉默與書籍的隻字片語中,觸及那場浩劫的一角,未曾親歷過的時代巨影,時刻籠 |
| 出版社 /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6264120722 |
| ISBN10 / | |
| EAN / | 9786264120722 |
| 誠品26碼 / | 2682860544009 |
| 頁數 / | 414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4.8X21X2.1CM |
| 級別 / | N:無 |
自序 : 只是公開地向你說著我的私房話──《香草山》二十五周年紀念版序
二○○○年,《香草山》寫完時,廷生和寧萱的故事才剛剛開始──絕對不是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從此過上快樂幸福生活的故事。就在這一年,他們的生命中發生了兩件大事:失業與結婚。
在《香草山》結尾處,主人公廷生一畢業就失業,不僅僅失去一份工作,而是失去所有工作──中宣部長親自下令,不准他在中國任何學術、文化、新聞機構任職,也就是剝奪了他用文字謀生的可能。然而,他沒有做任何錯事,他只是說了些真話,寫了些文章。
幾個月後,他們舉行了一場簡單的婚禮,而結婚證卻足足等了兩年才拿到:廷生被已簽約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單方面毀約,其戶籍處於某種奇特的「懸空」狀態。他辦不到新身分證,也無法辦結婚證,淪為「黑戶」(沒有戶籍的人)。直到一年多以後,他才在一位素未謀面的讀者朋友幫助下,落下戶籍,辦好結婚證。
二○○○年,是廷生在北京十九年的生活的轉捩點:之前的七年,是校園裡的學生生活;之後的十二年,是離開校園後作為一名「非自由撰稿人」的堅持與抗爭。之前的七年,是沒有寧萱的一個人的孤獨寂寞;之後的十二年,是與寧萱一起並肩前行、相濡以沫。
《香草山》中提及的很多人物,後來都成了兩名主人公的好朋友。他們結婚後不久,就認識了劉曉波。第一次見面是在老鄉、詩人和餐廳老闆忠忠的出租房,廷生先到,與劉曉波這兩個「口吃的人」,期期艾艾,相對無言。還好,寧萱下班後趕到,靠著慧心妙舌,很快就讓氣氛熱絡起來。然後,大家一起圍繞著忠忠從老家帶來的阿姨快炒的泡椒雞雜和麻婆豆腐大快朵頤,有相似的胃,更有相似的心。
寧萱對人的直覺比廷生準確。此前,她一見到廷生的幾名朋友,立即悄然且單刀直入地告訴廷生,這幾個人不值得交往。後來,廷生果然與這幾個變臉成為刀筆吏的人分道揚鑣、割席斷袍。然而,與曉波第一次見面,寧萱一眼就看出,曉波是一位值得用生命擁抱的朋友,正如她第一次見面就認定廷生是可以託付終身的愛人。
這場友誼改變了廷生和寧萱的一生。此後,他們與曉波一起參與了此後數年間驚濤駭浪的人權活動,不知不覺就成了「國家的敵人」。寧萱在背後默默出謀劃策,有一年,獨立中文筆會在北京郊外舉辦自由寫作獎頒獎典禮,就是寧萱以公司的名義租導覽車,接送與會者。
還有喜歡醉酒與吹笛的廖亦武,用嚎叫來朗誦詩歌〈大屠殺〉、心比蓮子苦的廖亦武。有一次,寧萱帶老廖去訪問坐過二十年大牢的北京家庭教會老牧師袁伯伯。剛進門,就有一群如狼似虎的警察衝進來。
寧萱很篤定,暗自吩咐老廖不要開口說話,不等警察開口,她就一個人「舌戰群警」,將警察的訊問變成了傳福音的課堂。她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那些來勢洶洶的警察居然圍坐著聽了兩個小時,似乎若有所思卻一無所獲。
老廖沒有想到,表面上看文弱清秀的寧萱,居然比他這個老江湖還要臨危不亂、應對自如。從此,老廖對寧萱肅然起敬,寧萱成了他的「畏友」。他離婚時,寧萱對他的不忠一番痛斥,他對這位比他年輕十多歲的女子只能乖乖地低眉順首。
後來,廖亦武將採訪袁伯伯的故事寫入《上帝是紅色的》一書,那是半部當代中國家庭教會的歷史,那是中國的信仰者用血來證道和殉道的歷史。
廷生因與劉曉波一起起草中國人權報告,與劉曉波一起被傳喚的那天,寧萱的爸爸媽媽正在他們北京的家中做客。
經歷過一九四九年之後歷次政治迫害的爸爸媽媽,親眼目睹女婿被警察帶走,沒有驚慌失措,而是有條不紊地找出廷生的十多本日記本,一本本地燒掉。他們知道,必須在警察上門抄家前將這些「證據」燒毀,警察就無法用日記來羅織各式各樣的罪名了。以前,他們目睹自己的父母如此做,他們也曾如此做。他們知道,在中國,日記與毒品一樣危險。中國的歷史果然是不斷重複和循環往復的。
燒掉的紙灰,他們用馬桶沖走。結果,很快馬桶被堵住了。寧萱聞訊回家後,看著兩老的「傑作」,哭笑不得。沒有一個中國人擁有「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家,警察闖進每個人的家,都如入無人之境。沒有一個中國人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連寫日記都會成為罪證的國家,誰能有平安呢?
警察帶走廷生後,又來傳訊提前下班趕回家的寧萱。寧萱在回家的計程車上,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通訊錄,給上面的十多名西方記者和外交官打電話,告知他們廷生被警察抓走的消息。她早已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來。所以,警察對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還挺會炒作的,才半個小時,你就將消息弄得天下皆知了。」寧萱回敬警察說:「是你們先抓我先生的,我把你們做的事情公之於眾,不是炒作。」
此前,寧萱認識了很多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妻子,她們都向她傳授過遭遇警察的經驗──被傳訊時,身上要多穿幾層衣服,一是為了保暖,因為看守所通常很冷;二是為了避免警察和獄卒們投來淫邪的眼光──他們將囚徒當做任其擺布的「行貨」,不會有絲毫的善意。
於是,寧萱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換下白領的套裝,穿上秋衣、秋褲和厚厚的外套,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然後等待警察的敲門聲。
果然,警察將她帶到派出所後,故技重施,向寧萱重複了曾對劉曉波的妻子劉霞說過的那番話:趕緊離婚吧,這樣你就不用再過擔驚受怕的生活了。
警察沒有讀過劉曉波寫過劉霞的詩,也沒有讀過《香草山》,所以,他們的挑撥企圖踢到了鐵板上。
二○一○年冬,廷生和寧萱被被國保警察非法軟禁在家,家中的電話、網路全都被切斷。他們家的門口安裝了多個攝像頭,外牆上還有紅外線監測器,警察儼然將他們當作可以飛簷走壁的雌雄大盜。
有一天,寧萱突然高燒,要出門去醫院診治。多名身強力壯的國保警察堵住大門,領頭的那個滿臉橫肉的隊長惡狠狠地叫囂:「不准去!就是不准去!你死在家裡,我們也有人負責!這是周永康書記的命令!」多年後,被稱為「中國的貝利亞」和「中國的希姆萊」的周永康淪為秦城監獄的終身囚徒,廷生和寧萱在美國過著哈金所說的「自由生活」。上帝用祂特有的幽默實現了公義,公義永遠不會遲到。
幸好有一名好心的鄰居幫忙叫來救護車,醫生與警察交涉良久,才被允許上門來查驗。結果,醫生說,病人高燒,非常危險,必須上醫院。醫生又去與警察交涉,警察才允許寧萱上救護車去醫院,警察在後面跟著。而廷生仍然被軟禁在家,不能陪同寧萱去醫院。
那是寧萱一生中離死亡最近的一次,她一度高燒昏迷。愛上「國家的敵人」,就被歸入「國家的敵人」的黑名單,成為被肆意打壓和凌辱的「賤民」,這是共產黨株連九族的法治。
一個月後,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那天,廷生被一群祕密警察綁架,之後遭受了慘絕人寰的酷刑折磨,一度昏死過去。由於「上級」下的命令只是發洩劉曉波獲獎讓當局顏面大失的憤恨,教訓教訓這個劉曉波的親密助手,並未下令將其酷刑致死,所以警察們手忙腳亂地將其送到醫院急救。
經過幾個小時急救,廷生終於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醫生告知,如果遲送到一個小時,估計就很難施救了。但醫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廷生剛要告訴醫生自己被身邊的這幫惡徒施加酷刑的真相,一名身穿便衣的國保警察將醫生拉走,另一人在廷生耳邊惡狠狠地說:「閉嘴,再說就拔掉你的針頭和氧氣罩,弄死你。」
在廷生被人間蒸發的那幾天,寧萱仍然被軟禁在家。就在廷生九死一生的那天晚上,她心有不祥之感,輾轉反側,無法入眠,一夜之間,大把的頭髮由黑變白,且落滿枕頭。原來,伍子胥過韶關,一夜白頭,不是傳說。
卡夫卡說過,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東西就是愛。無疑,從未經歷過生死考驗的愛情,輕如鴻毛;而經歷過生死考驗的愛情,才能不磷不緇、歷久彌新。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廷生與寧萱終於攜帶三歲的幼子遠走美國。祕密警察一直將他們全家送到登機口。沒有自由的地方不是祖國。他們不喜歡「流亡」這個過於悲哀的詞語,樹挪死,人挪活,《詩經‧碩鼠》有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其實,人所需不多,一個可以安眠的枕頭,一張可以自由書寫的書桌,還有藍天和沃土,僅此而已。
離開,固然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也是勇敢者的決斷,如卡繆所說,「生活是你所有選擇的總和。那麼,你今天在做什麼?」廷生和寧萱義無反顧地做出了決斷,離開或許意味著永遠不歸,那個東亞的舊大陸密佈霧霾,不值得留戀。由此,他們擁有了卡繆所說的「幸福的四個條件」:生活在露天,愛另一個人,沒有野心,創造──創造就是活兩次。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晚上,廷生在台北唐山書店舉辦新書《拆下肋骨當火炬》的發表會。剛剛結束,打開手機,突然接到一名英國記者的來電:劉曉波去世了。正要從唐山書店地下室幽暗狹窄的樓梯走上去的廷生,如遭雷擊,雙膝發軟,差點從樓梯上滾落。
劉曉波的絕筆,是他去世前幾天為劉霞的攝影集寫的序言:「一隻鳥又一隻鳥穿過我的目光,抓住一個人的審美後,就將終生在他的生命裡穿行,蝦米(劉霞)的詩出自冰與黑的交匯,如同她的攝影拍下了詩的黑與白。瘋狂與面對苦難的平靜,慘烈的小娃們在胸膛的敞開中向煙幕放散,披著黑紗的木頭人也許來自見證耶穌復活的寡婦,或《馬克白》中的女巫。不,不,都不是,那是蝦米筆下獨一無二的曠野孤枝,是灰暗的地平線中一朵染滿沙塵的白百合,──獻給亡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他一直說,他是為亡靈而活,如今,他是為亡靈而死。
劉曉波說過:「我相信黑暗是我的宿命。」如今,他骨瘦如柴,緩緩遁入無比的黑暗,如戰死的海軍士兵的遺體被同袍緩緩投入大海。曉波走了,那個國家從此被詛咒為「兇手的國度」。此刻,廷生和寧萱與中國的臍帶被活生生地剪斷,有一種從所未有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從身體深處傳來,擴散,持續。他們被迫與生命中最寶貴的一部分告別,包括那段與劉曉波在一起的青春。
《香草山》這部作品在二○○○年完成,但廷生和寧萱的故事還在繼續演繹。以上,只是呈現他們生命之旅中的幾處起承轉合,讓讀者可以以管窺豹。或許,今後某一天,會有一本《香草山》的後傳或續集問世?
少年情懷總是詩,《香草山》中的少年情懷,如同曇花一現,即便作者自己,在以後的作品中也很難重現;但是,若有《香草山》的後傳或續集,必定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風貌,那是塵封更久的醇酒,那是放在箱底多年又重新時尚的舊衣,那是葉慈吟唱的「愛你白髮蒼蒼的容顏」。
台灣攝影大師馮君藍牧師為寧萱拍攝了很多肖像,其中一幅名之為《珍珠》,他寫道:「聖經中說,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珍珠。我所認識的寧萱姊妹,正是這樣一顆遠勝珍珠的珍珠。她因為讀了余杰的一本書,欽慕他在文字中所顯現的道德勇氣和高貴靈魂,主動與之通信,而生發愛情,並在兩人第一次見面,就答應余杰的求婚。在之後婚姻的日子裡,即使面臨許多想像不到的艱難困苦,以及來自政府的壓迫,她仍然以她的良善、對理想的忠誠,以及因著對愛與真理的信仰,勇敢去面對、去承受。」
二○○二年,《香草山》刪節版由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隨後,這本書出現在很多大學生宿舍中,撫慰了毫無詩意的時代成千上萬青年的荒蕪的心靈。但很快,中宣部下令禁止此書再版,儘管書中所謂的敏感字句都已被刪除。四年後的二○○六年,經過一名書商在幕後悄然操作,《香草山》在珠海出版社推出新版本,這也是作者在中國出版社最後一次公開出版作品。同樣,它再次被禁。
二○一一年,經台灣編輯及出版經紀人黃珮玲牽線,全本的《香草山》在台灣遠流出版社出版。
那些浸潤著愛的文字,輕鬆跨越了國族和時代,《香草山》在台灣找到了無數知音,贏得了悠長共鳴。
轉瞬之間,《香草山》完稿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等於四分之一世紀。而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二十五年後,廷生與寧萱的愛情依然如《香草山》第一頁那樣單純、清冽、芬芳。不悔少作,對每個寫作者來說是一件天大的難事,而《香草山》就是一本不悔之書。此時,遠流版已絕版,由秀威推出《香草山》二十五週年紀念版,是紀念,也是眺望,是祝福,也是感恩。
T.S.艾略特有一首〈給我妻子的獻詞〉,他的妻子是那個「高個子的姑娘」,而廷生的寧萱,也是一個「高個子的姑娘」。所以,T.S.艾略特的這首詩可以借用來作為廷生給寧萱的獻詞,作為《香草山》二十五週年紀念版序言的結語:
這是歸你的─那飛躍的歡樂
使我們醒時的感覺更加敏銳
那歡欣的節奏統治睡時的安寧
合二為一的呼吸。
愛人們散發彼此氣息的軀體
不需要語言就能想著同一的思想
不需要意義就說著同樣的語言。
沒有無情的嚴冬能凍僵
沒有酷烈的赤道炎日能枯死
那是我們只是我們玫瑰園中的玫瑰。
但這篇獻詞是為了讓其他人讀的
只是公開地向你說著我的私房話。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初稿,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定稿,美東北維州綠園群櫻堂)
內文 : 〈寧萱的信〉
廷生:
你好。
我自覺很冒昧給你寫信。我原是不能接受給陌生人寫信這樣冒昧行為的人。
我曾經有過數次被文字打動的經歷,也曾有過與這文字後面的心靈結識的衝動。但出於漠然悲觀的天性,最終寧肯默默地與文字交流。迄今為止從未寫過一封給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給了我極大的打擊,因為他就是我曾經想要寫信的人。而如今,信還在心裡醞釀,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
我體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與悔恨。
世事喧囂,人生寂寞。我一直以為,支撐我生活的動力,便是羅素所稱的三種單純而又極其強烈的激情: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對於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而在這樣的動力下生活,註定是孤獨的,無盡的、近於絕望的孤獨。
我想,在這片已經不再蔚藍、不再純潔的天空下,如果還有一雙眼睛與我一同哭泣,那麼生活就值得我為之受苦吧。
於是,因為王小波,因為孤獨,因為生命的脆弱與無助,我終於提起了筆,給你,嚴重而真誠。
作個不恰當的對比,許廣平第一次冒昧給魯迅寫信的時候,提了一個大而無當的問題:人生遇到歧途怎麼辦?我自覺我這封信雖沒有提問,卻也大而無當,不知所云。可魯迅認真回答了許廣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卻從未絕望。你呢?還有一顆易感而真誠的心嗎?
最後,我要告訴你,我是個女孩,美麗,也還年輕。
寧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寧萱的日記〉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起床來鬼使神差地給一個陌生人寫了一封信──除了他寫的一本書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
很久沒有寫信了。雖然每天都坐在電腦前,但在鍵盤上敲出的都是與心靈無關的文字──是比八股還要八股的專案可行性報告、是格子裡填滿資料的報表、是給其他部門的例行公事的通知書……日復一日,這些文件已經塞滿了我的大腦。
忽然,我覺得很累、很累。我來到這家龐大的外資公司已經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個二十剛剛出頭的女孩,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當上了部門經理。我上學得早,因為父母工作忙,沒有時間照料我,讓我五歲便上了小學。我在小學和中學又各跳了一級,所以上大學的時候只有十五歲。大學畢業還不到二十歲。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幾天的聚會上,畢業之後難得一聚的大學同學都異口同聲地這麼說。當年在我下鋪的女孩,還只是銀行的一個普通營業員。最有「出息」的男同學,也僅僅是政府部門的一個小科長。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這些不是我夢寐以求的。我內心有一種聲音在對我說:「你並不屬於這裡。」這個聲音每天都在心靈深處響起,由遠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紅的熔岩在幽暗的地殼中翻湧著。那麼,我的靈魂究竟屬於什麼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裡才能夠獲得寧靜和愉悅呢?
公司占據整個的一座大廈,我的部門在十樓,整層樓就是一間開放式的辦公室。每個職員有一個透明的隔間。幾十個職員,像一群家養的鴿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樣的「籠子」裡。
巨大的中央空調,每時每刻都在發散著無窮的能量,冬暖夏涼。我不喜歡空調,我寧願房間裡的溫度與外面的溫度一模一樣。無論冷也好,熱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溫度最好。可是,我們的皮膚已經適應了空調製造的虛假溫度,反而無法適應大自然本身真實的溫度。我們的肌膚在虛假的溫度之中麻木了,我們的心也一樣。我們親手把自己裝進一個虛假的盒子裡。
我每天對著電腦,用電子郵件和電話跟同事們聯繫。儘管大家同處一室,卻談不上有什麼心靈的溝通。這就是「現代化」的公司中的慣例。在公司安裝著藍色玻璃的辦公室裡,每個人各司其職: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處理事務,一動不動;或者匆匆地走來走去,沒有片刻時間左顧右盼。每個人都表情嚴肅,卻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然而,偌大的公司裡,沒有一個人能夠與我一起分享看風景時的心情。英國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說《窗外有藍天》,很久以前看過,書中具體的情節我已經記不清了,卻記得那個小小的、簡單的、窗外有片藍天的房間。
我沒有一個房間,但我有一個角落。
我經常往遠方眺望,遠方依稀可見煙雨迷濛的瘦西湖,瘦西湖邊上白塔的塔尖也還有模糊的輪廓。可惜,湖邊的高樓越來越多,視線也越來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把樓房越蓋越高,為什麼樓房與樓房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人們把鴿子關進鳥籠,最後自己也住進了鳥籠。
我喜歡童年時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個小院子曾經就在瘦西湖的邊上。屋簷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跡,木梁上的燕子窩中有時落下一兩片羽毛。可是,在幾年前的房地產開發熱中,這個可愛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連同我童年溫軟的記憶。
我喜歡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歡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於同事對我說,你這麼年輕,為什麼總是穿著冰冷的、壓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對這樣的詢問,我笑而不答。心中卻隱隱作痛。黑色是內斂的、是悲哀的、是冷靜的、是堅強的。記得一篇小說中寫道:「很多有傷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為這樣不容易讓別人看到疼痛。」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願意讓旁人窺視到我的內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籬。我讓自己與外部世界保持著一分距離。像一隻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蟲,凝固,但是安全。
讀那本名叫《火與冰》的書,也有好長一段日子了。書中那些剛強的句子打動過我,更打動我的卻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邊沒有書。我當時讀的那本已經很破舊的書,並不屬於我。讀過之後,我也不想去書店買一本新的。因為讀過之後,這本書在「精神」的意義上就已屬於我了。書裡的好些句子我幾乎能夠背誦下來,也能夠感受到作者寫作時的心情。它們讓我如此牽腸掛肚。
從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著雨,天色灰濛濛的,像《紅樓夢》裡面那些讓作者和讀者一起哭泣的、所謂「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章節。此時此刻,我想起《火與冰》中那些憂憤的句子。在北國的風沙中,他有衝冠的怒髮嗎?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顆憂憤與感傷的心。
我給他寫信的時刻,不是我有意挑選的,卻恰好是一個孤獨與哀痛交織的時刻。他一定跟我一樣需要安慰。他身邊有安慰他的朋友嗎?
我不知道他的詳細地址以及與他有關的一切。然而,讀過一本他寫的書就足夠了──從「物質」
的意義上來說,那本書我僅僅擁有過一天(更準確地說,一個夜晚)的時間。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進公司以後唯一一件「假公濟私」的事:我把這封用一頁便籤寫就的短信,放進一封特快專遞裡,填好他的姓名地址。在吩咐祕書寄出一大疊商業信件的時候,把它混在公司的信件中發了出去。我實在怕自己沒有勇氣走到郵局親手投出這封突發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顯示,他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那麼,地址就簡單地寫上「北京大學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園讓我魂牽夢繞。中學時,我曾經沒日沒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後還是沒有能夠踏進去。就因為高考沒有發揮好,差了幾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樣,不情願地飄落到西湖邊上的那座校園裡。「暖風熏得遊人醉,西湖歌舞幾時休」,西湖美則美矣,卻不是一個念書的好地方。大學四年,濃濃的失落感一直伴隨著我。
畢業後,漸漸忘卻了有關校園裡的一切。照片都是會褪色的,記憶也一樣;花朵都是會飄落的,夢想也一樣。廷生的出現,重新勾起我昔日的夢想和創傷。他屬於那座校園,那座蔡元培和魯迅的校園,那座「五四」青年的長衫和白圍巾飄飄蕩蕩的校園,那座在血與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園。那座校園已經成為史詩,成為紀念碑,成為神話。北大的意義,早已經超越了一所大學。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麼的幸運啊。
他能否收到這封信,在我的信寫完以後,已經不重要了。寫信是對虛無的一種反抗。但寫完以後,我寧願忘記它,讓它像一個夢一樣在我的生命中消失。舉重若輕。
正如《世說新語》中那個有名的「雪中訪戴」的故事。我很喜歡這個古老的故事。長袖飄飄的王子猷、鵝毛般的雪花、披著蓑衣的船夫、劃在溪水中的木槳……我要是畫家,我會畫這樣的一幅神韻流動的水墨畫。那麼,我也來學學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還得去上班。睡吧,睡吧。今天的日記寫得太長了。
最佳賣點 : ★一本誕生於世紀末的奇書,意外搭起了兩個燃燒熱誠的靈魂。這不只是一段愛情故事,更是一場對極權與真相的凝視與解構。
★以書信與日記交織的敘事,在文字的縫隙間窺探歷史的血色陰影,尋覓希望的微光。《香草山》推出25周年紀念版,這是一場愛情與自由的對話,也是時代與記憶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