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札記 (增訂版)
| 作者 | 李歐梵 |
|---|---|
| 出版社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音樂札記 (增訂版):本書是李歐梵教授兩本音樂隨筆《交響》《音樂札記》的合集。對作者來說,古典音樂就是日常生活,至少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典音樂從來沒有死,還是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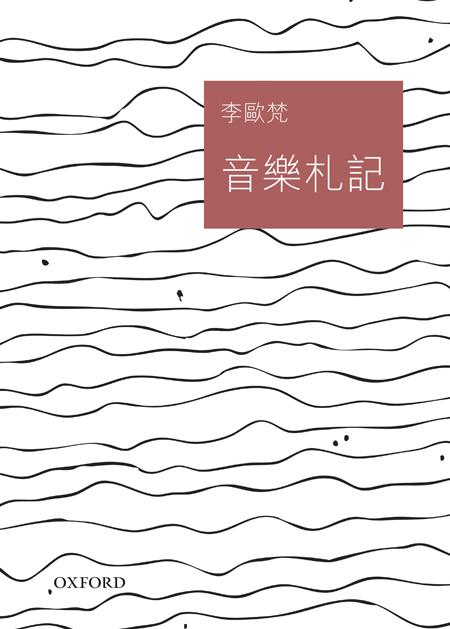
| 作者 | 李歐梵 |
|---|---|
| 出版社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音樂札記 (增訂版):本書是李歐梵教授兩本音樂隨筆《交響》《音樂札記》的合集。對作者來說,古典音樂就是日常生活,至少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典音樂從來沒有死,還是活 |
內容簡介 本書是李歐梵教授兩本音樂隨筆《交響》《音樂札記》的合集。對作者來說, 古典音樂就是日常生活, 至少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典音樂從來沒有死, 還是活生生的。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李歐梵2015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河南太康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中央研究員院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曾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著述包括:《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學的徊想》、《西湖的彼岸》、《上海摩登》、《狐狸洞話語》、《世紀末囈語》、《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清水灣畔的臆語》、《我的哈佛歲月》、《蒼涼與世故》、《又一城狂想曲》、《交響》、《睇色戒》、《人文文本》等。
產品目錄 第一部分 聽莫扎特的心路歷程 莫扎特音樂司以養生 《魔笛》狂想曲 陳酒愈醇一聽莫扎特《費加羅婚禮》 看賴聲川的《費加羅婚禮》 波恩的莫扎特 還我莫扎特 後期莫扎特 莫扎特和蕭斯達高維契一天堂對話錄 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一(紀念節曰) 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二(我讀《見證》) 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四(形式主義的渾沌?) 發現蕭奇斯達高維契之五(「反對形式主義的小天堂」) 發現爾斯達高雄契之六(革命也斷腸) 發現爾斯達高雄契之七(輕與重) 發現肅斯達高維契之八(樂觀與悲觀) 今天我也聽馬勒 馬勒的《復活》交響曲 馬勒的音樂盛宴 聽馬勒,談「港樂」 馬勒的第四交響樂 生命的奉獻一談馬勒的第八交響樂 聽《大地之歌》 壯觀的演出一聽馬勒第八交響曲 馬勒的《第九交響曲》 拉陶成竹在胸 柏林愛樂樂園 - 一流音樂家的互動 聽柏林愛樂樂團 漫談狄信湯瑪斯 三藩市交響樂團 美國樂壇新星的《電子吉他協奏曲》 香港文化中心 - 不能聽馬友友演奏巴哈 古風今詮 華人音樂家印象 香港聆樂手記 文學、 電影 、音樂 「敝帚」並不「自珍」 - 有覆於戴天者 《夢幻曲》的童年回憶 布拉姆斯晚年的鋼琴小品 第二部分 貝多芬的晚期風格 紀念西貝流士 霍夫曼斯塔爾與《玫瑰騎士》 浪漫的餘燼 向蕭斯達高維契致敬 聽葛利格 葛利約夫的神奇音樂 郭文景歌劇美首演驚艷 史克里亞賓的神秘音樂 指揮家掠影 芝加哥時代的蕭提 紀念托斯卡尼尼 紀念卡拉揚 激情的魔力 談根特萬德 指揮家的魔術大師 和迪華特-席談 誰還記得杜拉第 艾森巴哈的馬勒 張弦執棒紐約愛樂技驚香港 紀念羅斯托波維奇 紀念里希特:一位「謎」樣的鋼琴大師 天賦的抒情男高音 閒談五位女高音 誰是Diva 聽音樂會札記 我的天王歌星 海菲茲站和雷賓 我的唱碟入門經 遨遊歐洲的音樂節和音樂景點 我的音樂因緣與姻緣 李子玉
| 書名 / | 音樂札記 (增訂版) |
|---|---|
| 作者 / | 李歐梵 |
| 簡介 / | 音樂札記 (增訂版):本書是李歐梵教授兩本音樂隨筆《交響》《音樂札記》的合集。對作者來說,古典音樂就是日常生活,至少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典音樂從來沒有死,還是活 |
| 出版社 /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0199426331 |
| ISBN10 / | 0199426333 |
| EAN / | 9780199426331 |
| 誠品26碼 / | 2681207486002 |
| 頁數 / | 414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聽莫札特的心路歷程
年輕時候,我並不大喜歡聽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因為在中學時代,每天中午學校的播音器播出都會莫扎特的歌劇序曲 《費加羅婚禮》、《魔笛》、《唐。喬望尼》。聽來聽去,似乎都差不多。但有時也禁不住聞聲起舞,獨自指揮起來。
多年後到美國留學,看了一部歐洲電影,名叫Elvira Madigan,片中的背景音樂是莫扎特的C大調第二十一鋼琴協奏曲(K467),就此迷上了。後來我自己拍了一部無聲小電影,靈機一動,也用他的第二十三號鋼琴協奏曲(K488)的第二樂章作配樂,自我陶醉,從此愛上了莫扎特的所有鋼琴協奏曲。每當課業壓力太大的時候,我必以此調劑心靈。
這兩年在香港任教,又異想天開,想以莫扎特的音樂來修身養性,特別是他的弦樂五重奏(K516),並開始在《信報》寫文章,大力吹噓,自鳴得意。最近又發現:其實莫扎特的音樂中最動人的還是人聲,香港小交響樂團的指揮葉詠詩也曾提到:要把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奏得好,必須把它的樂句彈得像歌唱一樣,才能收到行雲流水之效。我的首選當然還是《費加羅婚禮》──還有三十多首詠嘆調,這些曲子,長短不一,真是美不勝收,有的很像莫扎特的歌劇選曲,有的卻單獨存在,供特殊場合或演唱會之用。例如其中一首(K505),當然包括一段-段頗長的鋼琴伴奏──人聲、琴聲和樂隊合成一體,猶如把鋼琴協奏曲放在歌劇詠嘆調之中,真是別開生面。還有一首是我的摯愛Vorrei Spiegarvi,O Dio! (上帝,我如何表達,K418)》更是動人之至,中間那段「啊-啊」的花腔裝飾音,技巧甚難,技術到了極高的境界,也把我的心帶到九霄雲外,原來這是一首情歌。
「天若有情天亦老」──在歲月日長的時候聽莫扎特,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看來莫札特的音樂將伴我足此生。
莫札特音樂可以養生
古典音樂可以養生?你有冇搞錯?
不少人早上起來做運動,做晨操,隨著急速的音樂旋律,伸手彎腰,蹦蹦跳跳,我覺得對我這種「後中年」或「前老年」的人太激烈了。我和妻子醒來也做晨操,但作的是一種較溫和的「五一五平衡操」,把渾身的穴位和關節先疏通了,然後起床。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音響,此時剛睡醒,太多希望有一個寧靜的自我時間和空間,不喜歡聽到別人嘮嘮叨叨的講話,但打開收音機,台台都有人在講話,實在受不了,只好關上收音機,選幾張古典音樂的唱碟來聽。
清晨時分頭腦不能夠承受太多的刺激,所以音樂選擇也以較溫和或輕鬆的為主,大部頭的交響樂或歌劇還是晚間聽為宜。我近來最喜歡聽的是莫札特的弦樂四重奏和五重奏(四種弦樂器加一把中提琴),認為這才是養生的「妙藥」!
有人說母牛吃草時聽莫札特的音樂,體內牛奶就會增多,襁褓中的嬰兒多聽莫札特的音樂,也會更有智慧。這類傳說我卻半信半疑,況且我早已過幼童時代,現在只會在學院裏「俯首甘為儒子牛」的身分,教書不用擠奶,但需用腦,人到了這個歲數,只求自己身心健康,多活幾年,與吾妻常相廝守。這個願望卻和莫札特的生平大相逕庭,他生前命途多舛,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五歲。不過,他仍然為後世留下了如此豐富的音樂遺產,我從中選幾首四重奏來調養身心、陶冶性情,又有何不可?
早上聽莫扎特,別有一番滋昧,特別是弦樂的聲音更能浸入我心(我幼時學過小提琴)。莫扎特的音樂旋律永遠那麼優美,節奏輕盈,聽來絕不拖泥帶水,令我全身舒暢。只聽小提琴奏鳴曲則略嫌單薄,而四重奏或五重奏則猶如四五好友娓娓私語,更帶有一種人道精神,無形中感受到一種「做人」的樂趣,而不像聽現代作曲家如勛伯格那麼絕望。這當然是我的主觀想法和願望,你可以不信。
更妙的是莫扎特的音樂節奏更適於健身,以我甚喜歡的《G小調弦樂五重奏》(K516)為例。開始的第一樂章(快板)就使我不自覺地隨著節奏「搖頭擺尾」起來,但耳朵裏傳來的卻是第一小提琴和第一中提琴的對話,所以我也時左時右地傾聽(用耳機聽更傳神),主旋律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變奏,直到結尾時我的頭部也左右前後搖擺得差不多了。到了第二樂章的Menuetto,我從坐姿改為站姿,竟然跳起宮廷舞來,跨著小方步,或在原地踏步,雙手開始指揮,兩臂略作伸展,一邊聽著那兩把中提琴的聲音在輕輕地飛來飛去,而第一小提琴的聲音似乎早已飛向雲端,只有第二小提琴和大提琴還在打拍子。到了第三樂章(不太慢的慢版),音調緩和了一點,我又坐在沙發上靜聽,卻逐漸感受到一股衷傷,似乎莫扎特在偷偷地流眼淚,我也屏息靜氣,隨著那股傷感的調子,緩緩地做深呼吸。當旋律漸慢時我不自覺地彎下身子,兩手幾乎著地,想要向莫扎特的亡魂頂禮膜拜,繼之又仰起身子,嘆了一口氣,隨著節拍點頭。到了最後第四樂章,開始時又是慢板,小提琴和大提琴一句接一句地互相傾訴,中提琴卻在旁伺候,一波又一波的情感湧了出來,我聽呆了,不覺閉上眼睛,但節奏又突然轉成快板,於是又帶著我跳起舞來,但又覺梅莫扎特欲言又止,把悲情隱藏在較快的節奏後面。於是我又「搖頭擺尾」起來,兩腿在原地作小步舞,兩臂似指非指,上下作展翼狀,頓覺自己的靈魂也飛上了天。
一曲聽完,不覺已過了半個鐘頭,我的身心都被洗滌得乾乾淨淨!翻開此曲的解說,這才發現此曲是莫扎特喪父不久之後作的,怪不得「欲蓋彌彰」還是掩蓋不了悲情,但他的樂曲節奏──不論是快板或慢板──都像是行雲流水,帶給聽者一股無以名狀的安慰和快感。經過半小時的修身養性的功夫之後,就該出門「搏命」去了。
看至此處,很多讀者一定會說,你早已半退休了,所以才有閒情聽音樂,我們一早起身就要去趕地鐵上班,早飯都來不及吃,何來時間聽音樂?此言不虛。觸動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一件真實的遭遇。在一次音樂會中見到我妻以前在保險公司工作的一位同事,相談甚歡,因為他也是一個古典音樂迷,年紀比我輕得多,他告訴我說,每天上午工作前一定要聽一個多小時的古典音樂,才有精神去「搏命」。
除了養生之外,古典音樂的用途更多。我在讀書寫作時必聽音樂,即使不能專心聽每一個音符,當「背景音樂」聽也自得其樂。此時我就會聽莫扎特的交響樂和鋼琴協奏曲,特別是後者。他一生作了三十多首鋼琴協奏曲,曲曲精彰。開車上班的人在車中聽這種音樂也最適合,保證輕鬆愉快,心平氣和。我聽著則更有寫作靈感。因為這些曲子勾起了我不少回憶,內中尤以第23號鋼琴協奏曲(A大調,K488)為最。記得三十多年前我還在哈佛做研究生的時候,讀書之餘喜做「玩電影」,用8厘米的攝影機拍了一部二十多分鐘的默片,在首映這部「處女作」時,我就用這首曲子作配音。片中有一景,一個華人留學生孤苦伶仃回家自己做飯吃,還特別在餐桌上點了蠟燭,然後又去開唱機,邊吃邊聽莫扎特的這首協奏曲的慢板樂章。雖然我臨場手忙腳亂,但演出還是很成功,在自己和一位朋友租住的公寓裏,大家濟濟一堂,有人為我拍下一張做「放映師」的珍貴照片,曾被牛津大學出版社採用作拙著《我的哈佛歲月》的封面。我的這本書也是在莫扎特的音樂聲中寫出來的(走筆至此,耳邊卻傳來莫扎特弦樂四重奏第18號K464的慢板樂章,今天只聽莫扎特)!
因此多年來在懷舊之餘,我對這首鋼琴協奏曲也情有獨鐘,百聽不厭。有時候一邊聽「老版本」的莫扎特鋼琴協奏曲,一邊重溫經典名著,真是別有一番滋昧在心頭。就以此曲為例,從第二樂章的「慢板」(Adagio)到第三樂章的「頗快板」(Allegro Assai),在高手如魯賓斯坦的演奏之下,轉接得天衣無縫,樂隊的節奏與鋼琴互相唱和,我聽時不知不覺又點起頭來,此時又在心目中默念菲茨拉爾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流暢的英文句子,音樂和文學在腦中混在一起,真是不亦樂乎。誰說讀菲茨傑拉爾德(Fitzgerald)必須聽爵士樂,就因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正是「爵士年代」?於是我又想到理論家(也是古典音樂愛好者)薩伊德所謂的「對等讀法」(contrapuntal reading)──把文本和其所產生的社會脈絡作「對等」讀,我為何又不可以把莫扎特和菲茨傑拉爾德對著讀,也許真的犯了「政治不正確」的大忌!管他呢,反正我閱讀文學經典和聽古典音樂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個人身心的愉悅。
到晚飯時間,老婆為我做了各樣素食,美味可口,但我還是先要選出一張莫扎特的唱片助興,他的夜曲,不是一般常聽到的《小夜曲》──半個世紀前我在新竹中學做初中生的時候,每天中午在教堂吃午餐「便當」的時候,學校的播音器都會傳來這首極熟悉的調子,我實在有點聽厭了──而是他的兩首Serenade《哈弗納》(Haffner)和《郵號角》(Posthorn),吃著吃著,我又跳起舞來,老婆罵我一句「神經病」,我說這樣可以幫助消化,又是養生之道,何樂而不為 。
對於我在日常生活中每天聽莫扎特,有人也許會問:如果不喜歡莫扎特怎麼辦?我的回答是:換上你喜歡的作曲家就行了。莫扎特之外,還有海頓,試試他的《玩具》、《時鐘》或《驚愕》,如果嫌海頓「爸爸」太老氣了,還有永遠的布拉姆斯。
說起布拉姆斯,香港小交響樂團的指揮葉詠詩也十分愛好他的交響樂,還特別指揮了一場介紹布拉姆斯的音樂會,聽眾反應熱烈,我也躬逢其盛,增長不少音樂知識。最近她又在一另場音樂會中指揮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速度奇快!我邊聽邊想,如果拖了我上台指揮此曲,如果也用這個速度的話,我必會昏倒在台上!
不錯,我有時也用布拉姆斯的四首交響曲來運動健身,聽著他那種欲言又止的衷怨樂句,我又會「揭竿而起」──只要手邊有任何像指揮棒的東西,如鋼筆、鉛筆、刀叉或筷子皆可,大力揮舞,把情緒揮發出來,一個樂章尚未告終,我早已大汗淋漓,這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如果布拉姆斯的四首交響曲仍然太沉悶,還有他的《匈牙利舞曲》,可以隨歌起舞。聽不慣布拉姆斯,也可以聽較輕鬆的德伏扎克,他和貝多芬一樣,作了九首交響曲,尤以第九(別號「新世界」)最有名,也是我在家對老婆表演的拿手好戲。當然,更輕盈也更適合運動的是他的《斯洛伐克舞曲》,優美的節奏可以帶你神遊波希米亞的草原。
走筆至此,才發現自己又在為古典音樂做廣告,在香港這可能是一種反潮流的行為。年輕人或會怪我:「老頭子才會用古典音樂來健身養生,我們不要慢板,只要快板!」不錯,流行曲抓住了年輕人的欲望脈搏和節奏,但內容未免太單薄了一點吧!其實古典音樂中以性和慾望為主題的也不少,拉威爾(Maurice Ravel, 1875-1937)的《波烈羅》一向被視為做愛的音樂,其實不然,它只能做﹝前奏曲﹞後面的「重頭戲」要配以奧弗的《布拉挪之歌》(Carmina Burana),那才是高歌狂歡、高潮迭起的音樂!但最好還是雙方帶了耳機聽,以兔影響鄰居的睡眠,因為他們明天一大早還要起床上班,為賺錢而「搏命」。
《魔笛》狂想曲
二OO六年是莫扎特誕生二百五十週年,舉世同慶,但各地慶祝的方法也各異。
一月二十七日是莫扎特誕生日,是晚,香港小交響樂團和香港電台第四台合辦莫扎特的慶生音樂會,竟然也在音樂會前唱起「生日快樂」的歌曲來了。我聽後不以為然,對朋友說:唱這首歌不夠創意,莫扎特在天之靈也聽不進去,何不唱他的歌劇《魔笛》中的那段帕帕基諾和帕帕基娜的愛情二重唱?想莫扎特聽到了一定高興。不料該場音樂會的壓軸戲就是這首二重唱!原來第四台主辦的選舉結果適時揭曉:港人最喜歡的莫特作品就是《魔笛》。
太好了!《魔笛》真是老少咸宜,充滿了歡樂的氣氛,雖然是莫扎特死前最後的一首歌劇作品,但絲毫沒有顯露窮途潦倒的情境。況且這齣歌劇的首演不在維也納的宮廷豪宅,而是在郊區的一家戲院,莫扎特還帶了他的幼子親自去觀賞表演。據影片《莫扎特傳》(Amadeus)的描述(且不管是否屬實),這本來就是給一般平民看的歌劇。
時過境遷,莫扎特的全部作品都進入「高雅」之堂,成了古典音樂。其實莫扎特應該是雅俗共賞的,每當我哼起那首帕帕基諾/基娜(連兩個角色的名字也像Twins)的二重唱,都禁不住拉著我妻跳起搖滾舞來!香港電台第四台的古典音樂節目主持人鍾子豪,他說也是在中學時代初聽莫扎特的《魔筒》序曲才逐漸入迷的,和我一樣;不過他聽的是電結他版,「發現變化很多,每句句子雖然好長,但與搖滾樂每四個bar重複一次很不同。它是不斷變奏,不斷發展下去的。」於是他買回原裝莫扎特唱片來聽,逐漸上了癮,走上音樂之路。
而我則是在中學時代,每天中午休息時,學校的擴音器就會播出《魔笛》和《費加羅婚禮》等莫扎特歌劇序曲,時間一久,他的音樂也潛移默化進入我的「下意識」中去了 。
以職業性的方式高調談論莫扎特音樂的妙處,非我所長,我寧願把我心目中的莫扎特用普通的語言說出來,獻給大眾,與民同樂。因此才妙想天開,除了早已發表演說,並寫過莫扎特可以養生論外,此次又不自量力,想把歌劇《魔笛》的故事改寫成武俠小說,說不定哪一位香港藝壇的奇才可以將之搬上舞台,甚至拍成電影。故事大綱如下:
話說遠古之未來,奧國武夷山上狂風大作,有恐龍來襲,內中最兇之億年巨龍,把一個年輕王于咬在嘴上,即將噬而吞之。說時遲那時快,突然雷電交作,巨龍受電劈而斃,原來有三位美貌仙女及時趕到,勇救落難王子塔米諾,此時這位年輕王子早已嚇得魂不附體,昏迷不醒。三仙女見其貌如潘安,不禁個個生戀慕之情,都想學白蛇青蛇一樣還俗嫁給他。爭執不,只好乘雲駕霧而去,歸報主子,原來此三女皆黑夜仙后之侍女也。
未幾,塔米諾王子醒來,不知身在何處,卻發現腳邊臥著巨龍屍體,不禁大驚失色,又將昏倒之際,忽聞遠處有人唱歌,伴著風笛聲,徐徐而來,隨即見到一個似人似鳥的捕鳥人,邊走邊唱兒來,名叫帕帕基諾,並自稱是屠龍大俠!塔米諾連忙上前謝救命之恩,不料背後三仙女突然又出現,大聲喝斥曰:「帕帕基諾,你又犯過!現罰你以水帶酒、以石頭代饅頭,不許吃喝玩樂!」又唸起咒語,令帕帕基諾三緘其口──三日內不得說話。三仙女與塔米諾依依難捨而別,行前留下照片一幀,卻是黑夜仙后之獨生女芭米娜的玉照,嬌小迷人,王子一望鍾情,恨不得立時與之結為美眷。
王子正意亂情迷之際,突見地上冒起一陣黑煙,原來黑夜仙后終於駕到,塔米諾及眾仙女連忙叩拜。女后曰其掌上明珠已遭魔王撒拉斯圖所拐,生死不明,故求塔米諾前往營救,如成功歸來,則以女相許。又命三仙女解除帕帕基諾之符咒,如成功歸來,則以女相許。又有三仙童自天而降,在旁指引帶路。二人不感怠慢,行行復行行,不到數個時辰,就見到遠處金光閃閃,乃撒拉斯圖之城堡也。
走筆至此,第一幕的故事才說了一半,因篇幅所限,只好賣個關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但如繼續說到第二幕,則故事的哲理味也漸濃,內容涉及十八世紀歐洲貴族之秘密「黑社會」的入門儀式(initiation rites),莫札特當年亦曾參加過一個黑社會,但此類祕密結社並非練武之用,而是清談啟蒙玄學,故此中學問大矣。然而如拍成電影,可以輔之以特技效果,一定老少咸宜,因此我先要列出這部影片的理想「卡士」,把各路精英一網打盡:
塔米諾──鄭伊健
芭米娜──梁詠琪(傳二人雖已分了,但演戲又何坊?何況還是莫札特的《魔笛》!)
帕帕基諾──周星馳(但我妻認為此配角,星爺可能不願屈就,遂提名曾志 偉,亦甚佳)。
帕帕基娜──吳君如(與曾志偉應屬絕配)
撒拉斯圖──黃秋生(遽聞他也希歡莫札特的歌劇)
黑夜仙后──鄭佩佩(《臥虎藏龍》之後,對這個角色一定駕清就熟)
三仙女──Twins加上林嘉欣
編劇、填詞──陶傑、邁克
導演──胡恩威、林奕華
監製──成龍
配音──莫札特
這些明星都不會唱歌劇,怎麼辦?不要緊,可以乾脆改編為特技武打神怪片,
把莫札特音樂以電子吉他奏出來,做幕後配音。如仍願把莫札特的歌劇以廣東話
唱出,則可演雙簧,並請香港歌劇團的總監莫華倫另組歌唱班子唱出來。
至於在下,當然也有表演慾望,只不過才華不足,只能演個小配角如撒拉斯
圖殿下的祭司,在第二幕才登場,跑跑龍套,過過癮,則於願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