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preter of Maladies
| 作者 | Jhumpa Lahiri |
|---|---|
| 出版社 |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醫生的翻譯員 (增訂新版):★鍾芭.拉希莉首部作品,普立茲文學獎得獎作。★全球暢銷一千五百萬冊。★書名同名短篇〈醫生的翻譯員〉,同時也獲得歐亨利獎(O.HenryAdwar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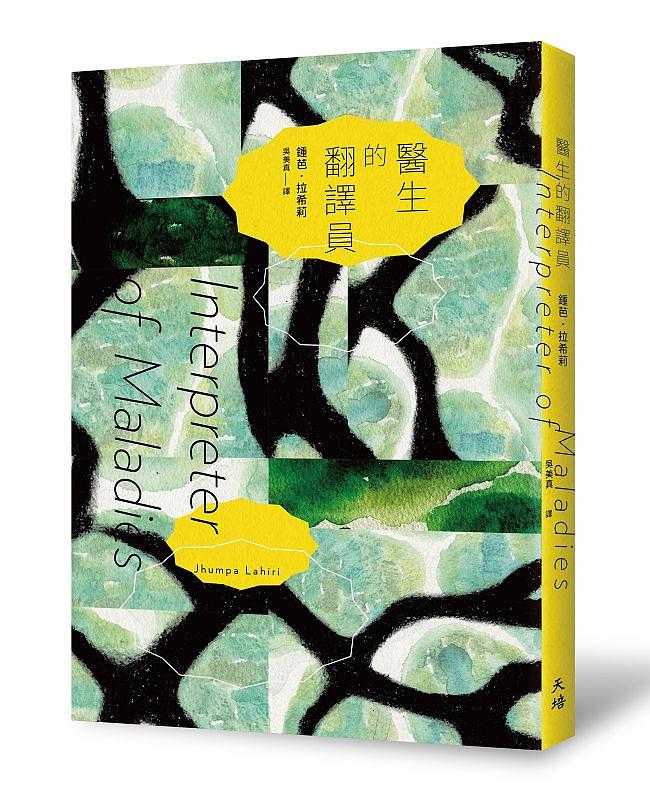
| 作者 | Jhumpa Lahiri |
|---|---|
| 出版社 |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醫生的翻譯員 (增訂新版):★鍾芭.拉希莉首部作品,普立茲文學獎得獎作。★全球暢銷一千五百萬冊。★書名同名短篇〈醫生的翻譯員〉,同時也獲得歐亨利獎(O.HenryAdward) |
內容簡介 ◎鍾芭.拉希莉首部作品,普立茲文學獎得獎作。◎全球暢銷一千五百萬冊。◎書名同名短篇〈醫生的翻譯員〉,同時也獲得歐亨利獎(O.Henry Adward)、最佳美國短篇小說獎(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二○○○年普立茲獎和《紐約客》小說新人獎、海明威獎◎《中央日報》出版與閱讀十大好書榜《醫生的翻譯員》入選二○○一年翻譯類好書榜◎專文導讀:作家/郭強生《醫生的翻譯員》共收錄普立茲文學獎得主鍾芭.拉希莉的九篇短篇小說。其中同名篇章<醫生的翻譯員>除了榮獲二○○○年普立茲獎、海明威小說獎、紐約客小說新人獎等大獎,也獲得歐亨利獎及最佳美國短篇小說獎。鍾芭.拉希莉善於捕捉平凡中的深刻,轉化為筆下簡單乾淨的文字,訴說最動人的故事。例如首篇<一件暫時的事>讓已經失愛的夫婦,在無光的晚餐中,反而能真誠的面對彼此;<醫生的翻譯員>描繪妻子百轉千迴的心事,而丈夫卻一概未覺,兩人漸行漸遠的必然;<皮札達先生來晚餐>則從孩童眼中看著大人對於家鄉的渴望。其他篇章或者在故事中突顯印度文化的瑰麗或腐朽;或者從異鄉人的失落感擴及現代人的孤寂,充滿美麗的異國情調,引發每個人內心深處對心靈原鄉的嚮往。作者三十二歲出版第一本書即獲普立茲大獎,是繼阿蘭達帝.洛伊《微物之神》後再度掀起的印度海外文學熱潮的印裔美籍女作家。「《醫生的翻譯員》是印度裔美籍作家鍾芭.拉希莉獲得普立茲獎的短篇小說集。集子中收錄九個短篇小說,就文學技巧而言,它們最大的特色在於:反璞歸真,手法近乎平淡,沒有運用任何繁複艱澀的文學技巧。小說回復它的原初面貌:說故事,把故事說得動人、親切、誠懇,卻不流於煽情。」--台大外文系教授/邱錦榮「在這九篇故事中,拉希莉小心翼翼的輕探,但她的觀察卻非常精準,故事有苦有樂,並未受懷舊影響而過度美化。」--《出版者週刊》「在這本收錄九篇閃閃發光、引人共鳴的短篇小說集裡,印度如影隨形。拉希莉寫出了人們面臨新環境、關係與文化的調適上極為複雜的過程。」--《柯克斯書評》「拉希莉一出手即不同凡響。她的文字極富魅力,讀來讓人絲毫不覺是年輕作家的首部作品。」--《紐約時報》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印裔美國作家,出生於倫敦,成長於美國羅德島,畢業於美國波士頓大學,目前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二○○○年以短篇小說集《醫生的翻譯員》獲普立茲文學獎;第一部長篇小說《同名之人》曾改編電視劇,《陌生的土地》則獲得弗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第二部長篇小說《低地的風信子》入圍美國國家書卷獎決選、英國曼布克獎決選。新作《另一種語言》則獲維亞雷吉歐–維西利亞國際獎(Premio Internazionale Viareggio-Versilia)。此外她亦曾獲海明威筆會文學獎、馬拉末筆會獎、歐亨利小說獎。拉希莉也曾於二○一四年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義大利語界翻譯小說獎(Premio Gregor von Rezzori)、DSC南亞文學獎,她亦獲古根漢研究基金,並於二○一二年受邀擔任美國藝術文學學會會員。■譯者簡介吳美真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班肄業。譯有《麥迪遜橋》、《沙郡年記》、《微物之神》、《汀克溪畔的朝聖者》、《從月亮來的男孩》等書。
產品目錄 鄉愁的消逝(導讀)郭強生一件暫時的事皮札達先生來晚餐醫生的翻譯員(獲歐亨利小說獎及最佳美國短篇小說獎)一個真正的「都爾旺」性 感賽恩太太的公寓受到福佑的家祕 方第三暨最後一個大陸
| 書名 / | 醫生的翻譯員 (增訂新版) |
|---|---|
| 作者 / | Jhumpa Lahiri |
| 簡介 / | 醫生的翻譯員 (增訂新版):★鍾芭.拉希莉首部作品,普立茲文學獎得獎作。★全球暢銷一千五百萬冊。★書名同名短篇〈醫生的翻譯員〉,同時也獲得歐亨利獎(O.HenryAdward) |
| 出版社 / |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9583572 |
| ISBN10 / | 9869583571 |
| EAN / | 9789869583572 |
| 誠品26碼 / | 2681619747005 |
| 頁數 / | 288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導讀 : 鄉愁的消逝 郭強生
即使你對政治或第三世界毫不關心,對文學理論後殖民文化分析一無所知,鍾芭‧拉希莉這本榮獲美國文學最高榮譽普立茲獎的短篇小說集仍是引領你進入文學欣賞門檻的最佳選擇。有些「重量級」的文學作品,非得一籮筐的術語才能把它的好處說個清楚,但對於《醫生的翻譯員》我寧願捨棄我學說式的讀法。譬如回溯到E. M. Forster的《印度之旅》,討論「印度」在西方文學中的隱喻功能(metaphor)。或者我也可從二○○○年美國兩項文學大獎皆由亞裔移民雙語作家包辦,提出族裔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觀察報告。另外更明顯可作的文章便是集子中的女性角色們不是許配為婚便是作人情婦。印度文化中的父權陰影怎麼了得!然而時下小說除上述之外還能給予讀者更多難得、冠冕堂皇的題目,我想還是留給一些我不得不找話說的作品吧。我最想討論的,其實也是最根本,卻在近幾年最不受重視的觀點,那就是──小說應該怎麼寫?
整個八○年代在後現代、後結構風潮狂飆下,小說這個文類幾乎已到了愛怎麼寫就怎麼寫的化境,各類實驗性小說紛紛出籠,一片大鳴大放好氣象。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在千禧之初曾特別策劃專題,討論新世紀的小說走勢。任碧蓮(Gish Jen)這位唯一被厄普戴克(John Updike)選入《美國世紀最佳短篇小說》的華裔小說家發表了以下的意見:「美國作家多年來一貫追求的是求新求變強調獨特風格的路線,反應美國文化中個人主義的特色。但是近年來一些嶄露頭角的新作,尤其是移民文學,它們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對大師、名著的嚮往。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中,你可以聽見他們彷彿在說﹃我也想這樣寫寫看!﹄」
然而我以為,將哈金、鍾芭‧拉希莉……這幾位文壇新貴的作品貼上「傳統」的標籤,列入大師模擬(mimesis)派別並不完全妥當。哈金來自中國,改以英語創作小說,收穫豐碩。拉希莉這位印度新移民的後裔,專寫印裔在美國的鄉愁及憧憬,處女作一鳴驚人。他二人還是波士頓大學(BU)創作研究所的同班同學。哈金以《等待》一書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拉希莉這本《醫生的翻譯員》除了普立茲獎外,在二○○○年同時拿下了海明威小說獎及紐約客小說新人獎。為什麼他們在同儕眼中技巧稱不上創新的作品,能讓書評及評審委員驚豔?
讀完拉希莉這本小說集後,這個問題的答案至少對我個人來說可以說十分清晰了。作家要具備天份,而天份不光在遣辭用句的造詣上,更重要的是對人情世故的體會,有過人一等的細膩真誠。拉希莉及其他非盎格魯薩克遜英語系小說家由於自身文化背景的特殊,對社會觀察及人與人之間衝突矛盾的描繪,都直接關係自身的信仰認同,題材的本身輻射面即已十分寬廣,不必再用結構奇巧或語言創作來增加「深度」。拉希莉最難能可貴之處是將抽象的殖民文化論戰,或看似陳舊的異鄉情緒落實,並賦與新義。要達到這樣的效果無非是考驗小說家說故事的本領。與其說拉希莉是復古,或是模擬大師,不妨說是她肯定了小說中的幾樣基本元素:佈局(plot)、觀點(point of view)、人物(character)及題旨(theme),以下我便以全書中我最喜歡的一篇〈賽恩太太的公寓〉為例,剖析作者如何善用並發揮這幾項小說要領。
一、觀點 這篇故事以小男孩艾略特的觀點作主軸,從他眼中我們看到了這位印度太太生活的點點滴滴。賽恩太太追隨在大學數學系任教的丈夫移民美國,為貼補家用在佈告欄上貼出廣告願意擔任課後保母。艾略特這個典型美國現代社會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小男孩便這樣一腳踏進了這個生活習慣迥然不同的印度家庭裡。他看到了賽恩太太的不快樂和失落感,卻也同時看到了他的世界,他的社會對賽恩太太這樣的新移民的態度,但是巧妙的是,在艾略特的注視下,賽恩太太對美國生活(如單親家庭)及文化(如絕對自我及隱私)的觀點也同時浮現,交插成為雙向式的觀照。
二、佈局 故事中必然要有事件,這個故事中有兩件事情緊緊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一主一副,卻又互成因果。主要事件是賽恩太太要考駕照,副線是賽恩太太在魚市場訂購的新鮮生魚如何取回。不諳駕駛的賽恩太太先是要求丈夫每天在教書空檔來回奔波,之後又自謀出路不成。駕照問題與取魚在故事終了匯成一線,令讀者不得不驚訝拉希莉在整個故事佈局上的細緻與自然。
三、人物 小說中最難處理不是主要角色而是其他陪襯性的次要人物。拉希莉除了成功塑造了賽恩太太這個令人同情的角色外,對於艾略特的母親,賽恩先生,甚至魚市老闆都能要言不繁,幾個細節便讓這些背景人物躍然紙上。沒有了這些配角的畫龍點睛功能,整個故事的真實感勢必大打折扣。
四、題旨 失落與錯置,寂寞與懷鄉是這篇故事的表面主題。相較於許多移民文學掉入了感傷濫調,賽恩太太的故事卻有深一層的主題 關於成長。這又教讀者到了結尾不得不會心讚歎,為何選用艾略特做為敘述的觀點。艾略特最後成了鑰匙兒童,他即將面對的是美國強調獨立,卻也充滿疏離的成人世界。究竟賽恩太太是艾略特的保母,還是艾略特在照顧賽恩太太?賽恩太太與艾略特的未來同樣充滿挑戰和未知。這二人的命運就這樣短暫的交會,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像是與自己的故鄉漸行漸遠。不耽溺於鄉愁,不重複刻板文化印象,在淡淡的哀傷中總隱藏了生命的契機是拉希莉這本集子的精髓。如果說她對傳統寫實小說還有某種鄉愁式的嚮往,她也以這部作品證明了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沒有人能夠背棄忽視。在她靈動的文筆帶領下,讀者也都有了回家的感覺……。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戲劇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內文 : 在茶攤,達斯先生和太太爭論誰該帶提娜去洗手間。最後,當達斯先生指出前一晚幫提娜洗澡的人是他時,達斯太太讓步了。卡帕西先生從後視鏡看到達斯太太拖著她那雙大半裸露在外且刮過腿毛的腿,穿過後座慢慢移到他那輛龐大的白色「大使」的另一邊。當她們走向洗手間時,她沒有拉小女孩的手。
他們正要去參觀位於科納拉克(konarsk)的太陽神殿。那是一個乾燥、陽光燦爛的星期六,持續吹來的海風緩和了仲夏的熱氣,是觀光的理想天氣。一般而言,上路後,卡帕西先生不會這麼快就停車,但是那天早上在桑迪維拉旅館載到這一家人後不到五分鐘,小女孩就開始抱怨了。當卡帕西先生看到達斯夫婦和他們的孩子站在旅館的柱廊下,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們很年輕,也許還不到三十歲。除了提娜外,他們還有兩個男孩,隆尼和巴比,他們的年紀似乎十分相近,牙齒被閃亮的銀色矯正器遮蓋著。這一家人看起來像印度人,但是他們的穿著打扮卻像外國人,孩子們穿著筆挺、鮮艷的衣服,戴著有半透明帽舌的鴨舌帽。卡帕西先生十分習慣外國觀光客;因為他會說英文,公司經常派他載他們觀光。昨天他載的是一對來自蘇格蘭的老夫婦,兩人都有一張佈滿斑點的臉,頭上蓬鬆而稀疏的白髮暴露出被太陽曬黑的頭皮。相較之下,達斯先生和太太那兩張年輕的深褐色臉顯得醒目多了。當卡帕西先生介紹自己,他兩手合什,以示問候,但是達斯先生卻像美國人那樣,緊緊握住他的手,使他的手肘也感覺得到他的握力。而達斯太太則牽動一邊的嘴角,恭順地對他微笑,但是顯然對他沒有任何興趣。
當他們在茶攤旁等待,隆尼──看起來像兩個男孩當中的哥哥──突然自後座爬出來,一隻綁在地上木樁上的山羊引起他的興趣。
「別碰牠。」達斯先生說,他的目光自一本平裝的旅遊手冊往上瞥了一眼,手冊封面以黃色字邊印著INDIA(印度),看起來像是國外出版的,他那帶著猶豫且略顯尖銳的聲音彷彿尚未發育成熟。
「我想給牠一片口香糖。」男孩邊疾步往前走,邊回頭大聲說。
達斯先生大步走下車在地上蹲了蹲以活動雙腳,他的臉刮得乾乾淨淨,看起來就像隆尼的放大版。他戴著一頂寶藍色的遮陽帽,穿著短褲、球鞋和T恤。他身上唯一複雜的東西只有掛在脖子上的相機──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長鏡頭,以及數不清的按鈕和標示。他皺著眉頭,看著隆尼衝向那隻山羊,但是顯然無意干涉。「巴比,留意不要讓你哥哥做出傻事。」
「我不要。」巴比動也不動。他坐在卡帕西先生旁邊的前座,正在研究一張貼在存物箱上的象神照片。
「不必擔心,」卡帕西先生說。「牠們很溫馴。」卡帕西先生四十六歲,頭髮漸漸往後脫落,而且已完全變成銀色。但是在他空暇時,會用蓮花油塗抹他黃褐色的臉和沒有皺紋的額頭,使人可以輕易想像他年輕時的模樣。他穿一條灰色長褲和一件搭配的夾克式襯衫,有腰身的短袖襯衫有著大大的尖領,是由薄但耐穿的人造纖維做成的。他向裁縫師指明樣式和布料──這是他當導遊時最喜歡穿的制服,因為即使長時間坐在駕駛座上,這種襯衫也不會被壓縐。透過擋風玻璃,他看著隆尼繞著那隻山羊移動,並迅速在牠的腹側摸一下,然後又快步跑回車裡。
「你在小時候離開印度的?」當達斯先生再度回到乘客座位,卡帕西先生問他。
「喔,我和米娜都在美國出生,」達斯突然以充滿自信的神情說。「在美國出生和長大。我的父母親現在住在這裡,在阿桑梭爾(Assansol)。他們退休了,我們每隔兩年就來看他們。」他轉頭看著小女孩跑向車子,她那件背心裙上寬鬆的紫色蝴蝶結在她狹窄的棕色肩膀上啪嗒跳動。她將一個洋娃娃抱在胸前,洋娃娃的黃色頭髮彷彿曾被一把不鋒利的剪刀剪過,以作為一種懲罰方式。「這是提娜第一次到印度?是不是?提娜!」
「我再也不必上洗手間了。」提娜說。
「米娜在哪裡?」達斯先生問。
卡帕西先生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達斯先生和小女孩說話時,竟然直稱她太太的名字。提娜指向達斯太太所在的地方:她正向在茶攤打赤膊的男人買東西。當達斯太太返回車裡時,卡帕西先生聽到另一個打赤膊的男人唱一句印地語流行情歌,但是達斯太太似乎並不了解歌詞,因為她沒有對那男人表示出惱怒、困窘,或做出任何反應。
他觀察她。她穿一件長度在膝蓋之上紅白相間的格子裙,一雙有方形木跟的無帶便鞋,一件樣式像男性內衣的緊身上衣。上衣的胸部裝飾著一個草莓形的印花布貼花。她是一個矮小的女人,有一雙像爪子般的小手,手指塗上晶晶發亮的粉紅色指甲油,以搭配她的嘴唇。她的身材略顯圓胖,頭髮側分,只比她丈夫的頭髮長一些。此外,她戴著一副帶粉紅色的暗褐色巨大太陽眼鏡,拎著一只幾乎和她的軀幹一樣大的草編袋,形狀像碗,袋裡的水瓶伸出外面。她慢慢走著,拿著一個以報紙摺成的大紙包,裡面有撒上花生及辣椒的爆米花。
達斯太太上車。「這趟觀光要多久?」她問,並關上車門。
「大約兩個小時半。」卡帕西先生回答。
聽到這個,達斯太太發出一個不耐煩的嘆息,彷彿她這輩子都在馬不停蹄地旅行。她以一本摺疊起來的孟買英文電影雜誌搧涼。
「我以為太陽神殿只在普里(Pun)以北十八哩的地方。」達斯先生說,並輕敲旅遊手冊。
「通往科納拉克的道路路況不佳。事實上,我們得走五十二哩。」卡帕西先生解釋。
達斯先生點頭,並重新調整相機的肩帶,因為它已開始擦痛他的頸背。
發動車子之前,卡帕西先生伸手到後面,確定每一道後門裡的鎖穩穩地鎖住了。車子一開始移動,小女孩便開始玩弄身邊的門鎖,讓它前後移動並喀噠作響,但是達斯太太沒有說什麼話阻止她。她有點兒無精打采地坐在後座的一端,沒有把她的爆米花分給任何人。隆尼和提娜坐在她的兩邊,兩人都啪啪作響地吹著鮮綠色的口香糖。
「看,」當車子開始加速時,巴比說。他以手指指著路旁高大的樹。「看。」
「猴子!」隆尼尖叫。「哇!」
那些猴子成群沿樹幹而坐,有閃亮的黑臉、銀色的軀體、水平的眉毛和冠狀的頭;牠們長長的灰色尾巴在樹葉間懸垂下來,像一條條的繩子。幾隻猴子以皮革質的黑手抓自己,或者擺動腳。當車子經過時,牠們瞪視著。
「我們叫牠們『長尾葉猴」,」卡帕西先生說。「在這一帶,牠們十分普遍。」
他一開口說話,其中一隻猴子便跳到路中央,讓卡帕西先生突然煞車。另一隻則跳到車子的引擎蓋上,然後跳走。卡帕西先生按喇叭,孩子們開始興奮起來,他們吸了口氣,以手半遮住臉。達斯先生解釋,他們不曾在動物園外看過猴子。他要卡帕西先生停下車,讓他拍一張照片。
當達斯先生調整遠長鏡頭時,達斯太太將手伸入草編袋裡,拿出一瓶無色的指甲油,然後將它塗在食指的指尖上。
小女孩伸出一隻手。「我也要搽指甲油。媽咪,也幫我搽。」
「別吵我,」達斯太太對著她的指甲吹氣,然後微微轉動身體。「妳害我搞砸了。」
小女孩專注地為洋娃娃塑膠身體上的圓裙扣上鈕釦,然後解開鈕釦。
「照好了。」達斯先生說,並蓋上長鏡頭的蓋子。
車子沿著佈滿灰塵的道路行駛時,發出相當吵鬧的嘎嘎聲,使他們不時突然地從座位上跳起來,但是達斯太太繼續塗指甲。卡帕西先生減緩車速,希望更平順地行進。當他伸手去拉排檔桿,坐在前座的男孩配合他的動作,將他光滑的膝蓋擺到一旁。卡帕西先生注意到這個男孩的膚色比其他孩子的膚色淡,「爹地,為什麼在這輛車子裡,司機也坐錯邊?」男孩問。
「笨蛋,他們這裡都是這樣。」隆尼說。
「別叫你弟弟笨蛋,」達斯先生說。他轉向卡帕西先生。「你知道,在美國……他們搞混了。」
「喔,是的,我很清楚,」卡帕西先生說。他儘可能細心地再度拉排檔桿,當他所接近爬坡路時,他加速。「我在『豪門風雲』影集裡看過,你們的方向盤在左邊。」
「什麼是『豪門風雲』?」提娜問。現在她拿她那赤裸的洋娃娃猛擊卡帕西先生後面的椅背。
「已經停止播放了,」達斯先生說,「是電視影集。」
他們全都像兄弟姊妹,當他所經過一排棘椰樹時,卡帕西先生心裡想。達斯先生和太太的言行舉止就像哥哥和姊姊,不像父母。他們彷彿只在那天照顧那些孩子;你很難相信平常他們必須為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負責。達斯先生輕敲鏡頭蓋和他的旅遊手冊,偶爾他讓拇指甲劃過書頁,製造出一種刮擦的聲音。達斯太太則繼續塗指甲,而且仍然沒有拿掉太陽眼鏡。提娜不時重新要求她幫她塗指甲,因此達斯太太輕輕將一滴指甲油滴在小女孩的手指上,然後再將那瓶指甲油放回草編袋裡。
「這輛車子不是有冷氣嗎?」她問,依舊對著她的手吹氣。提娜那邊的車窗壞掉了,無法搖下來。
「不要再抱怨,」達斯先生說,「並沒有那麼熱。」
「我叫你叫一輛有冷氣的車子,」達斯太太繼續說。「你為什麼這樣做?拉吉,只為省幾個愚蠢的盧比?你為我們省了多少錢?五毛美金?」
他們的口音正像卡帕西先生在美國電視節目上所聽見的,雖然不像「豪門風雲」裡的口音。
「卡帕西先生,每天帶遊客看相同的東西不是很令人厭倦嗎?」達斯先生問,並完全搖下他那邊的車窗。「嘿,你介意把車子停下來嗎?我只是想拍這個傢伙。」
卡帕西先生將車子停到路邊,而達斯先生則拿相機拍一個赤腳的男人,後者以一條髒兮兮的頭巾裹住頭,坐在由兩隻閹牛所拉的一輛載滿一袋袋穀物的牛車車頂。那人和牛都瘦削而憔悴。坐在後座的達斯太太注視著另一邊窗外的天空,幾乎透明的雲迅速從另一朵雲前飄浮而過。
「我真的渴望看到它,」當他們繼續上路時,卡帕西先生說。「太陽神殿是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因此,來這裡是我的一個獎賞。我只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當導遊,其他日子裡,我有另一個工作。」
「喔?在哪裡?」達斯先生問。
「我在一間醫生診所工作。」
「你是一個醫生?」
「我不是一個醫生,但是我為一個醫生工作,當他的翻譯員。」
「為什麼醫生需要翻譯員?」
「他有許多說古吉拉特語(Gujarati)的病人。我父親是一個古吉拉特人。但是在這個地區,許多人──包括醫生──不會說古吉拉特語。因此,醫生要我在他的診所工作,為他翻譯病人所說的話。」
「很有趣,我沒有聽過這類的事。」達斯先生說。
卡帕西先生聳聳肩。「這工作和其他任何一種工作一樣。」
「但是十分浪漫,」達斯太太迷迷糊糊地說,打破她久久的沉默。她舉起帶粉紅色的棕色太陽眼鏡,將它放在頭頂上,像一個冠冕狀頭飾。她的眼睛第一次在後視鏡中和卡帕西先生的眼睛交會:蒼白、稍嫌太小,凝視著卻似乎昏昏欲睡。
達斯先生伸長脖子看她,「有什麼浪漫的?」
「我不知道,某種東西。」她聳聳肩,皺了一會兒眉頭。「卡帕西先生,你要不要嚼一片口香糖?」她愉快地問,然後將手伸入她那只草編袋裡,拿給他一小塊以綠、白條包裝紙包裝的方形口香糖。卡帕西先生將它放入嘴裡,一種濃稠的甜液立即滿溢到他的舌頭上。
「再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你工作上的事,卡帕西先生。」達斯太太說。
「妳想知道什麼?夫人。」
「我不知道,」她聳聳肩,咀嚼著一些爆米花,舔一舔嘴角的芥子油。「告訴我們具代表性的情況,」她靠回座位,頭傾斜在一片陽光之中,且閉起眼睛。「我想要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好的。前幾天一個喉嚨痛的男人走進來。」
「他抽菸嗎?」
「不抽,這很奇怪。他抱怨說他覺得喉嚨裡彷彿有幾根長長的稻草。我告訴醫生,醫生便能夠開出適當的藥。」
「真棒!」
「是的。」遲疑一會兒後,卡帕西先生同意她的話。
「因此,這些病人全部倚賴你,」達斯太太說。她慢條斯理地說,彷彿說出心裡所想的話。「就某方面而言,他們倚賴你勝於倚賴醫生。」
「妳是什麼意思?這怎麼可能?」
「嗯,比如說,你可以告訴醫生,那疼痛就像一種燃燒的感覺,不像喉嚨有稻草的感覺。病人絕不會知道你對醫生說些什麼,醫生也不會知道你說錯了。這是一種重大的責任。」
「是的,卡帕西先生,你在這裡擔負著一項重大的責任。」達斯先生附和。
卡帕西先生不曾認為他的工作如此值得讚賞。對他而言,那是一種沒有人感謝的工作。他解說病人的疾病,細心而周到地翻譯許多腫脹骨頭的症狀、無數腹部和腸胃的痙攣、人們手掌改變顏色、形狀和大小的地方,而他從不認為這件事是高尚的。醫生的年紀大約只有他的一半,他喜歡穿喇叭褲,喜歡就國會黨說一些毫無幽默的笑話。他們一起在一間空氣污濁的小診療室工作。在熱氣中,卡帕西先生做工精巧的衣服黏在他身上,儘管天花板上變黑的電風扇扇葉在他們頭頂上轉動。
這個工作是他失敗的象徵。年輕時,他是一個孜孜不倦地學習外語的學生,擁有許許多多的字典。他夢想成為外交官和達官顯要的翻譯人員,解決人民和國家之間的衝突,解決唯有他能夠明白的雙方的爭端。他靠著自修學習外語。在他父母為他安排婚姻之前的每個晚上,他在一本接一本的筆記上列出常用的詞源。有一個時期他相信如果有機會,他可以以英文、法文、俄文、葡萄牙文和義大利文──更遑論印地語、孟加拉語、歐里西語和古吉拉特語──和人交談。現在,他只記得一點歐洲用語,一點代表碟子和椅子之類的零散字語。除了印度的語言外,英語是他唯一能夠流利使用的語言。卡帕西先生知道這不是一項了不起的才華。有時候,他擔心他的孩子光憑著看電視,英文就會比他好。然而,當導遊時,他的英文仍然派得上用場。
他的第一個兒子於七歲時患了傷寒,就這樣,他第一次認識醫生,也因此接下這份翻譯工作。那時候,卡帕西在一所初級中學教英文。他藉著他的翻譯技巧支付愈來愈高得離譜的醫療費用。最後,在一天晚上,男孩死在他母親的懷裡,四肢因高燒而發燙,然而,他仍然得支付葬禮的費用。此外,其他的孩子太快出生,他必須照顧一個更新、更大的家庭,必須讓孩子們上好學校,必須為他們請家庭教師,必須買好鞋子和電視,必須想出無數其他的方式來安慰他的妻子,讓她不會在睡夢中哭泣。因此,當醫生說他願意以高出他中學教師一倍的薪水雇用他時,他接受了。卡帕西先生知道他的妻子不看重他的翻譯工作。他知道這個工作會讓她想到她失去的兒子;他也知道她憎惡他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解救的其他生命。當她提到他的職位,她會說他是「醫生助手」,彷彿翻譯工作和量體溫或換便壺是同等的。她不曾向他問及來到醫生診所的病人,也不曾說他的工作是一種重大的責任。
因為這個理由,當達斯太太對卡帕西先生的工作表現出高度的興趣時,他感到受寵若驚。和他的妻子不一樣,達斯太太提醒他,他的工作是一種知性的挑戰。此外,她也使用「浪漫」這個字眼。她對他丈夫的態度絲毫不浪漫,然而她使用這個字眼來描述他。他在想,達斯先生和太太是否合不來,就像他和他的妻子一樣。也許除了三個孩子和十年的共同生活外,他們也沒有多少共同點。他在自己的婚姻裡看出的信號也出現在他們的婚姻裡 為芝麻小事爭吵、冷漠、久久的沉默。她沒有對她的丈夫或孩子表示興趣,但是她突然對他表示興趣,這一點使他產生一些陶醉感。當他再度想到她如何說出「浪漫」這兩個字時,這種陶醉感更加強烈了。
開車時,他開始審視自己映在後視鏡裡的影像。他慶幸自己早上穿那套灰色的西裝,而不是那套棕色的,因為後者的膝蓋部位有略微鬆垂的傾向。他不時朝鏡中的達斯太太瞥一眼。除了看她的臉外,也看她胸部之間的印花布草莓,以及她頸上的金棕色凹處。他決定向達斯太太描述一個又一個病人:一個年輕的婦女抱怨她的脊椎骨有雨滴下的感覺,一位男士的胎記開始長毛。達斯太太專注地聆聽,以一把像橢圓形針氈的小塑膠梳子梳頭髮,並問更多的問題。孩子們很安靜,專心地找出樹上的猴子,而達斯先生則埋首於他的旅遊手冊,因此,卡帕西先生和達斯太太似乎像是在進行私人交談。就這樣,半個小時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