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
| 作者 | 羅桂環 |
|---|---|
| 出版社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
| 商品描述 | 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歷史上的歐洲人是怎麼認識中國生物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將各種原本生長於西方的動植物引至中國,進而讓它們變成了今天世人所熟悉、但對當時中國人卻可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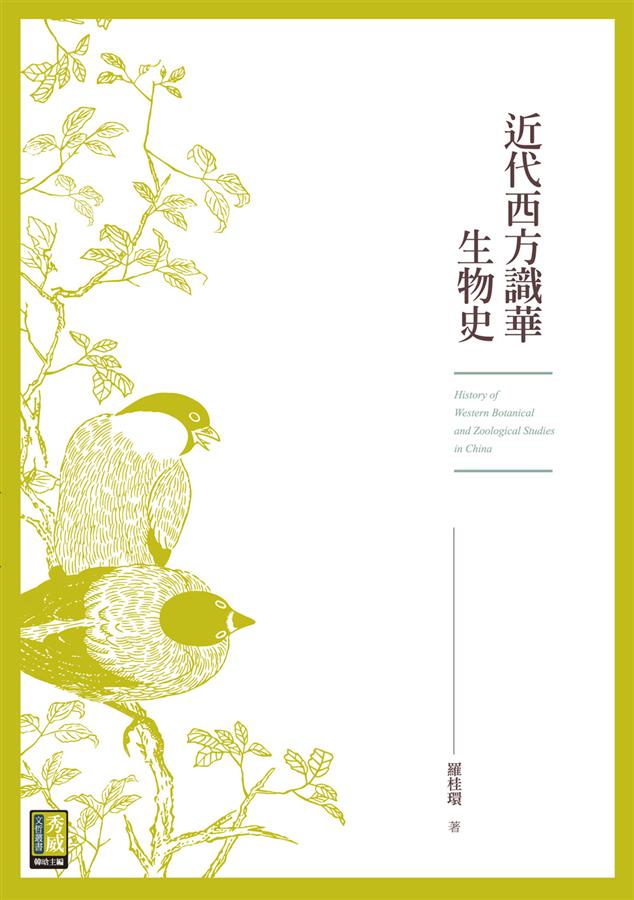
| 作者 | 羅桂環 |
|---|---|
| 出版社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
| 商品描述 | 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歷史上的歐洲人是怎麼認識中國生物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將各種原本生長於西方的動植物引至中國,進而讓它們變成了今天世人所熟悉、但對當時中國人卻可能 |
內容簡介 歷史上的歐洲人是怎麼認識中國生物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將各種原本生長於西方的動植物引至中國,進而讓它們變成了今天世人所熟悉、但對當時中國人卻可能聞所未聞的模樣? 本書根據作者長期研究的資料,介紹了從明代晚期葡萄牙人由海上進入中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段期間,西方各國對中國生物學的考察、收集和研究的情況。 本書首先闡述了西方研究對生物學發展的影響,同時也記述了這段時期西方各國將各類動植物引種中國的有關史實,展示了西方對中國作為一個生物多樣性異常豐富的中心,以及他們稱之為「園林之母」和「重要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認識歷程。本書在敘述生物學與相關歷史的同時,亦展現了中外交流史的重要面向。
作者介紹 作者/羅桂環福建省連城縣人。1982年1月畢業於蘭州大學生物系,進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工作。此後一直從事中國生物學史、環境保護史和「西北科學考查團」科學活動,以及中國栽培植物起源和發展史方面的研究。1996年開始任研究員。曾任古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所研究部常務副主任、中國科技史學會生物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以及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目前主要從事中國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傳播方面的工作。
產品目錄 序「秀威文哲叢書」/韓晗 前言/羅桂環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我國的生物資源及其特點 第二節 西方人在我國收集生物的各個階段 第三節 西方人在華的生物收集活動的總體考察 第四節 西方對華生物採集、研究的影響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在華的收集活動 第一節 葡、法等國傳教士在華的生物收集活動 第二節 西歐商人和植物園在華的生物收集和引種活動 第三節 俄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三章 鴉片戰爭後英國領事人員等的生物收集活動 第一節 英國在香港等地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二節 福瓊在華東南的茶種和園藝植物收集 第三節 英國人在長江流域的植物標本採集 第四節 英國人在華的動物學收集 第四章 英國園林學家等在中國西部等地的收集 第一節 威爾遜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引種 第二節 福雷斯特等在華的花卉引種和生物學收集 第三節 20世紀上半葉英國在華的動物收集 第五章 鴉片戰爭後俄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一節 在我國東北和北京的考察和收集 第二節 俄國軍人在我國西北的探查 第三節 俄國人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考察收集活動 第六章 鴉片戰爭後法國傳教士等在華的收集與考察 第一節 外交人員和考察隊成員在華的生物收集 第二節 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植物收集 第三節 法國傳教士在華的動物學收集活動 第七章 美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一節 19世紀美國人在華的生物收集 第二節 美國自然博物館等機構在華的動物收集 第三節 美國農業部和地理學會在華的引種和收集 第四節 旅華美國生物學者的採集活動 第八章 其他西方國家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一節 德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二節 奧地利和瑞典等國學者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九章 近代西方對中國生物的研究 第一節 植物學方面 第二節 動物學方面 第十章 西方引種我國的重要植物及其影響 第一節 西方人對「中國─園林之母」的闡釋 第二節 西方對華經濟植物的引種 第三節 從人參到西洋參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
| 書名 / | 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 |
|---|---|
| 作者 / | 羅桂環 |
| 簡介 / | 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歷史上的歐洲人是怎麼認識中國生物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將各種原本生長於西方的動植物引至中國,進而讓它們變成了今天世人所熟悉、但對當時中國人卻可能 |
| 出版社 /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
| ISBN13 / | 9789863265962 |
| ISBN10 / | 9863265969 |
| EAN / | 9789863265962 |
| 誠品26碼 / | 2681646595006 |
| 頁數 / | 392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6X23CM |
| 級別 / | N:無 |
自序 : 【前言】
記得在上學的時候,曾經在哪裡看到過一篇外國人論述我國生物的文章,當時就覺得有點奇怪,心想,他們憑什麼議論中國的動植物?他們真的瞭解中國的動植物嗎?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所裡搞科學史。在一次清理辦公室的時候,很偶然發現趙鐵橋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帝國主義侵華史的一個側面─評近代外國人在華的生物學考察1。說起來趙先生與我還是校友,他似是我們系上搞魚類分類的王香亭教授的七八級研究生,和其他同級的另外幾個研究生常和我們七七級的本科生一起做實驗。但我和他並不熟,可能都沒說過話。當時也就知道他是系上的研究生,出入相遇點個頭而已。我能知道他是我們校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後來回到原來的單位─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的緣故,因為我的一個要好的同學也分到那裡。他告訴我一些關於趙先生的情況,後來我才把這個名字和具體的人聯繫起來。他的文章比較全面地提到了近代在華考察生物的主要外國人物,評述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獨具慧眼,非常生動,語言酣暢淋漓,很有文采。由於那時文化大革命才剛剛結束,所以他的文章多少有點批判文章的意味,而且似乎未列參考文獻,可能出於這個原因,當時我所編發的刊物沒有發表。但它無疑使我明白西方人對中國的很多生物是有瞭解的。
在工作期間,有段時間我突然對栽培植物的起源傳播有興趣,結果翻閱了貝勒的《西方在華植物發現史》,這本書在記述1900年前西方人考察、收集中國植物方面史料之翔實,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就這樣對西方人在華的生物考察史逐漸有了興趣。後來又受到我所的杜石然先生和北京林業大學的汪振儒先生的鼓勵,便逐漸地開始探討這方面的工作。
大家知道,作為一個文明非常古老的國度,我們的祖先在探索周圍自然的時候,積累了大量的辨識生物類別及利用生物資源的知識。在古代社會中,這種知識積累的速度在世界範圍內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進入16世紀後,西方的科學技術開始迅速發展。出於資源搜求和殖民擴張及學術發展等各種目的,西方各國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長期和大規模的考察、探險,和生物標本收集,促進了當時博物學的迅速發展。相形之下,我國遠遠地落後了。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我國被迫對西方開放,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他們積累的有關我國生物資源的知識已經遠遠超出國人自身所具有的水平。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已經編出《中國植物志綱要》、《中國和蒙古的獸類》、《中國鳥類嘗試目錄》、《中國的爬行類》、《中國的淡水魚類》等一系列頗有影響的專門著作。
如果不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民族,對於誰在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上繪製過地圖,拿走過什麼東西,為什麼是這樣,是應該有所瞭解的。古人曾說過「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近代歷史中,我們有很多的經驗教訓需要吸取。具體到西方人在華的生物學考察和研究這個方面,因為他們的這種活動,無論在農林經濟、園林藝術、自然保護等方面,還是在近代生物學發展方面,都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考察和探索是有意義和必要的。毫無疑問,它也構成近代中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
對於這方面的工作,外國學者向來比較注意,我國學者則較少顧及。這裡面可能有多種原因。一方面,對西方人而言,它是一種值得誇耀的業績,對於業績津津樂道是人之常情;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這是一種落後的見證,提起來總有一種沉重的感覺,不提也罷。當然,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這是因為,從事生物學研究的學者,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不太可能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只能在回顧某一專門學科史時,作一些概略的介紹。除上面提到的趙鐵橋的文章外,還有已故著名微生物學家戴芳瀾的〈外國人在華採集真菌考〉、動物學家張孟聞的〈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述論〉、植物學家方文培的〈近代中國植物學發展史略〉等等。這樣的文章一般敘述過略,或涉及面較窄。而傳統的史學工作者則可能覺得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太專門,尤其是沒有生物學基礎的學者做這項工作太費勁。因此,筆者作為一名科學史工作者,雖然自知這項研究遠非易事,但仍覺得有責任去探討。
西方對我國生物的考察、收集和研究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本上可以說告一段落。經過約50多年這樣一段時間的「積澱」,其後果也逐漸地明晰起來。現在作的審視、結論無疑比以往更為容易和更有把握。從「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角度而言,意義也該深遠一些。儘管本人深知學識有限,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姑且抱著一種拋磚引玉的意識,不揣淺陋地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希望它能對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生物學,更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提供一點借鑒和思考。
鑒於本書的內容提到許多生物名稱,如果都加上拉丁學名,篇幅未免太大。因此作者儘量選在經濟上、學術上和園林價值高的物種加上學名,並在書後加上必要的人名和地名以及生物名稱的索引。以便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書中的內容。同時也列出主要的參考文獻。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筆者有幸得到諸多先生的幫助。筆者非常感謝北京林業大學的汪振儒教授、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的吳征鎰院士這兩位植物學界前輩熱情告知有關資料;同時也非常感謝美國康奈爾大學鷹岩(Kraig Adler)教授將資料豐富的《中國兩棲爬行動物學》一書相贈。另外還要感謝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所的李雲峰先生,昆明植物所彭華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王揚宗先生,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易華先生等熱情將有關資料相示。筆者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所國魯來先生幫助翻譯德文資料,以及浙江師範大學的趙鐵橋先生熱心地指正了拙作五、六、十章中存在的一些錯誤和不當之處。筆者也謹在此對歷屆所領導,以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已故李明先生多年來對本人的工作所給予的支持、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筆者深知自己水平有限,疏漏甚至謬誤之處在所難免,祈請讀者多多指正。
羅桂環
2001年12月6日
內文 :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在華的收集活動】(節錄)
一、早期傳教士在華的資料收集活動
在世界發展史上,13世紀前後蒙古人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無疑是一件影響極為深遠的大事。它的存在導致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交往迅速增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期間,來到東方為元朝宮廷服務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根據自己見聞撰寫的《遊記》,在14世紀和15世紀時的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的這本《遊記》給西方人傳播了大量關於東亞財富和文明的知識,極大地豐富了西方人對當時世界的想像力和引起他們對東方的嚮往。另一方面,中國的航海羅盤傳入歐洲使西方人遠離海岸穿越大西洋成為可能;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的西傳和流行,使古希臘及阿拉伯的科學知識得到迅速的傳播。而古希臘和阿拉伯科學知識的普及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歐洲的文藝復興,使那裡的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革,資產階級作為一股新興的強大的社會勢力登上當地的歷史舞臺,生產關係的變革使生產力開始迅速提高。
當時西方流行的托勒密時代的地理思想―雖然是錯誤的,但卻鼓勵了西方人到海上的探險;與此同時,在15世紀下半葉的時候,瀕臨大西洋的南歐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造船技術日益發達,逐漸成為頗具航海實力的海上強國,也使這種探險成為可能。當然,這一時期還有推動上述兩個國家進行海上冒險的重要動力,那就是東方的商品,尤其是香料和絲綢。因為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絲綢在歐洲早已享有盛譽;印度的產品在市場上也很受歡迎;但後來受蒙古人衝擊而聚集在黑海東南一帶、與西歐人有著不同宗教信仰的奧斯曼土耳其人佔據了歐洲的東方,並最終於1453年佔領了中西方貨物重要的交易港口和中心君士坦丁堡後,切斷了上述貨物的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從海上找一條新的路線前往生產絲綢及調味香料的中國和印度,無疑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出海遠行冒險的主要原因之一。
香料對西歐各國人們的日常生活意義非同尋常。據說中世紀的歐洲,每當晚秋來臨、青草枯萎以前,人們總要大批屠宰牲畜,用鹽把肉醃在大桶裡。此時需要大量的香料,以保持肉類的鮮美味道而不至於腐爛變質。不僅如此,香料對於歐洲的肉食烹調也幾乎是必不可少的。當時香料是如此為人所重,以至西歐市場上的香料價格相當於黃金的價格。平時他們通過與中東貿易得來的香料不僅價格很貴,而且經常由於與他們敵對的穆斯林發生各種戰爭切斷供應,土耳其人在其東方崛起後更是如此。顯然,能找到新路線去香料產地的國家就意味著不盡的財源。為了迅速擴充財富和勢力範圍,葡萄牙人進行了影響深遠的海上擴張冒險事業。這些導致了對美洲的發現和對歐洲通往亞洲航線的發現,推動了歐洲人地理大發現活動的進行,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哥倫布前往亞洲的過程中意外地發現美洲大陸後不久,千方百計尋找胡椒和肉桂產地的葡萄牙人首先實現了發財的夢想。1497年,瓦斯特•達•伽馬(Vasco Da Gama)奉葡萄牙國王的命令從裡斯本出發,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經莫桑比克於1498年到達印度西海岸的科澤科特,從那裡運回大量的胡椒。成功地進行了一次香料倒賣。在打通了去往印度的海路之後,初嘗甜頭的葡萄牙人沒有因此滿足。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聽說馬六甲的商業非常繁榮,那邊有真正的香料群島―馬魯古群島,不但出產胡椒,還出產印度沒有的調味香料丁香和豆蔻等;更具誘惑力的是香料價格遠比印度便宜。於是他們繼續向東挺進,很快於1511年佔領了馬六甲海峽,進一步打開通向太平洋的門戶,遠航到夢寐以求的馬魯古群島,把那裡的廉價香料運回歐洲,逐步控制了歐洲的香料市場,取得了巨大的商業利潤。
毫無疑問,香料是早期推動西方人進行海上冒險的一個主要原因。但隨著歐洲社會變革的深入,科學技術逐漸進步,生產隨之發展,經濟力量不斷壯大,西方人出行的目的也發生不少變化。不久,不僅葡萄牙、西班牙,而且荷蘭和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也迅速開始進行海上擴張。香料的獲取雖然仍很重要,但在海外尋求各種珍寶、黃金礦藏和皮貨資源以及搜捕奴隸和獲得新的殖民地,開拓海外市場逐漸成了他們外出冒險的主要目的。而這些都是導致西方進行持續地理大探險的根本原因。西方人在海外進行擴張的同時,伴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逐漸開始注意所到之處的自然狀況,其中包括動植物的種類和分布。他們在我國的活動也是如此。
葡萄牙人在由馬六甲海峽向東擴張的過程中,於1516年來到我國的廣東沿海,並逐漸駐足澳門,和我國進行貿易。他們從我國輸入大宗的絲綢、生絲及藥物大黃和樟腦等貨物。當時西方生物學還比較落後,急功近利的商人注重的是直接經濟效益,還不可能想到從我國搜集各種生物有何價值。因此,在西方學者眼中,早期來華的葡萄牙人在收集中國的生物方面幾乎沒有值得稱道的成就。一般認為他們值得一提的生物收集是:1545年,葡萄駐印度果阿的總督把我國的甜橙(Citrus sinensis)引回到裡斯本栽培。他們運到歐洲的一些我國植物產品,如肉桂和大黃,早在羅馬帝國時代即通過間接的途徑輸入歐洲。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與中國的長期交往中,他們從未購置過中國人普遍運用的飲料―茶葉。儘管1559年,威尼斯的一位作家已在其《中國茶》(Chai Catai)及《航海與旅行記》(Nevigatione et Viaggi)二書中提到中國的茶葉。不過據說他是從一個波斯商人那裡得到資料的。教會西方人喝茶的是後來的荷蘭人。他們的船曾於1607年在澳門運載一些茶葉到爪哇,這被認為是歐洲人從我國購運茶葉的最早記錄。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早期來華的葡萄牙人沒有從中國進行過生物收集,但是他們購買回去的陶瓷器皿、絲織工藝品上通常繪有各種花鳥蟲魚,給西方人提供了不少有關中國生物的初步知識。
緊隨葡萄牙商人之後,西方天主教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把更多的地方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而迅速行動。一批批狂熱的西方傳教士很快來到我國。他們以弄清楚中國的社會形態和自然狀況,進而改變中國人的信仰為己任,為當時西方的殖民政策服務。不少傳教士極富冒險精神,又沒有政治和商業身分,所以比較容易尋找到各種途徑進入我國內地。開始時,他們的說教在這個文化底蘊十分深厚的文明古國中並沒有多大的成效,但這並未使他們氣餒。傳教士們迅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不斷地利用新的手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應當承認,早期來華的傳教士中,確實有不少頭腦靈活而且文化素質較高。因此,他們很快找出了有效的一招,那就是除傳教佈道外,通過作一些科學和醫學知識的傳播工作,以此喚起當地人對他們的注意和相信,進而不再厭惡它們的說教甚至接受他們的宗教觀念。稍後,有些傳教士竟然也能憑藉自己掌握的先進科學技術知識滲入到朝廷。
這些人在所到之處盡可能地瞭解當地的文化和自然狀況,不失時機地收集我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社會制度、風土人情、自然地理、物產資源等包羅萬象的情報資料。向上級教會組織和所派出的國家報告。這一方面是為了使西方教會儘快瞭解中國的情況,更好地開展在華的傳教工作,另一方面則是服務於西方的商業和政治目的,以期得到教會和社會各界廣泛的支持。所以,傳教士從我國發出的大量信件和報告,在客觀上成為當時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傳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在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面說過,我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是一個長期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立國的國度,所擁有的農業及醫藥生物資源之多格外引人注目。因此早期的那些傳教士中,有不少人在留心我國人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同時,很自然也把注意力放在收集我國的生物資源尤其是經濟動植物的資料方面。這些資料被送回西方後,經有關志書的傳播,很快激起當時忙於尋找資源和市場的英、法等諸多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生物資源的強烈興趣。早期(16~18世紀之間)來華的傳教士以葡萄牙、意大利、法國的居多,在收集有關情報資料中,也以這三國的傳教士為主。
1556年,據說有個叫達•克洛茲(Gasper da Cruz)的葡萄牙傳教士來華傳教,1560年返回本國,隨即在葡萄牙出版過有關茶葉的作品。隨後於1575年,一個名叫赫拉達(M. de Herrada)的天主教傳教士,從菲律賓馬尼拉隨大明帝國訪問呂宋的官員乘船到了福建漳州、泉州和福州,在那地方遊歷了三個月。他收集的有關植物資料,後來被其教友門多查寫入《大中華帝國志》一書。順便指出,門多查的著作是根據一些試圖深入中國的奧古斯丁和方濟會修道士的報告整理而成的。書中記有板栗、甜瓜和荔枝,據說這是西方人的筆下首次提到荔枝。此外書中還提到泉州人已經種植玉米等情況。
早期在華傳教的一代宗師利瑪竇(Matthieu Ricci)在華居留時,曾用意大利文記下有關中國和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情況,這就是《耶穌會把天主教引進中國劄記》(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et Christianita nella Cina)之手稿。1615年,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N. Trigault)把它翻譯成拉丁文,並將書名定為《由耶穌會進行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 Jesu)一書。此書不是很嚴格的翻譯,有些是金尼閣增添的資料。它隨即曾被譯成多種西方文字。書中記載了中國的不少物產。其中包括一些歐洲所沒有的水果,如我國華南一些省份產的龍眼、荔枝,一些種類的柑橘,以及柿子等。書中還提到中國出產各種食用香辛調料,其中以肉桂和生薑產量居多;此外還有胡椒、丁香、豆蔻等。還說中國出產一些其他地方沒有的藥材,包括麝香、大黃和土茯苓,而且價格極為便宜。書中敘說中國的建築都用木材,樹木種類很多,有的樹木很硬。當然書中也提到特有的飲料―茶。說茶是一種小樹葉,用來泡水喝的味道很好,不但能提神,而且助消化。另外,書中還記載中國有蠟樹(烏桕)和能產「油漆」的漆樹,漆樹產的漆用途廣泛,並認為這類樹應該很容易移植到西方。書中還提到我國特有的經濟昆蟲―能產蠟的白蠟蟲。說白蠟蟲產的蠟很乾淨,不會有細木枝、樹皮等雜質。這是西方著作首次提到這種經濟昆蟲。此外,書中還記載中國森林中多有老虎、熊、狼和狐狸等野獸;北京有不少人工豢養的大象等等。
1621年,普魯士(德國)傳教士鄧玉函(J. Terrenz)來華,此人據說是一個博物學家和收藏家,曾將西方的有關解剖學著作譯成漢文。有文獻記載,他曾「每嘗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將遍償而露取之,以驗成書,未成也。」似在我國考察、收集過生物,但是否收集過標本資料送回西方,不太清楚。後於他一年來華的著名普魯士傳教士湯若望(J. A. Schall von Bell),曾寫過一本題稱《韃靼地區的植物和荊棘》的作品。1643年,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 de Semedo)根據在華傳教士收集的資料,寫了《中國通史》一書,書中提到許多中國產的各種經濟植物,包括遼東的人參,華中的漆樹,臺灣的胡椒和肉桂,以及海南的花梨木。還有觀賞植物臘梅以及各種水果等。另外,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M. Martini)在他1655年出版的《中國新圖志》一書中,同樣記載了許多中國很有用的植物。包括經濟植物中的茶、桑、櫟、蠟樹、竹子、漆樹、花梨木、棉、麻、甘蔗等;觀賞植物蓮花、牡丹、木芙蓉、茉莉、桂花;以及藥用植物人參、大黃和土茯苓。
另一方面,當時不少傳教士在寄回歐洲的信件中也大量提到有關我國的經濟動、植物資料。尤其是帶有我國特色的茶、苧麻、蟲蠟樹和花可用來製作黃色染料的槐樹等經濟植物,以及水果如佛手柑、柿子。隨著來華傳教士的增多,他們活動的地域也不斷擴大。據17世紀下半葉楊光先的《不得已》記載,當時傳教士所及已達13個省的許多地區。因此,從各地寄回歐洲的有關信件報告也不斷增多。
隨著對我國植物資料掌握的增多,某些傳教士還開始撰寫中國植物著作的嘗試。這項工作首先由波蘭傳教士卜彌格(M. Boym)開始進行。卜彌格1644年來華,在澳門學過幾個月的漢語。隨後在海南島傳教。1656年,他編了一本題稱《中國植物志》的小冊子。但這個傳教士無論中文水平或是植物學知識都很差,從事這項工作顯然力不從心,書中所記的全部22種植物中,大部分是東南亞群島上的植物,如榴槤、腰果(原產南美,一名檟如果)、菠蘿、菠蘿蜜、芒果等。書中記載比較地道的中國植物大概是柿子(圖2-1)、枇杷和荔枝。書中還包括一些動物資料,如豹子、鳳凰和野雞、綠毛龜、松鼠、蛇等。另外,這個傳教士還注意過一些別的中國植物。在他留存的一部題稱《中國事物概述》的手稿中,他記有中國的漆樹、人參和茶等經濟植物。這位頗具冒險精神的傳教士還寫有《中國地圖冊》和《中藥標本》等作品。在前一作品中,繪有雉、玉蘭、荷花。
到了17世紀末,傳教士在華的生物收集活動日趨活躍。這裡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從17世紀最後25年起,來華的傳教士主要是法國人。與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傳教士相比,法國傳教士的科技、文化素質明顯要高。他們當時在中國確實幹了一些令外國學者信服,讓中國統治者滿意的工作,如用天文學的方法測定許多地點,繪製中國地圖等。所以他們中有些人深得清統治者的器重。同時,這些法國傳教士也非常善於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對有關我國的情況進行廣泛的調查和記述,為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學術進步做出貢獻,以此喚起西方各國政府和教會對他們工作的興趣和支持。總體而言,他們在收集我國情報資料方面堪稱十分出色。不僅收集到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而且也有一些實地調查報告和實物收集。在整個西方人在華的生物收集史中,法國傳教士之活躍和取得的成就之高,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1843年拉萼尼作為法國特使來華簽署《黃埔條約》,條約中設有為傳教士在華傳教謀得各種便利的專門條文,實有其歷史原因。
1687年,法國傳教士李明(L. Le Comte)來華。他是最早來華組織法國耶穌會的五位教士之一。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關於中國目前狀況的新觀察報告》一書。書中李明記述了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將我國甜橙引回種植的情況,對他在福建所見的茶樹及其栽培情形也作了記載。他指出,中國大部分地方管這種植物叫做茶(Cha)只有福建的方言中念作Te。他還對飲茶與健康的關係進行瞭解。此外,還記載了北京近郊及陜西、山西、四川種植煙草的情況,他可能是注意到我國種植煙草的第一個西方人。他的書中還提到我國特產的作物大豆、古老的調味植物花椒、以及水果蘋婆和人參等經濟植物。另外,他還撰有《論中國的植物》。與李明同年來華的另一耶穌會傳教士張誠(J. F. Gerbillon),到過北京南苑窺視過麋鹿,由於觀察得不真切,加上可能在冬天,麋鹿已經脫角,有點像騾子或驢,因此他記作野騾子。他的記述為日後譚衛道(A. David, 1826-1900)到那裡尋求此種珍稀動物提供了線索。
進入18世紀後,法國的幾個傳教士在收集中國有重要經濟價值的生物資料方面,非常令人矚目。先是1708年,杜德美(P. Jartoux)利用受命繪製地圖去東北進行地理測量的機會,調查了我國名貴藥材人參的產地。他於1711年4月12日寫給印度和中國傳教區總巡閱使的一封信中,對人參的產地、形狀、生長狀況和採集的方法都作了細緻的介紹。另外對人參的藥效和用途也進行了記述;並認為當時已經法國傳教士和皮貨商作過相當調查的加拿大地區也應產人參。他還繪了一幅人參圖(圖2-2)。並將這幅圖和它的說明寄給了收信人。
曾因協助雷孝思等人因繪製中國省圖受康熙嘉許的馮秉正(J. F. M. A. M. De Mailla)也曾留意於我國的生物資源。他在1715年寫給一個神父的信中曾述及臺灣的生物。他在信中說:「田野長著許多小麥和水稻,印度的多數水果也能在這裡見到,如橙子、菠蘿、番石榴、番木瓜、可可等……我們在這裡見到了桃子、杏子、無花果、葡萄、栗子、石榴等。中國人種植一種他們叫作西瓜的瓜,它比我們的瓜大很多」。信中還說:「除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鹿和猴子外,其他猛獸比較罕見……島上也有熊、野豬、虎和豹」
接著是1723年,另一法國傳教士,也是巴黎法蘭西科學院駐華的通訊院士巴多明(D. Parennin),送回一批中藥到巴黎法蘭西科學院,其中有兩種非常名貴的中藥材,分別是冬蟲夏草(圖2-3)和三七。他在寫給法蘭西科學院的學者的第二封信中是這樣介紹冬蟲夏草的:「它具有大致與人參相似的功效,不同的是經常服用不會像人參那樣引起出血。它能增加和恢復因勞累過度或久病而失去的體力。我本人對此有親身體驗。」他在信中指出:「三七比冬蟲夏草易得,這是野生於雲、貴、川諸省山區的一種植物。」用少量的這種植物根末,「便可止住咳血和出血,如對它做一些(化學)分析,或許能發現它還具有我不知道的許多其他功效。」此外,他還在信中介紹了大黃、當歸、阿膠和阿片(鴉片)等中藥的產地和用途。巴多明還曾陪皇帝(康熙)到承德的木蘭圍場打過獵,簡單記述過那裡的植物情況。當時,另一法國傳教士殷弘緒(F. X. d'Entrecolles)則在寄回法國的信中說及柿子、佛手和樟樹等特產我國的果木。
除法國傳教士之外,當時其他一些國家的傳教士也非常積極地給本國彙報有關我國的生物資料。1714年,意大利傳教士利國安(P. Jean Laureati)在給本國一個貴族寫的一封信中,提到中國的各種糧食作物。還說中國出產種類繁多的水果,有橙子、檸檬、荔枝、梨、李子、蘋果、木瓜、芒果、香蕉、石榴、葡萄、核桃。還提到我國的不少蔬菜如白菜、萵苣、菠菜、南瓜、黃瓜等。信中還提到我國特有的觀賞動物―金魚;以及一些野生動物,包括猴子、鹿、山羊、熊、鷹、野雞、蝮蛇、蝴蝶、海參等。同時介紹了它們的經濟價值。
1735年,法國牧師杜赫德(Du Halde)根據在華傳教士寄回的書信資料等,編了《中國概述》,其中有數章內容講述農業、醫藥和生物,這部分內容不少譯自《本草綱目》。此書有好幾種西方文字的版本,對西方瞭解中國的生物資源起過重要的啟蒙作用。
最佳賣點 : 歷史上的歐洲人是怎麼認識中國生物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將各種原本生長於西方的動植物引至中國,進而讓它們變成了今天世人所熟悉、但對當時中國人卻可能聞所未聞的模樣?透過本書,長年從事中國生物學史的羅桂環教授向讀者展現了中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