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ight Shift: Real Life in the Heart of the E. R.
| 作者 | Brian Goldman |
|---|---|
| 出版社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夜班急診室: 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也不要來得太早。」在醫療上,時機就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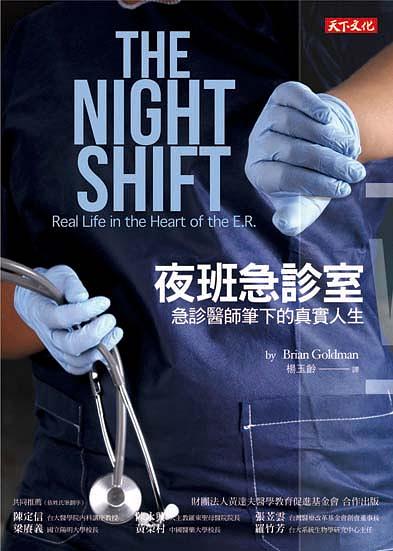
| 作者 | Brian Goldman |
|---|---|
| 出版社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夜班急診室: 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也不要來得太早。」在醫療上,時機就是 |
內容簡介 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也不要來得太早。」在醫療上,時機就是一切。如果你來得太遲,我沒有辦法救你;如果你來得太早,我恐怕會看不出你哪裡有問題,因為症狀太過輕微。有好幾種戲劇性的手段,可以在急診室引起關注。一種是停止呼吸,另一種是昏厥並倒地。脫衣服或是在候診室尿尿,也會產生不錯的效果。來場癲癇發作也行。說得殘酷一點,急診醫師的工作是「輸送肉品」。所謂肉品,就是指你們啦。每一年將幾萬名病人從急診室送出去,需要決斷、效率和狡滑,外加一點兒運氣。我(作者高曼醫師)發現,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大重要目標,不只在於幫助需要醫療照護的人,我還想要治療醫療體系本身,去揭露它的真面貌,揭露它所有的長處、短處和藉口。急診室既是生死一線之隔的地方,也是醫療糾紛的是非之地,每個夜晚都在上演悲歡離合的人生戲劇,有時以喜劇收場,有時以悲劇收尾。高德曼醫師以誠懇而帶有淡淡幽默的筆調,用一篇篇真實的故事,告訴我們:所有你想像不到的肥皂劇情,都有可能在急診室裡活生生上演。我寫這本書,是為了你們。你們當中大部分人,遲早會需要像我這樣的急診醫師的服務。你們當中很多人可能會想知道,在急診室那道玻璃門背後的真相,以及你們是否可以信任那裡的醫護人員……我希望能夠帶領你們進入急診室,展示急診室真正的運作方式,讓你們像我一樣了解急診室。我希望經由這樣做,能揭開這份職業的神祕性,讓你們更容易理解、以及面對「掛急診」這回事。—— 布萊恩‧高德曼(本書作者)
各界推薦 「感人肺腑……帶您一窺急診室大門背後, 那個有時充滿戲劇性、有時平淡到乏味的,生與死僅一線之隔的世界。」 --加拿大《國家郵報》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布萊恩‧高德曼(Brian Goldman)在舉世少見的醫、媒兩棲職業生涯中,高德曼醫師賦予自己的任務是:解開醫學世界的神祕。《夜班急診室: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透過一則則精采故事,告訴大家:急診室可不像電視劇塑造的那樣。《夜班急診室》揭露了急診室裡,外人難以窺知的內部運作模式,並指出一名好的急診醫師,需要具備怎樣的觀察力、決斷力和處置力;並且坦誠檢視今天醫學界面臨的諸多問題,包括:論件計酬制、醫師為什麼會犯錯、病人與醫師之間關係的分際,醫師與藥廠之間的互惠文化……提供他獨到的洞見。高德曼醫師在TED Talk主講的「我們能談談醫師會犯錯嗎?」(Doctors Make Mistakes. Can We Talk About That?)已吸引了超過一百萬人次瀏覽。他的最新著作是《醫師的密語》(The Secret Language of Doctors)。■譯者簡介楊玉齡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譯作《生物圈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推薦獎、《雁鵝與勞倫茲》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兒腦開竅手冊》、《奇蹟》、《念力:讓腦波直接操控機器的新科技‧新世界》、《幻覺》等數十冊(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
產品目錄 出版合作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前言 急診室的真實人生第一章 生命的氣息 第二章 子宮的悲喜劇 第三章 漫漫長夜,等待,再等待 第四章 恐懼與嫌惡 第五章 「夜襲者」與「常客」 第六章 看緊你的住院醫師 第七章 夜深,人累 第八章 忘不了,那些逝去的名字 第九章 迷途的愛情 第十章 傾聽無言的呼救 第十一章 每隔幾年,就有壞事發生第十二章 下班 感謝
| 書名 / | 夜班急診室: 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 |
|---|---|
| 作者 / | Brian Goldman |
| 簡介 / | 夜班急診室: 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也不要來得太早。」在醫療上,時機就是 |
| 出版社 /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3207344 |
| ISBN10 / | 9863207349 |
| EAN / | 9789863207344 |
| 誠品26碼 / | 2681058628002 |
| 頁數 / | 325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第一章 生命的氣息
⊙ 星期五夜晚,九點十五分
住在多倫多北區的我,連走帶跑的趕往我家附近的地鐵站,一步兩個臺階往下衝,生怕不能準時趕到醫院。我最恨上大夜班遲到了。我受不了看見同事對我擺臭臉,因為他操勞到晚上還不得離開,必須等遲到的我來接班。說我神經質也可以,從小我就不是會曠課的學生(雖然我經常幻想這麼做),我總是擔心不能準時。不過,我的個性很一致,如果有同事接我的班遲到,我也一樣不高興。
讓我壓力更大的,是每次接班前都會油然而生的焦慮感。雖說我看急診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每次上班前,我還是會緊張。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即使我有這麼多的經驗,還是有些東西我不知道,有些技術我比不上同事。很少有醫師願意承認這個,但是,我可不怕說實話。
等到我的地鐵列車進站,我就開始放鬆下來。往南開到西奈山醫院不需要太久,至少我這麼想。然而,就在快抵達我要下車的車站時,列車忽然尖叫一聲,停了下來。擴音器廣播說,另外某個地方發生緊急事件,所以造成了「輕微的延誤」。我的血壓頓時升高,我咒罵這樣的等待。我最恨自己不能掌控了。謝天謝地,在漫長的十分鐘之後,列車開始慢吞吞的前進,開向我的目的地。
我快步爬上地鐵站的樓梯,進入深沉的夜色之中。我想直接衝進醫院的急診室,但還是先在Tim Hortons停下來,買一大盒一口甜甜圈,外加一大杯咖啡。喝咖啡可以讓我保持清醒;甜甜圈則是給護理師們享用,這樣她們更容易記得,在我的病人情況惡化、尤其是心臟快要停止的時候,趕緊讓我知道。
我匆匆經過莫雷街上的西奈山醫院入口,然後下了臺階,沿著走廊進入急診醫師的辦公室。我換上綠袍,抓起我的聽診器,扔了幾顆普衛醒錠到口裡(很多值夜班的醫務人員都服用普衛醒錠,以幫助頭腦保持清醒),和著咖啡吞下肚。你如果是一名五十幾歲的急診醫師,你真的需要利用各種方式保持頭腦清醒和敏銳。
我無聲的向我的病人祈禱,那是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也不要來得太早。」在醫療上,時機就是一切。如果你來得太遲,我沒有辦法救你;如果你來得太早,我恐怕會看不出你哪裡有問題,因為症狀太過輕微。
接著,在我開始值班之前,我喃喃自語的說出一句不敢大聲說出口的禱告:「拜託,不要讓我搞砸了。」
在通往急診室的走廊上,我踏進候診室,看看今天有多忙。這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三十張椅子塞在三點五公尺乘三點七公尺大的空間。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屬朋友,占據了大約四分之三的椅子。一部電視機安裝在候診室靠近外門口的角落,面對著護理師。這種座位安排意味著,半數的病人及訪客除非歪著脖子,否則是看不到電視的。
我站在分隔候診室與急診室的雙扇推門外。在我右手邊,一名護理師正在檢傷站幫病人量血壓。一排病人等著要掛號。在我正前方,兩臺救護車的擔架床分別由兩組醫護人員包夾著,上頭各躺一位病人。後頭還有四位病人躺在擔架床上,形成一條隊伍,蜿蜒到相連的走廊上。嗯,今晚將會很繁忙。
⊙ 夜間十點整
「高德曼醫師,請到急救室,立刻!」病房祕書的嗓音嘹亮的從擴音器裡放送出來。
一名七十二歲的老婦人,我姑且稱她為蘇菲亞,癲癇正在發作。她的手臂和腿很有節奏的抽動著,一道白色的口沫出現在她嘴邊。她的眼睛是張開的,但是眼神呆滯,直視前方。一名護理師在旁邊呼喚她,她沒有回應。
「她有肺癌,正在做化療,」一位送她來的救護員這樣告訴我。
「她有癲癇病史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他邊回答,邊和另一位救護員一起將她從救護車的擔架床,轉移到我們醫院的輪床上。
「她發作多久了?」
「差不多兩分鐘,」他說。
癲癇發作是由腦內過量的活動或是同步的活動引發的短暫狀態。有癲癇,通常代表你天生具有這方面的傾向。其他原因還包括:出生時因缺氧導致腦部損傷,曾經罹患腦膜炎或是中風。另一個常見的病因則是腫瘤。蘇菲亞的肺癌令我擔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腦裡,那會是很不祥的致命發展。但是推論病因可以等一下,現階段我得先止住她的癲癇發作。發作時間拖得愈長,腦部缺氧而受損的風險就愈大。
「給她十毫克的二氮平(diazepam),」我下達指令。
一名護理師將這種鎮定劑(目前能採用的、可快速止住癲癇發作的藥物之一)抽到一管針筒裡,然後幫她注射。不出一分鐘,發作就停了,我的病人開始甦醒過來。就在發作剛剛停止的當兒,蘇菲亞的兒子走了進來。
「我是高德曼醫師,我負責照顧你母親。請問她有癲癇病史嗎?」
「沒有,」他說:「只有癌症。」
我解釋癌症可能已經擴散到他母親的腦裡,我們暫時用二氮平把發作止住了。我指示護理師,用靜脈點滴幫她注射第二種藥物,叫苯妥英(phenytoin),以防止癲癇復發。我告訴蘇菲亞的兒子,我們會把他母親安置在急救室裡,注意她的情況。
「讓我們先做一次頭部電腦斷層掃描,」我對護理師說,心裡默默盼望她腦中沒有任何癌細胞的影子。
這可不是我先前對今晚值班所期待的——良好的、輕鬆的開始。
身為急診醫師,我的首要職責是應對病人。如果你有一個傷口,一處扭傷,或是斷了一根骨頭,我的工作就是把你修補起來,然後打發你回去。如果你得了危及性命的重病,我的工作就是先保住你的性命,直到我或其他醫師想出你的問題是什麼。如果你想自殺,那麼我的工作就是阻止你得逞。
我的第二個職責是應對這個急診體系。說得殘酷一點,我的工作是「輸送肉品」。所謂肉品,就是指你們啦。每一年將大約四萬七千位病人從急診室送出去,需要決斷、效率和狡滑,外加一點兒運氣。西奈山醫院總共有四百七十二個床位,大部分時間,超過百分之九十都有人占用。要找一張空病床,一直都很困難。樓上每有一位病人不能出院,樓下急診室裡就會有一位病人沒法往樓上送,而候診室裡也會有一位病人沒法進到急診室來。
我一次只能看一位病人,但是誰也無法攔阻數不清的病人源源不斷上門來,或攔阻救護員半小時內送來半打躺在擔架床上的病人。對於這種嚴酷情況,我們稱之為受到「撞擊」或是「洪水氾濫」。有一次,一名檢傷護理師看到一整排病人從掛號處排到急診室入口,不禁嘆息道:「巴士剛剛進站。」那是我最喜歡的表達方式之一。
我們一邊和時鐘賽跑,一邊努力執行安全又有效率的急診醫療。二○○一年,美國急診醫學會發布一篇立場聲明,指出醫師每小時看診人數不應該超過二點五人。然而,有一篇由芝加哥急診醫師冉恩(Leslie Zun)撰寫的報告發現:各式各樣的行動準則要求急診醫師,每小時看診一點八人到五人之間。
平常我在剛開始值夜班的時候,效率最高,每小時可以看三到五位病人。而每天晚上協助我的,還有十到十二位護理師(包括檢傷分類護理師)、至少一位住院醫師,以及可能再多一位醫學生。照護像蘇菲亞這類緊急病人,很刺激,我很喜歡。但是當病情像她一樣嚴重的病人來到急救室,我得丟下一切事務,去照護她,於是生產線就得暫時停擺。而且就算我拚命趕工,也沒有辦法在初次看診時,就完成與病人的互動。因為通常需要好幾個鐘頭後,才能拿到病人的X光或電腦斷層掃描結果,而我也才能叫病人回家或是安排他們住院。隨著夜色漸深,我總是必須不斷再評估既有的病人,但同時還必須看新病人。到了清晨四、五點,我每小時只能再診療大約兩位新病人了。
另一個拖慢急診醫師的因素是,我們必須面對頻繁的干擾。急診室裡的每一個人,不論是護理師、病人、家屬或住院醫師,好像都認為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和我們閒聊兩句。我就遇過當我在為病人進行骨盆檢查時,住院醫師就那樣走進來,和我大談他們的病人。
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的急診醫師屈森(Carey Chisholm,也是美以美醫院急診創傷中心的醫師),曾經研究急診室值班期間最常見的干擾。他發現:平均而言,急診醫師一個晚上會遭到干擾五十二次。其中二十一次干擾非常嚴重,迫使急診醫師停下手邊所有的工作,開始做別的事。
在航空界大家都曉得,干擾機師會釀成很嚴重、甚至是致命的錯誤,因此航空業會盡量防範,讓干擾減到最低。但是在急診室可沒有。你可能正在試圖搶救某人的生命,護理師卻在一旁要求你下口頭醫囑,開一份止痛藥。你如果膽敢聲稱你正在忙,別人就會用一種「發什麼脾氣」的眼光看著你。
吵雜是急診室工作的另一項妨礙。西奈山醫院急診室經常會發動一波波強烈的機械警鈴攻勢。病人床邊的警鈴會發出一串由兩個音符組成的聲音,中間有稍長的停頓。那音符就和一九七五年由巴西歌手莫利斯.艾伯特演唱的經典搖滾歌曲〈感覺〉(Feelings,原為法國作曲家Louis Gaste所寫)的頭兩個音,一模一樣。每次一聽見那警鈴聲,我心中就會立刻開始播放那首歌。沒辦法,我就是會這樣。
加上人們痛苦的尖叫,精神病人的妄想哀號,以及阿茲海默症和其他失智病人一再重複的唸誦,讓人禁不住好奇,醫師怎麼有辦法像我們這樣專心工作呢?
急診室可不像電視劇塑造的模樣
情況並非一向如此。一九二三年,這所醫院剛成立,是一所擁有三十三張病床的婦產暨康復醫院。一九五三年,新的西奈山醫院在大學大道開張,位置就在知名的多倫多兒童醫院對面。一九七三年,醫院往北邊搬了一戶,到現在的位置。如今西奈山醫院已經成為訓練醫學生和住院醫師的頂級醫學機構。我們非常自豪,因為我們擁有世界級的研究機構,而且我們照護了一個日漸增長的社區,裡頭有許多複雜的病人。對此我很了解,因為我們在急診室見過很多。
一九八四年,我剛開始在西奈山醫院工作時,每次值班大約看八到十二位病人(每天從那扇玻璃門進來的病人約七十人)。那樣的年代早已成為過去。人口增長,加上鄰近關閉了好幾家醫院,意味著我們的病人數量大大攀升。現在,西奈山醫院的施瓦茨—雷斯曼急診中心,每天要看一百二十名到一百三十名急診病人(一年約合四萬七千人),而且還在增加之中。有時候,我們急診室一天看診的病人超過一百六十名。在平常的星期五大夜班,我在次日早晨七點交班前,得看三十位到四十位病人。
而且改變的不只是數量。我們所謂的劇烈程度,也就是病人的病情嚴重程度,也改變了。以前我們大部分看的病人都是心臟病發或肺炎或潰瘍。如今,最典型的西奈山急診病人可能是糖尿病、高血壓、心血管問題、腎衰竭或是癌症。先進的血管成形技術以及更好的化療,帶來利弊參半的結果。病人的壽命變長了——在我剛開始行醫時,九十幾歲的病人非常稀有,如今已變得很尋常。
隔開候診室與急診室的那扇門,「簡直就是通往另一個宇宙的門,」曾撰寫過許多本醫學書籍的佩齊(Wayne Pezzi)醫師這麼說。佩齊醫師在美國從事急診醫療已超過十年。他說,急診室可不像電視劇塑造出來的樣子,一個光鮮亮麗的、或是不斷出現很刺激的急症創傷的世界,雖說那些描述也有吻合的時刻。
「人們一想到急診室,最先想到的就是鮮血、腸子,」佩齊醫師說:「其實他們也應該要想到糞便、尿液、嘔吐物,以及從各種部位冒出來的膿液、不堪一提的骨盆分泌物,此外還要面對鬧脾氣、滔滔不絕的髒話、威脅、各種言詞辱罵,偶爾還會被人揍兩拳。事實上,急診醫師大部分所做的事,以及必須忍耐的事,都與光鮮亮麗正好相反。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噁心的事,例如幫某位病人『解除阻塞』。(我的白話翻譯是:把直腸裡的硬大便給摳出來。)」
和電視不一樣,這裡沒有源源不絕的擔架床通過推門,一隊醫護人員一邊推著擔架床奔跑,一邊忙著嘗試各種動作來搶救垂死的病人。這種場面在西奈山醫院尤其少見,因為除了特殊狀況之外,這裡並不診療槍傷或車禍傷患。那些病人通常會給送往市內其他專門處理那類型創傷的醫院。
但這並不表示西奈山醫院的病例缺乏戲劇性,只是方式不同。我們診療的病人各式各樣,從心跳停止到未知皮疹都有。少數病人面臨死亡的風險,但是大部分沒有。就某個程度而言,他們全都自認病情嚴重,否則不會跑到急診室來。在這裡,他們有時候得熬過漫長乏味的候診時光。
我會成為急診醫師,幾乎是一個意外。讀醫學院時,我對神經科學產生了興趣,也就是專門處理中風及其他腦部疾病的專科。我太喜歡這一科了,四年級的時候,我就做出一個現在想來很衝動的決定:我要成為小兒神經科醫師。我順利申請進入多倫多的兒童醫院來實習。一九七九年,我在醫學院的最後一年,我到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神經科,接受兩個月的輪訓。當時約翰霍普金斯有一項世界著名的神經科學住院醫師計畫。我去那兒受訓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贏得未來的指導老師的青睞。
訓練期間,我開始懷疑自己的生涯抉擇。更糟糕的是,我覺得很孤單,很想家。在我受訓的一個關鍵日子,我本來預計要上臺報告,結果卻睡過頭,錯失了在上級面前表現的機會。
我悽悽慘慘的回到多倫多。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明白,那天早晨,我的守護天使其實是救了我。現在我知道,神經科學對我來說,是一條沒指望的路。哦,我還是可能做得不錯。但是在我靈魂深處,有某種創新的東西在攪和,好幾年後才會明朗。睡過頭,讓我免於對未來職業及生活的懊悔。
不過,我當時已經向兒童醫院提出申請,而且也獲准擔任第一年住院醫師,算是我第一年接受兒童神經科醫師的專業訓練。我不能退出。我完成那一年的訓練,然後轉到當時的新寧醫院,在那裡接受為期一年的內科住院醫師訓練。
到了那個時候,我已知道自己想要寫作。我曾嘗試寫一篇小說,但是沒能完成。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環球郵報》的科學版。那次成功經驗讓我相信,我想要開發自己在寫作上的興趣。剛好就在那個時候,急診醫學向我招手。我認識一些住院醫師同事在當地醫院的急診室兼差、賺外快。我決定也要嘗試一下,很快就發現急診醫學非常刺激,而且能讓人獲得智能上的滿足。更棒的是,它是兼任的工作,讓我有很多時間來寫作,以及從事廣播工作。
在這一行,犯錯是會害死人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在我開始急診醫師生涯沒多久,我經歷到第一次以急診主治醫師身分,參與搶救心跳停止的病人。我那時是在多倫多藍領社區的西北總醫院值夜班。
就像許多壓力大的工作環境,例如執法人員、記者等等,醫學老鳥總是會觀察(和測試)新人,看他們能不能在壓力下保持冷靜,並判斷他們是否具有幽默感。資深護理師和救護員對年輕醫師的評判,往往最是嚴格。他們碰過太多自大的醫學院畢業生,這些人不懂得尊敬前輩醫護專業人員所擁有的廣博知識與經驗。
一天晚上,一名男病人心臟病發,被送進急診室。他失去心跳起碼已經十分鐘了,甚至可能更久。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已經死了,但是急救小組還是得嘗試讓他復甦,希望奇蹟能夠發生。我在當住院醫師期間,曾經上過高級心臟救命術的課程,這是一次將理論轉化為實務的機會。身為急救小組龍頭,那天晚上我的角色是:找出我們的病人心跳停止的原因以及如何挽救。貼在我的病人胸口的電極片告訴我,他是心搏停止——沒有心律,而且將他搶救回來的機會很小。
情急之下,我趕忙讓心臟電擊去顫器充電,準備用三百焦耳的電流能量去震搖他的心臟。我把凝膠塗在電擊器上,然後壓在病人胸前,一個在胸骨右側,一個在病人左乳頭上。我大喊「clear」(離手),要所有與病人輪床接觸的人閃開,以免受到電擊。經過小心確認後,我按下電擊器上的按鈕,然而,迎接我的卻是一縷輕煙以及刺鼻的皮肉燒焦味。原來我不小心讓其中一個電極碰到一條心電圖描記器的引線,而那條引線接在病人胸口的一片貼紙上。我驚駭的發現,那片紙竟然燒了起來,雖然只有短短一下子。
一名頭髮斑白的護理師(她看起來好像在過去幾十年生涯中,每天都要抽個兩包香菸的樣子),從她那遠近兩用眼鏡片上方瞥了我一眼,一邊輕輕搖著頭說:「好啦,他就算原本沒死,現在肯定也死了。」這話引發一陣哄笑。我也跟著笑,但心裡覺得好丟臉。這是一次令人謙卑的經驗,我很高興它發生在我職業生涯的初期。
做我們這一行,犯錯是會害死人的,而這份沉重的責任並不容易面對。(我可以稍感欣慰的說,本案不是這種狀況;當時我們不管怎麼做,都無法挽回這人的生命。)有些醫師發現,很難承認自己也是凡人,也會犯錯。有些醫師發覺,去面對這個醫療體系裡有某些部分失靈,需要改進,也同樣困難。如果承認這些不足之處,他們可能就必須質疑工作裡的某些面向,而他們寧願不要去承認或檢視。
那名護理師的黑色幽默,那天確實挫了我的銳氣。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那樣的當頭棒喝,因為我對待自己總是比別人對待我更加嚴格。但是,這個經歷至少無害。它始終是一個鮮活的記憶,關於我有可能犯下大錯,以及當我造成錯誤時,需要用哪一種態度來回應——在本案例,是用幽默和謙遜來回應。
當時我無法真正欣賞那名護理師的幽默,因為我被這種生死攸關的場面嚇呆了,就像你在幫病人插管的時候(所謂插管,就是將一條呼吸管插入病人的氣管裡)。我們做這個動作,是因為病人的肺部損害太過嚴重或是充滿液體,如果不靠人工呼吸器,無法吸入足夠維生的氧氣。我們這樣做的另一種情況是,當病人意識非常低弱,可能是因為頭部受傷或酒醉或嗑藥,以致無法防止食物或是嘔吐物從食道湧出來、灌進肺部,這種狀況稱做抽吸(aspiration)。抽吸的病人有可能當場呼吸停止,或是在幾天之後,因吸入性肺炎和休克而死亡。
在我職業生涯早期發生的另一件插曲,也對我在急診室的工作方式產生重大的影響。有一位病人因為精神問題住進某家醫院,但是他不告而別,自行離院,就是我們所謂的「逃走了」。不久之後,他進入地鐵站,跳到一列電車面前,當場死亡。我當時工作的那家醫院的救護員,將他的屍體帶回醫院,因為他必須經過正式的死亡宣告。
他們將他送到一個房間,安置在一張床上,然後用被單覆蓋起來,只露出頭部。當時我還沒有看過太多屍體,而每次凝視一具沒有生命的軀體,對我來說,總是肅穆的一刻。他的眼睛好像睡著般閉著,彷彿終於掙脫心魔,得到安息。然而,當我掀開被單時,立刻一陣反胃。我原先並不知道電車令他身首異處。救護員開了個玩笑,把他的軀體翻轉過來,因此他的頭雖然是臉朝上,但是他的身體卻是背朝上。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我差點嘔吐出來。
那天晚上救護員的所作所為,非常侮辱人。我能欣賞黑色幽默,也隨時準備受人消遣,就像那天我電擊失敗,護理師對我的嘲諷。但是這個舉動,實在太超過了。說句公道話,那件事發生在超過二十年前,現在我所認識並且一起工作的救護員,都相當謙恭和敏感,而且相當專業。近年來,我從沒聽過像那樣的惡作劇。如果今天發生這種事,我會非常驚駭。沒錯,醫療工作人員可能對生老病死見怪不怪,因為我們看得太多了。但是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變得如此殘酷無情,把受苦之人的自殺,當成開玩笑的材料。那樣做,我們有可能變得麻木不仁,無法碰觸自己的良心,也無法體會在急診室裡的病人及其摯愛的人所受的苦痛。我希望自己永遠不要變成那個樣子。多年前那幅可怕的影像,對我來說依然歷歷在目,它成為我的提醒者,提醒我:以醫師身分接觸他人時,要用我希望自己的親朋好友受對待的方式,來對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