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奪路: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 作者 | 王鼎鈞 |
|---|---|
| 出版社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關山奪路: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耗費十三年書寫,大跨度地調動時空、融合個人經驗與時代全景,描寫國共內戰時期,天下已亂之況。「戰爭年代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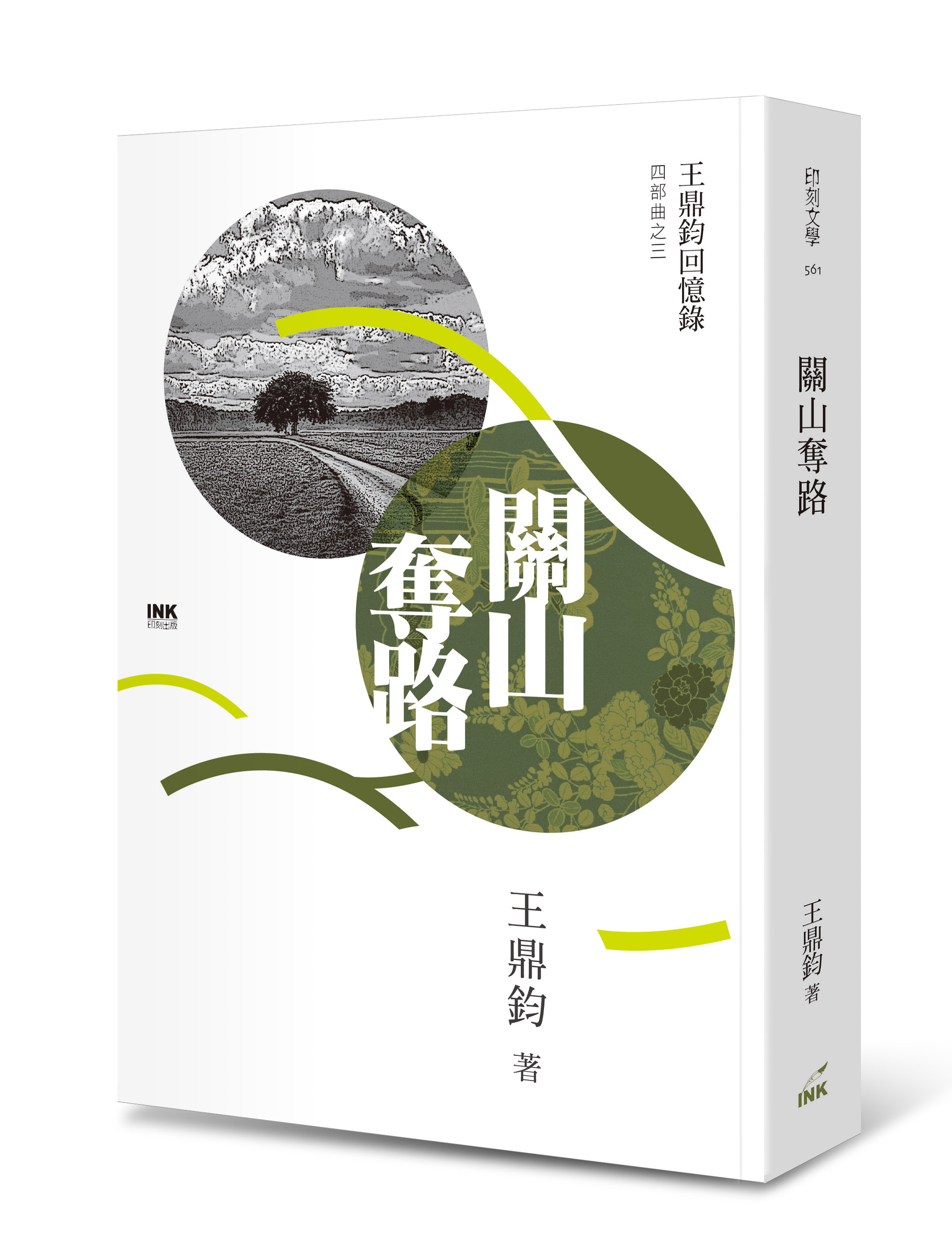
| 作者 | 王鼎鈞 |
|---|---|
| 出版社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關山奪路: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耗費十三年書寫,大跨度地調動時空、融合個人經驗與時代全景,描寫國共內戰時期,天下已亂之況。「戰爭年代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 |
內容簡介 耗費十三年書寫,大跨度地調動時空、融合個人經驗與時代全景,描寫國共內戰時期,天下已亂之況。「戰爭年代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控訴、吶喊而已,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采。憤怒出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昇華了,人生的精采才呈現出來,生活原材變成文學素材。」--王鼎鈞內戰四年,千萬顆人頭落地,千萬個家庭生離死別,看見多少瘋狂,多少憔悴,多少犧牲,多少殘毁……戰爭年代的經驗雖然痛苦,但不是吶喊、控訴、絕望或痛恨。耗費十三年撰寫與修改,《關山奪路》描寫出國共內戰時期,天下已亂之況。國軍有國軍的說法,共軍有共軍的紀錄。然而雙方皆有如走馬燈,去了又來,來了又去。世事有遠因近果,表象與內幕,偶然及必然,真誠偽裝交雜,最重要的是,藉個人離亂的遭遇,顯現火燄山似的戰爭年代,從悲痛中認識人性。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王鼎鈞1925年生,山東省臨沂縣人。抗戰末期棄學從軍,1949年來台,曾任中廣公司編審、製作組長、專門委員,中國文化學院講師,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幼獅文化公司期刊部代理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人間」副刊主編,美國西東大學雙語教程中心華文主編。目前旅居美國。曾獲金鼎獎,台北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獎章,中山文化基金會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吳魯芹散文獎。1999年《開放的人生》榮獲文建會及聯合副刊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三十」。2001年,獲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傑出華人會員」獎牌。著有散文「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碎琉璃》、《山裡山外》、《左心房漩渦》、《小而美散文》。小說《單身溫度》。論著「作文四書」《靈感》、《文學種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等。
產品目錄 編輯前言代序 寫在關山奪路出版之後竹林裡的決定,離開漢陰憲兵連長以國家之名行騙參加學潮,反思學潮最難走的路,穿越秦嶺新兵是怎樣鍊成的(上)新兵是怎樣鍊成的(下)兩位好心排長怎樣庇護我由寶雞出發 另一種流亡南京印象 一叠報紙南京印象 一群難民我愛上海 我愛自來水我患了某種過敏症瀋陽市的馬前馬後我所看到的日俘日僑憲兵的學科訓練憲兵的勤務訓練左翼文學重陶紀事我第一天的差事我從文學的窗口進來東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淪小兵立大功 幻想破滅我的名字王鶴霄貪污哲學智仁勇秦皇島上的文學因緣從學運英雄于子三看學潮滿紙荒唐見人心山東 天敵之下九條命山東 由洗衣板到絞肉機東北 那些難忘的人滾動的石頭往那裡滾天津中共戰俘營半月記為一隻眼睛奮鬥膠濟路上的人間奇遇上海市生死傳奇(上)山東青年的艱苦流亡上海市生死傳奇(下)參考資料
| 書名 / | 關山奪路: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
|---|---|
| 作者 / | 王鼎鈞 |
| 簡介 / | 關山奪路: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耗費十三年書寫,大跨度地調動時空、融合個人經驗與時代全景,描寫國共內戰時期,天下已亂之況。「戰爭年代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 |
| 出版社 /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3872290 |
| ISBN10 / | 9863872296 |
| EAN / | 9789863872290 |
| 誠品26碼 / | 2681584487005 |
| 頁數 / | 480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4.8X21X2.5CM |
| 級別 / | N:無 |
自序 : 寫在《關山奪路》出版以後
最近,我和作家朋友有一次對話。他說:咱們這麼大年紀了,還寫個甚麼勁兒呢!我說:我們是幹甚麼的,我們不是要為社會為讀者寫東西嗎?他說:現代人寫回憶錄時興別人替你執筆啊。我說:我是廚子,我請客當然親手做菜。你已寫過很多了!是的,我已經寫過不少,可是我總是覺得不夠好,總希望寫出更好的來。你現在寫的夠好嗎?我不知道,我聽說「從地窖裡拿出來的酒,最後拿出來的是最好的」。
回憶錄第一冊《昨天的雲》,寫我的故鄉、家庭和抗戰初期的遭遇。第二冊《怒目少年》,寫抗戰時期到大後方做流亡學生,那是對我很重要的鍛鍊。第三冊《關山奪路》,寫國共內戰時期奔馳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後我還要寫第四本,寫我在台灣看到甚麼,學到甚麼,付出甚麼。我要用這四本書顯示我那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
對日抗戰時期。我曾經在日本軍隊的佔領區生活,也在抗戰的大後方生活。內戰時期,我參加國軍,看見國民黨的巔峰狀態,也看見共產黨的全面勝利,我做過俘虜,進過解放區。抗戰時期,我受國民黨的戰時教育,受專制思想的洗禮,後來到台灣,在時代潮流沖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裡解構,經過大寒大熱,大破大立。這些年,咱們中國一再分成兩半,日本軍一半,抗日軍一半;國民黨一半,共產黨一半;專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傳統一半,西化一半;農業社會一半,商業社會一半;由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這一半。有人只看見一半,我親眼看見兩半,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教我作個見證。
今天拿出來的第三本回憶錄《關山奪路》,寫我經歷的國共內戰。這一段時間大環境變化多,挑戰強,我也進入青年時代,領受的能力也大,感應特別豐富。初稿寫了三十多萬字,太厚了,存二十四萬字,仍然是三本之中篇幅最多的一本。
國共內戰,依照國民政府的說法,打了三年,依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打了四年,內戰從哪一天開始算起,他們的說法不同。內戰有三個最重要的戰役,其中兩個:遼瀋、平津,我在數難逃,最後南京不守,上海撤退,我也觸及靈魂。戰爭給作家一種豐富,寫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來,作家搬石頭蓋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內戰、抗戰永遠有人寫,一代一代寫不完,也永遠不嫌晚。
我們常說文學表現人生,我想:應該說文學表現精采的人生,人生充滿了枯燥、沉悶、單調,令人厭倦,不能做文學作品的素材。甚麼叫「精采的人生」?
第一是「對照」。比方說國共內戰有一段時間叫拉鋸戰,國軍忽然來了、又走了。共軍忽然走了、又來了,像走馬燈。在拉鋸的地區,一個村子有兩個村長,一個村長應付國軍,一個村長接待共軍。一個小學有兩套教材,國軍來了用這一套,共軍來了用那一套。一個鄉公所辦公室有兩張照片,一張蔣先生,一張毛先生,國軍來了掛這一張,共軍來了掛那一張。有些鄉鎮拉鋸拉得太快,拉得次數太頻繁,鄉長就做一個畫框,正反兩面兩幅人像,一邊毛先生,一邊蔣先生,掛在辦公室裡,隨時可以翻過來。這都是對照,都很精采。
第二是「危機」。比方說,解放軍攻天津的時候,我在天津,我是國軍後勤單位的一個下級軍官,我們十幾個人住在一家大樓的地下室裡。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軍攻進天津市,我們躺在地下室裡,不敢亂說亂動,只聽見梯口有人喊「出來!出來!交槍不殺!」接著咚咚咚一個手榴彈從階梯上滾下來。我們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彈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彈,感覺手臂像燒透了的一根鐵,通紅,手榴彈有點軟。叨天之幸,這顆手榴彈冷冷的停在那兒沒有任何變化。那時共軍用土法製造手榴彈,平均每四顆中有一顆啞火,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大概我們中間有個人福大命大,我們都沾了他的光。這就是危機,很精采。如果手榴彈爆炸了,就不精采了,如果沒有這顆手榴彈,也不夠精采,叨天之幸,有手榴彈,沒爆炸,精采!
第三是「衝突」。比方說,平津戰役結束,我在解放區穿國軍軍服,這身衣服跟環境衝突,當然處處不方便,發生了一些事情,今天想起來很精采。後來由於一次精采的遭遇,我又穿解放軍的衣服進入國軍的地盤,我的衣服又跟環境衝突,又發生了一些精采的事情。衝突會產生精采。
在《關山奪路》這本書裡,對照、危機、衝突各自延長,互相糾纏,滾動前進。楊萬里有一首詩:「萬山不許一溪奔」,結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們家鄉有句俗話:「水要走路,山擋不住。」我還聽到過一首歌:「左邊一座山,右邊一座山,一條河流過兩座山中間。左邊碰壁彎一彎,右邊碰壁彎一彎,不到黃河心不甘。」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采的人生。
由第二冊回憶錄到第三冊,中間隔了十三年,這是因為:
國共內戰的題材怎麼寫,這邊有這邊的口徑,那邊有那邊的樣板,我沒有能力符合他們的標準,只能寫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應該沒有政治立場,沒有階級立場,沒有得失恩怨的個人立場,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覽眾山小。而且我應該有我自己的語言,我不必第一千個用花比美女。如果辦不到,我不寫。
我以前從未拿這一段遭遇寫文章。當有權有位的人對文學充滿了希望、對作家充滿了期待的時候,我這本書沒法寫,直到他們對文學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認為你成事固然不足,敗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讓你自生自滅了,這時候文學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個真正的作家。
戰爭年代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控訴、吶喊而已,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采。憤怒出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昇華了,人生的精采才呈現出來,生活原材變成文學素材。如果我辦不到,我也不寫。可敬可愛的同行們!請聽我一句話:讀者不是我們訴苦伸冤的對象,讀者不能為了我們做七俠五義,讀者不是來替我們承受壓力。拿讀者當垃圾桶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啦啦隊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弱勢團體任意擺布的時代也過去了!讀者不能只聽見喊叫,他要聽見唱歌。讀者不能只看見血淚,他要看血淚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見染成的杜鵑花。心胸大的人看見明珠,可以把程序反過來倒推回去,發現你的血淚,心胸小的人你就讓他賞心悅目自得其樂。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寫,為了雕這塊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寫自傳,因為人最關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讀者並不愛看別人的自傳,因為讀者最關心的也是他自己,所以這年代,人了解別人很困難。我寫回憶錄在這個矛盾中奮鬥,我不是寫自己,我沒有那麼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我希望讀者能了解、能關心那個時代,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所以我這四本書不叫自傳,叫回憶錄。有些年輕朋友說,他的父親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他知道的太少,所以對父親祖父的了解也很少,他讀了這本書多知道一些事情,進一步了解老人家。他太可愛了!
國共內戰造成中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希望讀者由我認識這個變局。可能嗎?我本來學習寫小說、沒有學會,小說家有一項專長:「由有限中見無限」,他們的這一手我學到了幾分。當初我在台灣學習寫作的時候,英國歷史家湯因比的學說介紹到台灣,他說歷史事件太多,歷史方法處理不完,用科學方法處理;科學的方法仍然處理不完,那就由藝術家處理。他說藝術家的方法是使用「符號」。照他的說法,文學作品並不是小道,藝術作品也不是雕蟲小技,我一直思考他說的話。
我發現,凡是「精采」的事件都有「符號」的功能,「一粒砂見世界,一朵花見天國」,那粒砂是精采的砂,那朵花是精采的花。我本來不相信這句話,詩人幫助我,一位詩人顛覆莊子的話作了一首詩,他說「我把船藏在山洞裡,把地球藏在船上。」還有一位詩人寫〈下午茶〉,他說下午在茶裡。牧師也幫助我,「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法師也幫助我,他說「納須彌於芥子」。四年內戰,發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寫成一本書,每一個小時都可以寫成一本書,我用符號來處理,我寫成一本書。
中國人看國共內戰,這裡那裡都有意見領袖,這本書那本書都有不同的說法。我寫第一冊回憶錄《昨天的雲》盡量避免議論,維持一個混沌未鑿的少年。寫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幾十年後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現在這本《關山奪路》,我又希望和以前兩本不同,我的興趣是叙述事實,由讀者自己產生意見,如果讀者們見仁見智,如果讀者們橫看成嶺、側看成峰,我也很高興。
除了跟自己不同,我也希望跟別人不完全相同,有許多現象,別人沒寫下來,有許多看法,以前沒人提示過,有些內容跟人家差不多,我有我的表達方式。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說跟別人完全一樣的話,我是基督徒,我曾經報告我的牧師,請他包容我,一個作家,他說話如果跟別人完全相同,這個作家就死了!做好作家和做好基督徒有矛盾,好基督徒要說跟牧師一樣的話,說跟教友一樣的話,作家不然,我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價,大家衣帶漸寬終不悔。今日何日,為甚麼還要勉強做學舌的鸚鵡?為名?為利?為情?為義?還是因為不爭氣?
我的可敬可愛的同行們!「自古文人少同心」,我說的話應該跟你不一樣,你說的話也應該跟我不一樣。東風吹,戰鼓擂,今天世界上誰怕誰!一個人說話怎麼總是跟別人不一樣?這樣的人很難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僱員?好朋友?好黨員?可憐的作家!他只有一條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個浮士德,把靈魂押給了文學。
文學藝術標榜真善美,各位大概還記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璇唱過,咱們別因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輕了它,寫歌詞的人還真是個行家:
真善美,真善美,他們的代價是腦髓,是心血,是眼淚。……是瘋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悶,多少徘徊,換幾個真善美。多少犧牲,多少埋沒,多少殘毀,賸幾個真善美。……真善美,欣賞的有誰,愛好的有誰,需要的又有誰……
這首歌唱的簡直就是一部藝術史!內戰四年,千萬顆人頭落地,千萬個家庭生離死別,海內海外也沒產生幾本真正的文學作品。我個人千思萬想,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難萬難,顧不了學業,顧不了愛情,顧不了成仁取義、禮義廉恥。看見多少瘋狂,多少憔悴,多少犧牲,多少殘毀。我有千言萬語,欲休還說。我是後死者,我是耶和華從爐灶裡抽出來的一根柴,這根柴不能變成朽木,雕蟲也好,雕龍也好。我總得雕出一個玩藝兒來。……我也不知道「欣賞的有誰,愛好的有誰,需要的有誰」。一本書出版以後有它自己的命運,自己的因緣。
最後我說個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體裡頭結成的,但是明珠並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憶錄是我對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對國家社會的回饋,我來了,我看見了,我也說出來了!
(在《關山奪路》新書發表會上講話,二○○六年七月,紐約)
內文 : 天津中共戰俘營半月記
解放軍攻克天津的時候,對處理大批俘虜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繳械就擒的國軍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離開住所。路上只見掉下來的招牌,斷了的電話線,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沒人看我們,我偷偷的看他。我們走進一所學校,只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擠滿了房子,擠滿了院子。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律不佩符號,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比方說,士兵穿又髒又舊的軍服,連長穿乾乾淨淨的軍服,團長穿嶄新的軍服。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裡管理我們,我們人數這麼多,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身旁幾個通信兵,門口幾個衛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
雖說是押送和集中監視,他們並未怎樣注意我們,反倒是我,我沒忘記我是(或者準備是)一個作家,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雖說是東北解放軍入關,那些戰士並不魁梧健壯,個個臉色憔悴,嘴唇皸裂,雙手赤紅,我擔心他們生凍瘡。有人光著頭,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沒人伸手來摘我們的皮帽子,很難得!他們沒穿大衣,腰間紮著寬大的布帶,想是為了禦寒。裝備陳舊,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土布的顏色單調,軍容灰暗,只有腰間插著一雙布鞋嶄新,兵貴神速,他們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還記得國軍宿營的時候,照例派人四出偵察,報告說百里之內並無敵蹤,於是放心睡覺,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神通就在這雙布鞋。個別看,解放軍哪裡是雄師?何以集體表現席捲江山?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沒有答案。
我設法擠到辦公室門口去看指導員,他抽菸,看不出香菸牌子,聞氣味品質不壞。一個國軍軍官擠進來向他介紹自己是是甚麼團的團長,跟指導員攀同鄉,團長是在戰鬥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經好多天沒回家了,要求指導員行個方便,讓他回去看看孩子,他發誓一定回來報到。又有一個軍官擠進來,他說他跟解放軍司令員劉亞樓是親戚,劉亞樓指揮解放天津的戰鬥,目前人在市內,他要求去找劉亞樓見面。那位指導員一面抽菸一面微笑,慢動作撕開香菸盒,掏出鉛筆來寫字,他用香菸盒的反面寫報告,向上級請示。通訊兵去了又回來,字條上面批著兩個字:「不准」,用的也是鉛筆。他們的公文程序怎麼簡化到這般程度,我非常驚異。指導員拿批示給他們看,不說話。
戰鬥結束了,許多國軍軍官沒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牽著小孩出來找丈夫。她們有人找到我們這一站,衛兵不許她們進來,但是可以替她們傳話,「某某團的副團長某某在這裡沒有!你太太帶著孩子在門口找你!」這樣的話由大門外傳到大門裡,由院子裡傳到屋子裡,沒有反應。於是有人高聲喊叫,重複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有回聲。於是有人低聲議論,就算他在這裡也不敢出頭承認,他還想隱瞞身分呢。那時國軍軍官被俘後常常謊報級職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將校官冒充尉官,這樣做都是枉費心機,以後還有多次清查,總有辦法把你一個一個揪出來。
俘虜實在太多了,解放軍不斷增加臨時收容的地方,我們這裡一批人疏散出去,騰出空間,於是進行下一個程序,「區分山羊綿羊」。第一步,軍官和士兵分開,他們把士兵帶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軍官和中校以下的軍官分開,他們又把上校以上的軍官帶走了。斬頭去尾,我們中間這一段人數最多,這才發現我們那個單位只來了我們十幾個呆鳥,別人早有脫身之計,人人祕而不宣。兩個月後我逃到上海,發現我們的新老闆先到一步,住在一棟花園樓房裡。四個月後我逃到台北,陸續遇見許多同仁,他們也都是狡兔。
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指導員不再微笑,也沒有講話,他只是冷冷的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只是冷冷的工作,一片「晚來天欲雪」的感覺。他們為甚麼不講話?這是不祥之兆嗎?由鬧烘烘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虛,胡思亂想,想起滾進地下室的手榴彈,想起德國納粹把俘虜運到郊外集體槍決。
還好,我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楊柳青,東看西看好像沒有楊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倉,看見碉堡殘破,交通壕翻邊,鐵絲網零亂,大概是砲兵猛轟造成的吧,想見戰鬥還是很激烈。我們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這夜無星無月,野外有人不斷發射照明彈,(為甚麼?)顯示最後的戰時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見隊形蜿蜒。途中隊伍距離拉得很長,身旁沒人監視,可是一個人也沒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農家,老大娘為我們燒火做飯,整天僅此一餐,可是並不覺得餓。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隊解放軍同行。我放慢腳步,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他們,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我注意他們的槍械,那時,共軍用「小米加上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砲,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我只看見日軍的制式步槍「三八式」,國軍的制式步槍「中正式」。我心頭一懍,想起我在瀋陽揹過擦過的那枝槍,那枝槍流落何方?我還記得它的號碼,真想看看他們每個人的槍,看他們的號碼離我多近多遠。解放軍打天津,除了飛機以外,大砲機槍衝鋒槍甚麼武器都有,據「火器堂」網上資料,抗戰八年,內戰四年,聯勤的兵工廠大約製造了五十萬枝中正式步槍,我想平津戰役結束時,總有三十萬枝已經握在解放軍手中了吧?韓戰發生,中共派志願軍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聯軍大戰三百回合。
我們一直往北走,天氣忽然起了變化,風沙撲面而來,那風沙強悍詭異,難以形容。我拉低帽沿,掏出手帕遮臉,閉緊眼睛趕路,每隔幾秒鐘睜開一條縫,看一看腳下的路,塵土細沙趁勢鑽進來。四面一片濛濛的黃,空氣有顏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難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時我只為眼睛擔憂,作家可以沒有手,沒有腳,必須有眼睛。現在我知道,那天我們遇上了「沙塵暴」,西北風挾帶內蒙的塵沙,向南撲來,它一年比一年嚴重,現在已經形成天災,華北東北都成災區。現在「沙塵暴」過境的時候,人取消戶外活動,飛機停飛,沙塵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沒法耕種,人民沒法安居。專家總是往壞處想,他們憂慮多少年後,東北華北一半變成少漠。倘若真有那麼一天,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國共兩黨興兵百萬,血流成河,爭的就是這幾粒沙。
當時風沙中辛苦掙扎,哪會想這許多,我只擔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風也停了。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瓦房很多。我們先在村頭一字排開,解放軍戰士抬了一個籮筐來,我們在軍官監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鈔票,銀元,戒指,手錶,都放在籮筐裡,我能了解,這是防止我們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進去,鋼筆,照片,符號,日記本,我明白,這是要從裡面找情報。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張符號以外,甚麼財物也沒有。我的職位是個上尉軍需啊,軍隊裡不是常說「窮書記、富軍需」嗎,解放軍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實際上是個「窮書記」?似乎懷疑,倒也讓我過關。他強調受訓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還,這位軍官是我們的指導員。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裡,屋裡沒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階級鬥爭」取走了一切浮財。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應該是民伕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櫺,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來。既然門窗「洞」開,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要看要聽,十分方便。夜間風雪出入自如,彷彿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
我必須說,解放軍管理俘虜還算和善寬鬆,伙食也不壞,一天兩餐,菜裡有肉。當然我們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後,第一件事情是集體跑步,這時,住在這個村子裡的俘虜全員到齊,大概有兩百人左右,解放軍駐紮的武力大約是兩個班,果然一以當十。跑步之後,大家在廣場集合,班長登台教唱,第一天學的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天夜裡降了一場淺淺的雪,天公慈悲,沒颳大風,早晨白雲折射天光,總算晴了。第二天學的是「換槍換槍快換槍,蔣介石,運輸大隊長,送來大批美國槍。」我聽了不覺一笑,也不知他們有幽默感,還是我有幽默感。
所謂受訓,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難,終於有這麼一天,早操以後,班長教唱,劈頭就是「蔣介石,大流氓,無恥的漢奸賣國賊。」我張口結舌,這未免太離譜了吧?這並不是侮辱蔣氏,而是侮辱我們的知識程度。我讀過教會歷史,當年羅馬帝國打算消滅基督教,把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拆來擺在地上,命令教徒一個一個踐踏,如今解放軍玩的是同樣的把戲,可是跟羅馬統治者比,格調太低了。大約人同此心,解放軍班長領頭起句以後,全場默然,指導員一向不說話,臉色像上了一層釉子,這時帶著槍兵走過來,指著我們的鼻子喝問:「你為甚麼不唱?為甚麼不唱?」隊伍裡這才有了嗡嗡之聲。他不滿意,又一個一個指著鼻子喝令:「大聲唱!大聲唱!」隊伍裡的歌聲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學唱,於是被指導員帶進辦公室。我模仿朱連長向副團長抗辯的態度,立正站好,姿勢筆挺,有問必答,一口一個「報告指導員」。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厲聲斥責,「你已經解放了,為甚麼不唱解放軍的歌?」我告訴他,我是唱八路軍的歌長大的。不待他考問,我自動唱起來,我採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樹林裡,有我們無數好兄弟。」唱了兩句,馬上換另外一首,「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再換一首,「延水濁,延水清,情郎哥哥去當兵,當兵要當八路軍。」再換一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軍不打抗日軍。」
他大喝一聲:「夠了!你這些歌現在沒人唱了,你到這裡來受訓,就是教你趕上形勢。」我說報告指導員,八路軍的那些歌真好,我們愛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現在教的歌哪裡比得上?現在這支歌怎麼這麼低俗?這哪裡像解放軍的歌?我不顧他的反應,連唱帶說,他用銳利的眼神觀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後來我知道,他們認為抗拒爭辯都是真情流露,他們對「真情」有興趣,如果我馬上無條件適應,他反而認為是虛偽,引起他們的戒備懷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問我對這裡的生活有甚麼意見。「報告指導員,沒有意見。」怎麼會沒有?他不信。「報告指導員,抗戰的時候,國民黨的游擊隊捉到了八路軍要活埋,我們都是該死沒死的人,在這裡吃得飽,睡得好,當然沒有批評。」這幾句話他聽得進。你對國民黨還有甚麼幻想?「報告指導員,沒有任何幻想。」是不是還想倚靠蔣介石?「報告指導員,我跑江湖混飯吃,從來沒倚靠蔣介石。」大概這句話太沒水準,他皺了一下眉頭。那麼你對自己的前途有甚麼打算?「報告指導員,我的父親在南京做難民,我要到南京去養活他。」我簡化問題,隱瞞了弟弟和妹妹。他說南京馬上要解放了,全中國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說他也有父母,個人的問題要放在全國解放的問題裡解決。
他靜待我的反應,我默不作聲。
他拿出一本小冊子來交給我,他說這是我從未讀過的書,他用警告的語氣說,「接受新知識的時候要用心,還要虛心。」他等著聽我的心得報告。那時候我的左眼開始腫脹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們逆風行軍,塵沙傷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問我的病痛,他顯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讀他指定的教材。
俘虜營裡沒有醫療服務,班長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紗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來,乍看外表,倒是很像個傷兵。冷風吹拂,我發覺自己跑進指導員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標。他們閉上一隻耳朵,沒再強迫我唱歌,我難道已在享受某種優待?代價是甚麼?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隱身,也許因而不能脫身,我那年才二十四歲,對中共多少有用處。
五年前我也許願意加入共青團,可是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大我,紀律,信仰,奉獻,都是可怕的名詞,背後無數負面的內容。我一心嚮往個人自由,我曾在新聞紀錄片裡看見要人走出飛機,儀隊像一堵磚牆排列在旁邊,新聞記者先是一擁而上,後是滿地奔跑追趕,我當時曾暗暗立下志願,從那一堵牆中走出來,到滿地亂跑的人中間去。其實「自由」也有陰暗面,那時我還不知道「事情總是向相反的一面發展」,以螺旋形的軌跡尋求救贖。
我已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養活父親,幫助弟弟妹妹長大。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渙散的」社會裡去苟活。我必須奔向南京。
腳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嗎?顯然沒有。如果我的左眼長期發炎得不到治療,必定失明,中共不會要一個殘廢的人,那樣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我猜父親看見一個「眇目」的兒子回來,不會有快樂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許會得到慷慨的施捨。我在兩利兩害之間忐忑不安。那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他自己也面臨選擇:損失一個兒子、或者僅僅損失兒子的一隻眼睛。
我始終沒讀指導員交給我的那本書,只是偶然揭開封面看了一眼。果真「開卷有益」,封面裡空白的那一頁蓋了一個圖章:「東北軍政大學冀熱遼邊區分校圖書館」,正好蓋在左下角。我大吃一驚,天造地設,一張空白的公文紙,可以由我寫一張路條。我以前從未想到逃走,這時左右無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來。解放軍顯然還未建立文書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沒有能力鑑別公文真偽,如果他們不放我,我也有辦法!圖章的印文是楷書簡體,草莽色彩鮮明,後來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廢棄篆書。
左眼越來越痛,「難友」朱少校幫助我,他說用食鹽水沖洗可以延緩病情。我到附近農家討鹽,一位太太說,她家的鹽用光了,還沒有補充,她讓我進廚房察看,柴米油鹽一無所有,鍋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進另一農家,當家的太太說她可以給我一撮鹽,但是必須班長許可。我又到處去找班長。
討到了鹽,朱少校捲起袖子,客串護士。每一次我只能討到一撮鹽,好一個慈悲的班長,他天天帶我奔波找鹽,他走在前面,我在後面六英尺左右跟著,他沉默無聲,農家看他的臉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穫不是食鹽,我有機會看到「老解放區」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沒有房門。我沒看見男人。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打麥場邊怎麼沒有一群孩子嬉戲,沒有幾隻狗搖著尾巴團團轉,怎麼沒有老翁抽著旱菸袋聊天,怎麼也沒有大雞小雞覓食,也沒見高高堆起來的麥稈高粱稈。安靜,清靜,乾乾淨淨,一切投入戰爭,當初「不拿人民一針一線」,而今「人民不留一針一線」,這就是解放戰爭的魅力,這就是每一個班長的驕傲。
我在俘虜營的那段日子,外面發生了兩件大事,蔣介石總統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傅作義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們看不到報紙,兩件事都由班長口頭宣布,我還記得,蔣氏引退的消息夜晚傳到俘虜營,我們都已躺好,宿舍裡沒電燈,班長站在黑暗裡說,蔣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視事」。我了解《中華民國憲法》,其中提到總統「缺位」和總統「因故不能視事」,兩者有很大的區別,班長聲調平靜,用字精準,把「不能視事」重複了一次,表示強調,很有政治水準。也許是黑暗遮住了臉孔吧,大家竟鼓起掌來,那時大家在心理上忽然變成觀眾,歹戲拖棚,不如早點落幕,散場回家。
散場以後一定可以回家嗎?天曉得!資料顯示,內戰第一年,六十萬俘虜參軍,第二年,七十萬俘虜參軍。濟南十萬俘虜,或參軍,或勞動生產,一個不放。中共佔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硬仗已經打完,俘虜太多,無處消耗,索性由他們投奔國民黨,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又要防範他們,雙方必然產生矛盾,他們縱然抗拒洗腦,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成為活性的「病灶」。世事總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繫於大人物一念之間。必須說,中共這一著高明!國軍退守台灣,大陸失敗的教訓深刻難忘,萬事防諜當先,盡力布置一個無菌室,那千千萬萬「匪區來歸官兵」跟有潔癖的人吃一鍋飯,難免動輒得咎,軍政機構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額外消耗多少元氣。
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萬年曆顯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歲次己丑,牛年!我的生肖屬牛,我的本命年,而我命在旦夕。事後推想,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大約是為了留些「去思」,過年這天午餐加菜,質量豐富,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據說是團政委。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踩高蹺」,親切,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作中國的「國風」。他們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個解放年,鑼鼓喧天鬧得歡,我給大家來拜年。」先是縱隊繞行,然後橫隊排開,唱到最後一句,全體向我們鞠躬,我又覺得折煞。
團政委登台訓話,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記得牢。他的氣質複雜,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文質彬彬,威風凜凜,陰氣沉沉。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跟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黨人完全不同,後者比較陰沉。有人解釋,中共陰沉是由於俄共陰沉,俄共陰沉是由於氣候嚴寒。有人作另一種解釋,中共陰沉是因為他們捨身革命,生活在逮捕和屠殺的陰影之下,因而培養出特殊的氣質。還有一說,中共黨員長期浸潤在唯物辯證之中,而唯物辯證法是一種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