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一個島
| 作者 | 席慕蓉 |
|---|---|
| 出版社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給我一個島:寫《七里香》時的席慕蓉,是清澈的溪流,在年輕時涓涓地流著。那時我不認識她。等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奔忙在故鄉路上的席慕蓉了……她這時發現,自己的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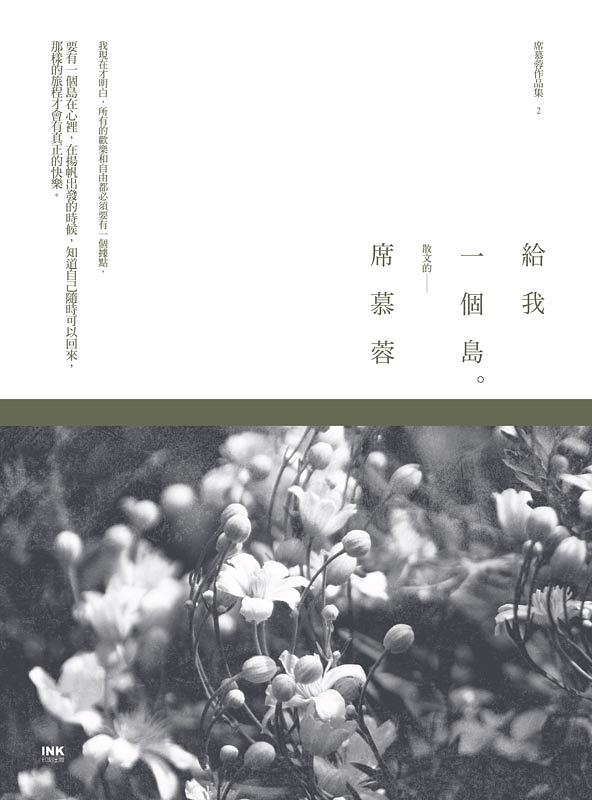
| 作者 | 席慕蓉 |
|---|---|
| 出版社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給我一個島:寫《七里香》時的席慕蓉,是清澈的溪流,在年輕時涓涓地流著。那時我不認識她。等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奔忙在故鄉路上的席慕蓉了……她這時發現,自己的生 |
內容簡介 寫《七里香》時的席慕蓉,是清澈的溪流,在年輕時涓涓地流著。那時我不認識她。等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奔忙在故鄉路上的席慕蓉了……她這時發現,自己的生命中居然還有一個浩淼的大海。我為她感到幸運,不是每個作家都可以遇到溪流,也遇到大海的。席慕蓉很誠摯,她可以擔當得起這樣的轉變,或者說命運。 ── 陳丹燕〈讀書記〉小島上泊岸之心的內在抒情集,草木花徑間的青春短歌。 我心中的島,聚焦於此──我現在才明白,所有的歡樂和自由都必須要有一個據點,要有一個島在心裡,在揚帆出發的時候,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來,那樣的旅程才會有真正的快樂。寫給幸福的,是愜適的常日寫生、感懷抒情與對原鄉的吶喊。滿室的琴聲,馬纓丹的鄉愁,那年夏天孤獨的樹,大漠草原裡的戈壁黃羊……那童年樹下的女孩,教室裡美的守護者,布魯塞爾的旅人,彎泉的父與女……是乘風破浪歡暢的的揚帆者抑或北方曠野裡狂奔的野馬,如今,都在心的小島上泊岸了。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席慕蓉祖籍蒙古,生於四川,童年在香港,成長於台灣。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曾在國內外舉辦多次個人畫展,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及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等。曾任台灣新竹師範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並為內蒙古大學、寧夏大學、南開大學、呼倫貝爾學院、呼和浩特民族學院等校的名譽教授,內蒙古博物院榮譽館員,以及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的榮譽公民。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五十餘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詩作被譯為多國文字、在蒙古國、美國及日本都有單行本出版發行。
產品目錄 新版序自序輯一 塊玉之緣暑假˙暑假「扎鬚客」俱樂部寫生圓夢昨日「?!」騙婚記粧台魔手舊事默契海洋虛幻的柵欄琴音徒然草輯二 短歌恍如一夢蝶翅透明的哀傷河流與歌泰姬瑪哈面貌荷田手記之1荷田手記之2嚴父貝殼荷葉十字路口馬櫻丹雞蛋花台灣百合爭奪梔子花唯美鏡裡與鏡外孤獨的樹此刻給我一個島輯三 關於創作我的抗議常玉美術課矛盾篇美術教育最後的一筆得失之間生命的訊息論席慕蓉詩與詩人婉轉綿長關山月畫幅之外的寫給生命蓮池輯四 夏夜的記憶傅先生傅太太夏夜的記憶街景畫展紅塵記憶模糊的願望可以依憑的記憶我們共有的疼痛自由的靈魂她的一生欲愛的神殿輯五 寶勒根道海彎泉胡馬依北風故居經卷大雁的歌父親教我的歌父與女仰望九纛此身黃羊、玫瑰、飛魚附錄 兩封朋友的信
| 書名 / | 給我一個島 |
|---|---|
| 作者 / | 席慕蓉 |
| 簡介 / | 給我一個島:寫《七里香》時的席慕蓉,是清澈的溪流,在年輕時涓涓地流著。那時我不認識她。等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奔忙在故鄉路上的席慕蓉了……她這時發現,自己的生 |
| 出版社 /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5933449 |
| ISBN10 / | 9865933446 |
| EAN / | 9789865933449 |
| 誠品26碼 / | 2680740418006 |
| 頁數 / | 296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7X23CM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海洋
在海邊, 給我說了一個故事。
他有一個朋友,曾經在遠洋輪船上做過事,同船有個希臘水手,長得像希臘雕像一樣完美,人很活潑又肯認真工作。只是,每到一處港口,就會早早地跑下船去,一直要到開航前的最後幾分鐘,才再急匆匆地跑回來。
朋友知道海上的寂寞,所以,當這個年輕的阿波羅向岸邊不斷揮手時,他也總會跟著水手的目光望向那碼頭上的女子。
走過了幾處港口之後,朋友萬分驚訝地發現在每一個碼頭上向這水手道別的,竟然都是同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原是法國一所學院的教授,在四十歲那年識得了這個希臘水手之後,就狂熱地愛上了他。於是,辭去了教職,緊跟著這條船的航線到每一個停泊的港口來等待她年輕的愛人。這樣追隨了兩年之後,他們終於結了婚,在法國南部定居了下來。
海浪在陽光下起伏,我說這不是很美嗎?
微笑地看著我,再繼續說下去:
「可是,兩年之後,他們又離婚了。水手重新回到船上,他說到最後夫妻終日默默相對,說不上一句話,還不如回來面對海洋。」
讓這兩個人分開的原因,我想,只有眼前這廣闊而又深沉的海洋才能完全明白的罷。
馬櫻丹
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學會了逃學。
要逼得我逃學的課不是國語也不是算術,而是勞作課。
勞作老師很兇,很黑很瘦的婦人,卻常在臉上塗了過多的脂粉。
勞作課要做紙工,把彩色紙裁成細條,再反覆編結起來,上下交叉,編成一塊小小的蓆子。有那手巧的同學,會配顏色,不同色的紙條編在一起,可以編出像彩虹一樣的顏色來。
而我什麼也不會,剪得不齊,摺得不整,也根本沒辦法把那些紙條編在一起,總是會有些掉出來,有些跑開去。滿頭大汗地坐在教室裡,老師逼急了,我就逃學。
逃得也不遠,就在學校旁邊的山坡上。山坡沒有大樹,只長滿了一叢又一叢的馬櫻丹,足夠遮掩我小小的身體。我一個人躺在花下面,陽光總是柔和的,無所事事的我摘著馬櫻丹,仔細觀察著那些像彩虹一樣的小花朵,我想,我對色彩的初級教育應該就是從那些個逃學的時刻開始的。
從香港到了台灣,滿山仍然是一叢又一叢的馬櫻丹。新竹師專後面的山上也有著一片和童年記憶裡非常相似的山坡,住在新竹的那幾年,我常帶著小小的慈兒爬上坡去。在柔和的陽光裡,我們母女倆採摘著花朵,聽著遠遠坡下傳來的學校裡的鐘聲,總會有一些模糊的光影從我心裡掠過。
而那樣的日子也逐漸遠去了,一切的記憶終於如光影般互相重疊起來。只有在我經過每一叢馬櫻丹的花樹前的時候,他們才重新帶著陽光,帶著鐘聲,帶著那彩虹一般的顏色向我微笑迎來。
論席慕蓉
從前,我總以為寫詩是件很個人的事,與他人並無關連。不過,現在的看法有些改變了。
自從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七月︽七里香︾出版之後,十幾年來,詩集的讀者從台灣逐漸延伸到大陸、到海外的華人世界,甚至那些被譯成蒙文的短詩,竟然一直傳到我的夢土之上傳到那遙遠的蒙古家鄉。我才發現,原來那終我一生也無法一一相認的廣大而又沉默的讀者群,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他們雖然安靜無聲,卻又像是波濤起伏的溫暖的海浪,綿綿不絕地傳送到我心中,讓我感受到了人間的真誠與善意。
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同時也遭遇到一些困擾。在最初,因為詩集如此暢銷,似乎前所未有,所以常會被寫詩的人當作一種現象來討論,這也是正常的。但是,其中有少數人的態度非常激烈,甚至發行小刊物對我作人身攻擊。對這些,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因為,我相信,時間會為我作證,替我說明一切的。
十幾年都已經過去了,時間果然一一為我作了證明:首先,我並沒有因為「暢銷」就去大量製造,從七十年到如今,我只出版了四本詩集。而在這段時間裡,許多位文壇前輩也表示了他們的意見,四本詩集中,有兩本分別得到了中興文藝獎章與金鼎獎,另外還有一本被推介為青年學子的課外讀物,在書單上,與多位作家的經典作品並列。最近,一位得到文學獎的年輕詩人在簡歷上說,他是先讀到我的詩,然後才開始去研讀名家的詩作,終於自己執筆寫起詩來的。這讓我覺得很榮幸。可見,有詩集讓年輕人對詩發生了興趣,對「文學」來說,並不是絕對無法容忍的壞現象了罷?
但是,昨天,朋友在電話裡告訴我,說是不久以前,有詩人在報紙上說:「他的一位寫詩的朋友宣稱,如果自己的詩集銷得像席慕蓉的一樣,他就要跳樓自殺!」卻讓我在哈哈大笑之後又覺得有極深的無奈,不得不在這裡說幾句話了。
文學中有多少層次!有多少不同的境界與面貌!為什麼卻總是繞著「銷售」這個題目打轉呢?
為什麼總喜歡說:這人是暢銷作家,那人是嚴肅作家,似乎認定只有這兩者而且兩者必然對立!其實,除了某些刻意經營的商業行為之外,書的銷路,根本是作者無法預知也不必去關心的。因此,我們可以批評一本暢銷書寫得不好,卻不一定可以指責這個作者在「迎合」大眾,因為,這可能會與實情不符!
反之亦然,不暢銷並不一定就等於創作態度嚴肅(而且,只有態度嚴肅並不等於寫出來的就會是偉大的作品罷?)。因此,在創作之前,先自封為「嚴肅作家」,實在是種很奇怪的態度。先給自己戴上了一頂高帽子再來提筆,豈不也是戴上了另外一種名利的枷鎖?
我自認是個簡單而真誠的人,寫了一些簡單而真誠的詩,原本無意與任何人爭辯。我只是覺得,如果有人努力要強調自己「不屑於暢銷」的清高,那麼,他內裡耿耿於懷,甚至連自己也無法察覺的,是否依然只是「銷售」這件「庸俗」的事呢?
給我一個島
你知道嗎?在那個夏天的海洋上,我多希望能夠像她一樣,擁有一個小小的島。
她的島實在很小,小到每一個住在島上的居民都不能不相識,不能不相知。
船本來已經離開碼頭,已經準備駛往另外一個更大的島去了,但是,忽然之間,船頭換了方向,又朝著小島駛了回去。
我問她為什麼?是出了什麼事嗎?
她微微一笑,指著把舵的少年說:
「不是啦,是他的哥哥有事找他。」
碼頭上並沒有什麼人,只看見遠遠的山路上,有輛摩托車正在往這邊駛來。天很藍,海很安靜,我們也都靜靜地坐在甲板上等待著,等待著那越來越近的馬達的聲音。
果然,是少年的哥哥要他去馬公帶一些修船的零件回來,樣品從碼頭上那雙粗壯黝黑的手臂中拋出,輕緩而又準確的,被船上另一雙同樣粗壯黝黑的手臂接住了。沒聽到有人說謝謝,也沒聽到什麼人說再見。只有船上的少年微微向岸上揮一下手,船就離開了。
回頭望過去,小島靜靜地躺在湛藍的海上,在幾叢毗鄰的房屋之間,孩子們正在遊戲追逐,用石砌成的屋牆聽說可以支持一千年,灰色的石塊在陽光下有一種令人覺得踏實和安穩的色澤。
再延伸過來,在島的這一邊,是連綿著的又細又白又溫暖的沙灘,長長的一直伸到海裡。天氣很晴朗,海水因而幾乎是透明的,從船邊望下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海底的珊瑚礁。
我問她:
「這是妳的家鄉嗎?」
「是我先生的,他是在這個島上出生的。」
她的回答裡有著一種不自覺的歡喜與自豪,讓我不得不羨慕起她來。
船在海上慢慢地走著,在廣闊的海洋上,船是多麼自由啊!從小到大,一直喜歡坐船,喜歡那一種乘風破浪的歡暢,不論在那裡,往前走的船永遠能給我一種歡樂和自由的感覺。但是,我現在才明白,所有的歡樂和自由都必須要有一個據點,要有一個島在心裡,在揚帆出發的時候,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來,那樣的旅程才會有真正的快樂。原來,自由的後面也要有一種不變的依戀,才能成為真正的自由。
我多希望,也能夠有一個小小的島,在這個島上,有我熟悉的朋友,有我親愛的家人。
我多希望,也能夠有一個島,在不變的海洋上等待著我。
不管我會在旅途上遭逢到什麼樣的挫折,不管我會在多麼遙遠的地方停留下來,不管我會在他鄉停留多久,半生甚至一生!只要我心裡知道,在不變的海洋上有一個不變的島在等待著我,那麼,這人世間一切的顛沛與艱難都是可以忍受並且可以克服的了。
你說,我的希望和要求算不算過分呢?
夏夜的記憶
那個夏天的夜晚,在海邊暗黑的公路上,風還真大,一陣陣地迎面直撲過來。小貨車沒有車蓬,站在車上的她很慶幸自己剛才的決定,堅持不坐在前座要站到後面來,這樣才能和這朵荷花靠得很近,才能用手扶著它的長長的梗莖,不致於被陣風所吹折。
小貨車的車主,住在信義路,多年來都幫她運畫,是老朋友了,才肯在接到她懇求的電話時,答應吃了晚飯就從台北過來,幫忙把這一缸荷花運到溫州街去。
荷花養在淡水鄉間她的工作室旁邊,原來有六缸,但是偏巧那幾天就只這缸有一朵蓓蕾。還好,花苞還算飽滿,離水也夠高,想是這一兩天內應該就會完全綻放了罷。
下午接到朋友的電話,說是住在溫州街大家都敬愛的老教授生病了,他院中原來有兩缸荷花,今年卻一個花苞也沒有,朋友想,若是她能把淡水的荷花運一缸過去放在窗前,讓久病的老教授隔著窗賞一賞荷,也許心情會舒暢些罷。
她馬上答應了。
其實她也知道這位老教授生病的消息,可是一直不敢去探望,因為自己並不是他的學生,怕會打擾。溫州街那幢宿舍從前倒是去過兩次,那兩缸荷花她也見過。第一次去就是因為有朋友知道她養荷,要她去給這兩缸荷放些肥料。
那時候是春天,老教授笑呵呵地站在玄關上,看她用棉紙包了些乾燥的有機肥往缸邊的軟泥塞下去,還問她為什麼這些荷不肯開花?她也不知道,只好猜測也許是陽光不夠充足的緣故。
溫州街的院子很小,房間更小,可是,她去的那兩次,總覺得屋裡屋外都有一種從容坦蕩的氣勢,像它的主人。那年,老教授身體健康,笑聲宏亮,朋友帶了好酒去,窗外的芭蕉有幾抹新綠一直明晃晃地要把陽光映照進屋子裡面來。坐在屋角,插不進什麼話,可是她覺得能夠聆聽就是一種幸福,很願意就這樣一直安安靜靜地坐下去。
而這天晚上,在撲打的強風裡用身子和雙臂護衛脆弱的花梗,她心中也只有一個念頭,希望到了台北的時候,把這缸荷安安靜靜地放到窗下就走,不要驚動了病人。
想不到,在駛近溫州街宿舍的時候,大門已經開啟,屋子裡燈光很亮,有人站在玄關上叫她進去,原來老教授已經坐在桌前在等候她了,還對她連聲道謝,要她坐下,說要寫幾個字送給她。
可是,這並不是她的原意。原來的她不過只是聽從了朋友的建議,把花送到。就只是這麼單純的一個心意而已,並不是要來求什麼報償的。
不過,在主人堅持要她坐一坐,等著他在畫冊的扉頁上題字之後,她也順從地坐下了。
因為,她忽然醒悟,在這樣一位長者的面前,她整個的人整個的心幾乎都是透明的,一切的解釋其實都沒有必要,他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恭敬地接過了那幾本書冊,再談了幾句話,她就站起來鞠躬告辭。在走出大門之前,又回頭向院子裡望了一眼,荷花缸已經好好地安放在窗下,燈光照在枝葉上,那朵花苞孤獨地挺立著,一點也沒受到損傷,可是,怎麼好像比剛才在車上時顯得小了許多?
會開嗎?
在回去的路上,她就開始擔起心來。溫州街的院子裡是沒有風,可是也沒有充足的日照,花會開嗎?
淡水的荷花倒是陸續地開了又謝了。在這段時間裡,聽說老教授又進了醫院,病情時好時壞,她很想知道,在入院之前,那窗下的荷究竟開了沒有?卻羞於啟齒。
天氣慢慢轉涼,十一月上旬,從報上看到長者辭世的消息之時,她正在淡水的畫室,窗外霧氣罩滿了山林,心中空落落的。隔了這生死的大幕,她想,無數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答了,更何況那小小一朵花的微不足道的訊息呢?於是,從此就把這個問題擱下了。
想不到,五年之後,她竟然收到了一份禮物,那是老教授的親友與弟子編成的一本紀念畫集。轉交給她的一位學者在電話上告訴她說:
「他們說你那天晚上送過去的花,後來開了,老師坐在窗戶前面也看見了。所以想把這本老師畫梅的畫冊送給你,當作紀念,也謝謝你。」
放下電話,心裡覺得很熱很緊,眼淚就禁不住地滾落了下來。那天晚上在風裡在暗黑的公路上緊靠著荷花荷葉的枝梗往前奔馳的感覺忽然都回來了,所有的細節都清楚再現,那層層荷葉在風裡翻飛時散發著的清香,那枝梗上細小的凸刺碰觸到裸露的腕臂時的刺癢,那從海上吹過來的陣風撲打到臉上和身上時的微暖又微涼,還有,當車子進入市區之後,在街角幾次遇到路人投來的訝異的眼光……
疑問終於得到解答,在那天晚上用了全心全意所護持過的那一朵荷,終於如她所願地綻放過了,而在窗前,她所敬愛的長者也看到了,原來,那就是她為老教授所做的唯一也是最後的一件事啊!
熱淚是為了那一個夏夜的記憶而流下來的。在熱淚中,她好像更看清楚了一些,在那個夏天的夜晚,她那樣全心全意地護持著一朵荷,除了是為著自己所敬愛的長者之外,恐怕還有那不自知的一部分 是面對死亡、面對那就在前方任何人都無法躲避那巨大而又黑暗的帷幕時所激起的反抗與不甘罷。
彎泉
人的名字,是一種歸屬與辨別的標識,土地的名字也是。
人的名字在一生裡通常不會更改,土地的名字原來也應該如此。
可是,在人類歷史上,為什麼每次在政權轉換了之後,總要先將土地重新命名?
我的家鄉在近代就換了許多不同的名字。父親年輕的時候在籍貫欄上填的是「察哈爾盟鑲黃旗」,我的戶口名簿上寫的是「察哈爾盟明安旗」,而如今,在家鄉的族人們卻又要稱這塊土地是「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了。
朋友說,我的遭遇還不算太悲慘,總比要被迫把自己美麗的故鄉改口叫做「仁愛鄉」、「忠孝鄉」要好一點,起碼還有一部分是來自自己文化的根源。
可是,如果要呼喚故鄉,如果在生命的路途上要回頭呼喚故鄉,有誰不渴望能夠找到一個古老、樸素,是由自己的祖先所命名,而又到如今還存活著的名字呢?
因為,只有這樣的名字,才能更貼近那塊土地,也只有這樣的名字,才能更貼近我們的心。
那怕只是座荒涼的山,那怕只是條淺淺的溪流,只要能夠逃過了被更改、被塗抹的命運,留下了一條可以與「昔日」相連接的線索,就是給亂世的子孫們最好的禮物了。
這份禮物,終於給我找到了。
三年之前,初次見到父親的那片草原,才知道她保有了一個古老的名字 「寶勒根道海」,用漢文的意思來說,就是「彎泉」。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最早來自那個年月,也不知道還能保留多久。我只知道,今天,這是父親與我以及我們的族人之間,唯一可以共享的愉悅和安慰。
彎泉,寶勒根道海。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依靠的線索,開始去尋找一個古老而又樸素的文化。每次翻閱那些歷經浩劫的斷簡殘篇,彷彿能夠隱隱地感覺到民族血脈的躍動,充滿了頑強的生命力。
正如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所說的一樣,每種文化都有著要強烈保持自身本色的願望,因為,唯有如此,她才不至於消失和滅亡。
幾十年都過去了,一直要到踏上草原之後,要到了今天,我才開始了解:原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那因為蒙古而流下的淚水並不完全是「衝動」,那在心中固執的渴望也並不完全是「狹隘」,所有的現象都牽連於一種內在的需求,是文化與種族加諸於每一個團體之上的,不得不如此的需求。
一切都不過只因為我是一個蒙古人罷了。認識了這樣的處境之後,心裡反而釋然了,重壓卸下,那蒙古文化裡明朗美麗的特質反而在處處向我顯現。在這裡試著把這些心情寫下來,就用草原的名字作為篇名,獻給遙遠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