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d Piper
| 作者 | Nevil Shute |
|---|---|
| 出版社 |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花衣吹笛手 (啾咪文庫本):「我不是勇者,只是個老人罷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翁稷安專文歷史導讀|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感性賞析★情報不明、糧食短缺、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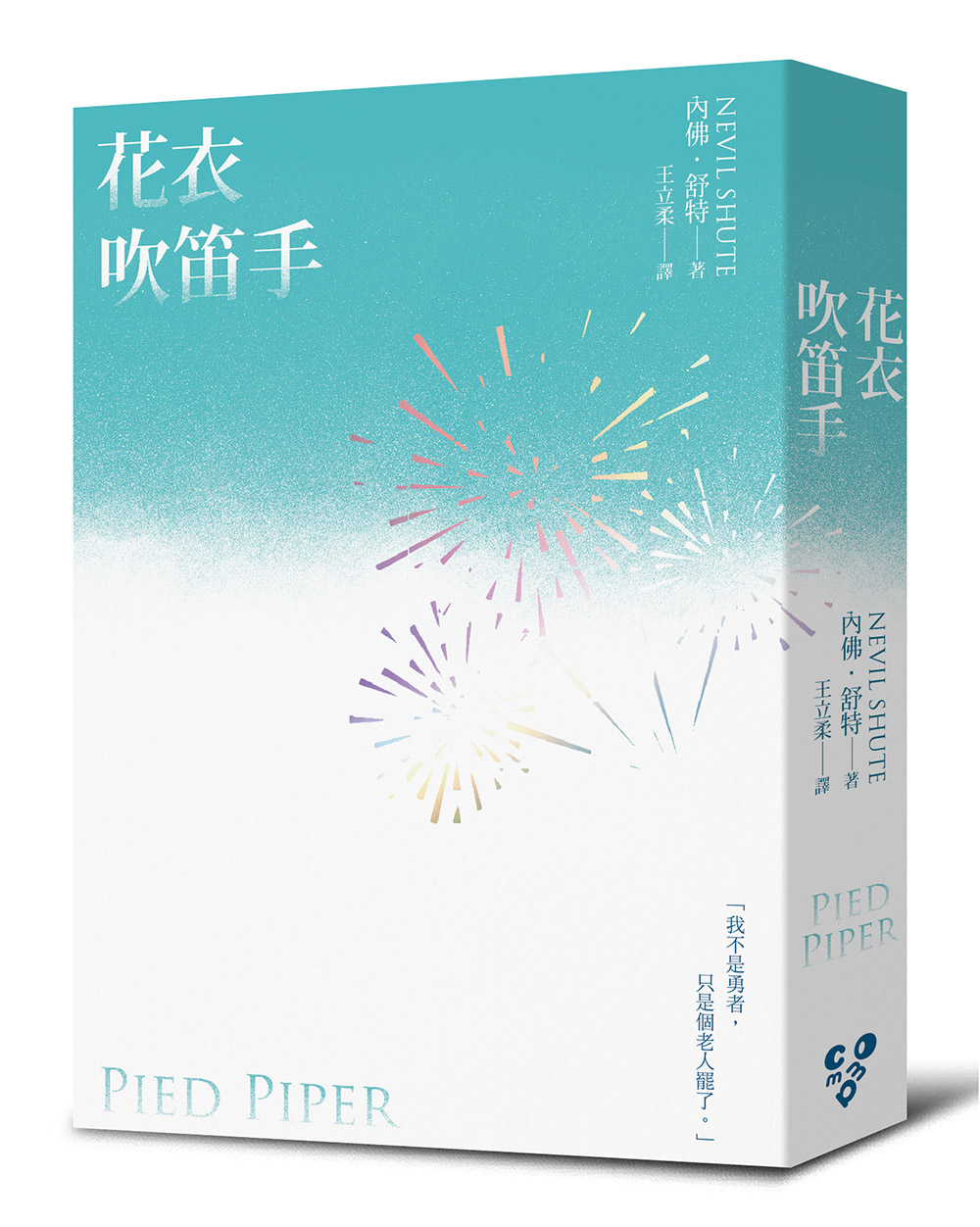
| 作者 | Nevil Shute |
|---|---|
| 出版社 |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花衣吹笛手 (啾咪文庫本):「我不是勇者,只是個老人罷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翁稷安專文歷史導讀|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感性賞析★情報不明、糧食短缺、累 |
內容簡介 「我不是勇者,只是個老人罷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翁稷安專文歷史導讀|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感性賞析★情報不明、糧食短缺、累得要死,還有⋯⋯愈來愈多的小鬼!★一位英國老紳士的療傷之旅,劇情急轉直下,變成橫越戰區的「特別行動」。★每一場相遇,在戰爭烽火之下,都是一次次人性與勇氣的考驗。「您要走的時候,有沒有可能帶我的孩子一起回英國?」「老弟啊……我快七十歲了。您若把孩子託給強壯一點的人,會比較保險。」「或許是吧,但其實也沒有別人了。」曾經,花衣吹笛手是歐陸社會的終極惡夢:當不祥笛聲響起,各家孩童便像是小動物般乖乖出門,一個個跟在花衣吹笛手後頭踏上離家之路,從此人間蒸發。原本諷刺人性本惡的殘酷傳說,透過《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作者內佛.舒特的機智詮釋,轉生成為在納粹陰影下見證人性光輝的英倫「帶子狼」傳奇!七十歲的英國紳士約翰.辛尼.哈爾德為了撫平內心傷痛,決定前往法國侏羅省山間釣魚度假,不料納粹侵略法國,讓回程旅途危機四伏。逃亡之際,他遇見一對夫婦,承諾將他們的兩個孩子帶回英國。誰知才剛上路,哈爾德竟遇到更多人託孤。這一個倉促組隊、成員莫名其妙愈來愈多的拼裝家庭,有機會逃離納粹占領的法國嗎?遭遇死亡威脅的哈爾德和孩子們能否成功脫困,抵達遠方的家?一段讀了讓人手心冒汗、深深為書中人物祈禱平安的戰地救娃大冒險!他四面受敵,懷著凝重的心情,帶著孩子往鎮上走去⋯⋯本書特色◆逗點與台大翻譯所合作經典新譯系列第二發!◆精準描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被遺忘的場景細節。◆有點嚴肅的老爺爺VS很難掌控的小小孩,讀了讓人嘴角上揚,內心超緊張!◆與《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齊名,讓人讀完發願好好活著的動人小說!
各界推薦 好評推薦★「在烏克蘭遭遇戰爭的當下,本書如今比以往更具時代意義⋯⋯同時也傳遞更積極的訊息,即便人到遲暮,依然能有所作為。」——蘇珊.埃爾金(Susan Elkin,美國評論家)★「文字簡潔、優雅又易讀,這是一個精彩絕倫的故事。」——強納森.柯(Jonathan Coe,英國作家)★「本書出自說故事大師之手,在平實的文字間累積出驚人的戲劇張力。」――《紐約時報》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內佛.舒特 (Nevil Shute, 1899-1960)「慧黠且充滿迷人丰采的小說家,值得萬眾矚目……簡言之,內佛.舒特是那種真正探觸到想像力與情感的小說家。」——《泰晤士報》生於倫敦,於1950年遷居澳洲墨爾本。年輕時因口吃而無法在英國皇家陸軍航空隊執行任務,轉而開啟了航空工程師的生涯,對英國的飛船與飛機工業貢獻良多。二戰期間加入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而後又在多種武器研發部協助開發祕密武器。英國戰時宣傳部曾派遣他於諾曼地登陸戰役中擔任通訊記者。具備軍事專業的舒特,擅長以細膩視角觀察描寫社會各階層的人物,筆調清晰、情節明快,創作題材涉及階級、種族與宗教,也包括愛情。受二戰期間兒童流離失所的悲劇所震懾,舒特化用了描述神祕人以魔笛誘拐兒童出走的德國傳說《哈梅爾的花衣魔笛手》,寫成小說《花衣吹笛手》,以年邁紳士不怕危難、解救戰爭兒童的故事,提醒當代讀者銘記愛與信念之重,在必要時刻做正確的決定,勇往直前。譯者簡介王立柔台大中文系、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畢業。曾任《新頭殼》、《風傳媒》及《報導者》文字記者。現為自由工作者,從事新聞、翻譯、口述影像撰稿及創意寫作。對許多事物都抱持濃厚的興趣,經常懷疑自己是「技多而不精」的梧鼠,期許有一天能變種為「技多且精」的珍禽異獸。合作請洽: [email protected]
產品目錄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譯後記:替別人做決定好難!文學翻譯的任性與節制/王立柔導讀:召喚善良的笛聲/翁稷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賞析:內佛.舒特的魔笛/廖志峰(允晨文化發行人)附錄:哈爾德旅程路線圖
| 書名 / | 花衣吹笛手 (啾咪文庫本) |
|---|---|
| 作者 / | Nevil Shute |
| 簡介 / | 花衣吹笛手 (啾咪文庫本):「我不是勇者,只是個老人罷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翁稷安專文歷史導讀|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感性賞析★情報不明、糧食短缺、累 |
| 出版社 / |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6267606230 |
| ISBN10 / | |
| EAN / | 9786267606230 |
| 誠品26碼 / | 2683003245005 |
| 頁數 / | 528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0.5x14.5x1.8cm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第一章
他的名字叫約翰.辛尼.哈爾德,是我在倫敦一間俱樂部的會員。有天晚上八點左右,我到俱樂部吃晚餐,因為開了一整天關於戰爭的會議而疲憊不堪。他恰好就在我的前頭進入俱樂部,看起來有七十歲了,個子很高,但略顯憔悴,走路不太穩,進門時還被腳踏墊絆了一下,踉蹌地向前跌,接待員趕緊上前扶住他的手肘。 他低頭打量那塊墊子,用雨傘戳了戳。「該死的東西,勾到我腳趾了⋯⋯謝謝你啊,彼得斯。我看我是老囉。」
接待員露出笑容,「好幾位先生最近都絆了一下,我前幾天才跟總管說呢。」
「哦,那就再跟他說一次,說到他處理好為止。總有一天你會發現我摔死在你腳邊。你可不希望發生這種事,對吧?」他略帶戲謔地微笑著。
「是啊,先生,我們當然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接待員說。
「我想也是。這可不是大家想在俱樂部看到的。我不想死在腳踏墊上,也不想死在廁所裡。彼得斯,你還記得麥克福森上校就是死在廁所嗎?」
「我記得,先生。那真是令人心痛啊。」
「是啊。」他沉默一下又說,「總之,那種死法我也不要。趕快叫總管把墊子弄好,就說是我要求的。」
「沒問題,先生。」
老人走開了。我一直都在後面等著,因為接待員那邊有我的信。他在窗口把信交給我,我匆匆翻了一下,隨口問道,「那是誰啊?」
他說,「先生,那位是哈爾德先生。」
「他好像很在意自己的下半生呢。」
接待員並沒有笑。「是的,先生。很多上了年紀的人講話都是那樣。哈爾德先生已經在我們的俱樂部很多年了。」
我變得恭謹了一點,「是嗎?我不記得在這兒見過他。」
「他前幾個月好像都在國外,先生。但這趟回來,他看起來老了很多,身體恐怕也不太行了。」
我轉身走開,「這場天殺的戰爭對他這把年紀的人來說很辛苦。」
「是的,先生。確實如此。」
我進入俱樂部,把防毒面罩掛在鉤子上,再把手槍皮套也解下來掛上去,帽子蓋在最外面。我晃過去查看自動收報機的最新消息,不好也不壞。我們的空軍仍在德國魯爾區大展神威,羅馬尼亞繼續與鄰國爭鬥不休。法國失守的這幾個月來,局勢一直都是如此。
我到餐廳享用晚餐時,哈爾德已經在那裡了,除了我們之外沒什麼人。他的侍者年紀和他差不多大,在哈爾德用餐時站在桌旁和他聊天。兩人的對話自然而然傳入我耳中。他們在談論板球,重溫一九二五年的對抗賽。
我獨自用餐,所以比哈爾德更早吃完。到櫃檯結帳時,我問收銀員,「那邊那位侍者叫什麼名字?」
「應該是傑克森?先生?」
「對,就是他。他在這裡多久了?」
「噢,非常久了,可以說一輩子都在這裡。我記得應該是一八九五年還是一八九六年來的。」
「那還真是久啊。」
他笑著找錢給我,「是啊,先生。但波爾森——他在這裡的時間更久。」
我去了樓上的吸菸室,駐足在擺滿期刊的桌前。當我漫不經心地翻閱一本會員名冊,發現哈爾德在一八九六年就加入俱樂部了。
這麼說起來,這對主僕檔一起廝混了一輩子。
我拿了幾本有插圖的週刊,點了咖啡來喝,接著穿越房間,走向俱樂部最舒適的那兩張並排椅子,準備閒散消磨一個鐘頭左右,再回自己的公寓。幾分鐘後,我身邊傳來腳步聲。哈爾德彎下修長的身軀坐進另一張椅子,一個男孩主動為他送上咖啡和白蘭地。
不久,他輕聲開口,「在這個國家連一杯像樣的咖啡都喝不到,實在是太奇怪了。就連這種俱樂部也泡不出好咖啡。」
我放下報紙。假如這位老先生想和我聊聊,我沒什麼意見。這一整天我都在那間舊式辦公室工作,雙眼盯著報告、撰寫交接紀錄。能摘下眼鏡休息一會兒感覺還不錯,我已經非常累了。
我摸索著口袋裡的眼鏡盒,「我有次聽一個賣咖啡的傢伙說,在我們這種氣候,磨好的咖啡粉保存不了。可能是溼度之類的關係。」
「磨好的咖啡粉不管在什麼氣候都會壞掉,」他的語氣相當篤定,「直接買磨好的咖啡粉當然泡不出好咖啡。應該要買豆子,要煮的時候再磨。但他們才不會這樣做呢。」
他又繼續談了一會兒諸如咖啡、菊苣咖啡之類的事。接著,話題自然而然轉向白蘭地。他很讚賞俱樂部的白蘭地,「我曾經擁有一家酒廠的股份。」他說,「很多年以前,在艾希特市。但上次大戰過後沒多久就賣掉了。」
我猜他大概是這間俱樂部的美酒委員會成員。我說,「經營那種生意一定很有趣。」
「噢,那當然。」他興致盎然地說,「好酒是一門有趣至極的學問——有趣至極,這我可以保證。」
在這個挑高深長的房間裡,基本上只有我們兩人。我們放鬆地窩在並排的椅中靜靜說著話,每一句話之間都停頓良久。在疲累的時候,這種淺嚐輕啜的對話是一種享受,就像品味陳年白蘭地。
我說,「我小時候常常去艾希特市。」老先生說,「我對艾希特市非常熟,在那裡住了四十年。」
「我叔叔在那附近一個叫史塔克羅斯的村莊有間房子。」然後我說出叔叔的名字。
他微笑,「我替他代理過,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替他代理過?」
「我的事務所替他代理過。我是弗爾傑姆斯與哈爾德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追憶著往事,說了許多叔叔、家人的事情,還有他的馬匹和佃戶。我們的對話變得愈來愈像獨白,偶爾會有一、兩個字從我嘴裡溜出,讓他能繼續講下去。透過他沉靜的嗓音,我看見的是一段永不復返的時光,是我印象中的童年光景。
我平靜地躺進椅子抽菸,疲憊漸漸消散。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運,能夠有人聊聊戰爭以外的事。大多數男人的心思都縈繞在這場戰爭或上一場戰爭,內心有股緊繃的衝動,使得對話一再回到戰爭上。但是戰爭似乎早已遠離這名身材精瘦的老人,他的興趣轉移到了比較和緩的主題。
很快地,我們聊起釣魚。他非常熱衷釣魚,我也有一點點經驗。大多海軍軍官都會帶著一根釣竿和一把槍上船。我有些下午會在岸邊釣魚,在世界各地許多地方都釣過,通常會因為用錯毛鉤而以失敗收場。不過他可是個中好手,足跡遍布英倫諸島及歐洲許多地區。在以前那個年代,鄉村律師的生活並不緊湊。
他談著釣魚和法國的事,讓我想起自己的一段經歷。「我在法國看過幾個傢伙用某種怪好玩的飛蠅釣法,」我說,「他們會拿一支巨大的竹竿,大約二十五英尺長,在一端綁線——不用捲線器,他們用的是溼毛鉤,然後在湍急的水裡來回拖行。」
他露出微笑。「沒錯,」他說,「他們就是這樣釣的。你是在哪裡看到這種釣法?」
「在熱克斯附近,」我說,「基本上是瑞士境內。」
他若有所思地露出微笑,「我對那裡很熟,真的很熟。」他說,「聖克洛德。你知道聖克洛德嗎?」
我搖搖頭,「我對侏羅省不熟悉。那是莫雷附近吧?對嗎?」
「是的,離莫雷不遠。」他好一會兒沒說話。我們就這樣一起在靜謐的房間裡休息。不久後,他說,「我今年夏天想去河邊,就想試試用溼毛鉤釣魚。應該滿好玩的。你要曉得魚群會去哪裡覓食,可不只是拿毛鉤到處亂碰這麼簡單,要放對地方才行,就像放乾毛鉤一樣謹慎。」
「要有策略。」我說。
「說得好。策略其實都一樣的。」
對話又出現一陣頗為自在的停頓。沒隔多久,我說,「只是恐怕要再過一段時間才能去那裡釣魚了。」到頭來,竟然是我開啟了戰爭的話題,避而不談還真難。
他說,「是啊,真可惜。之前,我在那裡的河水變得適合釣魚前就必須先走了。那裡在五月底以前都沒什麼魚可以釣,河水很混濁,水位也太滿——因為融雪嘛,你也知道的。但到了八月又是枯水期,沒辦法釣,天氣也太熱。六月中是最適合的時節。」
我側過頭,「你今年去過那裡嗎?」因為他隨口提起的五月底,正是德軍從荷蘭和比利時大舉入侵法國,而英軍也正在進行敦克爾克大撤退的時候,法軍那時則被逼回巴黎和更遠的地區。五月底似乎不是老人家到法國中部釣魚的最佳時機。
他說,「我是四月去的,原本預計整個夏天都要待在那裡,後來卻得離開。」
我帶著些許笑意注視著他,「回家路上有沒有什麼狀況?」
「沒有,」他說,「還好。」
「我猜你有車吧?」
「沒有,」他說,「我沒車。我開車技術不太好,而且幾年前就不得不放棄,視力不行了。」
「那你是什麼時候離開侏羅省?」我問。
他想了一會兒。「六月十一日,」他最終開口說,「應該就是那天。」
我困惑地皺起眉頭,「鐵路的狀況還好嗎?」因為工作使然,我聽了不少那幾週法國的情況。
他笑了笑,若有所思地說。「狀況不太好。」
「那你是怎麼離開那裡的?」
他說,「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
就在他說話的當下,外頭傳來一連串規律的轟隆聲,似乎在一英里外有四顆炸彈接連落下。這棟堅固的建築物稍微晃了晃,地板和窗戶都嘎吱作響。我們緊繃不動地等待。接著,警笛的呼嘯聲此起彼落,也聽見尖銳的砲火聲從公園傳來。敵人再次發動攻擊。
「該死,」我咒罵著,「現在怎麼辦?」
老先生頗有耐心地微笑,「我要留在原地。」
這麼做有其道理。雖然為了貪圖舒適而逞強是愚蠢之舉,但我們頭上還有三層堅固的樓層。當然,我們也討論了一番,並研究起天花板是否能支撐屋頂的重量。幾經思考,我們不覺得有必要離開座位。
年輕的侍者來了,帶了支手電筒和一頂鋼盔。
他說,「先生,防空洞在地下室,從貯藏室的門就能過去。」
爾德問,「我們一定要去嗎?」
「如果您願意。」
我問,「安德魯斯,你要下去嗎?」
「不,先生。我必須待命,以免來了燃燒彈之類的。」
「嗯,」我說,「去做你該做的事吧。等你有了空檔,再給我一杯瑪薩拉酒,但你先忙你的要緊。」
哈爾德說,「聽起來不錯,我也要一杯瑪薩拉——沒有燃燒彈的時候再給我,我會在這裡等。」
「沒問題,先生。」
他走掉後,我們再次放鬆下來。差不多晚上十點半了。侍者關掉所有燈光,只留下我們頭部後方的閱讀燈。我們坐在一汪柔和的黃色光暈中,整個房間偌大而陰暗。倫敦這種時候本來就沒什麼交通噪音,外頭幾乎無聲無息。好一段距離外傳來尖銳的警哨聲,有輛車飛馳而過。沒有多久,寂靜再次籠罩了長長的帕摩爾街,只是遠處仍有砲火聲。
哈爾德問我,「你覺得我們得在這裡坐多久?」
「直到空襲結束吧,上一波持續了四小時。」我頓了頓,「有沒有人會擔心你的安危?」
他回答得頗為迅速,「噢,沒有。我自己一個人住,你知道的,就在俱樂部的住所。」
我點點頭,「我太太知道我在這兒。我剛剛在想要不要打給她,但空襲期間實在不該占用電話線。」
「他們也是這樣宣導。」他說。
沒過多久,安德魯斯為我們送來瑪薩拉酒。他離開後,哈爾德舉杯對著光線端詳,接著評論道,「嗯,這種度過空襲的方法還不賴。」
我露出微笑,「這倒是真的。」然後我轉過頭,「你說這一切剛開始時你人在法國,你在那裡遇到很多次空襲嗎?」
他放下幾乎還沒動的酒,「不是真正的空襲。路上有幾波轟炸和機槍掃射,但不算太嚴重。」
他如此輕描淡寫,我過了一會兒才意會過來。儘管這麼說有些冒昧,我還是開口,「為了一段恬靜的釣魚假期就在今年四月跑去法國,似乎有點太樂觀了。」
「嗯,大概是吧。」他沉吟著說,「但我想去。」
最佳賣點 : 與《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齊名,讓人讀完發願好好活著的動人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