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力與限界: 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 作者 | 黃道炫 |
|---|---|
| 出版社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張力與限界: 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蘇維埃革命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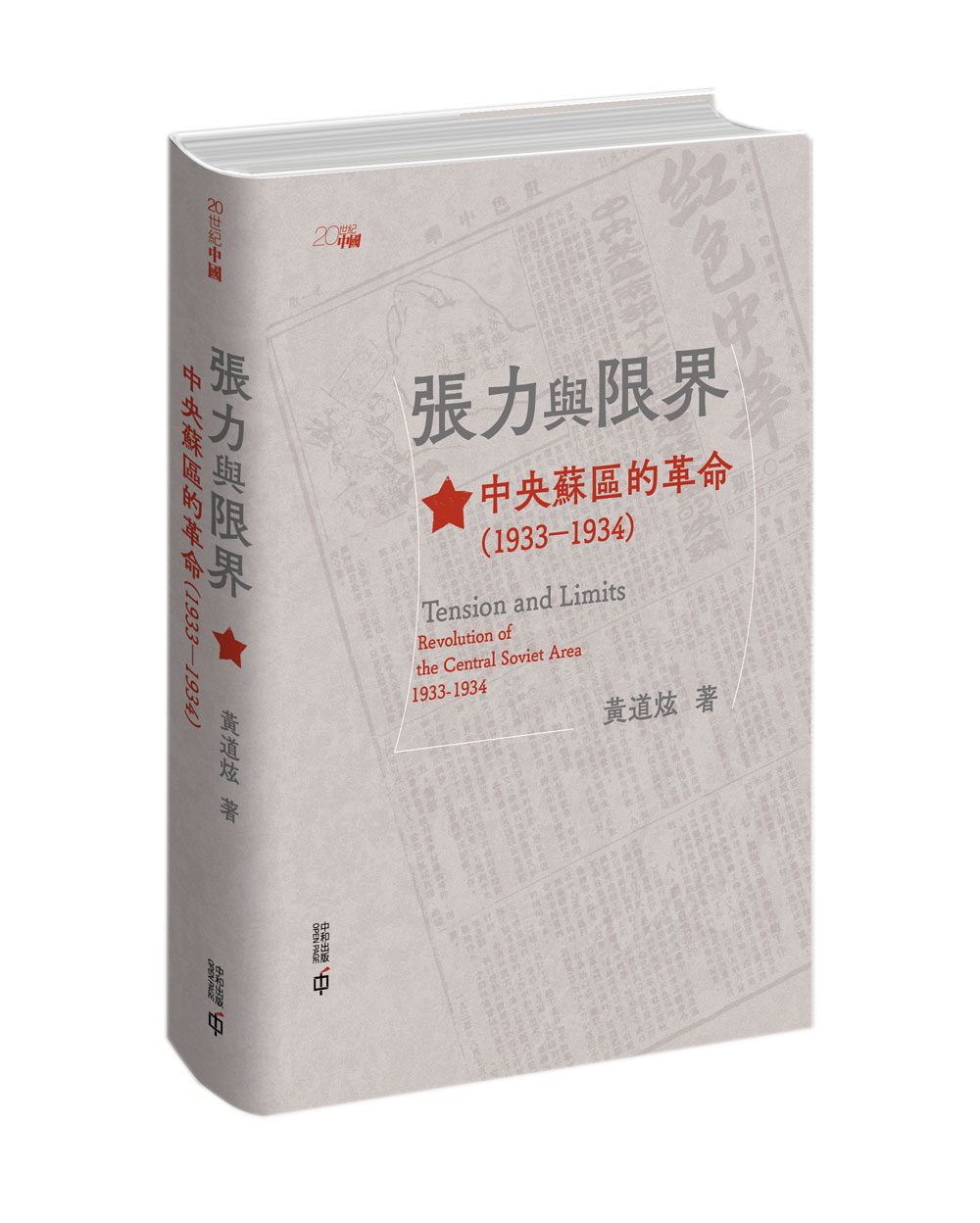
| 作者 | 黃道炫 |
|---|---|
| 出版社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張力與限界: 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蘇維埃革命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 |
內容簡介 蘇維埃革命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過對蘇區的獨立控制,顯現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動員能力和控制藝術。 ——黃道炫 中央蘇區史,在中共黨史中是一段「別樣的經歷」。1927年國共分裂,中國共產黨憑藉其真誠的信仰、嚴密的組織、強大的動員,僅僅數年後幾十萬人的中共武裝即矗然挺立。不過,再強的張力也有限界,到1930年代中期,諸多不利因素共同擠迫着中國革命,中央蘇區遭遇嚴重挫折。本書循着中共在中央蘇區成長、壯大以及遭遇挫折的複雜軌跡從中央蘇區的煉成、燃燒的革命、消耗戰中的資源陷阱、內外擠迫下的社會政治困境、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等內容展開講述,展現了1933—1934年前後中央蘇區的革命與建設。 中國革命是一個持續推進的過程,每一代革命者都付出了犧牲。革命,將在撤離中央蘇區的路途上,重新出發。
作者介紹 黃道炫研究員。1966年生於江西贛州。1986年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黨史。1989年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華民國史。出版、發表《蔣家王朝1・民國興衰》《洗臉⸺1946~1948年農村土改中的幹部整改》等專著、論文。
產品目錄 目 錄 引子 歷史的彈性 001一 中央蘇區的煉成 0071.中央蘇區的成長 0072.新形勢與新任務 0193.從毛澤東眼中走進蘇區 0294.國共較量中的地緣政治 095二 燃燒的革命 1101.中央蘇區的黨 1102.中央蘇區的政權 1303.宣傳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 1554.社會革命的宣傳與實踐 1655.婦女:地位上升最快群體 1796.群眾:組織與改造 1967.紅軍:堡壘的堅強核心 209三 第五次「圍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 2191.國民黨軍的作戰準備和作戰方針 2192.國民黨軍作戰基礎的增進 2333.國民黨軍的作戰部署 2394.「七分政治」的具體實施 243四 第五次反「圍剿」:中共絕境求生 2671.中共的反「圍剿」準備和作戰方針 2672.「短促突擊」戰術 2823.紅軍的正規化建設和防禦原則 294五 消耗戰中的資源陷阱 3031.結構性的限制—中央蘇區的人力與物力 3032.經濟力的挖掘 3273.財政緊張下的民眾負擔 3454.查田運動:理念、策略與現實 358六 內外擠迫下的社會政治困境 3751.肅反問題 3752.工作作風問題的滋生 3883.群眾逃跑 3954.擴紅與開小差 4035.「赤白對立」 416七 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 4321.運動與攻堅 4322.福建事變爆發與國共的應對 4633.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爭奪 5004.紅軍戰略轉移的準備 5375.紅軍實施轉移 565結語 革命的張力 589附 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經過要圖·廣昌戰役 592後記 593
| 書名 / | 張力與限界: 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
|---|---|
| 作者 / | 黃道炫 |
| 簡介 / | 張力與限界: 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蘇維埃革命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 |
| 出版社 /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88869558 |
| ISBN10 / | |
| EAN / | 9789888869558 |
| 誠品26碼 / | 2682903170004 |
| 頁數 / | 600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3*15.2*4.2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內文
(試讀頁) 1933年秋國共的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開始時,位於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正處於全盛時期。雖然在此之前長江流域與中央蘇區可以形成掎角之勢的幾個大的蘇區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經相繼被國民黨軍佔領,但當時仍然不會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後的秋天,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蘇維埃區域就會在國民黨軍強大壓力下,隨着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而易手。失敗的結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長途跋涉之路,尋找繼續生存、發展的機會,突圍中的艱難也導致了中共在奪取政權前最重要的一次領導層變換。同樣讓人很難預想到的是,經歷了如此慘痛的挫折,在對手看起來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陝北站住腳跟;而且這次失敗實際上就是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前最後的一次戰略性失敗,從此中共的革命奪取政權之路大有直濟滄海之勢。
失敗總不是件讓人愉快的事,與中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進程的描述相比,對於中共歷史上這樣一次重要的失敗經歷,具體的研究和闡述不是很多,有許多問題我們尚不能得其詳,簡單的原則論述和具體的歷史運行脈絡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而當我們重複當年更多的是基於政治考慮的結論,以「左」的錯誤為這次失敗定性時,往往忽視了其中包含的歷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後面,被斷送的可能是一個個正在具體影響着社會歷史的細節,歷史離開了細節,總讓人想到博物館那一具具人體骨骼,的確,那是人,但那真的還是人嗎?
其實,翻開中共壯麗歷史的長卷,在欣賞波瀾壯闊的勝利畫面之餘,偶爾體味一下這一段別樣的經歷,也許可以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如果考慮到成敗、禍福之變,誰又能說,這樣的失敗就完全沒有意義呢?!就整個蘇維埃運動而言,後人(雖然是外國人)曾有過中肯的評斷:「儘管蘇維埃運動遭到失敗,但是政治、軍事和社會經濟活動的經驗以及經受過組織和動員蘇區居民的各種方式的嘗試和失敗的考驗,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東方各國共產黨中唯一擁有實際上執政黨經驗的黨,擁有絕無僅有的農村工作經驗以及軍政骨幹的黨。這(加上其他條件)也成為抗日戰爭年代裏黨員人數和武裝力量較快增長和發展的基礎。」 這樣的說法放到第五次反「圍剿」的這一時段中,也並非就沒有針對性。蘇維埃運動是中共革命過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階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從不可能到可能的創造奇跡的過程,因此所謂的超越階段之類的說法更多只具有邏輯上的意義。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的思想和邏輯基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個中央政權,通過對蘇區的獨立控制,顯現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動員能力和控制藝術。事實上,雖然具體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此後續有調整,但中共革命的幾個重要原則諸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土地革命、社會再造等,在這一時期已經牢固確立,由蘇維埃革命開始,中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革命建國的道路。
蘇維埃革命高歌猛進的初期階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1927年國共分裂時,中共幾乎是白手起家開始武裝反抗,僅僅數年後幾十萬人的武裝即矗然挺立,締造出國共合作共同北伐後的又一個傳奇。中共在這其中表現出的讓人感覺無窮無盡的能量,不僅當年的對手為之震驚,即連多年後的覽史者,也很難不為之傾倒。不過,神話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暫時畫下了一個逗號,再強的張力也有自己的極限,中共在多種境遇下實現的超常發展,到這時,似乎終於到了該停歇一下的時候了。從歷史的大勢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領導固然不能辭其咎,但這些被歷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輕人,其實本身也是歷史的祭品。無論和共產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後人相比,他們改變了的或者可以改變的東西實屬有限,在滾滾的歷史大潮面前,他們難以擔當引領潮流的重任,更多時候乃是隨波逐流。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的航向。後人從他們身上看到的許多問題,既不一定是他們的造作,也不一定為他們所獨有。對此,毛澤東曾在中共內部會議上中肯談道:
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
毛澤東的評判,主要是從中共內部着眼,而鄧小平則從國共相爭的大背景,透視過當年「圍剿」與反「圍剿」成敗得失的幕後玄機:
如果有同志參加過十年蘇維埃時期的內戰,就會懂得這一點。那時不管在中央蘇區,還是鄂豫皖蘇區或湘鄂西蘇區,都是處於敵人四面包圍中作戰。敵人的方針就是要扭在蘇區邊沿和蘇區裏面打,盡情地消耗我蘇區的人力、物力、財力,使我們陷於枯竭,即使取得軍事上若干勝利,也不能持久。
中共兩位超重量級人物的論斷,客觀、公正、獨具慧眼,為我們提供了歷史多樣性認識的範本。
如果不是過分執着於結果的話,面對1933-1934年蘇維埃革命的歷史進程,冷靜地想一想,中共在贛南、閩西這樣一個狹小地區內,依靠極為有限的人力、物質資源,在國民黨軍志在必得、幾傾全力的進攻下,竟然能夠堅持一年之久,最後又從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夠令人驚歎的。何況,無論是事後諸葛的我輩,還是當年那些參與創造歷史的人們,只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熱,對於此時國際國內背景下,紅軍在國民黨統治中心區江南的可能命運,應該都或多或少會有不那麼樂觀的預判。中共和紅軍的成長,如毛澤東當年論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着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和統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仔細排列一下當時各蘇區的名稱,諸如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湘鄂西、鄂豫陝、川陝等,就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所有這些蘇區都位於數省交界的邊區,都利用着南京政府控制軟弱的條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絕對不能低估。然而,這一切,到1930年代中期,已在悄悄發生着變化。隨着地方實力派挑戰的相繼被擊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斷強化,對全國的控制力逐漸加強,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顯弱化,迴旋空間被大大壓縮。當國民黨軍大軍壓境、全力擠迫、志在必得時,成長中的中共最好的命運大概也就只能是順利擺脫,韜光養晦,以求東山再起了。
這是一個中共成長壯大的時代,但遠不是中共掌握政權的時代,超常的能量,也無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蘇區的發展,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毛澤東、朱德發揮自己的天才劍走偏鋒(比如在軍事上的天才創造、對力量的精準把握)的結果,從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陝,或許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劍走偏鋒。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坐下來,平心靜氣,不抱成見,盡可能避開歷史進程中現實需要帶來的政治口水,更多通過當年的而不是後來的,描述性的而不是價值評判的歷史資料,回首這一段曾經不那麼願意直面的歷史。歷史展現雖然不會像文學作品那樣羅曼蒂克、激動人心,但卻可能更有益於後人了解歷史的本然進程,以從中汲取養分、獲得智慧。實際上,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思考,面對着他們自己的問題,別人很難越俎代庖,因此,作為一個以國共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為聚焦點的研究,本書或許承擔不起總結經驗的責任,也未必真的能夠提供若干教訓,更多的只是想呈現一種面對歷史的方式,即盡可能不在預設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對原初的過程。儘管,原初的歷史是如此複雜,複雜得也許會讓人感覺混亂,但光怪陸離既然提供給了世界,應該也就預備給了歷史。
平心而論,即便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們也未必能洞察秋毫,何況那已經永遠逝去的人和事,因此,原初的歷史和我們的認知之間,恐怕總是會存在距離,所謂歷史的彈性大概就是由此而來吧。在無限豐富的可能面前,歷史研究者沒有理由不謹慎和謙卑以對。當然,這絕不意味着放棄對歷史本真的探求,在不確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確定的唯一,是歷史研究者無法逃避的宿命,否則,我們因何而存?!
最佳賣點 : 填補黨史空白
聚焦於中央蘇區具有轉折意義的特定時刻
豐富珍貴史料
通過大量的史料真實還原了中國共産黨在蘇區革命時的場景
敘史客觀、通俗好讀
學術著作的深刻與豐厚,又有通俗閱讀的淋漓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