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微笑 (第4版)
| 作者 | 聖嚴法師 |
|---|---|
| 出版社 |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
| 商品描述 | 拈花微笑 (第4版):世尊拈花示眾,迦葉破顏微笑,盡虛空遍法界,皆在說最上大法。本書是以淺近的語文,表達常人都能看懂的佛法,由基礎的佛學常識,到專門的禪學思想,由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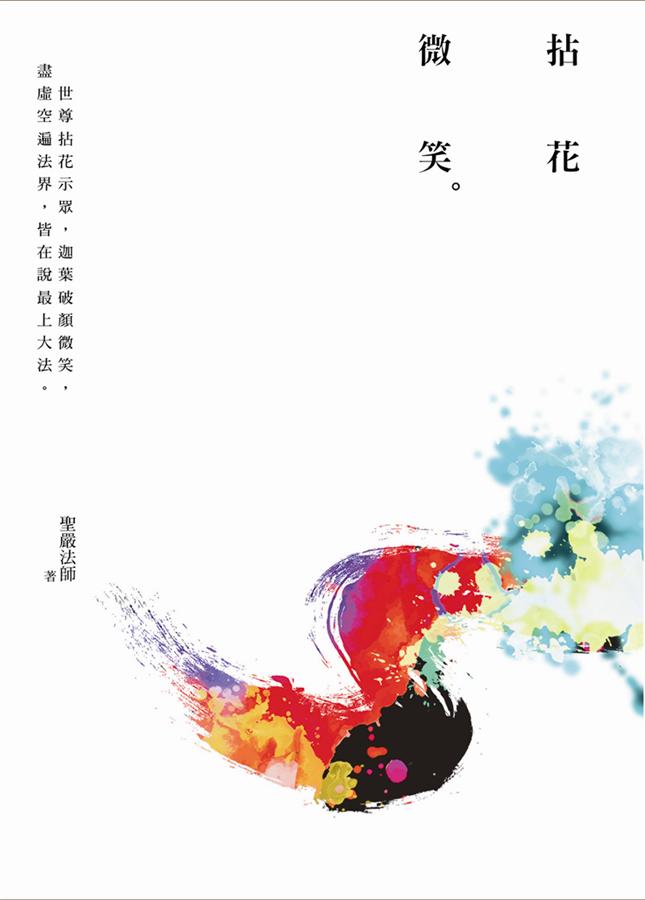
| 作者 | 聖嚴法師 |
|---|---|
| 出版社 |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
| 商品描述 | 拈花微笑 (第4版):世尊拈花示眾,迦葉破顏微笑,盡虛空遍法界,皆在說最上大法。本書是以淺近的語文,表達常人都能看懂的佛法,由基礎的佛學常識,到專門的禪學思想,由一 |
內容簡介 世尊拈花示眾,迦葉破顏微笑, 盡虛空遍法界,皆在說最上大法。 「本書是以淺近的語文,表達常人都能看懂的佛法,由基礎的佛學常識,到專門的禪學思想, 由一般生活中實用的禪學修養,到長期專修的禪修境界,做了層次化的介紹。 」 --聖嚴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聖嚴法師(1930-2009年)聖嚴法師1930年生於江蘇南通,1943年於狼山出家,後因戰亂投身軍旅,十年後再次披剃出家。曾於高雄美濃閉關六年,隨後留學日本,獲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75年應邀赴美弘法。1989年創建法鼓山,並於2005年開創繼起漢傳禪佛教的「中華禪法鼓宗」。聖嚴法師是一位思想家、作家暨國際知名禪師,曾獲臺灣《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著作豐富,中、英、日文著作達百餘種,先後獲頒中山文藝獎、中山學術獎、總統文化獎及社會各界的諸多獎項。聖嚴法師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主張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推動全面教育,相繼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文理學院、僧伽大學等院校,也以豐富的禪修經驗、正信的佛法觀念和方法指導東、西方人士修行。法師著重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傳佛法,陸續提出「心靈環保」、「四種環保」、「心五四運動」、「心六倫」等社會運動,並積極推展國際弘化工作,參與國際性會談,促進宗教交流,提倡建立全球性倫理,致力世界和平。其寬闊胸襟與國際化視野,深獲海內外肯定。
產品目錄 自序佛法無邊因緣果法大與小有與無新與舊生與死善與惡放下與擔起休閒與修行在家與出家疑心與疑情守一與守心活路與絕路最上一層樓──禪宗戒定慧的三個層次狹路相逢絕處逢生拈花微笑生死事大魔境降魔禪病療法禪的修行與體驗中國的維摩詰──龐居士附錄:禪與新心理療法
| 書名 / | 拈花微笑 (第4版) |
|---|---|
| 作者 / | 聖嚴法師 |
| 簡介 / | 拈花微笑 (第4版):世尊拈花示眾,迦葉破顏微笑,盡虛空遍法界,皆在說最上大法。本書是以淺近的語文,表達常人都能看懂的佛法,由基礎的佛學常識,到專門的禪學思想,由一 |
| 出版社 / |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
| ISBN13 / | 9789575987749 |
| ISBN10 / | 9575987748 |
| EAN / | 9789575987749 |
| 誠品26碼 / | 2681547101009 |
| 頁數 / | 320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自序 : 自序
本書《拈花微笑》,從其性質而言,實是《禪的生活》的續集。距《禪的生活》的問世,已整整兩個年頭,此期間,我沒寫成其他新書,可見不是多產。
因為我於一九八二年八月,應新加坡佛教總會之邀,去南洋訪問一個月,以氣候及水土不服,抱病回到臺灣,住院療養一個多月之後,體力始終未能恢復,加上臺灣及美國兩地的道場法務,和教育及文化工作的推動,每有力不從心之感。所以,在此以前,是主動地要講要寫,以期能使更多的人,獲得佛法的利益;在那之後,竟爾變為被動,由於農禪寺每週週日禪坐會,以及少數無法推辭的演講會必須要講,加上《人生》月刊的鐵定要稿,就在這樣的因緣之下,又完成了關於禪修的這一本書。
本來,一個專精於禪修生活的人,不宜多涉人事及文字;雖然古代的偉大禪師們,多有道場以接眾安眾,並且通達經教以方便化眾,而像我這樣以推動佛教教育文化與禪修方法並重的人,實在不是傳統禪師的型範。雖然像日本禪宗史上的偉人道元及白隱,是兩位以多病知名的禪師,但絕大多數的禪者,確能予人以銅筋鐵骨、體魄健壯、山亭嶽峙的印象。而我個人,只因得到一些修持佛法的受用,往往能夠處於身心勞累而不厭煩,事雖多而心自寧,氣雖虛而不浮躁,體雖弱而不苦惱的狀態;常懷淨願而少惹私欲,成事不為己,失敗無所損。偶爾仍有煩惱習性在心中現起,幸而我時以慚愧心自勵,故能瞬息消逝。每以聖賢的心行自期,恆以悠悠的凡夫自居。禪宗固為頓悟法門,我的立場則講求層次分明,用以自警,勿以凡濫聖,勿以染亂淨,不得倒因為果而稱無上究竟,這也是我繼續出書的原因之一。
本書共收二十四篇稿子,其中〈中國的維摩詰──龐居士〉曾發表於《獅子吼》月刊,〈禪的修行與體驗〉載於《菩提樹》雜誌,餘者均係在《人生》月刊刊載過的文章。其中正篇二十三篇,除了〈佛法無邊〉講於加拿大,〈因緣果法〉是為臺北「緣社」的婦女團體所講,〈禪的修行與體驗〉講於臺北市的中國佛教居士會,其餘都是由農禪寺禪坐會的講稿修訂而成,性質大致相近。多半都是貼切著現實生活而談禪法的修行,僅少數幾篇陳義比較深入,組織比較緊密,但也尚無一篇是讓人看不懂的文字。有人將同一篇文字,一讀再讀,均有新的領會,對我自己而言,也有同樣的作用。因我要求自己的言論,務必要有經義及祖語的依據,雖然使用自己的文字工具,卻不敢僅以個人的禪修經驗來妄論佛法,此乃唯恐落於「離經一字,即同魔說」的情況而不自知。故在重讀自己的講稿時,既有知誤修正的好處,也有溫故知新的利益。出書固為讀者,更是為了幫助自己。
另收有一篇附錄〈禪與新心理療法〉,是一位英國心理學教授克魯克博士(Dr. John Crook),在美國東初禪寺訪問我時的對話筆錄。
綜看本書,是以淺近的語文,表達常人都能看懂的佛法,由基礎的佛學常識,到專門的禪學思想,由一般生活中實用的禪學修養,到長期專修的禪修境界,做了層次化的介紹。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序於臺北北投農禪寺
內文 : 善與惡
世間只有壞事、惡事,沒有壞人、惡人。佛說:「眾生皆可成佛。」只要不做壞事惡事,便可成佛;世間只要有一人成佛,他所見到的世界,便全是如佛一樣的好人好事了。而一般的世人多數是凡夫,當然有善惡好壞之分;對聖人來說,善惡由心造,心淨國土淨,便無善惡區別的必要了。
《六祖壇經》中,我們看到衣缽傳承的故事。當然神秀書寫出「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偈子以後,受到了五祖弘忍大師的認可,並告諸大眾說:「好好誦持並依照這偈子修行,可免墮惡道,獲大利益。」神秀雖然沒有得到衣缽,然而,他是五祖當時的一位首席弟子,仍傳承了五祖,成為北方佛教的重鎮,很受武后則天之世朝廷及士庶的崇敬和禮遇。
當五祖看到惠能的偈子「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時,將衣缽密付惠能,並連夜送他過江到南方去。待五祖逕自回轉黃梅以後,一連數日沒有上堂,眾人疑惑,詢問之下,始知五祖的衣缽,已被人傳到南方去了,於是五祖座下所有的人都大為緊張。這時的神秀倒沒有採取行動,反而是以一位四品將軍惠明為首的數百人隨後追?,冀圖把衣缽從惠能手中奪回。兩個月後,當六祖惠能行至大庾嶺時,尾隨追來的人群中,還是惠明率先趕到。
惠明是先朝陳宣帝的後代,因此世代受到隋、唐冊封為將軍,只享有俸祿,不掌兵權。這是政治上懷柔政策,籠絡前朝的遺民,不使他們造反的手腕,所以,惠明也就冠有將軍的名號,人們呼之為陳將軍。出家後跟五祖修行,很受五祖弘忍大師的器重和大眾的擁護。只是他既沒有寫偈子,衣缽當然無份,聽說衣缽到南方去了,便集合數百人向嶺南直追,立意要把衣缽弄到手。
惠能眼看被追上了,便將衣缽放在一塊磐石上,躲進草叢裡。惠明欣喜若狂地急忙上前伸手去取,誰知衣缽就如同在石上生根一般,任憑他使盡所有的力氣,依然是紋風不動;這才猛然有所覺悟,立即跪下很虔誠地說:「行者,我是為法而來,不是為衣缽而來!」惠能見狀,就現身說:「法是可以用暴力搶得到的嗎?你連衣缽都難以奪走,何況法呢?!」惠明很惶恐地乞求開示,這時惠能就說:「你既然是為法而來,請先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如是沉默良久,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正在這時,哪個是惠明上座的本來面目?」
也就是說:在沒有生死以前的你是誰?平常吃飯、睡覺、走路、說話的你,都是假的,只是軀殼在動,心在胡思亂想。身體原是父母所生,生後不斷地新陳代謝;心是許多念頭的起滅不已。常人所知的身心,都非真正的我。要找本來面目,有一個辦法,就是不要生起善惡是非等的分別心,若能一切不思量,正在此時,看看你本來的面目在哪裡?本來面目,可以叫它「佛性」、「真如」、「法身」,這都是名詞而已。真正的本來面目,一定要自己看到了才算,否則只是隔靴搔癢罷了!惠明禪師聽到六祖說這幾句話以後,馬上開悟,而且是大悟。他為了避諱,不敢與惠能同用惠字為名,故改號道明。
為什麼同樣一句話,你們聽了不開悟呢?要知道,道明禪師出家已經很多年了,而且求法心非常懇切。從《六祖壇經》上看,他是追趕了兩個月,而且數百人當中,只他一人追上六祖,其他的均在中途退卻,光是這份追的耐力,就不容易了;何況他在黃梅,既有悟道之心,一定也是一位非常用功的人。
守一與守心
先講四祖道信禪師和五祖弘忍禪師之間的一段故事。
有一天,道信禪師在前往湖北省黃梅縣的途中,遇見一個小男孩,長得非常清秀奇拔,於是問他:「喂!你姓什麼?」小孩回答說:「假如有性的話,便不是常性。」老子《道德經》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小孩的意思是「性可性非常性」,也就是說,假如有性的話,這一定非常性。「常」是經常的意思,佛法則說:「實性無性。」這小孩居然答得出這種話,確實不簡單。
於是,道信禪師又問:「你究竟姓什麼?」小孩回答:「我是佛性。」道信禪師問他「姓」什麼?問的是家族的姓,小孩卻答非所問地說:「我是佛性。」那也等於是「道可道非常道,性可性非常性」。而什麼是「性」是「常」呢?只有「佛性」是常「性」,是永恆不變的空性。
道信禪師很訝異地又問:「你沒有自己的姓嗎?」小孩說:「性是空的。」後來,道信禪師就到小孩的家裡,向他父母乞這小孩出家,而小孩的父母也非常難得且很高興地將小孩送給道信禪師。於是,小孩也就成為道信禪師的弟子,法名弘忍。那時弘忍只有七歲,就跟隨了道信,一直到弘忍成年悟道為止。可見他們師徒倆,在一起生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而他倆的思想、禪法都很相似。
拈花微笑
人生在世,結交朋友能得知己,任用屬下終成心腹,彼此共事而有默契,如此,凡事皆能心領而神會的話,一定可以得心應手,無往不利。生死不渝地互相信賴,非語言文字所能溝通;血淚交融的體驗,刻骨銘心的感受,亦非語文所能形容。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唯有過來人,才能夠體會這些無法透過語文來表達的心境和感受。
做父母的比較容易知道孩子們的需要,孩子們卻不容易知道父母的苦心;聖賢可理解一般大眾的苦難,而凡夫卻不知道聖賢的胸襟是什麼。中國古代的聖君賢相,洞察民間疾苦,只要有一人遇到不幸,就覺得是他們自己沒有盡到責任。而儒家「親親而仁民」的理論根據便在於此,對於自己的骨肉、自己的族類,如手足同體,如唇齒相依,如枝葉同根,共榮辱,同命運。這都是由於高瞻遠矚,體驗深切,方能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整體感。「自古聖賢都寂寞」,正因為普通人對他們的心胸莫測高深,故以為寂寞;其實他們先天下人之憂而憂,後天下人之樂而樂,既與天下人同憂戚、共喜樂,怎麼會寂寞!
《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文殊菩薩問維摩詰居士:「你害了什麼病,怎麼會害病的?」
維摩詰說:「一切眾生,從癡生愛,故生了病。眾生既害了病,所以我也害病;如果一切眾生的病痊癒了,我的病也就好了。為什麼呢?因為菩薩是為了眾生而入生死,如果眾生得離病苦,菩薩自然無病。」
諸佛菩薩,能與眾生的心相通,眾生卻無法知道諸佛菩薩究竟對眾生做了些什麼?唯有有了相等體驗的人們,始能互相了解,而且只要一揚眉、一瞬目等的小動作為暗示,就代表了全部的感受,完成了彼此的溝通。這便稱為「以心印心」,心與心相應了;否則,彼此無法對流,僅是單向通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