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dforsaken Grapes: A Slightly Tipsy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 of Strange, Obscure, and Underappreciated Wine
| 作者 | Jason Wilson |
|---|---|
| 出版社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叛逆的葡萄: 踏上珍稀葡萄酒旅程:被葡萄酒教父羅伯‧派克稱之為「天殺的葡萄」!(GodforsakenGrapes)稀有的、原生的、即將滅絕、自然的、有機的葡萄品種這是一本葡萄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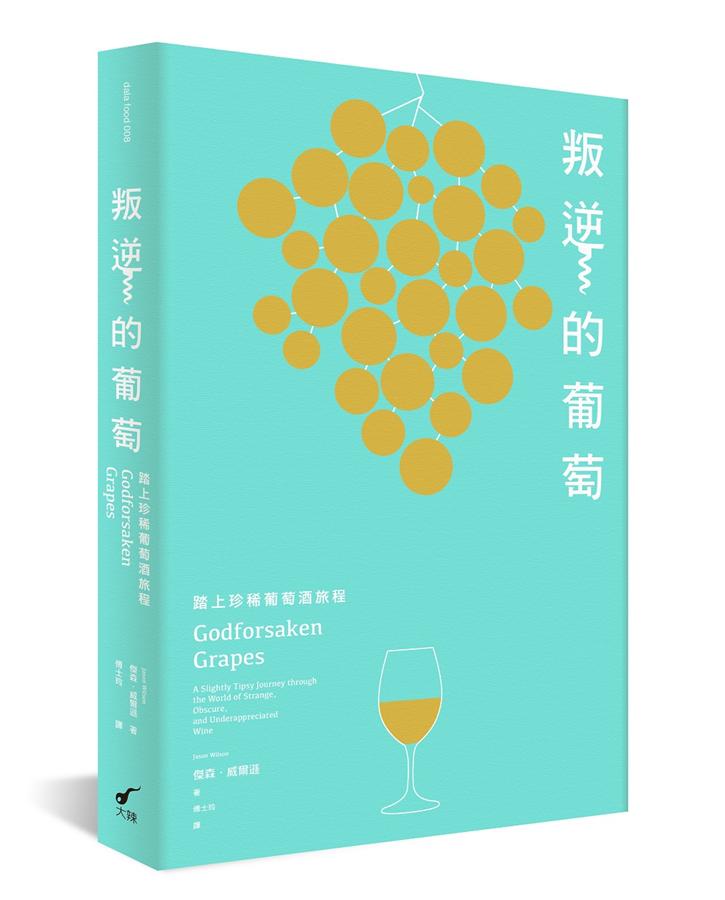
| 作者 | Jason Wilson |
|---|---|
| 出版社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叛逆的葡萄: 踏上珍稀葡萄酒旅程:被葡萄酒教父羅伯‧派克稱之為「天殺的葡萄」!(GodforsakenGrapes)稀有的、原生的、即將滅絕、自然的、有機的葡萄品種這是一本葡萄酒 |
內容簡介 被葡萄酒教父羅伯‧派克稱之為「天殺的葡萄」!(Godforsaken Grapes) 稀有的、原生的、即將滅絕、自然的、有機的葡萄品種 這是一本葡萄酒的酒徒冒險
各界推薦 【媒體好評】 「年度最佳葡萄酒書專書。」──紐約時報 「2018年十大最佳美食書。」──Smithsonian Magazine 「逸趣橫生、饒富啟發,研究深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旅行加上遊記,威爾遜以實現個人口味偏好,提供了一個充滿活力、高度個人化,更冒險的飲酒建議。」──Punch 「憑藉考古學家的狂熱決心,旅行者的好奇心,以及對其主題的百科全書知識,傑森威爾遜深入了解稀有葡萄酒的世界。原創,迷戀,並且非常有洞察力。喝下來!」──安德魯‧麥卡錫Andrew McCarthy(演員、導演、紐約時報暢銷書《最遙遠的歸途》作者) 【名人推薦】 楊子葆(葡萄酒作家、現任駐愛爾蘭代表) 韓良憶(美食旅遊作家) 黃麗如(《酒途的告白》作者、專欄作家) 陳上智Patrick (台灣侍酒師協會總編輯) 劉文雯Melinda(阿爾薩斯Domaine BOHN家釀酒莊民宿主人、旅遊作家) Célia(法國酒商、專欄作者、葡萄酒部落客) Jean-François Gallon & Yola(在布根地經營La Quarréenne有機自然酒專賣店、Jean曾任LV全球書店經理) 葡萄酒是一座迷宮」,善哉斯言,而我慶幸有作者擔任嚮導,引領著我走入那一座既真實卻又如夢一般的迷宮,即使始終徘徊其中,亦不覺懊悔。――韓良憶 威爾森的珍稀葡萄考察旅程,不只是喝在地的葡萄酒去感受自然酒的風味、看清楚葡萄園本來的面目,在一趟又一趟的酒途中,他也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人生,第一次在義大利寄宿家庭喝到的那口酒滋味、在歐洲漫長轉機的那杯瑞士葡萄酒、在歐洲爆發難民潮時的葡萄園風景――一個又一個與酒與人相遇的故事,勾勒出葡萄酒是生活裡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既重要又尋常,既獨特又能安撫人心,在不同的國度裡,葡萄酒照映出人生的模樣。――黃麗如 誰說葡萄酒一定要喝名牌?一定要迷信學院專家的話或分數?在酒鄉看著這本書,深深體會作者那股深愛葡萄酒的特有張力,作者非常了解葡萄酒農,他以那種不同於一般學院派的思維,給予了葡萄酒一把鑰匙,一把打開通向真正享受葡萄酒樂趣之門的鑰匙。――劉文雯Melinda 跟著作者用充滿好奇的心,和一張願意嚐鮮、渴求各種葡萄酒的嘴,探索那些完全沒聽過的產區和葡萄品種。精采幽默的文字,讓人一拾起,便欲罷不能!――Célia 世界上已知有近1,368種葡萄酒──從Altesse到Zierfandle──我們卻只用其中的20種葡萄來釀造80%的葡萄酒。譬如卡本內蘇維濃(Cabernet Sauvignon)是波爾多最知名的葡萄品種,但如今舉世掀起一股ABC情結──Anything but Cabernet,追求卡本內(Cabernet)以外的稀有葡萄酒。 作者也認同這股風潮,不再迷信高階酒,出於個人嗜好,一一探查這類葡萄酒史,尋找滋味獨樹一格的酒,以及它們的根源。他超越所謂的「貴族葡萄」,嚐遍瑞士、奧地利、葡萄牙、法國、義大利、美國及其他國家,形形色色晦澀難懂的葡萄酒,而這些統統都是被我們忽略低估的葡萄品種。在這個過程中,他研究了為什麼這些葡萄酒失寵(或者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取得它),進而調查出地緣政治、經濟和時尚如何改變我們的飲料。這是一部品酒家冒險旅行的紀實文學,也是作者寫給葡萄酒的一封有趣的情書。 本書基本上是造訪葡萄酒的旅行書,但沒有旅行書的按圖索驥形式,作者將基本的葡萄酒發展歷史與知識融在行文故事間,使得知識性的部分不艱澀,故事又有豐富的文化性,而且探討了多位知名品酒家與他們的方法學,對入門者相當具參考性。 作者說書寫的動機是為了解決自己的疑問和好奇,因此對需要閱讀葡萄酒入門書的讀者,是易懂易讀也有共鳴的,對稀有品種葡萄的故事有好奇的讀者即使已經擁有基礎的酒類知識,也不至於覺得本書太淺顯,可以說囊括了更多了目標讀者。其文筆是典型美國媒體專欄作家的風格,敘事清晰有條理,用字遣詞有個人風格,描寫生動有畫面。
作者介紹 傑森‧威爾遜烈酒評論家。為《華盛頓郵報》定期撰稿人 ,多年來其飲料專欄屢獲殊榮。作品出現在很多的報紙、雜誌和網路專欄裡,撰寫關於各式酒類、美食與旅遊,如《舊金山紀事報》、《費城每日新聞》、《費城雜誌》、Philly.com、《紐約時報》、NewYorker.com、 AFAR、 國家地理旅行者等。同時也開設葡萄酒與烈酒課程。在他的非酒生活中,是《The Best American Travel Writing》系列編輯。著有《Boozehound》以及《The Cider Revival》等書。網站:jasonwilson.comEmail:jason@jasonwilson.com傅士玲筆名王約、穀雨,臺灣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所、喬治梅森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畢業,媒體出版經歷近30年。曾任職漢聲雜誌、商業週刊出版公司、壹週刊,2012-2014華府作家協會會長。譯有《威尼斯共和國:稱霸地中海的海上商業帝國千年史》、《新歐亞大陸:面對消失的地理與國土疆界,世界該如何和平整合》、《偷書賊:建構統治者神話的文化洗劫與記憶消滅》、《紙的世界史》、《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時光的禮物》等。著有《蔣公獅子頭》等。文章散見於商業週刊、世界日報等。Email:emafu63@yahoo.com.tw
產品目錄 contents 獻詞 推薦序 中文版序 Part 1 天空之藤 Chapter 1 危機重重的葡萄 Chapter 2 族繁不及備載的頂級酒莊 Chapter 3 葡萄酒與街頭潮流 Chapter 4 阿爾卑斯山葡萄酒 Chapter 5 波歇可是地名還是一種葡萄? Chapter 6 當酒評失控時 Part 2 旅行在消失的葡萄酒帝國──昔日的奧匈帝國 Chapter 7 佶屈聱牙的日耳曼酒名 Chapter 8 老套的意義 Chapter 9 藍色法蘭克與茨威格博士 Chapter 10灰皮諾、藍莓燉飯和橘酒 Part 3 以稀有為賣點 Chapter 11等待孽子巴斯塔多 Chapter 12錢尼也喜歡的波特酒 Chapter 13來一杯獨角獸葡萄酒 Chapter 14往前看,往東看 Chapter 15你的鴿舍有多大 附錄 叛逆的葡萄地名詞典 101個值得追尋的品種 致謝
| 書名 / | 叛逆的葡萄: 踏上珍稀葡萄酒旅程 |
|---|---|
| 作者 / | Jason Wilson |
| 簡介 / | 叛逆的葡萄: 踏上珍稀葡萄酒旅程:被葡萄酒教父羅伯‧派克稱之為「天殺的葡萄」!(GodforsakenGrapes)稀有的、原生的、即將滅絕、自然的、有機的葡萄品種這是一本葡萄酒 |
| 出版社 /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9855754 |
| ISBN10 / | 986985575X |
| EAN / | 9789869855754 |
| 誠品26碼 / | 2681892130006 |
| 頁數 / | 280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最佳賣點 : 稀有葡萄品種的新浪潮
《紐約時報》年度最佳葡萄酒書專書
自序 : 【自序】
中文版序
去體驗吧!
品嚐稀有葡萄帶來的驚豔
葡萄酒太常被加上威望和品牌的偏見,被視為奢侈品,和所謂「對的」汽車、家具、精品包一樣。關於葡萄酒的話題,總脫離不了老生常談的那一批品牌地名──波爾多一級酒莊(First Growth Bordeaux)、特級園布根地(Premier Cru Burgundy)、納帕谷(Napa Valley)。而且,話題總不可避免地都強調相同的老葡萄品種:卡本內蘇維濃(Cabernet Sauvignon)、黑皮諾(Pinot Noir)、夏多內(Chardonnay)。
然而,在過去十年間,美國與歐洲的葡萄酒愛好者開始注意到葡萄酒單上,除了如雷貫耳的名字以外,多了不常見的名稱。在許多時髦餐廳和酒吧裡,細讀酒單會很可能會發現怪異、佶屈聱牙的葡萄品種,它們來自於很多即使時至近期,大家甚至不知道種植葡萄的地方。對來自鮮為人知地區的鮮為人知葡萄趨之若鶩,逐漸興起於二十一世紀,大家對智利的卡門內爾(Carménère)、西班牙的阿爾巴利諾(Albariño)、奧地利的綠菲特麗娜(Grüner Veltliner),大肆吹捧。即使深受歡迎的阿根廷馬爾貝克(Malbec),十二年前無人知曉。但時至今日,這些葡萄,還有許多和它們類似的葡萄,都是高級葡萄酒狂熱分子的心頭好。
多年來,葡萄酒產業一直都在朝向單一文化現象演變,本地葡萄品種遭到淘汰,以種植更能立刻獲利、更符合大眾市場需求的釀酒葡萄,諸如黑皮諾、夏多內或灰皮諾(Pinot Grigio)。我常感到震驚,很多人大啖豪華大餐,非常在意他們吃進身體裡的食物,可是開的葡萄酒要不是最便宜、充滿各種添加物的廉價酒,就是炒作過頭定價過高──兩者都是單調乏味的葡萄品種,隨處可得。
然而,在一些狹小的地帶,有一些英勇的葡萄農始終致力於堅持種植本地品種,而不是剷除它們。種植稀有品種葡萄的這類農人,往往也矢志採用有機種植、手工採摘和天然釀酒技術,不含大量添加劑,這或許並不奇怪。因為在這些有機物裡,可能隱藏著解決氣候變遷和疾病難題的線索。也或許,這些罕見卻有形能被觸摸的葡萄品種,在葡萄酒商店裡往往能帶來某些最好的價值。
葡萄酒總是和權力和金錢綁在一起。數百年來,一直都有守門人在決定哪些葡萄是「好的」,哪些是「壞的」。舉例來說,白高維斯(Gouais Blanc)是一款白葡萄,但自中世紀以來曾經在整個歐洲遭到不同的皇室律法禁止栽種。君王們認為它是一種太過淫亂、沒教養的葡萄,只能釀造劣酒──亦即中世紀法文的「gou」。諷刺的是,透過DNA檢測卻發現,白高維斯是八十餘種葡萄的母株,其中有好幾種的父株是黑皮諾,包括夏多內,說不定還有麗絲琳(Riesling)。
幾個世紀以來,一個又一個帝王接而連三做類似裁決,規定可以栽種哪些貴族葡萄,而其他的則加以禁止。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大家偏愛法蘭克王國的葡萄酒更甚於「來自匈人」(Heunisch)的產品;「來自匈人」是帶有貶意的字眼,用來形容所有來自東斯拉夫領土的東西。
西元1395年,布根地公爵(Duke of Burgundy)禁絕嘉美葡萄(Gamay,謂之是「非常壞且不忠貞的品種」),堅持只能栽種黑皮諾。數百年以來,哈布斯堡(Habsburg)的葡萄酒都是舉世最重要的產物,然而一旦帝王衰亡,這些葡萄酒很多竟被遺忘了將近百年之久。
今天,雖非帝王,但守門人要不是有權有勢的葡萄酒評論家,用100分為滿分的計算方式打分數;要不就是大都會裡時髦餐館裡,引人矚目無所不知的侍酒師。說什麼最貴的葡萄酒,或是顯赫產區名牌葡萄酒,或是贏得90分以上的酒才值得一嚐,我們有些人對這類觀點根本不以為然。
我們這些喜歡晦澀或「怪異」葡萄的人, 喜歡喝阿提斯(Altesse)和藍佛朗克(Blaufränkish)、內格芮特(Négrette)、白羽(Rkatsiteli)、茲瓦卡(Žilavka),還有數十種其他所謂的「天殺」
的葡萄(Godforsaken Grapes)。我們努力保護它們,原因就如同我們要拯救傳家寶番茄、蘋果和傳統牛隻,還有建立龐大的種子銀行一樣。前所未曾品嚐過的每一顆新葡萄,都讓我們有機會嘗試新口味。在這個日益全球化、同質化的世界,這不僅僅只是件虛榮的事。
嘗試不一樣的東西吧。試試怪異的東西。讓自己接觸你從未考慮過的滋味。品嚐能讓你暫停一瞬間,集中注意力去體驗的某些東西,並感受任何事物。希望我的葡萄酒探險之旅能對你有所啟發。
傑森.威爾遜
Jason Wilson
內文 : 【內文試閱】
Chapter 2
族繁不及備載的頂級酒莊
Château du Blah Blah Blah
我心知肚明,倘若要竭盡所能體驗多達一千三百六十八種葡萄品種,就必須拓展我的品酒視野,大膽擺脫我的南澤西風土條件一陣子。因此,數週後,我整裝再訪歐洲。
9月的早晨,正待出發,我和當年還在念小學的小犬威斯一起早餐,吃著新鮮的美國康科特(Concord)葡萄。我們是在靠近遺產酒莊的心情農場採的葡萄,只有8月至9月初才吃得到它們。嚐著愉快親手採摘的夏末新鮮康科特葡萄,完全不同於吃那些智利進口大量生產的無籽葡萄。
威斯想當學校裡五年級生的糾察隊長,那天他要發表演講爭取隊友投票支持他。我要他重寫講稿,因為他把隊長,還有負責任兩個詞拼錯了,而且有幾個地方他連自己都看不懂自己的手寫字。所以,他惱怒離開廚房的餐檯。
突然之間,正在重寫講稿的威斯抬起頭來,「酒莊會用這些葡萄釀酒嗎?」他問。對小犬而言,他的提問其來有自。他從很小的年紀就接觸葡萄酒,親眼看過為父的我在同樣這個餐檯上品酒,也與我同行造訪過西班牙、義大利與奧地利的葡萄園與酒莊。
「不會,」我說。「通常不是這種葡萄。這種葡萄是用來榨果汁或做果凍用的。」
他看似失望透了。一邊氣嘟嘟用橡皮擦擦掉另一個拼錯的詞「負責任」。「為什麼不會?」他問。
「嗯,」我說,「有些人會用這種葡萄釀酒。但是,這種康科特葡萄釀的酒通常真的很糟糕。」
「可是它們吃起還這麼甜這麼棒,」他說,「為什麼會做出糟糕的葡萄酒?」
我的腦海開始搜尋海量的資訊:康科特葡萄在1840年時被發現,它們生長在麻省的康科特河(Concord River)沿岸。……康科特是一種「滑皮」葡萄品種,意謂果皮很容易脫落, 使得壓榨困難。康科特葡萄通常酸度過高,以至於不可口,同時卻也糖分過低,難以轉換成釀酒所需要的酒精濃度。
當然,這些事對威斯來說都很難懂。所以我便說:「它們就是這樣,只能做出糟糕的酒。」
「嗯,」他說,「你有沒有想過,說不定只是因為大家還沒有找出用它們做出好酒的辦法?」他放下鉛筆。威斯說不定也能當警方訊問時的警官。
「你是哪種等級的侍酒師?」他問我。
「什麼?」我說,「你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的那部電影,演一些人努力想成為優秀侍酒師,」他說。
我知道他說的是《頂尖侍酒大師》(SOMM)──這部紀錄片突然使得葡萄酒服務生成為時髦差事,也驅使很多年輕人想成為認證的侍酒師。 威斯最近和我一起坐在沙發看這部片。
「你到底是什麼等級?」
「我不是侍酒師,」我說,「我沒有任何等級的證書。」
「噢。」他聳聳肩說道,然後回頭去寫他的講稿。我默默無語又吃了一把康科特葡萄。我的兒子在不知不覺中敏銳地觸及了一個敏感的課題。我在宣稱康科特葡萄釀酒品質低劣時,是權威的,甚至是威權的。 但我又算哪棵蔥,有資格對康科特葡萄酒,或任何以美洲葡萄後裔釀製的酒,或世上任何葡萄說東道西?
權威和履歷至上主義,在葡萄酒業界不斷甚囂塵上。葡萄酒充滿著糟透了的認證、教條、標示、會員制。我浸淫於這個世界──常常很笨拙──但沒有可掛上牆的裱框證書以資證明我是個專家。我也不是知名或有權勢的品酒作家,不像羅伯.派克(Robert Parker)那號人物,一直是全球最如雷貫耳也最具影響力的品酒家。我也不是「侍酒師大師公會」(Court of Master Sommeliers,簡稱CMS)出身,沒有那一枚徽章。而且我絕非財富過人足以成為蒐藏家,能在葡萄酒拍賣會上為傑出的年分佳釀一擲千金。
正當我終於開始能收費為葡萄酒撰稿的同時,我的滿腹知識全靠自己摸索而來,憑著我滿腔熱情,到處旅行品嚐負擔得起的酒──也常常去那些我負擔不起的地方。但這不是說,我腦中因此就沒有累積數千種葡萄酒的浩瀚經歷,沒有伴隨深度遊走眾多葡萄酒產區,也沒有拜訪許多釀酒人。然而這過程是缺少組織土法煉鋼的自學。我個人的口頭禪之一是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 裡的一句話:「豐富勝於滋味。」
然而,任何人哪怕只喝過一杯酒,都能接觸到這樣一個想法,那就是,葡萄酒是一道要辛苦攀爬的螺旋梯,梯子頂端是所謂的絕美佳釀(Serious Wine),諸如波爾多和布根地之輩。
記得我生平第一次在波爾多面對這道梯子時,那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才剛剛發表一般的品酒文章,多半時間寫的都是即將上市的義大利和西班牙產區的酒,而我決心要來一趟結結實實的波爾多朝聖之旅。在寫稿報導烈酒和雞尾酒六年多,也終於出了書之後,我便已開始認真留意葡萄酒這個課題。可是,我厭倦討論「桶陳年」(Barrel-aged)義大利經點調酒內格羅尼(Negroni),還有自製苦味,匠人梅茲卡爾(Mezcal),精雕細琢的冰塊之類的話題。我估摸著,自己的飲酒知識比較容易轉向葡萄酒。當時並不知曉自己錯得多離譜。
波爾多的酒莊如今仍以分類制度區分出等級,而分類制度是1855年應法皇拿破崙三世要求,為巴黎世界博覽會所制訂的。今天市面上威名遠播價格最高昂的「一級園」(Premier Cru)酒莊,和一百六十年前法國第二帝國期間的威望與高價,幾無二致。在那之前,波爾多一直都是名聞遐邇的葡萄酒區,在十七世紀的荷蘭黃金年代(Dutch Golden Age))時,外銷到荷蘭。在那之前,波爾多起碼自十二世紀亨利二世(Henry II)和阿基坦的埃莉諾(Eleanor of Aquitaine)皇室婚禮開始,就外銷到大不列顛。長話短說,也就是,波爾多始終離不開權勢和金錢。
當我由酒莊集團總經理盧森堡王子羅伯(Le Prince Robert de Luxembourg)作陪,侷促不安坐在紅顏容酒莊(Château La Mission Haut- Brion)客廳裡時,波爾多始終離不開權勢和金錢這一點令我深有所感。羅伯王子告訴我,重要的品酒家如羅伯・派克等人,上週才剛訪問此處。閒談間,我提及這是我第一次到波爾多,王子難以置信地大笑不已。「從沒來過波爾多?但你寫品酒文章?」
「嗯,噢⋯⋯是呀?!」我說,但立刻改弦易轍。「我想是因為我花了大部分時間旅遊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國其他地方?我不知道。義大利,我想,我的葡萄酒知識多半從那裡得來。」
「噢,」王子用一種高貴的皇室氣度說,「所以你是義大利葡萄酒專家?哈,很好,我們這裡有一位義大利葡萄酒專家!」初中時忘了穿短褲,只好在大庭廣眾下把運動褲脫掉穿著白色緊身小褲褲參加籃球賽,打那次起,這是頭一回感覺自己可笑至極。羅伯王子言下之意彷彿是:你到底是怎麼預約到跟我一起品酒的?
我在皇室試酒室環顧四周,這裡有沉甸甸的木製家具,某些應該是名人的半身肖像,還有重要品酒家們坐著搖杯、吐酒、大發議論各款價值上千美元葡萄酒的高腳椅。我決定轉移焦點切入一個或許不太禮貌的問題:「在美國,有很多葡萄酒品酒作家和侍酒師說,波爾多再也無足輕重了。你對那些人有何高見?」
「事實上,」羅伯王子說,「大家必須寫點什麼東西。而波爾多顯然舉足輕重,因為他們必須寫點波爾多的什麼。那不過是棒打出頭鳥症候群罷了。」 ……
「等等,」我說,「你不擔心年輕一輩不喝波爾多?它甚至不在他們的興趣名單內?你不怕,當這個世代終有一日負擔得起你的葡萄酒時,他們根本不在乎它?」
「是,年輕一輩喝酒人口喜歡新世界葡萄酒的單純,那種容易詮釋的葡萄酒,」他說,而我不確定我能否正確傳達出王子聲音中帶著多少輕蔑,似乎蔑視了整整一代年輕的葡萄酒飲用者,他們根本買不起他的葡萄酒。
「無論如何,」他說,「我有信心,大家會回到波爾多傑出葡萄酒的懷抱裡。對高端葡萄酒的需求從未像現在這麼多。」這句話或許沒錯,但市場對波爾多葡萄酒的需求,絕大部分是受到亞洲新近崛起的蒐藏家所帶動的。你大可合理假設,在中國和印度,品味最終也將會有所改變,一如1980年代以來數十年間美國的情況,當時美國人「發現」波爾多(透過羅伯.派克)。現在肯定有中國的羅伯.派克了?在不久的將來,身上刺青的時髦年輕侍酒師們,還會對波爾多產生興奮反應嗎?
我沒想問他這幾個問題,因為,很明顯的,王子對於我們的對話毫無興致。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向我道別,祝福我第一趟波爾多之旅愉快。「好好享用那些義大利葡萄酒。」他說,面帶微笑外加擠眉弄眼。
接著獨留我和公關試飲2011年的九支年分酒。這些酒如何?令人驚豔。無庸置疑。最優等的一軍(Flagship First Label)葡萄酒,複雜又濃郁且豐富,無異於當年我的葡萄酒知識曾經品嚐過的好酒。可是,價錢呢?紅顏容酒莊(Château Haut-Brion)通常牌價超過千元美金一瓶。我大概僅試飲了一盎司2011年分酒,可能比絕大多數我的好友與讀者們嚐過的都多。我的描述會不會刺激你想要一飲波爾多?我的意思是,我有個開法拉利的朋友,另一個曾經和維多利亞祕密內衣模特兒約會過,可是他們倆的經驗並不曾讓我也想試一試。
有什麼葡萄酒比波爾多更令人膽怯?即使我的一干朋友當中有些是高級葡萄酒愛用人士,但感覺上,有點像是校園霸凌事件中無人敢挺身而出。「我完完全全受到波爾多的恫嚇,」一位剛拿到初階侍酒師證書的知名美食作家怯懦坦承不諱。「我經過店裡那排貨架,全部都是波爾多酒瓶,看起一模一樣。同樣顏色,同樣的書法體文字,同樣的金葉子,同樣畫著可恨的城堡(Château),永遠都是什麼什麼堡之類的、巴拉巴拉酒莊之類、法國的什麼什麼堡,我哪知道從何著手?」
當我第一次跟另一位朋友提起波爾多的問題時,身為高級餐廳館經理的友人十分震怒。「呃,我幹嘛要在意波爾多?」他幾乎吼了出來、 「誰買得起?他們幹嘛不全部都賣給中國億萬富翁?」 ……
在波爾多之旅前,業界聖經《葡萄酒觀察家》(Wine Spectator)的2012年封面刊登的是波爾多2009年分酒,該雜誌譽之為「經典」。封面文案宣稱「價值不菲二軍酒」,底下圖片──想來是為了彰顯這個所謂的「價值不菲」──是拉圖二軍酒(Les Forts de Latour)、拉菲堡珍寶 (Carruades de Lafite,拉菲堡副牌),兩者皆有著穩重的波爾多莊園的標準筆墨插圖。酒標一旁,編輯在封面右方羅列了價錢和品酒家的給分:拉圖堡93分,345美元;拉菲堡珍寶92分,400美元。
現在,我很確定這不是在嘲諷,因為我懷疑世上還有哪個雜誌比《葡萄酒觀察家》更正經的;因此,我假設編輯真心相信,花400美元買一瓶葡萄酒代表著「價值不菲」。或許這些編輯會說,「價值」一詞是相對的。最傑出的葡萄酒,特等「一軍」,也出現在雜誌封面上,作為一旁二軍的比對之用──拉圖酒莊(Château Latour)99分,1,600美元;拉菲.羅斯柴爾德酒莊(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98分,1,800美元。然而很清楚的是,以400美元,你買不到酒廠最棒的葡萄汁。400元,只能買到雜誌自己給分的一瓶A–(減)的葡萄酒。
波爾多之旅讓我獲益良多。畢竟那裡是擁有五十四個名號、八千五百個廠商的廣大葡萄酒區,釀製各種價錢的產品,有半數以上每瓶酒的售價低於7美元。可是,令人憂慮的是,太過強調特等一軍葡萄酒了。而且對我所遇到的一些年輕釀酒師而言,有點讓人憂心忡忡。……
自從一親波爾多芳澤之後,我已經讀到相當多品酒作家自白,說世上的模範葡萄酒其實再也不怎麼令他們驚豔。數年前,《葡萄酒觀察家》的頂尖專欄作家馬特.克萊默(Matt Kramer)首次發難在文章裡公開自白。「今日,更甚於以往,我發現自己迫切渴望充滿驚喜的味覺感受。」克萊默的文章標題是〈我為何不再買昂貴葡萄酒〉。他稱價格不菲的葡萄酒是「完全在意料之中」且「幾乎不再為我帶來驚奇」。
這股情緒隨著酒價飆漲火上加油。2016年8月,德高望重的英國品酒家安德魯.傑佛德(Andrew Jefford)在《醒酒器》(Decanter)雜誌上寫道,「在過往的一年裡,有時候我了解到,我與葡萄酒的關係有某些部分有所轉變。我不再想要最好的⋯⋯它或許精緻,但未必有意思。」
就在數週之後,喬恩.博尼(Jon Bonné)在《華盛頓郵報》上表示他個人對波爾多與布根地感到幻滅── 一如對納帕谷、托斯卡尼等等其他酒區亦如是。「我得到一個怪異的結論,」博尼寫道,「是的,那些葡萄酒很棒。可是沒有它們不會活不下去。」他補充,「套句伏爾泰的話,傑出儼然成了優良的勁敵。」
● ● ●
葡萄酒指南幾乎都以作者經由某瓶廉價酒進入葡萄酒世界的輕鬆故事著手。……
十九歲大二結束後的暑假,我才頭一回真正品嚐了葡萄酒。我在義大利遊學,住在克雷莫納省(Cremona),波河(Po River)附近一個叫做皮耶韋聖賈科莫(Pieve San Giacomo)的小鎮上的一個寄宿家庭。每天晚上,那個家的父親保羅都會切滿滿一盤帕馬火腿片,並從一大輪格拉娜.帕達諾乳酪(Grana Padano)上切一大塊下來。然後開一瓶葡萄酒;從穀倉陰暗的角落裡撈出沒有貼標籤的一公升瓶子,倒出嘶嘶冒泡的冰透紅酒──就是有一天早晨我閒逛進去看見他宰了一頭乳牛的同一個穀倉。保羅不作興花稍的酒杯,用的是我們在紐澤西家鄉謂之為「果汁杯」的玻璃杯。除了準備肉片、乳酪和葡萄酒之外,男人們是不准進太太廚房的,因此,安娜忙著張羅我們的晚餐,保羅和我就是啜飲著裝在果汁杯裡那沁涼冒泡的紅酒,坐在電視機前,在那些個悶熱的夜晚觀看吵死人的足球賽。
我從來不曾品嚐或見過像這樣的葡萄酒。酒液呈鮮紫色,倒酒時會形成一層厚厚的粉紅色泡沫。我很清楚家鄉父母餐桌上的納帕谷卡本內不會冒泡泡。保羅的葡萄酒必然帶有水果味,雖然比較辛辣沒那麼甜, 但令人感到陌生的是芳香。我父親的葡萄酒氣味像那些可以辨識的水果 ──李子、櫻桃、莓果──和這款嘶嘶冒泡作響的酒截然不同。這支酒有一點點怪味,說真的。好像我在佛蒙特州念大學時煞到的漂亮嬉皮妹。當時我無以名狀,不過記憶中,那股芳香聞起來有泥土味、鐵鏽味、動物體味、生氣勃勃味,幾乎像極了小村莊裡農場和蒙塵的街道。在當時,聞起來和嚐起來就像我夢寐以求的古老歐洲。……
● ● ●
皮耶韋聖賈科莫的夏日時光過後二十年,我造訪義大利的朗格(Langhe)酒區,它位於皮埃蒙特(Piedmont),造訪了多位釀造巴羅洛的酒商;那是一款由內比奧羅(Nebbiolo)葡萄所生產的葡萄酒,複雜而細緻──絕佳美酒的典型,是杜林(Turin)薩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的宮廷御用酒,有「眾王之酒,眾酒之王」稱號。 我品飲了幾十支驚人的巴羅洛,多半深沉強烈又好得不同尋常──有些已經熟成了數十年──再一次,這令我深信不疑,生長在義大利西北部的內比奧羅,能釀出舉世無雙最偉大的葡萄酒。
某個陽光明媚的週日下午,我參加了一個稱之為「巴羅洛之星」(Asta del Barolo)的拍賣會,是參訪行程最精采的高潮。拍賣會當天,我沿著巴羅洛蜿蜒狹窄的鵝卵石街道,爬上一座城堡,俯瞰世上最有價值的葡萄園,一望無際。得獎的年分酒賣給蒐藏家──其中有些人從上海、莫斯科和杜拜遠道而來。有群人透過直播現場競標,他們身在新加坡某家餐館裡。有位熟人,是住在香港的奧地利銀行家,他花了3千歐元標下三大瓶1980年代中葉的一公升裝葡萄酒。我鄰座是一位迷人的酒商,其家族所釀造的巴羅洛細緻絲滑,年年勇奪品酒家最高分;品酒家稱他們是「天才」、「令人屏息」。在午餐席間,我們大概試飲了十五款2009年的年分酒。後來,年輕一輩的釀酒師聊起爵士樂和碧昂絲最近某個週末造訪巴羅洛,據推測,他們一行人豪砸5萬美元在葡萄酒和松露上。
我沒騙人。像這樣和一群人在午後聚聚,煞是令人迷醉。我難以清楚說明我有多喜歡巴羅洛。這樣說或許很蠢,但那感受宛若美妙音樂,或站在宏偉懾人的藝術品前。我深愛它,以至於大家問我最喜歡什麼酒,我通常會說,「呃,對,當然是巴羅洛。」
然而那日城堡午後簡直如夢似幻。返家後,我還喝很多巴羅洛嗎? 不了,沒那麼多。說「巴羅洛」是我的最愛,實在是錯誤傳達我的日常飲酒習慣。我多常喝它?除卻專業的試酒,每當要買酒在家飲用或者在餐廳點酒,我一年喝巴羅洛大概兩、三次,或許四次,要是手頭闊綽。因為一公升裝的巴羅洛一瓶索價60美金,而在酒窖的話可能很快就漲價到百元美金。在餐廳的酒單上兩、三倍跑不掉。不了,即使我深愛巴羅洛,它始終都屬於特殊場合。
經過巴羅洛的洗禮之後,我一直在思索著葡萄酒的卓越性。因而決定增加一趟小旅行,拜訪我在皮耶韋聖賈科莫的昔日寄宿家庭。我突發奇想,問了丹妮耶拉──保羅的女兒──研究一下她父親常去何處買他那款冒泡紅酒,經過一番努力,我們找到了釀酒師。出乎我意料,釀酒師並不在摩典那,而是相反方向兩小時車程外的另一處,在皮亞琴察(Colli Piacentini)丘陵──一個我聞所未聞的地方。
迷了路,再拿丹妮耶拉和安娜之間的爭論當參考──坐後座的兩姝大暈車──我們終於順當來到釀酒師的車庫;他是八十高齡的安東尼奧,還見到了他四十多歲的女兒。安娜情緒很激動,上回她和保羅一同拜訪這位釀酒師是1990年初期。「我還記得你有一頭山羊,牠很喜歡吃葡萄!」她說。這頭山羊,不用說,早已駕鶴西歸很久了。
我們從不鏽鋼貯酒桶汲出釀酒師做的麗絲琳,清新爽脆(Crisp);還有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暗黃色白葡萄酒,是以當地一種神祕的奧圖戈(Ortrugo)葡萄釀成。安東尼奧告訴我,他的客戶多半是帶大罈子來買酒的,因為他們喜歡自己裝瓶,像保羅那樣。
「那個冒泡泡的紅酒呢?」我問道,「你還釀它嗎?」
他咧開嘴笑了,從車庫一角撈出一支瓶子,拿了一個白色寬口碗;當他倒出深紫色紅酒時,粉紅泡泡堆起了一圈又一圈。「我的客戶堅持要用白色的碗喝這款紅酒。」安東尼奧說,「這樣才能襯托出顏色和香氣。」
我閉上雙眼,深深吸了一口氣,才小啜一口;艱澀(Sharp)、清新、味道濃烈、泥土味(Earthy)。哇!碗裡的紅酒宛如時光機器。我再次重回十九歲,穿著勃肯鞋和美國的前衛搖滾樂團Phish的T恤,生平頭一回體驗到這款紅酒的香氣與風味。捧著這個寬口碗湊進臉差一點叫我在漆黑的車庫裡涕泗縱橫。
「呃,藍布魯斯科?不,不,不。這是古圖尼奧(Gutturnio)。」 我猜我一定說錯了什麼。說不定我一直都聽不懂方言。「那是藍布魯斯科的當地名稱嗎?」我問。
他又笑了。「不!它是古圖尼奧。是巴貝拉(Barbera)和伯納達(Bonarda)。」而伯納達則是科羅蒂娜(Croatina)的當地名稱。
等等⋯⋯什麼跟什麼?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告訴我自己,開啟我葡萄酒經歷的是藍布魯斯科。現在我才知道,它是一款叫做古圖尼奧的酒?我怎麼會從來沒聽過這支酒?它不像是新品種。後來我才曉得,羅 馬人用一種稱為「Gutturnium」(意謂法螺)的圓壺喝這款酒,因而得名。凱撒大帝的岳父擅長以這個葡萄產區釀酒,名聞遐邇。
我們坐在桌前,以乳酪和肉佐酒,安娜和安東尼奧緬懷著往日時光。安東尼奧說,他如今每年賣掉大約四千瓶酒,比二十年前少了一半。「噢,」他說,「很多客戶都垂垂老矣。」同時,年輕一代不如他的同輩那般喜歡當地的葡萄酒。「如今,大家想要不一樣的口味。他們可能想要雞尾酒和啤酒。」安東尼奧聳聳肩。「凡事終有時。凡事終將盡。」
霎時,被我用白碗搖晃著的卑微紫色古圖尼奧,把我帶到了我自己的過往,也帶到古羅馬時代,可也同時又把我連結到完全嶄新的知識 ──甚至似乎更甚於最傑出的巴羅洛。在皮亞琴察丘陵這座農場裡的這次奇特經歷,於我而言似是葡萄酒的本質,是人們以身相許迷戀於葡萄酒的理由,是葡萄酒如何成為我們生活一員的典範。
● ● ●
葡萄酒不是一道要去攀爬的梯子,並非如我們一直以來被教導的那樣。一點也不是。葡萄酒是一座迷宮,一座我們滿懷歡欣走進去的迷宮,我們無視於它將帶我們往何處去,而且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出路。 當我步步深陷於迷宮之中,我轉而棄守所謂的絕佳美酒,越來越背離習以為常的路徑。一個更廣大、更刺激的葡萄酒世界於焉為我敞開。我開始花越來越多時間研究這些釀酒葡萄,諸如西班牙加利西亞(Galica)的戈德羅(Godello),或義大利多羅米提山(Dolomites)的特洛迪歌(Teroldego),還有, 北馬其頓(Macedonia)的威爾娜(Vranac),法國朱羅(Jura)的特盧梭(Trousseau),或是義大利佛里烏利.威尼斯朱利亞(Friuli-Venezia Giulia)的斯奇派蒂諾(Schioppettino),甚至不計其數其他品種。
我在寫的葡萄酒文章裡,開始推薦鮮為人知的葡萄酒,譬如希臘原生種葡萄釀製的性感紅酒,比方說北馬其頓地區納烏薩(Naousa)的希諾瑪洛(Xinomavro)。沒錯,雖然,比起梅洛、白蘇維濃或田帕尼羅(Tempranillo),希諾瑪洛發音很拗口。但是希諾瑪洛──字意就是「酸黑色」──可是一款天后級的葡萄,極度挑剔難種植,大家將她比作內比奧羅(Nebbiolo),好像它可比大家競相逐標的巴羅洛城堡酒。 原因是,希諾瑪洛有泥土味,口感複雜,顏色淺,單寧厚重而且酸度宜人,散發著莓果與玫瑰甚至焦油的氣味,和巴羅洛很類似。事實上,很難從納烏薩的希諾瑪洛葡萄酒中分辨出比較年輕的內比奧洛酒──如果你能辦到,那是因為你感覺到納烏薩酒比它那穩重的皮埃蒙特表親色澤金黃。
怪的是,希諾瑪洛只要大約15至20美元,只有巴羅洛價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你大可在週二晚上開一瓶希諾瑪洛,配著烤豬肉剩菜做成的墨西哥捲餅,爽歪歪看電視喜劇《大城小妞》,喝完一瓶舒服得很。畢竟這才是關鍵之一。用離經叛道的葡萄釀成的酒迷人、非主流,但它們也最實際:它們回饋冒險犯難的酒徒絕佳的價值感。
每每想及有趣但負擔得起的葡萄酒,就想到法國西南區,例如多爾多涅省(Dordogne)、加隆(Garonne)和加斯科涅(Gascony)。 這些地區距離波爾多車程很近,可是這裡釀酒不用卡本內蘇維濃或梅 洛,這裡最出色的佳釀是以內格芮特(Négrette)、塔那(Tannat)、莫札克(Mauzac)、費爾莎伐多(Fer Servadou(和小蒙仙(Petit Manseng)製成。不,我可沒胡言亂語,真的。那些釀酒葡萄出自弗龍東(Fronton)、馬迪朗(Madiran)、馬西亞克(Marcillac)和加亞克(Gaillac)產區。那些都是真實的名稱,是這些葡萄酒的產區所在地。雖然法國西南地區是該國第四大葡萄酒產區,但在美國卻非常罕見。這並不是因為多爾多涅、加隆或加斯科涅是新興酒區。它們其實很古老。事實上,遠在波爾多之前,釀酒業便已隨著羅馬人的存在而在此地蓬勃發展了。
在馬迪朗的加斯科村一帶,數百年以來,大家一直都在用平易近人、鏽紅色的碩大葡萄釀造成紅酒,在這裡,塔那(Tannat)葡萄獨霸一方。2000年代中葉時,因為科學家發現塔那葡萄的多酚含量最高也最有效,而名噪一時;這些抗氧化劑可以預防癌症、心臟病和糖尿病等一系列疾病。縱然如此,它依然默默無聞。馬迪朗釀製的葡萄酒口感壯實,色深多汁,帶有黑櫻桃、黑橄欖和黑咖啡的基調;當天氣轉寒,樹葉開始飄零之際,這款葡萄酒喝來恰到好處。一瓶瓶馬迪朗葡萄酒恰能沖刷掉在加斯科涅吃下肚的滯膩餐食,那些招待我的主人大概想把我養成肥鵝的豐厚鵝肝、法式血鴨。每瓶馬迪朗售價平均大約都不超出25美元,大多數不到20元。
另一款相反的酒是口感較輕盈的紫紅色葡萄酒,用的是費爾莎伐多(Fer Servadou)葡萄製成,在它的兩大產區裡,加亞克(Gaillac)當地稱之為布洛可(Braucol),而在馬西亞克(Marcillac)則稱作芒索(Mansois)。費爾莎伐多和我喜愛的羅亞爾河谷卡本內弗朗類似,都有百搭食物的特點,但是它的芳香成分,譬如尤加利和乾燥迷迭香氣味,稍微更濃郁些,還有給人一種剛剛沖了澡的清新舒暢感,有點像那些古老愛爾蘭春天的廣告,廣告裡穿著高領毛衣溫文儒雅的傢伙贏得塞爾特姑娘芳心。我開過了每一瓶瑪西亞克都很快就喝光:這是測試葡萄酒易飲性最可靠的方式。加亞克和瑪西亞克零售價大多在25美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