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倒
| 作者 | 劉以鬯 |
|---|---|
| 出版社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對倒:※香港導演王家衛作品《花樣年華》電影靈感※被收錄重要文學選集:「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精選」、「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集」※故事架構以雙線並行類似電影蒙太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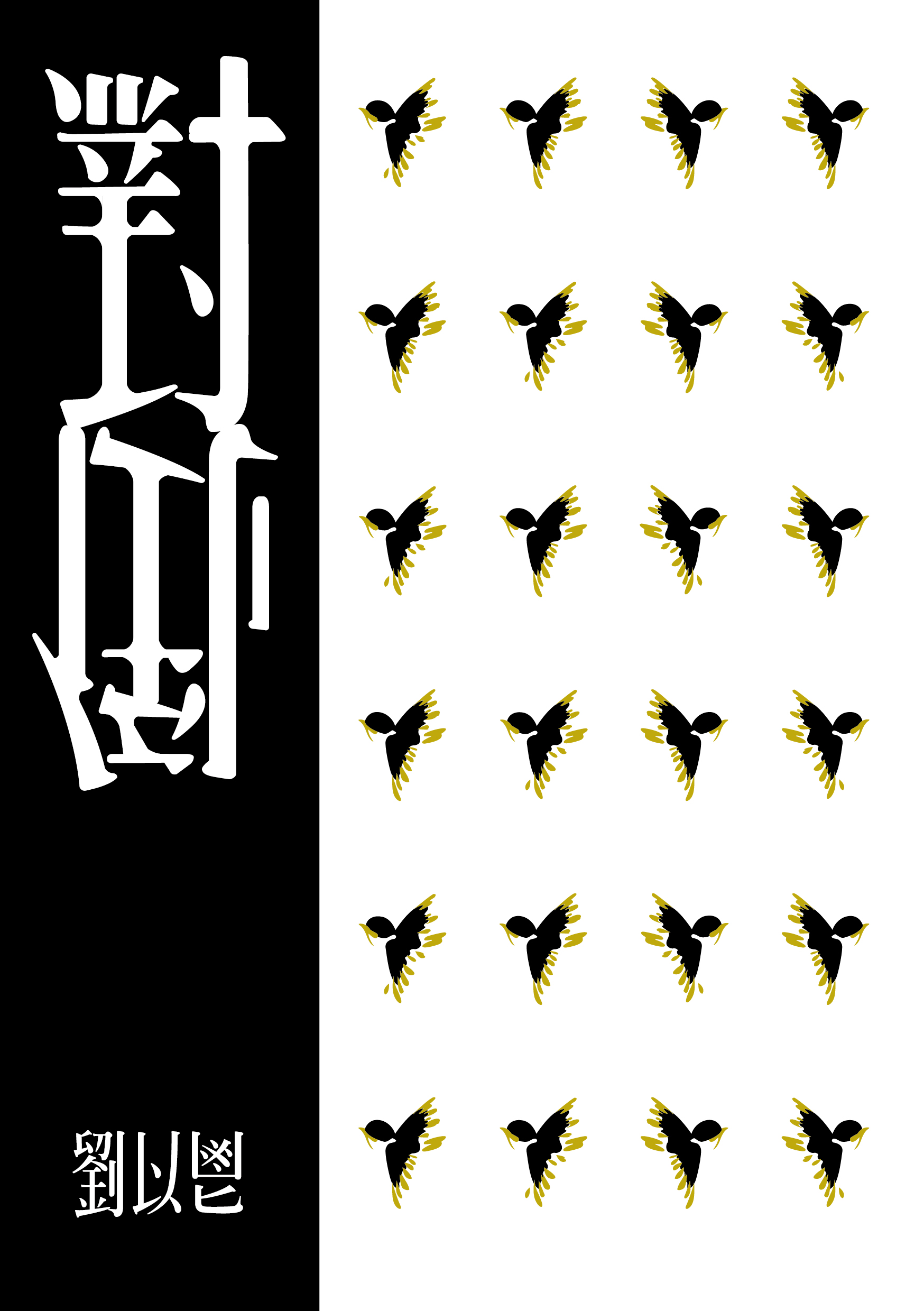
| 作者 | 劉以鬯 |
|---|---|
| 出版社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對倒:※香港導演王家衛作品《花樣年華》電影靈感※被收錄重要文學選集:「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精選」、「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集」※故事架構以雙線並行類似電影蒙太奇 |
內容簡介 ◎香港導演王家衛作品《花樣年華》電影靈感◎被收錄重要文學選集:「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精選」、「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集」◎故事架構以雙線並行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效果;內容敘述具戰後存在主義的風格「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這是電影《花樣年華》,也是劉以鬯。「讓世人重新認識,知道香港曾經有過劉以鬯這樣的作家,是最讓我開心的事。」——王家衛「對倒」一詞譯自法文「Tête-Bêche」,是集郵專家用來描述印刷時發生了錯誤,導致兩張相連、卻一正一反的郵票。由於稀少罕見,所以價值不凡。有趣的是,這種郵票一旦分離,就立刻失去價值,成為兩張平凡的郵票。1972年時,作者劉以鬯在倫敦吉本斯公司舉行的華郵拍賣上,投得一張「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因此激發作者從對倒的意境中聯想、發展出此小說情節。更在三十年之後,讓導演王家衛拍出《花樣年華》這部著名作品。本書主角淳于白是一位移居香港多年的男子,對城市充滿懷舊的傷感;亞幸則是浪漫天真少女,對未來憧憬富有想像。在同樣的街道擦肩而過;在同樣的時間流動中,轉向一樣的電視頻道;在戲院裡陌生的並肩而坐,偶有相望的成為彼此唯一的交會。看似兩個人各自的心境感受描繪,在性別、思想、年紀的對比呼應下,讓香港的時代樣貌更為具體。以雙線並行的架構,以及作者擅長的意識流文字,各自發展兩位不相識的男女主角故事,卻又如對倒郵票的相連關係,讓獨立的生命產生特殊的意義。本書收錄「短篇小說」及「長篇小說」;長篇在1972年的《星島晚報》開始連載;短篇則是1975年改寫並發表於當時的文學雜誌《四季》之中。前衛的書寫,震驚當時文壇且受到肯定,深刻地影響當代的香港文學界。雖然《對倒》早已成為華人經典,更在王家衛的《花樣年華》電影後紅極一時,翻譯成多國語言,竟從來未在台灣出版。我們希望藉著引介這部不斷激起漣漪的著名經典,讓台灣讀者有機會見證最美好的香港70年代,更能看到歷久彌新的小說文字,構築出來的迷人世。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哈佛大學東亞系與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王德威作詞人/李焯雄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浙江鎮海人。1941年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曾在重慶、上海、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任報紙、雜誌編輯、主編;主要作品有《酒徒》、《對倒》、《寺內》、《天堂與地獄》、《島與半島》、《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短綆集》、《見蝦集》、《劉以鬯實驗小說》、《龍鬚糖與熱蔗》、《端木蕻良論》等。其作品《對倒》及《酒徒》分別引發香港導演王家衛拍成電影《花樣年華》及《2046》。
產品目錄 新版前記序《對倒》短篇小說《對倒》長篇小說
| 書名 / | 對倒 |
|---|---|
| 作者 / | 劉以鬯 |
| 簡介 / | 對倒:※香港導演王家衛作品《花樣年華》電影靈感※被收錄重要文學選集:「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精選」、「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集」※故事架構以雙線並行類似電影蒙太奇 |
| 出版社 /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9214124 |
| ISBN10 / | 9869214126 |
| EAN / | 9789869214124 |
| 誠品26碼 / | 2681205688002 |
| 頁數 / | 224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H:精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節錄《對倒》短篇小說
【十一】
凝視鏡子裏的自己,淳于白發現額角的皺紋加深了;頭上的白髮增加了。那是一家服裝店,櫥窗的一邊以狹長的鏡子作為裝飾。淳于白凝視鏡子裏的自己,想起了年輕時的事情。
【十二】
亞杏見到那張照片,不能沒有好奇。將照片拾了起來,定睛一瞧,心就撲通撲通一陣子亂跳。那是一張猥褻的照片。照片上的情形,是亞杏想也不敢想的。她知道這是邪惡的東西;帶回家去,除非不給父母見到;否則,一定會受到責罵。她想:「將它撕掉吧。」但是,她很好奇。對於她,那張照片是刺激的來源,多看一眼,心裏就會產生一種難於描摹的感覺。「何必撕掉?」她想,「將來結了婚,也要做這種事情的。」她將照片塞入手袋。走入大廈,搭乘電梯上樓。回到家,才知道母親在廚房裏。於是,拿了內衣內褲走入沖涼房,關上房門,仔細觀看那張照片,羞得滿面通紅,熱辣辣的。她脫去衣服,站在鏡前,睜大眼睛細看鏡子裏的自己。
【十三】
凝視鏡子裏的自己,淳于白想起一些舊日的事情:公共租界周圍的烽火、三隻轟炸機飛臨黃浦江上轟炸「出雲號」的情景、四行孤軍、變成孤島的上海、孤島上的許多暗殺事件。然後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日本坦克在南京路上疾馳。
【十四】
亞杏照鏡時,總覺得自己的臉型很美,值得驕傲。也許這是一種自私心理,祇要有機會站在鏡前,總會將自己的美麗當作藝術品來欣賞。她不大理會別人對她的看法。
當她仔細端詳鏡子裏的自己時,覺得自己比陳寶珠更美,沒有理由不能成為電影明星。
當她仔細端詳鏡子裏的自己時,覺得自己比姚蘇蓉更美,沒有理由不能成為紅歌星。
她就是這樣一個少女,每次想到自己的將來,總被一些古怪的念頭追逐着,睜大眼睛做夢。在此之前,腦子裏的念頭雖然不切實際,卻是無邪的;現在,看過那張拾來的照片後,腦子裏忽然充滿骯髒的念頭。她想像一個「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鄧光榮,有點像李小龍,有點像狄龍,有點像阿倫狄龍」的男人也在這間沖涼房裏。這間沖涼房裏,除了她與「那個男人」,沒有第三個人。這樣想時,一種擠迫感,彷彿四堵牆壁忽然擠攏來,一若武俠電影中的機關佈景。她的臉孔紅得像燒紅的鐵,皮膚的裏層起了一陣針刺的感覺,心跳加速,內心有火焰在燃燒。她做了一個完全得不到解釋的動作:將嘴唇印在鏡面上,與鏡子裏的自己接吻。
對於她,這是一種新鮮的刺激。第一次,她有了一個愛人。這個愛人竟是她自己。
不敢對鏡子裏的自己多看一眼,也不敢再看那張拾來的照片,彷彿舊時代的新娘那樣,縱有好奇,也沒有勇氣對從未見過面的新郎偷看一下。她忽然認真起來了,竭力轉換思路,認為應該想想陳寶珠與姚蘇蓉了。在她的心目中,陳寶珠與姚蘇蓉是兩個快樂的女人。
進入浴缸,怔怔地望着自己的身體。這是以前很少有的動作,她祇覺得女人面孔是最重要的。那張照片給她的印象太深,使她對自己的體態也有了好奇。她年紀很輕;臉上的稚氣尚未完全消失。對於她,這當然不是一個發現;可是,認真地注意自己的體態時,有點驚詫。
將肥皂擦在身上,原是一種機械的動作。當她用手掌摩擦皮膚上的肥皂時,將自己的手當作別人的手。
她希望這兩隻手是屬於「那個男人」的。那個「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鄧光榮,有點像李小龍,有點像狄龍,有點像阿倫狄龍」的男人。
半個鐘頭之後,她躺在臥房裏,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她應該將那張照片擲出窗口的,卻沒有這樣做。她將它塞在那隻小皮箱的底層。
樓下那家唱片公司,此刻正在播送姚蘇蓉的「愛你三百六十年」。
【十五】
鏡子裏的他,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了。淳于白對那面鏡子繼續凝視幾分鐘後,不敢再看,繼續朝前走去。雖然人行道上黑壓壓地擠滿行人,他卻感到了無比的孤寂。──見到門飾充滿南洋味的餐廳時,推門而入。
餐廳是狹長的,面積不大,佈置得相當現代化。牆壁糊着深藍色的牆紙,燈光幽暗。食客相當多,淳于白卻意外地找到一個空着的卡位。坐定,向夥計要一杯咖啡。他見到一個年輕男子從門外走進來,瘦瘦高高,長頭髮,穿了一條「真適意」的牛仔褲,右手插在褲袋裏。褲子是藍色的,褲袋卻是紅方格的,牙齒咬着一支細長的香煙。進門後,那男子站在門邊睜大眼睛找人。淳于白旁邊有一隻小圓桌。小圓桌旁邊坐着一個年輕女人。這個年輕女人穿着長短袖的新潮裝,牛仔褲的褲腳好像用剪刀剪開的。
用牙齒咬着細長香煙的男子走到這個女人面前,拉開椅子坐下。
「肥佬走了?」年輕男子將話語隨同煙霧吐出。
「走了半個鐘頭。」女人用食指點點面前那杯咖啡,「這是第三杯!」
那年輕男子依舊用牙齒咬着細長香煙,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拿到沒有?」他問。
「祇有五百。」
「肥佬不是答應拿一千給你的?」
「他說:賭外圍狗輸了錢。」
年輕男子臉上出現怒容,連吸兩口煙,將長長的煙蒂撳熄在煙灰碟中。當他再一次開口時,話語從齒縫中說出:
「他答應拿一千給你的!」
「有什麼辦法?他祇肯給五百,」女人的語氣也有點憤怒;不過,臉上的神情卻好像在乞取憐憫。
「對付肥佬那種傢伙,你不會沒有辦法。」
「錢在他的袋中,我不能搶。」
年輕男子霍地站起,低頭朝外急走。那女人想不到他會這樣的,忙不迭追上前去,卻被夥計一把拉住。她問:「做什麼?」夥計說,「你還沒有付錢。」女人打開手袋,掏了一張十元的鈔票,不等找贖,大踏步走出餐廳。淳于白望着那個女人的背影,不自覺地露了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然後注意力被一幅油畫吸住了。那幅油畫相當大,兩呎乘三呎左右,掛在糊着牆紙的牆壁上。起先,淳于白沒有注意到那幅畫;偶然的一瞥,使他覺得這幅畫的題材相當熟悉。那是「巴剎」的一角。印度熟食檔邊有人在吃羊肉湯──熱帶魚販在換水──水果攤上的榴槤──提着菜籃眼望蔬菜的老太婆──鬥雞──濕地──凌亂中顯示濃厚的地方色彩。這是新加坡的「巴剎」。淳于白曾經在新加坡住過。住在新加坡的時候,常常走去「巴剎」吃「排骨茶」。尤其是星期日,如果不走去蜜駝律吃雞飯的話,就會走去「巴剎」吃「排骨茶」。
現在,他聽到姚蘇蓉的歌聲了。姚蘇蓉,一個唱歌會流淚的女人。當她公開演唱時,有人花錢去聽她唱歌;有人花錢去看她流淚。這是一個缺乏理性的地方,許多人都在做着不合理的事情。流淚成為一種表演,大家都說那個女人唱得好。
坐在上海舞廳裏聽吳鶯音唱「明月千里寄相思」,與坐在香港餐廳裏聽姚蘇蓉唱「今天不回家」,心情完全不同。心情不同,因為時代變了。淳于白懷念的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他祇能在回憶中尋求失去的歡樂。但是回憶中的歡樂,猶如一幀褪色的舊照片,模模糊糊,缺乏真實感。當他聽到姚蘇蓉的歌聲時,他想起消逝了的歲月。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種種,都是模模糊糊的。
一個臉色清癯的瘦子帶着一個七八歲的男童走進來。起先,他們找不到座位;後來,淳于白旁邊那隻小圓台邊的食客走了,他們佔得這個位子。
「我要吃雪糕,」男童說。
「不許吃雪糕,」瘦子說。
「我要吃雪糕!」男童說。
「不許吃雪糕!」瘦子說,「你喝熱鮮奶!」
「我要喝凍鮮奶,」男童說。
「不許喝凍鮮奶,」瘦子說。
「我要喝凍鮮奶!」男童說。
「不許喝凍鮮奶!」瘦子說。
瘦子向夥計要了熱鮮奶與雪糕。他自己吃雪糕。男童忍聲飲泣,用手背擦眼。
「不許哭!」瘦子的聲音很響。
「我要阿媽,」男童邊哭邊說。
「到陰間去找她!」瘦子的聲音依舊很響。
「我要阿媽!」男童邊哭邊說。
「你去死!」瘦子的聲音響得刺耳。
好幾個食客的視線被瘦子的聲音吸引過去了。瘦子不知。那個用手背擦眼的男童也不知。
「我要吃雪糕!」男童邊哭邊喊。
「不許吃雪糕!」瘦子惡聲怒叱。
「我要喝凍鮮奶!」男童連哭帶喊。
「不許喝凍鮮奶!」瘦子惡聲怒叱。
「我要阿媽!」男童連哭帶喊。
「你去死!」瘦子的聲音響得刺耳。
男童放聲大哭。瘦子失去了應有的耐性,伸出手去,在男童頭上重重打了一下。男童大哭。哭聲像拉警報。瘦子怒不可遏,站起,將一張五元的鈔票擲在台上;抓住男孩的衣領,用蠻力拉他。男童蹲在地上,不肯走。瘦子臉色氣得鐵青,睜大怒眼對男童呆望片刻,忽然鬆手,大踏步走出餐廳。男童急得什麼似的,站起身,追了出去。這時候,夥計將一杯雪糕與一杯熱鮮奶端了出來,發現瘦子與男童已不在,有點困惑。
「走了,」淳于白說。
「走了?」夥計問。
「桌上有五塊錢,」淳于白說。
夥計聳聳肩,拿走五塊錢,交給櫃面;然後將雪糕與鮮奶端到裏邊去。
四個上海女人在口沫橫飛地談論樓價。她們談話時聲音很大,別人也許聽不懂,淳于白卻聽得清清楚楚。甲女正在講述排隊買樓的經過。她說:「天沒有亮,我就去排隊了;排了幾個鐘頭,還是買不到。」乙女說,「我的姨媽,去年在灣仔買了五層新樓,每層兩三萬,現在每層漲到十幾萬。」丙女說,「樓價為什麼漲得這麼高?」甲女聳聳肩,「誰知道?」丁女說,「九龍有一個地方出售樓花,有人連面積與方向都沒有弄清楚,一下子買了十層。」乙女說,「香港真是一個古怪的地方,有些人什麼事情都不做,單靠炒樓,就可以得到最高的物質享受。」丁女說,「依我看來,炒樓比炒股票更容易發達。」甲女說,「對,你講得很對。炒樓比炒股票更容易發達。股票的風險比炒樓大,股票漲後會跌,跌後會漲;但是目前的樓宇祇會漲,不會跌。」丙女說,「話雖如此,現在的樓價已經漲得很高了。港島半山區的樓宇,漲到幾十萬一層,即使普普通通的,也要二十萬以上。」甲女說,「樓價還會上漲的,香港地小人多。住屋的問題,一直沒有徹底的解決。」甲女說,「樓價漲得越高,買樓的人越多!」……
淳于白點上一支煙。
【十六】
亞杏躺在床上,凝視天花板。樓下那家唱片公司已經播送過很多張唱片了。大部分是姚蘇蓉的唱片。「做了紅歌星之後,」她想,「不但每月可以賺一萬幾千,而且會有許多男人追求我。……許多男人。……許多像柯俊雄、像鄧光榮、像李小龍、像狄龍、像阿倫狄龍那樣英俊的男人追求我。……這些男人會送大鑽戒給我。這些男人會送大汽車給我。這些男人會送大洋樓給我。這些男人會送很多很多東西給我。……」
凝視天花板,天花板忽然出現聚光燈的照明圈。在這個照明圈中,一個濃妝艷服的女人手裏拿着麥克風,在唱歌。這個女人長得很美。她的背後有幾個菲籍洋琴鬼在吹奏流行音樂。奏的是「郊道」。亞杏很喜歡「郊道」這首歌的調子,她也會唱。有時候,全層樓祇剩她一個人,就會放開嗓子唱「郊道」。她的「郊道」唱得不錯。這個忽然出現在天花板上的女人也唱得不錯。她有點好奇,仔細察看,原來那個拿着麥克風唱歌的人,正是她自己。
雖然從未有過醉的經驗,卻產生了醉的感覺。她是非常留連那種景象的,睜大眼睛,久久凝視天花板。天花板上的牆景忽然轉換了,一若舞台上的轉景。那是一間佈置得非常現代化的臥房。這種臥房,祇有在銀幕上才能見到。床很大,地板鋪着地毯,四壁糊着鮮紅奪目的糊牆紙,窗簾極美。所有傢俱都是北歐產品。那隻梳妝台的式樣很別緻,梳妝台上放着許多名貴的化妝品。她坐在化妝台前,細看鏡子裏的自己。鏡子裏,除了她之外,還有一個男子。那男子站在她背後。那男子長得很英俊,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鄧光榮、有點像李小龍、有點像狄龍、有點像阿倫狄龍。那男子在笑。那男子在她耳邊說了一些甜得像蜜糖般的話語。那男子送她一隻大鑽戒。不知道怎麼一來,天花板上出現許多水銀燈,那是攝影場。剛搭好的佈景與現實鮮明地分成兩種境界:假的境界極具美感,真的反而雜亂無章。導演最忙碌。小工們則散在各處。攝影機前有兩個年輕人:男的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鄧光榮、有點像李小龍、有點像狄龍、有點像阿倫狄龍。女的就是她。
「紅歌星的收入也許比電影明星更多;但是,電影明星卻比紅歌星更出風頭,」她想。「一部電影可以同時在十個地區公映,可以同時在一百家戲院公映。」
她見到十個自己。
她見到一百個自己。
天花板變成銀幕。她在銀幕上露齒而笑。她的笑容同時出現在十個地區,同時出現在一百家戲院的銀幕上。
眼睛。眼睛。眼睛。眼睛。數不清有多少眼睛凝視她的笑容。這時候,樓下唱片公司又在播送姚蘇蓉的「今天不回家」了。她也會唱「今天不回家」。她覺得做一個電影明星比做一個歌星更出風頭。天花板上有許多畫報。天花板上有許多報紙。香港映畫。銀色世界。南國電影。嘉禾電影。星島畫報。四海周報。星島晚報。快報。銀燈。娛樂新聞。成報。明報。每一種畫報都以她的近影做封面。
母親走進臥房來拿剪刀,腳步聲使她突然驚醒。今晚吃飯時,將有一碗豆腐炒蝦。那些蝦,下鍋之前,必須用剪刀剪一下。
「什麼時候吃晚飯?」亞杏問。
「七點,」母親答。
「七點半,行不行?」
「為什麼?」
「我要去看電影。」
「五點半那一場?」
「是的,五點半那一場。」
【十七】
淳于白昂起頭,將煙圈吐向天花板。他已吸去半支煙。當他吸煙時,他老是想着過去的事情。有些瑣事,全無重要性,早被壓在底下,此刻也會從回憶堆中鑽出,猶如火花一般,在他的腦子一瞬即逝。那些瑣事,諸如上海金城戲院公映費穆導演的「孔夫子」、貴陽酒樓吃娃娃魚、河池見到的舊式照相機、樂清搭乘帆船飄海、龍泉的浴室、坐黃包車從寧波到寧海……這些都是小事,可能幾年都不會想起;現在卻忽然從回憶堆中鑽了出來。人在孤獨時,總喜歡想想過去,將過去的事情當作畫片來欣賞。淳于白是個將回憶當作燃料的人。他的生命力依靠回憶來推動。
他想起了第一次吸煙的情景。那時候,二十剛出頭,獨個兒從上海走去重慶參加一家報館工作。有一天,在大老鼠亂竄的石階上,一個綽號「老槍」的同事遞了一支「主力艦」給他,煙葉是用成都的粉紙捲的,叼在嘴上,嘴唇就會發白。淳于白第一次吸香煙,嗆得上氣不接下氣。那同事說,「重慶多霧,應該吸些香煙。」
給記憶中的往事加些顏色,是這幾年常做的事。
鄰座一個食客已離去,留下一份報紙。淳于白閒着無聊,順手將那份報紙拿過來翻閱。電訊版大都是越戰新聞;港聞版大都是搶劫新聞。這些新聞已失去新鮮感,使淳于白祇好將注意力轉在電影廣告上。當他見到鄰近一家電影院公映的新片正是他想看的片子,他吩咐夥計埋單。
【十八】
站在唱片公司門前,亞杏看到了許許多多唱片。每一張唱片紙套上印着歌者的彩色照片。亞杏很喜歡這些唱片;也很喜歡這些唱片的歌者。姚蘇蓉、鄧麗君、李亞萍、尤雅、冉肖玲、楊燕、金晶、貝蒂、鍾玲玲、鍾珍妮、徐小鳳、甄秀儀、潘秀瓊……
凝視這些彩色照片時,亞杏忽然見到了自己。那是一張唱片的紙套,與別的唱片紙套排列在一起。那張唱片名叫「月兒像檸檬」。紙套用彩色精印歌者的照片。歌者星目朱唇,美到極點。仔細端詳,竟是她自己。這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情;然而她卻見到了自己的照片。她一直喜歡唱「月兒像檸檬」。她覺得這首歌的歌詞很有趣。月亮像檸檬。一個像檸檬的月亮。這種意象,亞杏從未產生過。每一次抬頭望圓月,總覺得月亮像一盞大燈。有了這首歌之後,她一再強迫自己將月亮與檸檬聯在一起。她覺得自己最適宜唱這首歌,而且唱得很好。現在,在那些唱片堆中發現了一張由她唱出的唱片,又驚又喜,不自覺地跨入店內。站在櫃檯前,對自己的視覺全無懷疑。她伸出手去,將那張唱片拿到眼前一看,冷水澆頭,那是趙曉君唱的「月兒像檸檬」。紙套上的彩色照片是趙曉君,不是她。
「唱給你聽聽?」店員的話打斷她的思路。
她放下唱片,掉轉身,彷彿逃避魔鬼的追逐似的,疾步走出唱片公司。
穿過馬路,走向彌敦道。她想,「有一天,唱片公司會請我灌唱片的。」
突如其來的剎車聲,使她嚇了一跳。一輛汽車將一個婦人撞倒。
警察來了。
在汽車司機協助下,將受了傷的婦人抬到街角。這時候,婦人睜開眼來了。亞杏跟隨人潮走到街邊,見婦人已睜開眼睛,釋然舒口氣。
婦人仍在流血。警察拿了粉筆走入馬路中心,將車子的位置與車牌號碼寫在路面。警察做好這些工作後,司機將車子駛在路旁。那些被阻塞的車輛開始行駛了。交通恢復常態。
【十九】
交通恢復常態時,淳于白站在對街。好奇心雖起,卻沒有穿過馬路去觀看究竟。他祇是站在銀色欄杆旁邊,看警察怎樣處理這樁突發的意外事件。三十幾年前,當他還在初中讀書的時候,在回家的途中,見前面有一輛電車即將到站,飛步橫過馬路,鞋底踩在路面的圓鐵上,仰天跌了一跤。接着是刺耳的剎車聲,知覺盡失。當他甦醒時,有人在厲聲罵他,「想尋死,也不必死在馬路上!」──他用手掌壓在地面支撐起身體,想邁開腳步,兩條大腿彷彿木頭做的。
現在,當他見到那個婦人被汽車撞倒時,視線落在對街,腦子卻在想着三十幾年前發生過的事情。「死亡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想。三十幾年前,他曾經在死亡的邊緣體驗過死亡的情景。
救傷車來到,使這齣現實生活中的戲劇接近尾聲。
【二十】
這齣現實生活中的戲劇已接近尾聲。亞杏抬起頭來,順着警笛聲的來處望過去。警笛聲雖然響得刺耳,但是,救傷車的速度並不快。
救傷車在傷者旁邊停下。兩個男護士抬着擔架床走過來,先察看婦人的傷勢,然後用擔架床抬入救傷車。
亞杏低下頭,看看腕錶,離開開場的時間還有十分鐘。如果她想看那場電影的話,就不能浪費時間了。她邁開腳步,朝電影院走去。
【二十一】
淳于白輪購戲票時,亞杏走入戲院。雖然有些海報極具吸引力,亞杏見售票處有人龍,不敢浪費時間,立即走去排隊。「必定是一部好電影,要不然,怎會有這麼多的觀眾?」她想,「那男主角長得很英俊。」
【二十二】
「那女主角長得很漂亮,有點像年輕時的凱倫希絲,」淳于白的視線落在海報上。電影海報總是那樣俗氣的。「不過,女主角的容顏端莊中帶些甜味,」他想,「凱倫希絲主演『天長地久』時,既端莊,又美麗,非常可愛。這部電影的女主角與年輕的凱倫希絲很相似。」──想着三十年代的凱倫希絲,不知不覺已擠到售票處。座位表上的號碼,大部分已被紅筆畫去。淳于白見前排還有兩個空位:「G四十六」與「G四十八」。後者是單邊的,雖然距離銀幕比較近,也算不錯了。他伸出手指,點點「G四十八」,付了錢。售票員收了錢,用紅筆將「G四十八」畫掉,然後在戲票上寫了「G四十八」,撕下,遞與淳于白。淳于白望望海報上的女主角,懷着輕鬆的心情走入院子。帶位員引領他到座位,坐定。他抬頭一望,銀幕上正在放映一種香煙的廣告。
【二十三】
亞杏排在人龍中,見人龍越排越長,惟恐買不到戲票,有點焦躁不安。望望貼在牆上的海報,她想,「男主角長得英俊,有點像阿倫狄龍。如果不是因為男主角的叫座力強,就不會有這麼多的人走來看這部電影了。」──視線一直落在男主角的臉上,彷彿男主角的臉是一件精緻的藝術品。
排在亞杏前頭的那個男子瘦得很,臉孔清癯,呈露着病態的蒼白。他的身邊有一個男童。那男童的眼睛,紅紅腫腫,顯然哭過了。
「我要吃雪糕,」男童說。
「剛才,在餐廳的時候,要不是因為你吵着要吃雪糕,我也不會發那樣大的脾氣。」瘦子的語氣中含有顯明的譴責意味,「剛才,雪糕也沒有吃,熱鮮奶也沒有吃,白白送掉五塊錢!」
「我要吃雪糕!」男童說。
「不許吃雪糕!」瘦子惡聲怒叱,「再吵,就不帶你看電影了!」
「我不要看電影,我要吃雪糕!」男童說。
「你又來了,可別惹我生氣了!」瘦子臉上的顏色白中帶青。
男童側轉身子,睜大眼睛望着糖果部。那糖果部前面擠着七八個人,其中五六個是購買雪糕的。
「我要吃雪糕!」男童對瘦子說。
「不許吃雪糕!」瘦子惡聲怒叱。
「我要阿媽!」男童又哭了。
「你去死!」瘦子的聲音好像在跟什麼人吵架。
男童聽了瘦子的話,「哇」地放聲大哭。這哭聲引起許多人的注意。瘦子感到窘迫,所以惱怒。當他惱怒時,再也不能保持理智的清醒。在不受理性的控制下,他伸出手去,在男童頭上重重打了一下。男童哭得像拉警報。瘦子抓住男童的衣領,將他拉出戲院。這一幕就在亞杏眼前上演;亞杏不能不對那個男童寄予同情了。「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是無法從父親處得到母愛的,」她想。過了三四分鐘,輪到亞杏購買戲票。座位表上,畫滿紅線,使亞杏有點眼花繚亂,找不到一個未被紅筆畫去的空格。那售票員不耐煩在用那枝紅筆點點「G四十六」,意思是:「這裏有一隻空位。」亞杏見空位不多,祇好點點頭,將錢交給售票員。
拿了戲票,走入院子。帶位員引領她到座位
【二十四】
她與淳于白並排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