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精品集 4: 朱門 (最新譯校)
| 作者 | 林語堂 |
|---|---|
| 出版社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林語堂精品集 4: 朱門 (最新譯校):有史以來,中國人直接用英文寫中國,最成功的有兩位,一位是辜鴻銘,一位是林語堂。辜鴻銘刺毛姆筆下「享譽國際憤世嫉俗的學者」;林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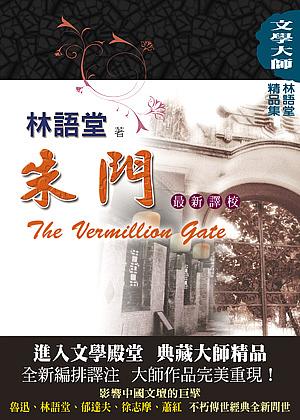
| 作者 | 林語堂 |
|---|---|
| 出版社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林語堂精品集 4: 朱門 (最新譯校):有史以來,中國人直接用英文寫中國,最成功的有兩位,一位是辜鴻銘,一位是林語堂。辜鴻銘刺毛姆筆下「享譽國際憤世嫉俗的學者」;林語 |
內容簡介 有史以來,中國人直接用英文寫中國,最成功的有兩位,一位是辜鴻銘,一位是林語堂。辜鴻銘刺毛姆筆下「享譽國際憤世嫉俗的學者」;林語堂則是賽珍珠筆下「根深於過去,盛開於現代」的「現代作家」,他們都是福建人,他們筆下的英文,全沒中國味;他們筆下的中國味,卻全是英文。 辜鴻銘生不逢時,林語堂適逢其時,他的作品,龍飛異域,鳳舞番邦,雄踞了一個世代。 *與《京華煙雲》並列為林語堂三部曲之一;林語堂另一文學代表巨著! *一個出身「朱門」卻敢於挑戰世俗的女子,一段不凡的愛情故事! *文學大師經典重現,全新譯校! 內文簡介: 為了愛,她不惜遠走他鄉; 為了愛,她可以不顧一切! 因為一場意外,讓他們邂逅並陷入情網; 也因為一場意外,讓他們不得不分隔千里, 一個「朱門」之女, 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捍衛珍貴的愛情, 不惜離鄉背景,衝破世俗羈絆,更跨越門第鴻溝, 終於找到渴望的幸福。 林語堂以其一貫的幽默筆法, 生動刻劃在新舊時代的交替下, 朱門世家的興衰、家族間的衝突; 和女子突破傳統的勇氣, 深刻且細膩的描寫了那個時代的故事。 杜柔安,一個出身於名門世家的大家閨秀, 心思細膩卻又多愁善感, 在一次學生的示威活動中, 意外結識了任職於報社的記者李飛, 從此開始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她看似柔弱,卻有著常人無法想像的韌性與堅強的毅力, 當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欲分家奪產的叔叔,以及傳統的價值評判時, 她敢於突破現狀,掙脫舊有束縛,對抗種種不公, 最後終得圓滿的結局。 而書中的三個女子:柔安、湘華、春梅, 正代表著豪門大戶的「門第」觀念逐漸瓦解, 也顯示了舊社會女子勇於追求自我的歷程。
作者介紹 林語堂(1895—1976),是一位以英文書寫而揚名海外的中國作家,也是集語言學家、哲學家、文學家、旅遊家、發明家於一身的知名學者。因翻譯「幽默」(Humor)一詞,以及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三本雜誌,提倡幽默文學,因此贏得「幽默大師」的美名。1935年在美出版《吾土與吾民》,自此享譽歐美文壇。次年移居紐約,致力寫作。1937年出版《生活的藝術》,成為翌年全美暢銷書冠軍。此後年年皆有新著,至1964年為止,共計出版《京華煙雲》、《蘇東坡傳》等三十餘部小說、論述、歷史傳記、英譯重編中國經典或傳奇。林語堂為福建龍溪(漳州)人。譜名和樂,17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改名玉堂。28歲獲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學位。1923年獲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返國後任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兼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講師。開始以語堂為名發表文章。歷任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教授和教務長、中央研究院英文總編輯、史語所兼任研究員,及上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英文教授。1928年編著《開明英文讀本》,風行全國。1966年,返台定居陽明山。1975年以《京華煙雲》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1976年3月26日病逝香港,四月移靈台北,長眠於故居後園中,享年八十二歲。
| 書名 / | 林語堂精品集 4: 朱門 (最新譯校) |
|---|---|
| 作者 / | 林語堂 |
| 簡介 / | 林語堂精品集 4: 朱門 (最新譯校):有史以來,中國人直接用英文寫中國,最成功的有兩位,一位是辜鴻銘,一位是林語堂。辜鴻銘刺毛姆筆下「享譽國際憤世嫉俗的學者」;林語 |
| 出版社 /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1466989 |
| ISBN10 / | 9861466983 |
| EAN / | 9789861466989 |
| 誠品26碼 / | 2680515689006 |
| 頁數 / | 384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本書人物純屬虛構。正如一切小說角色,他們取材自真實生活,卻是組合體。但願沒有人自認是某一個軍閥、冒險家、騙子或浪子的原版。如果某一位女士幻想她認識書中的名媛或美妾,甚至本身有過類似的經驗,那倒無傷大雅。
不過,新疆事變卻是千真萬確的,歷史背景中的人物也以真名出現:例如首次帶漢軍家眷移民新疆的大政治家左宗棠;一八六四至一八七八年領導大回變的雅庫布貝格;哈密廢王的首相約巴汗;日後被手下白俄軍團逐出新疆,在南京受審槍斃的金樹仁主席;繼承金主席成為傳奇人物的滿將盛世才;曾想建立中亞回教帝國,最後在一九三四年年尾隨同喀什噶爾的蘇俄領事康士坦丁諾夫跨向俄國邊界的漢人回教名將馬仲英等等。一九三一至三四年的回變有不少第一手的資料,例如史文海丁的《大馬奔馳》和吳艾金的《回亂》等書。關於這次變亂,本書只描寫了一九三三年的部分。
——林語堂〈自序〉
李飛坐在茶樓的一張內座上,凝視外面的大街和對面的鋪子。茶樓正對面是一家專賣絲綢綿織品的大店。二月天氣很冷,風沙也大,門上垂著厚厚的夾簾。右側有一間羊肉飯館。夏天裡飯店前門完全敞開,天冷的時候就用隔板和小門封起來,上半截安上玻璃框,可以看見裏面的動靜。
狂風颳起人行道上的塵土,人行道早已被騾車刻出一道道溝槽。雨天污水流不進人行道和柏油路之間的水溝,老騾車路的灰塵就化成一片泥沼,到了晴天,輕輕的和風又揚起滿天灰沙,吹得路人一頭一臉。騾車依照傳統,仍舊走人行道,不肯駛中間的大路。也許當局不准他們走車道吧。也許是車夫一輩子走泥漿路,習慣成自然了。街道有四十呎寬。為什麼市政當局只鋪中間呢?李飛的腦子向來充滿疑問。也許整條都鋪太花錢了。也許當局相信騾車天生就愛走泥路。框著金屬的大木輪會壓鬆嵌好的石塊,使汽車和黃包車專用的道路破壞無遺。這條路就像半途而廢的工程,給人行道帶來兩三吋的泥土,害本市顯得髒兮兮的。他不喜歡。他向來不喜歡半途而廢的作品。
剛剛他的腦子並不是特別想著這一個問題。他是在西安古城長大的,以它為榮,也希望看到它改良進步。隨著他的成長,城市也一天天改變,他覺得很有意思。他記得學生時代,他看到南北大道第一次裝上街燈,曾經激動異常。中央公園的設立,幾條道路鋪柏油,橡皮輪子的黃包車和汽車出現,都曾經引起他的興奮。他看過不少外國人——大多是路德教會的傳教士、醫生、教師,還有不少長腿的歐洲旅客或機師,穿著西褲和襯衫,面孔像半生不熟的牛排。他常常想,那種牛肉般的膚色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他看到這座恬靜的古城,唐代的名都,慢吞吞、不情不願卻一天天改變著。西安遠在內陸,是中國西北的中心地帶。他稱本市為「中國傳統之錨」。這是他的故鄉,他喜歡這兒的一切。西安不會變得太優雅。居民、風氣、政治和衣著的改變都是一片混亂。他喜歡這一片亂紛紛的矛盾。
現在他聽到樂隊演奏的聲音,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今天是星期五,又不是假日。他走到門口去看個究竟。警察樂隊剛剛開過,後面是一大排學生,正向「東大街」走去。這條街已經正式改名叫「中山街」,以紀念孫中山先生。不過本地人還是叫它「東大街」。有
一個好管閒事的執政黨擁護者曾經寫信給報社,建議誰若再把「中山街」叫做「東大街」,就由警察罰款。結果行不通。除了正式的公文,連警察本身也繼續用「東大街」這個名字。
李飛看看街上的情景。那是一幅活動的畫面。塵土飛到學生臉上,太陽也映在他們身上。一大排白布高舉在竹竿頂,學生手上拿著紙旗,隨風飛揚,上面寫著壯觀的標語。「支持第十九軍!」「全國團結!」「支援抗日!」「毋忘九一八!」這是支援一九三二年第十九軍抗日的示威,結果並沒有打成。
李飛暗自歡喜,尤其看到警察樂隊,心裏更高興。可見市政府支持學生的舉動。聽說北平的警察和學生發生打鬥呢。
他踏出門外。學生們容光煥發,在陽光裡微笑。隊伍有點亂,不過也無傷大雅。大家都圍在街上看遊行,高高興興閒聊著。參加的也有小學生。每一隊都由校旗前導。一隊男童子軍穿著厚厚的內衣,把制服都鼓起來,他們的笛子和銅鼓吸引了大多數人的注意。還有一列中學生走過,其中一個男生敲著煤油桶,群眾都笑起來。
有一隊是「女子師範學院」的學生。大部份穿冬季長袍,但是前面的十二個女生頭髮剪得短短的,只穿白襯衣、黑燈籠褲和布鞋。她們是排球隊的。幾個老太太看到她們白白的小腿,連忙用手去遮臉。
「羞死了!這麼大的閨女不穿長褲!」有一個人說。
男士們——店員啦,街上流蕩的年輕人啦——都看得目瞪口呆。一切都有點雜亂——就像近代的中國本身——新舊雜陳,亂紛紛的。
李飛轉身跟在女學生行列的後面。他喜歡噪音、樂隊、學生臉上的陽光、童子軍,還有那個汽油桶。中國的年輕人正向前邁進,雖然矛盾,卻充滿希望。他心裏一陣興奮,不下於以前第一次看見汽車走上東大街的心情。
少女們嘻嘻哈哈的。有幾個年齡較大的女生穿著高跟鞋,似乎跟不上隊伍,她們隨大家輕輕喊著口號,有點不好意思。連這一點他都喜歡。不過大多數女生年齡都不大,十七歲到二十歲左右。她們短短的頭髮,歡笑的面孔,各種毛料的圍巾——深紅色居多——看起來真漂亮。狂風不時由後面吹亂了她們的髮絲,塵土在街上迴旋,吹進她們眼睛裏。有些人用圍巾遮住鼻孔,有些人咳嗽了。她們的辮子和捲髮一擺一盪,簡直像風中的牧草。
李飛是國立「新公報」的西安特派員。他跟在遊行隊伍後面,倒不是因為記者的身分,而是他對這些很感興趣。他總覺得一定有妙事發生。如果遊行不出事,平平靜靜完成,那才真是奇蹟哩。
警察大隊長慷慨派出了管樂隊,他自己也是擁護抗日的年輕人。這並不表示,本城的警察機構一定贊成這次的舉動。事實上西安是一省的省會,主席是半文盲的軍閥,他聽說街上有學生示威,打了電話給警察局長,也就是他的小舅子,叫他驅散遊行的隊伍。
隊伍已經來到「滿州城」的東南角,清代的總督和滿州衛士都住在這兒,義和團之亂,慈禧太后逃出了八國聯軍的掌握,曾經來過這個地方,所以才取了這個名字。
李飛看到一條巷口排著大隊警察,約有三十人到五十人左右,都帶著長長的竹桿。警察樂隊已經走到彎路前五十碼。哨音一吹,警察就從各條巷子衝出來,一邊「呵!呵!呵!」大叫,一邊追趕學生。
李飛退後幾步,雙手叉在胸前,靜靜觀望。真怪,他自言自語說。敲竹打棍,又「呵!呵!呵!」亂叫,簡直像趕鴨子嘛。
接著就發生一場滑稽、英雄式的戰鬥。竹棒打不死人,學生們便英勇抵抗了一番。有些學生抓緊棍子的末梢,雙方展開拔河比賽,誰也不肯放手。
有一根竹竿彈起來,在空中翻了二十呎的大觔斗。很多棍子斷裂了,危險性反而增加,會刮破流血。雙方肉搏、扎刺、拉鋸、拔河、拍打、腳踢了好一會。塵土迷了雙方的視線。大體說來,學生覺得很有趣,警察就顯得滑稽可憐了。
混亂開始的時候,女子師範學院的學生已經來到街角。她們沒法前進,又不願意回頭。
現在有幾位警察轉向她們。
「我們去抓女孩子!」
「不要。」
「當然嘛。我們接受命令,要阻止示威的行列。不是挺有趣嗎?」
「我們去趕那些娘子軍!」
十幾個年輕人衝向那些少女。「呵!呵!呵!」他們帶著長棍子前進,有些完完整整,有些已經斷裂了。
少女們尖叫一聲,轉身逃走。誰都忍不住要看看排球隊豐滿雪白的膝蓋。